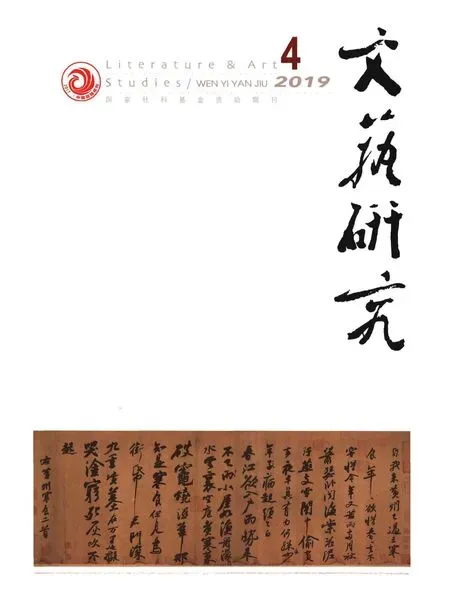空泛与错位的“非虚构诗学传统”
——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
李凤亮 周 飞

自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学界对“文学虚构”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理论探索。这一与审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逐步被确立为文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以此为对照,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①(引文凡出自该著中译本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一书中系统建构了一套关于中国的“非虚构诗学传统”。就其内涵,他在书中指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非虚构;它的表述被当做绝对真实。意义不是通过文本词语指向另一种事物的隐喻活动来揭示。相反,经验世界呈现意义给诗人,诗使这一过程显明。”(第16页)
关于此书构建的“非虚构诗学传统”,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有以下三种回应:第一,在怀疑与否定中西文学与文化二分法的基础上,强调中国诗学的独特历史经验与创作论话语②;第二,回到理论文本本身,还原宇文所安理论推演的本来面貌,强调其是一种阅读与批评传统,而非创作论话语③;第三,从跨语际沟通的角度出发,揭示西方汉学家的理论话语存在着创新与遮蔽的现象④。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宇文所安使用的概念范畴及其比较的合理性仍缺乏近距离的辨析与审察,大多止步于对其理论的接受与阐释,而未对其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矛盾错位之处予以揭示,缺乏真正的拆解与对话。本文正是从拆解“非虚构”这一概念的命名出发,发掘宇文所安在中西诗学比较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混淆与错位。
一
近些年,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阐释与批评著作陆续回流国内,受到本土学者的关注。汉学家特有的异质文化视角及成熟多样的阐释方法,使其在中国诗学研究中不乏创见。从理论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宇文所安的“非虚构诗学传统”作为一个独到的诗学思想命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无疑有其建设作用。但在认可这一作用之前,有必要对其比较的对称性进行考察。
首先是命名上的疑问。“非虚构诗学传统”在命名上不具有原发性,是一种“次命名”行为。“虚构”概念不是漫无边界的。“虚构”作为文学话语很少出现在经典西方诗学研究中。这一概念在动态的历史演变与静态的文类区分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性。顾明栋指出:“在欧洲的传统中,即使在18世纪小说作为一种主导文类已经建立起来时,有关虚构的理论书写仍然是零星的;到19世纪,文学理论中的主导话语仍持续关注诗歌与戏剧。”⑤就是说,“虚构”是十分晚近的文学概念,在20世纪之前较少被西方学界关注,更遑论成为一种文学传统。
从文类划分的角度,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将文学分为“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⑥,而他又进一步认为西方诗学的基础性文类是戏剧,“由于戏剧是唯一虚构的文类,那么我们把戏剧说成某种诗学的‘基础文类’,就应当是说得过去的。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戏剧能把抒情性和叙事性的事实转化成虚构”⑦。虽然戏剧文类可以将其他文类转换为虚构,但它不可能替代抒情诗与叙事文学在文类上的功能和作用,其差异性是根本的。当“抒情诗”取代“史诗”“戏剧诗”成为诗的专有名词时,诗与“虚构”概念的区隔被固定下来。法国学者热奈特就指出:“以史诗——戏剧——抒情诗三足鼎立的无穷变化为特征的新体系于是意味着抛弃虚构的一统天下而支持一定程度上公开宣称的双雄垄断局面,在新体系中,文学性从此与两大类型相联系,一方面是虚构(戏剧和叙事),另一方面是抒情诗,人们心目中的诗愈来愈经常地专指后者。”⑧也就是说,“虚构”与“非虚构”对具有叙事性或戏剧性的文类才有其阐释效用。具体到抒情诗之中,尤其是在具有强烈“情感—表现性”倾向的中国诗歌传统中,“虚构”与“非虚构”的命名本身就潜藏着强烈的异质性与冲突性。
另外,“虚构”与“非虚构”在中国传统诗学命题的探讨中并非对等的概念,在抒情诗文类中显得尤为零碎与边缘。“虚”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大丘也”⑨,指的就是大到没有边际之物。“虚构”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很少出现,二字连用时一般指日常用语中的谎言、胡说八道、不切实际之语,很少出现在专门的文学话语之中。在诗学话语中,“虚”很少单独使用,往往与“实”结合,形成某种对称关系。例如,“虚实相生”这一概念在绘画与诗歌领域中就较为常见。在谈到“虚”与“实”的对称关系时,贺晓武说:“艺术创作的实践证明,‘虚’与‘实’只有互生互变,才能表达我们丰富的生命内涵,才能把人性的复杂多变呈现出来。”⑩质言之,在中国的诗学话语中,“虚构”与“非虚构”并不是对称的关系,“虚”与“实”才是互相对称的命名。
中国人对“虚构”的理解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内涵。在中国人的世界中,真与假、虚与实之间存在更为丰富的意蕴。《红楼梦》里谈到“太虚幻境”时说,“假作真时真亦假”⑪。实际上,与西方世界从话语施为层面上理解的文学虚构不同,中国的“幻境”“梦境”与西方人所谓的创造一个“金的”文学世界⑫有着巨大差异。这一差异性不在于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意识不到作者正在通过虚构力与创造力制造“梦境”与“幻境”,而在于中国文化从情感表现角度超越了这种差异,从而回归情感的真实、意蕴的真实。中国文学注重虚构的效果,蒋述卓就曾指出,“从把握艺术的特性上看,中西方均注重艺术虚构的创造能力,认为艺术离不开虚构,虚构甚至能使本来的生活显得更真实”,而中国人更讲究“合情为真”,求“意之似、神之似”⑬。中国人在讨论艺术时,“虚”本身虽然并不具有自足性,却是通向“实”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高超的虚构能力能够有效抵达文本背后的“情感”“神”“意”等具有中国意味的概念世界。
因此,宇文所安的“非虚构诗学传统”在命名上就是不对称的。他从西方理论中抽取“虚构”一词,加上“非”作为前缀,强行移植到中国诗学,属于一种人为的有先后、有对照的命名行为,使得中国接受者在理解这一概念时,首先面临的是命名上的疏离感;而西方接受者则容易跌入东方主义的泥沼,仿佛中国的诗学概念天然就是拿来应对西方文学传统危机的,抑或只是一种“非”的异国想象。这从根本上也是反“世界文学”构想的。
二
在比较诗学中,比较的对象尤为重要。比较的对象提供了可比较的支点。中国学者之前大都从既有的理论成果出发,而忽略了检验其比较对象的合理性。加之,对现有概念的重新界定或适当调整是西方学者惯用的论述技巧,故而中国学者关于“非虚构诗学传统”的理论批判大都陷入与西方各说各话的尴尬境地。因此,回到比较的支点,厘清作为理论工具的概念,就成为考察非虚构理论适用性的必经之路。
从文类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学建基于戏剧之上,虚构是其核心要义。在抒情文类中,虚构虽然有其相对性,但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就是中西方学者在分析一首诗的内涵时较少使用“虚构”这一概念的原因。为了保持比较的对称性,应该拿西方的抒情诗论与中国的抒情诗论进行比较,才能得到较为公正的成果。宇文所安在书中确实用了两首抒情诗作为比较的起点。他选取了英国抒情诗人华兹华斯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和杜甫的《旅夜书怀》做案例分析。依据字面上的意思,杜甫的诗并无现实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华兹华斯的诗却较为写实,他在特定的时间,站在特定的角度,对1802年9月3日黎明的伦敦威斯敏斯特桥进行了详实的描写,以达到诗人本人所期许的“诗里没有虚假的描写”而“读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为伴侣”⑭的目标。作为专业读者的宇文所安却认为,与杜甫的诗相比,“对这首诗来说,这种对环境的兴趣并不重要。华兹华斯是否看到这一景观,有没有隐约地记住它,或者通过想象建构它,这些都无关紧要。诗句不指向历史上极具特殊性的伦敦;它把你引向的是另一种东西,某种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数量无任何干系的意义。这种意义令人难以捉摸,它的丰满性永远无法企及”(第2页)。这两种解读恰好体现了作者意图与读者阐释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也就是说,宇文所安所关注的并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本身,甚至拒绝了文本自身的权威,而将读者、尤其是接受过西方诗学/哲学传统训练的专业批评者放在了首位。这种批评阐释所抵达的意义甚至超出了诗歌文本自身的比较,扩展为背后的诗学体系、美学范畴以及哲学观念之争。
宇文所安的“非虚构”概念直接源自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非二元论哲学宇宙观的论述⑮。这种论述几乎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在中国人的哲学宇宙观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人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天、地、人共同显现自然之道。据此,宇文所安在“透明:解读中国抒情诗”一章中提出,“中西文学解读模式的不同与隐喻的相关问题以及诗歌虚构性或非虚构性的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假定文本的虚构性和存在一个隐喻的真理贯穿了西方的文学解读模式”(第30页),而“传统的中国读者都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诗是历史经验的实录式呈现”(第31页)。也就是说,西方诗学的阐释建立在现实与意义、现象与本质的深度模式之上,文学世界作为语言的虚构之物指向上层的真理世界,而其所使用的“隐喻”概念只能容身于这种深度之中,这暗示着表面的现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连贯的本质意义。对一个专业的西方读者来说,华兹华斯《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中的每一个语词符号、每一处地点景物都只是诗意的虚构之物,只是破解谜题的谜面,意义在诗中不透明、不显现。诗歌俨然成为一门专业之学,与普通读者分割开来,读者需要通晓一系列专门的批评方法与概念工具,才能知道这首诗并不旨在记录清晨桥上景色的美好,而在于“邀请读者欣赏自然的美丽,同时思考事物的统一性”⑯。
杜甫的《旅夜书怀》则不同。宇文所安认为,由于缺少主客二分的深度模式,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无限展开、相互关联的整体。“不仅一部文学作品因由世界的一隅与某人的意识的联结得以产生的这一过程是自然的,而且呈现这种联结的书写语言(文)本身也是自然的。”(第7页)按照这种理解,杜甫笔下的景物与景物自身都是自然,是自然中不同类别下相互对应、互为对称的实体。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没有人为地区分语言与自然物之间的差异。在这种阐释模式中,宇文所安用“类”代替了西方的“隐喻”概念。虽然二者都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但“隐喻”天然意味着深度与等级,暗示现象的不可靠,并指向了背后之物;而“类”则展现着事物之间的自然关联,书写语言与书写对象在“类”的概念中没有等级差异,诗歌语言是自然与透明的,既不模仿自然,也不藏匿自然。因此,在解读诗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时,宇文所安极力寻找语词与现实、人与景物之间的关联与平衡,“流动和无止境的运动,与稳定和坚固相对;独自旅行的一个人,与其他安全的生物相对;危险的直立、巨大、高贵,与弯曲、微小、普通相对”(第5页)。自然世界与诗的世界之间不是前者指向后者的隐喻关系,二者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自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类别。
“类”作为宇文所安创造性的概念发明,建基在这种非二元论的哲学宇宙观之上,与西方的“隐喻”概念格格不入。但如果抽离背后的哲学观念与理论预设,它与“隐喻”在文学修辞与结构功能上几乎毫无差别。这就是当认同“非虚构诗学传统”的余宝琳也在《隐喻与中国诗》中从修辞的角度“极力恢复隐喻这一概念作为中国诗歌中意义的一般模式”⑰时,宇文所安所遭遇的尴尬与挑战。宇文所安所使用的“隐喻”只指向“虚构”的概念,他并不是在修辞或文学的意义上理解“隐喻”,而是将之放到西方哲学的“洞穴隐喻”或“剧场隐喻”层面去理解的。这就抽空了比较的对象,将抒情诗作品以及关于这些作品的诗论空心化了。对于一个接受过西方文学理论训练的娴熟读者,不要说是一首抒情诗,就是一个碗、一张桌子,只要一进入语言的世界里,就都是虚构与隐喻的,它们指向的不是现实中的器物,而是其背后那看不见的意义与理念。这一比较不是文本中自然生成的,而是从文本外部有选择性地主观介入的。也就是说,宇文所安不在意所选的两首诗是否是抒情诗,即使选取中西方的马桶进行比较,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的马桶是“非虚构”的,它指向马桶自身以及木头的材质与整个自然的关联;而西方的马桶是一种“隐喻”,是其背后的意义,是文明对野蛮的驯服,是艺术合法性自身的证明等等,总之,就不是马桶本身。
自伊始,诗歌及其理论文本的比较就被抽空,它们与其说是比较的起点,不如说是一种可征用的资源,点缀背后预设的体系、范畴与观念之争。宇文所安反复强调中国的“类”与西方的“隐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诗歌作品本身在这方面非但隐而不显,甚至还在以文本自身的方式加以否定与消解。不妨再想一想,一首“1802年9月3日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凝视伦敦城”(第3页)而创作的诗,跟一首写在“微风岸”的诗,哪一首更让读者联想到现实生活?
三
由于抽空了比较的对象,跨语境的诗学比较在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的操作下,成了中国非二元论哲学宇宙观与西方二元论哲学宇宙观之争的延伸。诗学传统的权威自此不再由作者意图与语言文本来限定,而由读者(批评者)的阐释语境所圈定。在警惕这种阐释语境时,需要厘清概念工具的随意性,消除由此引发的范畴错位。
首先,宇文所安在书中刻意混淆了“人文”“文学之文”和“自然之文”(“天文”“地文”)等概念。他借助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谈道:“‘文’,审美图式,是某种潜在秩序的外部显现。从天地的最初构造到动植物,每一级都显现相应于它的种类的‘文’。在人,‘文’的外表不体现在人的身体上……在此处,‘文’通过重要的人类特征——‘心’显现。‘心’的活动的外在的、显明的形式就是‘书写’文,或者其重要的形式,‘文学’文。”(第6页)在阐释时,宇文所安认为“文学之文”(人文)与“自然之文”没有等级差别,只是不同的分类,各类目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文学作品就是对外在的物理实体的直接经验性的回应”⑱。在他看来,“文学之文”就是自然之文,这也就是其所谓的“透明”——字面的即是现实的。如此,刘勰笔下天地万物本身各异的自然纹路就被遮蔽了。这两类“文”(文字与纹路)在内在关联与外在使用上的差异性是宇文所安未言说的,他试图塑造一种“天文”和“地文”在“文学之文”中直接呈现的自然状态,不需要经由人文制作者丝毫的主观介入,“作家,不是‘复现’外部世界,事实上只是世界的显现的最后阶段的中介”(第7页),一切都是回应,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与此同时,他也简化了“人文”的内涵,将“人文”窄化为“文学之文”,忽略了人所制作的器物。人文包括人类文明的一切表征,其中,人类的制作活动起了关键作用,闫月珍指出:“器物是人文的载体。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又有所谓天文、人文之别,如《周易·贲》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人三才中,人是沟通天、地的中介,因而人所制作的器物就具有了沟通天、人的意义。”⑲“人文”不仅是“文学之文”,还包含人所制作之器物。一方面,器物是“文学之文”的书写对象,与其一道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器物制作的复杂程序又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规范性的话语表述,“从器物的创制发现天、地、人和事的规律,器物的要素渗透到了语言的规范性表述之中,由此形成了政治、伦理和文学艺术领域的规范性言说”⑳。“人文”的丰富性揭示了“文学之文”与器物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密切联系,彰显了人的制作能力与创造力。但在宇文所安眼中,自然与人的关系被倒置了。实际上,不是自然派生出了“自然而然”的观念。恰恰相反,“文学之文”与“器物”的“自然而然”是一种人为的美学效果,是人竭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美学标准之一,而不是自然本身。
在“人文”制作中,越是显得“自然而然”的,越是源自人的创造。西方哲学建基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二分上,很难处理人为性与自然性之间的冲突,只能将之合并到最高的神性创造上。人的创造性来源于其分享了神创造世界的某种神圣性。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西方学界的一些反思㉑。为了调和人为性与自然性之间的矛盾,饶芃子提出了“无为自然”与“妙造自然”的差别。她谈到:“文学写作的法则和要求是自然天意。不同的只是无为自然论者认为只有彻底无为才能合于自然法则而任其自然;妙造自然论者认为只有巧妙地人为才能领悟自然法则而顺理自然。”㉒换句话说,彻底的无为自然论没有办法解决人为性与自然性之间的冲突,在无限放大审美性的同时,反而会对“文学之文”加以否定;妙造自然论在承认自然天意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性汇流到自然性之中,人的创造力最终回归到自然的天赋与馈赠上。因此,刘勰也如此鞭策人文制作者们:“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㉓
其次,宇文所安不但割裂了《文心雕龙·原道》的一致性,也忽略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整体性,直接将“神思”“才略”“知音”等篇强调作者能动性、描述作者创作过程与语言鉴赏的文本抽离不谈,忽略了中国诗歌的制作性。这种论述取消了“文学之文”自身的人为性,混淆了自然与人为的差别,忽视了制作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也直接导致了其与西方文学、美学在比较上的范畴错位。在谈及中西诗学的比较对象时,宇文所安一贯主张:“中国的文学思想就建基于这种解释学,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建基于‘poetics’(诗学,就诗的制作来讨论‘诗’是什么)。”㉔实际上,宇文所安是拿“诗言志”(诗是一种显现)与“诗是一种制作”放置在一起进行不对称的比较,前者是读者论的范畴,探讨的是诗如何从自然中显现,以及读者如何阐释这种显现;后者是作者论的范畴,谈论的是诗的制作以及方法。在这种阐释语境中,宇文所安颠倒了作者创作与读者阐释之间的权威性,他只关注理想的读者,认为“一位中国诗人可能会写入一些地理上或历史上不可能的内容:评论者处理这种情况的尴尬是读者的假定受挫的标志”(第31页)。评论者是成熟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诗人在创作上的用心被评论者的“尴尬”所掩盖,评论者的“假定”被无限提升,从而混淆了作者技艺(使读者相信)与读者的理论假定(天然相信)。
虚构作为一种文学假定,是各文学要素共同呈现的效果,不能任由阐释者(批评者)随意割裂。新批评学者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说:“通常诗歌底叙述是依据一种‘讨论宇宙’,一种‘佯信底世界’,想象底世界,诗人与读者共同承认的虚拟的世界。一种‘伪陈述’,若是合于这种假设底系统,便会认为是‘诗的真实’,而不会认为是‘诗的虚假’。”㉕在其看来,关于诗的假定是诗人和读者共同承担的,而不是单从读者(批评者)层面假定的。作者与读者间借由作品文本勾连成一个整体,人为放大某一要素在阐释上虽然事半功倍,但必然与历史事实及逻辑推演相冲突。当读者将诗的表述当作真实的陈述时,他恰好参与到整个文学虚构的假定中,确证了作者的创作力。顾明栋也发现:“在中国传统的虚构理论中,虚构的认识论就是使人相信或者认虚作真。”㉖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才让作品呈现出真实逼真的效果,使读者相信作品中的人、事、物。
最后,宇文所安在书中所期许的理想读者既不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读者,也非某种动态传承中的阅读传统,只是作为跨文化批评者的他本人(及类似的专业读者),他越过了历史,无视经验事实,直接利用读者批评与阐释理论建构“非虚构诗学传统”,并回过头来阐释中国诗歌,完成自我的循环论证。一个简单的事实被忽略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批评者用这套“非虚构”的阐释方法去分析任何一首中国诗。自始至终,只有宇文所安一人如此分析杜甫的《旅夜书怀》。何来的传统?在这种不对称的比较语境中,他抽取出西方制作与技巧层面的“虚构”与“隐喻”来套中国的“非虚构”呈现与“类”,结果是一团浆糊,两边不沾。中西诗学在“虚构”与“非虚构”这对概念上的分野,并不是比较的产物,而恰恰是造成不对称比较的前提。
结 语
关于诗的比较离不开其固有的语言属性与审美特性。诗歌首先是一种语言作品,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这是阐释者据以言说的基础,是一切比较的前提。宇文所安在书中刻意绕开这一现实,通过无限溯源的言说方式忽略这一前提,从而由“文学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诗)直接跨到“文学之文”(作为一种理论预想的文)之中。这不仅模糊了中国文论中关于诗与文的分野㉗,也忽视了“文学诗”自身的文体变革与形式变迁。在宇文所安的理论预设里,真正的中国诗是单一、扁平的,局限于其所谓的应景诗之中。他认为这才是最具中国特点的非虚构诗,任何其他类型的诗(如乐府诗)都是文学的制度化与虚构,都是对现存秩序的妥协,都是西方诗学固有之物。
这种不对称的宏大叙事理论反而窄化了诗的文学内涵,甚至坠入比较上的不可通约性,即认为中国诗与外国诗本质上就是不同之物。在此论述中,唯一的语言事实被抽空,文学概念在两种不同的理论预设中互相抵触,以致失去了比较的基石。真正对称的比较应该是在中西虚构理论间进行,从而激活中国的虚构理论,找寻其与西方虚构理论的差异所在,这才是发明语境中的比较,才有可能抵达真正世界性的虚构理论,而不是预设某种片面理论立场的文化误读乃至文化偏见。文学与诗正是借由语言、虚构与隐喻才获得可比较的支点。无视这一现实,企图直接超越历史语境,只从本源处寻找差异性,极容易使已被各种文学常识与习性包裹的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颠三倒四,最终连“诗是什么”都成了问题。这也就是“非虚构诗学传统”看起来如此吊诡的原因——多种错位与颠倒缠绕在这一精致的理论机器的内部。
① Stepha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国内学者陈小亮翻译全书并发表了若干篇相关研究论文。中译参见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张隆溪最早质疑宇文所安的比较前提——中西文学与文化二分法,并从《文心雕龙》中摘取“神思”“夸饰”等创作论话语来拆解“非虚构诗学传统”。详见张隆溪《文为何物,且如此怪异》,王晓路译,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③ 陈小亮回归到文本语境,从宇宙观(创造—相关)、诗思方式(隐喻—类)、阅读传统(虚构—非虚构)三个方面进一步框定了“非虚构诗学”的概念内涵,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宇文所安的理论构架(参见陈小亮《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
④闫月珍:《跨语际沟通:遮蔽与发明——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构》,载《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2期。
⑤㉖ Gu Ming Dong,“Theory of Fiction:A Non-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Narrative,Vol.14,No.3(2006):312,323.
⑥⑦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王宇根、宋伟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第317页。
⑧ 《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⑨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⑩贺晓武:《虚构诗学——以伊塞尔文学思想为基础》,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中文系,2007年,第14页。
⑪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⑫ 锡德尼强调诗人的创造性,认为“它(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⑬ 蒋述卓:《中西艺术真实观的异与同》,载《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
⑭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高建平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161页。
⑮ 陈小亮说明了“非虚构诗学传统”有其“影响研究”层面的理论来源。她指出宇文所安接受了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见解,“被相沿认为(中国)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虚构之作。纯以实在的经验为素材的作品则被认为理所当然。诗歌净是抒情诗,以诗人自身的个人性质的经验为素材的抒情诗为其主流”,并认为“宇宙论、哲学的视角及文学非职业化的研究思路,以及所采用的比较文学方法等对后来西方汉学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命题的建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见陈小亮《论海外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命题研究的源与流》,载《暨南学报》2016年第2期)。
⑯⑱㉑ Ren Yong, “Cosmogony,Fictionality,Poetic Creativity: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s”,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50,No.2(1998):110,112,107.
⑰ 陈小亮:《论海外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命题研究的源与流》。
⑲闫月珍:《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⑳闫月珍:《作为仪式的器物——以中国早期文学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㉒ 饶芃子等:《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㉓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㉔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㉕ 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曹葆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㉗ 钱钟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指出,在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中,“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是两个格格不入的范畴,诗与文各有其规律与使命(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