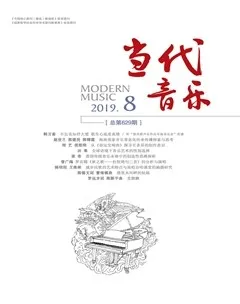艺术歌曲《木马》中的印象派音乐技法
[摘 要]
《木马》选自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早期创作艺术歌曲集《被遗忘的小抒情曲》中的第五首,此套曲写于1887—1889年间,属于德彪西早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歌词选自魏尔伦诗歌集《无言的心曲》之《布鲁塞尔:木马》。本曲是套曲当中风格极为诙谐、脍炙人口的一首。本文将通过分析歌曲的创作背景、曲式结构、和声技法以对这首作品所体现的印象派特征音乐语汇进行深刻了解。
[关键词]木马;德彪西;印象派;艺术歌曲
[中图分类号]J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19)08-0112-03
一、背景
法国艺术歌曲的起源、发展和繁盛时期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印象派绘画、象征主义诗歌和戏剧艺术在法国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德彪西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上逐渐走向成熟,印象主义音乐风格浮现发展的重要阶段,他善于运用印象派绘画技法般虚无缥缈、稍纵即逝的音乐描画技巧,因此被认为是“印象主义”音乐的先锋人物。“印象主义”起初被作为贬义词用于音乐,是一种由于和声线条不精确和曲式结构模糊而不受欢迎的写作手法。一般来说,传统和声的使用手法体现在于在西洋大小调上进行创作,而印象派的和声则打破了这种规则,以全音阶、五声音阶、中古调式为代表,全音阶的实质是在写作时通过设置临时变音使调式中的每个音居平等地位,从而削弱调中心感以体现更多可能性的和声色彩。在《木马》这首作品中,钢琴声部基本上维持着半音的连续进行,右手重音与左手低音层层呼应,甚至有同步的情况,弱化了传统和声的功能性,避免给出明确的终止式。
在那个文学艺术繁盛的时代,原有的学术型或古典型的美学定义被打破,新的美学流派破茧而出。印象主义摒弃浪漫主义重视宏大题材,以绘画激起人们感情的观念,将视觉重心移到凡人琐事,从平凡的题材中透露出对生活和大自然的喜爱[1]。印象主义绘画追求刻画实物周围的色彩与光影在瞬间的迷离变换,在对事物进行创作时总是考虑很多客观因素,使得本位思想被模糊。因此对于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而言,富有色彩效果的和声远比旋律重要。
在本作品中,我们能见到许多充满“印象风格”特色的音乐写法,如在写作歌曲插部时和弦连续以三全音和弦关系进行、尾声处使用低音减五度进行做色彩性上的递进,造成不协和的音响效果,凸显旋转木马的风趣幽默。德彪西坚信,法国音乐的要义,首先就是能带来快乐[2]。《木马》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歌曲中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无论贫困、饥饿的人都在木马的旋转中获得了快乐,而听众也从中获得别致的享受。
二、歌词来源
德彪西一生中公开发表了艺术歌曲六十余首,常以文学元素为中心素材进行创作,《被遗忘的小抒情曲》是其继《华丽盛宴》后出版的第二部艺术歌曲集,根据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一八七四五年出版的第四本诗集《无言的心曲》而作,此集代表了魏尔伦诗歌创作的高峰,此时身陷囹圄的魏尔伦已彻底摆脱了巴那斯派的影响,以一个成熟的象征派诗人的创作面貌出现在公众之前。《木马》讲述的是一个挨饿的穷汉强颜欢笑地骑在游乐场的旋转木马上,试图忘却自己的贫困、饥饿、烦恼和孤独。
《木马》在全曲一开头就采用了毫不犹豫的快速有力的颤音进入,营造出犹如拨浪鼓一般充满童趣的音色,让人暂且跳离前曲音乐呼吸间传递的压抑感并获得别致另类的
风格感受。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数次转换调性并使用了增减不协和音程,使调性徘徊游离,就像风吹过时树荫下冰冷的光与影叠致在一起,不规则而色彩斑驳。就木马这首作品而言,旋律不是十分突出,情感相对套曲中的其他歌曲而言似乎也比较单一,但当中所涉及的和声技法和调式调性却极为丰富,和弦结构的多样变幻使歌曲似一幅色彩缤纷的印象派画作。
三、歌曲曲式结构分析
本曲可划分为引子A、B、A1、C、A2、D、A3(尾声)。采用回旋曲式进行创作,但其并非典型的回旋曲式,因为叠部的每次再现都变换了调性,但在A、A1、A2的主题句的和声功能都是保持一致的。
引子从主调E大调的下属音进入并一直在低音声部以颤音的形式持续,描绘了木马正在蓄力、为旋转做准备的过程,右手节奏均等,皆是三连音+二八的组合,旋律和织体由高到底呈波浪状起伏流动,预示了旋转木马的永不停休。
A段(1-16)主题材料“转呀,转呀”旋律音“B-E”属-根四度跳跃的进行标志着木马开始旋转了,这是判断叠部出现的重要依据。整段的伴奏织体都在使用均等型的三十二分音符旋转式下行,快速短促的分解和弦使音乐充满童趣,描绘了木马正在快速旋转的热闹场面;在和声的运用上,第11、12小节前三拍均使用了连续的大三和弦的半音关系向上进行,前一小节分别运用A、bB、B上的大三和弦,后一小节分别运用F、#F、G上的大三和弦,和弦根音之间做半音级进并与旋律声部同步,这种连续的大三和弦平行进行使和弦没有立刻解决到稳定的音级上,因而调性色彩朦胧不清,如骑在旋转木马上般令人产生眩晕模糊之感,却又令人陶醉,调性飘移恰恰呼应了旋转木马的本质,直观表现出印象主义风格特征。
B段(17-26)转入了F大调,宣叙、朗诵式的音乐语调将镜头拉近至游乐场的多个角色,脸蛋红润的孩子、疲倦的母亲、黑衣的小伙子、红衣服的姑娘……本段衔接紧密、以持续不断下行、旋转的三十二分音符烘托出游乐场热闹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第17小节的和声进行是属功能到下属功能的进行,这在传统和声学中被称作“反功能”,原则上是不提倡使用的。作者却借此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怪异的音响效果,贴切地描绘出“孩子”与“母亲”“小伙”与“少女”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将这种“D-S”的进行重复了两小节之后,紧接着和声向下方级进进行到三级-二级-一级上,从整体上看此句的低音走向是Ⅴ-Ⅳ-Ⅲ-Ⅱ-Ⅰ的音阶式布局,旋律则恰恰相反是上行的,与低音形成反向。随即又转入了F大调的属调C大调,并与a小调不断交替,本段最后两小节的和声进行是从二级七和弦进行到bB上的大小七和弦,与第26小节低音“bB”和右手声部“C”构成的一个大九度音程共同构成一个复合性质的和弦。即此小节既延续了前小节的SⅡ和弦又是在为叠部A1作属准备。大小调式交替、复合和弦渗透的手法运用大大丰富了本段和声的色彩性,也生动表现了在游乐场的性格迥异的不同角色。
A1段(27-38)没有依从典型的回旋曲式叠部调性回归统一的传统,而是将主题材料“转呀,转呀”作下方一度转调模进至bE大调,场景随木马主题的再现切换到正在旋转的木马上,描绘了正当人们陶醉在嬉戏的时光中时,阴暗处的小偷已经看准目标蠢蠢欲动的画面,第35-38小节处转入了B大调,伴奏的右手声部使用了前八后十六、四个十六分音符、两个八分音符的前紧后松的节奏型,使氛围高涨而紧张,左手声部则是持续的二分音符颤音,表现木马仍在继续旋转。低声部属九和弦的七音“E”与根音“#F”叠致成大二度并在左手一直持续着,大二度不协和的音响加剧了紧张的色彩,产生戏剧冲突感,表现了对在木马上纵情玩乐的人们的担忧焦虑之情。
C段描绘了饥肠辘辘、疲累的人们仍身处游乐场当中没有离去,他们因为木马的旋转感到头晕目眩,但另一面却又为这种幼稚的把戏兴奋不已,身体虽不舒适但精神上又很愉快。本段主调性是B大调,第一小节的T6也可以看作是同主音小调b小调的下属六和弦,具有同主音大小调色彩的渗透,旋律与低音都是连续的半音化进行,同时做有两个声部的主音持续,又在两个主持续音下方声部形成了小三度音程关系,并以小三度关系作连续半音进行,连续的半音化写作导致了连续的不解决,这种半音化色彩性进行丰富了和声色彩的交织变幻,运用了印象主义色彩性的作曲技法。有趣的是第43、44小节,旋律以同音加不协
[HJ2.3mm]和的四度大跳的方式进行,“B”-“F”对应的和声功能分别为B上的大三和弦及F上的大三和弦,两个大三和弦之间以三全音关系进行,折射出不协和的色彩,又加以重音与歌词巧妙结合,形象地讲述了腹中空空的人们的快乐与低落交织在一起;第45小节使用了降六级和弦,折射了同主音小调色彩,本段结尾无明显的终止式收束,旋律音停在G大调属音上,低音则还是B大调的属音持续,这里可以看作是复合调性,表现了人们陶醉游乐的同时却感到迷惑不解的矛盾心情。
A2段调性为G大调,织体回到了旋转式的三十二分音符分解和弦,主题再现,表示木马仍然机械地旋转着,本段的音区最高到“G”,是全曲高潮部分,结束部分的和弦性质是bB上的大小七和弦,与D段衔接。
D段描绘了天色渐渐变暗,晚餐的钟声响起,人群渐渐散去,而木马还得继续旋转。本段旋律舒缓连贯,和声色彩逐渐丰富,从bB上的大小七和弦进入,低声部是大小七和弦的七音持续,穿插G上的小小七和弦,67、68小节的和声是bB上的增三和弦,69-74小节是D上的增大七和弦和#D上的小三和弦的交替,上述和弦的使用令调性处于游离状态,和弦之间相互独立且不属于任何一个调式的调内音,没有功能性的进行和解决,使调性披上一层朦胧缥缈的色调,为原本轻松谐谑的音乐氛围增添了一丝黯淡忧伤的色彩,将印象主义色彩性进行发挥到极致。
A3段是全曲尾声,描绘了夜幕降临,群星璀璨,教堂敲响了丧钟,但在游乐场里旋转的木马却感受不到悲伤,它不停歇地旋转着,带给人们忘却一切烦恼的快乐时光。“转吧,转吧”主题原样再现,调性回归至E大调,但速度变慢,旋律音符时值扩大一倍,伴奏织体变为左手震音、右手波音的形式,力度极弱,烘托出夜晚的静谧安宁;主题句的和声也发生了变化,原本“E”音和“B”音下方对应的和声应是T-D,而此处使用的则是S6-DTⅢ,同时低音“#C”-“#G”为#C大调主-属功能性进行,可看作复合调性的写法,为主题添了一丝夜空的朦胧神秘,丰富了调性的色彩性。84小节还原调式导音作小导和弦,渗入同主音小调色彩,下一小节又用升五音的大调导七和弦,通过大小调的色彩交替来铺垫美丽的星空下教堂钟声的清冷透彻。91小节处歌曲回原速,歌词写到“转呀,和着快乐的鼓声飞奔”,此处的织体再次使用了颤音,表现木马将在游乐场日复一日地旋转。91、92小节可看作同主音小调降三音的导五六和弦,调性色彩再度变化,值得注意的还有93-96小节伴奏的内声部进行“C”-“#F”、“E”-“#A”运用了减五度进行,是德彪西特色的印象主义色彩音乐的创作技法,尾奏织体以长音为铺垫模仿钟声敲响,右手间歇性出现前奏三连音素材,使音乐结束得更自然,令人沉醉在夜色中充满遐想。
总 结
德彪西在这首作品中频繁借助半音化色彩性进行、同音调色彩交替、复合调性等创作技法来达到其描绘虚无缥缈的印象主义色彩音乐的效果。光与色彩是他注意的核心,冷色调与暖色调交汇,与印象派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叠部的印象派因素相对较弱,主题句的和声功能和和弦结构变化较少,而插部的展开性更强,抒情处充满幻想,似以音符描绘一幅画,色彩初逐渐加深,间隙里还使用了过渡的颜色,色彩斑斓贯穿全篇。以B段举例,模糊调性,徘徊在F(六级关系离调)C-a(关系大小调五级)迷幻绚烂的音响效果。叠部的谐谑与D段的抒情对比,边缘化调式,回旋曲,带有奏鸣性回旋曲式(戏剧性的冲突)。既满足了回旋曲的题材,又在其中增加了戏剧性、斗争性与画面感。通篇用很多印象派的技法包住了主干音,使主干音既能体现出来又囊括了印象主义音乐色彩斑斓的和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