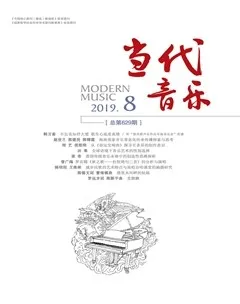我国传统音乐本体中的创造性思维探析
[摘 要]
音乐作品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在本文中,笔者从音乐本体的角度,通过谱例分析来探究我国传统音乐中体现出的创造性思维。结果显示:1聚合性思维以韵味为核心;2发散性思维包括线性思维与立体思维、单向思维与双向思维、 严密性思维与灵活性思维并存。说明我国传统音乐具有独特性和科学性,它是“深情的理性”与“逻辑的感性”交织而成的辩证统一体。
[关键词]传统音乐;音乐本体;创造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19)08-0011-05
音乐作品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从音乐本体的角度深入剖析我国传统音乐,可以折射出千百年来人们在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人在从事创造活动、解决尚无先例的问题中寻求独特而新颖的,并具备社会价值的思维成果的心理活动。[1]创造性思维包括发散思维、类比思维、臻美思维、迁移思维、重组思维、定势突破、隐喻思维、知觉思维等基本能力,[2]其主要成分是发散性思维和集中性思维。成语“房谋杜断”是指李世民的两个得力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擅长于发散性思维,总是能够提出多种精辟的见解和方案,但是往往不善于做出决定。而杜如晦在集中性思维方面具有优势,他会将问题略加分析,确定出其中的最佳方案。他们两人共同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盛世。因此,发散性思维和集中性思维二者相互联系,在创造性思维中缺一不可。笔者将从集中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两个方面探寻我国传统音乐本体中所蕴含的创作思维。
一、集中性思维(也称聚合性思维)
集中性思维是依据已占有的信息和各种设想,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求得最佳方案和结果的思维过程。[3]集中性思维在解决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一曲多变运用[4]”是受当时、当地经济环境以及音乐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在集中性思维下对现有音乐选择范围内求得最佳方案的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渐进创造力的产物。希克森特米哈里指出,社会环境、经济水平的富裕程度会影响人们的创造性,物质丰裕的环境对创造性的发挥通常更加有利。[5]因此,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渐进性的创造应时而生。王耀华先生在他的力作《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中将“一曲多变运用” 定义为“以一个腔调为基础,填上不同的唱词,或从表现不同乐思出发,对之进行旋律音调、节奏、板式、句式、腔句、正反调等变化,产生多种变体”[6]。例如【柳青娘】,其变体有85种以上;【万年欢】的变体25种以上;【清江引】变体54种以上。程晖晖于2015年通过“传统音乐曲牌索引及其统计系统”软件数据库的设计开发和导入校对等系列任务,截止到2016年11月,已输入近48000种曲牌(并不断更新)。[7]变体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令人惊叹。“一曲多变运用”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一大亮点、特色。
另一方面,“一曲多变运用”是集中性思维聚合于一个母体腔调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抓住了音乐母体的核心命脉,就是抓住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根脉。“万变不离其宗”,母曲的特征就是集各种变体于一身的聚焦点和向心力,也是千百年来传统音乐创作的基因密码。王耀华先生以其深厚的戏曲功底和文化底蕴,在他所著的《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中以大量戏曲音乐作为分析对象,同时以腔音、腔音列、腔节、腔韵、腔句、腔段、腔调、腔套、腔系统领全局,不难看出“腔”之重要性。由于“腔”“韵”相连,对“腔”的强调,实则核心是“韵”。这种独具中国“韵味”的音乐结构命名方式,在我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具有开创先河的引领作用。整本书以我国传统音乐神韵为主线,为中国传统音乐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进一步推进描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我国传统音乐聚合性思维的关键点是“一曲多变运用”中对“韵味”的追求。
“韵味”是在基本调中经常出现的、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同时最具稳定性的音乐元素。在基本调的各个成分中,体现为以下几种:
(一)腔音中的韵味:带腔的音,如苦音、欢音等由各种方言、音乐风格形成的中立音、微分音以及体现地域音色、音响效果的单音。
(二)腔音列中的韵味:由三音列之间音程的起落点、级进或跳进形成有张力、跨度、疏密特点的地域性、风格性腔音列。我国五声音阶是传统音乐的核心,因此,四度三音列是传统音乐的“染色体”[8],即集合【0,2,5】是五声音阶腔音列中的核心韵味。
(三)腔节、腔句中的韵味:这部分的韵味体现为“腔韵”。具体包括曲牌系统性腔韵与声腔系统性腔韵;曲牌性腔韵和板式性腔韵;曲目性腔韵;[9] 单一性腔韵、双韵对置与多韵循环;大韵、长韵、短韵与高韵、低韵、平韵;[10]还包括由多个腔音列组合而成的特性旋律音调;句头韵、句中韵、句尾韵和上下句首尾呼应;[11]多个单体型或复合型节奏组合而成的节奏型;基本定格的落音;合尾;相对固定的篇幅规模[12]等腔韵。
(四)腔段中的韵味:在集以上所有韵味元素及其不同排列组合的基础上,还包括调式调性转换、材料组织(如曲牌体等)、曲式结构(如起承转合)、板式结构(如散慢中快散)、段落规模、乐队配器、不同乐器的演奏法(如刮奏、满轮、滚、扫、揉弦等)、音色(如马头琴、琵琶、笙等)音响、本民族特色发声(如呼麦)等形成的腔段整体式韵味。
以上这些不同类型的韵味元素由历史文化、人文感情和地理风貌积淀而成,具有强烈的亲和感。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它不仅能够满足大众“审美”的“成长性需要”,更能够满足人们“归属与爱”的“缺失性需要”。由于“韵味”元素在曲调的反复循环以及一定的结构中具有保持不变或基本不变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传统音乐有章法和规律可循。多个“韵味”元素在腔调中独立、并置、重叠、连缀等多种形式的出现,使之成为整个基本调的核心,使音乐作品弥漫着浓厚的特色韵味。可见,“韵味”是“一曲多变运用”集中性思维的聚焦点和向心力。多个“韵味”元素排列组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就是区分“此曲”而非“彼曲”的根本基因,也是我们传统音乐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变化无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密码。
二、发散性思维
所谓发散性思维,又称辐射思维、放射思维、扩散思维或求异思维,是指大脑在思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射状。[13]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中的核心成分,也是音乐创作中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一)线性思维与立体思维并存
我国传统音乐以线性旋律为主的特征,决定了它存在明显的线性思维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在线性思维中仍存在大量的立体思维与数理逻辑关系。有些是显性存在的,如多声部民歌,戏曲曲艺音乐伴奏乐器中的多声部自由变奏,民族民间器乐合奏中多声部纵向结合等形成的,诸如:支声性和音、固定低音形成的和音、托腔装饰性和音、力度性和音、打击性和音等,这些都体现出我国传统音乐中的立体思维;还有许多是隐性存在的立体思维,笔者将着重在这方面进行探析。这种隐性存在的立体思维是站在微观元素的角度,好比用放大镜、折射镜等多途径对我国传统音乐“单音”“单线条”中隐含的细腻而丰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力的重新考量和发现。美籍华裔青年作曲家梁雷认为:“每个音好比是一粒种子或是一个容器:单个的音可以作为将许多不同的音乐参数置入其中的交叉点。”[14]他受启于中国的古琴音乐,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创立了 “一音多声”的技法,这是“传统东方音乐中单音细腻丰富的色彩变化以及潜在的多声部功能”[15]的探索。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证实了音乐与空间、数量之间的通感关系。如利拉赫·阿基瓦卡比等人的研究显示音高是具有空间定义的数组;[16]瓦尔特·比克的研究透露,感知音值会引起注意的空间转移;[17]等等。笔者认为,在传统音乐中存在以下隐性的数量关系与立体思维现象:
1节奏中的数量关系与立体结构
在云南民歌《放马山歌》[18](谱例1)中,板数为公差1(3-2-1)的递减关系,呈现出“螺蛳结顶”立体结构式的递减节奏型(谱例2)。除公差为1的数量关系外,还有公差是2的递减节奏,如十番锣鼓《十八六四二》[19]。另外,还有一种节奏形式是“鱼合八”,是递增递减节奏关系的组合,即递减型7、5、3、1与递增型1、3、5、7各对应句式的相加,总数为8。“鱼合八”不仅体现出传统音乐中严密的数理逻辑关系,而且还隐含着两个正三角、倒三角立体结构图。如谱例3所示“苏南吹打”中的《鱼合八》(不包括其每一句后面的固定结音节奏)[20]。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递增、递减节奏规律形成的立体图式多种多样,有宝塔尖、金橄榄、蛇脱壳等,由此可见,“横看成岭侧成峰”,从横向旋律中换一种视角,就可以抽取出其中暗含的立体结构和立体思维。[BW(D(S,,)]
2腔音列中的数量关系与立体结构
在旋律中,腔音列也存在多种立体空间的伸缩变化。如山西山曲《想亲亲想在心眼上》[21],旋律中运用了超宽音列,其中①处的11度、②处的8度以及③处的7度大跳,很好地描绘了思念中急切、火热而又跳动不安、起伏不定的情绪。这种空间立体感从线性旋律中跳然而出,见谱例4。
纵观全国的传统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长编》[22]中体现出旋律音调中腔音列音程空间立体感与各支脉传统音乐之间的联系:以中国音乐体系为例,秦晋支脉、北方草原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关东支脉、荆楚武陵支脉、巴蜀支脉、岭南支脉在腔音列上超宽音列居多,经常出现6~11度的大跳,空间起伏距离宽广;中州支脉、江淮支脉、吴越支脉、青藏高原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客家支脉、台湾山地支脉腔音列的立体程度就会逐渐缩小,而且窄音列、小音列、近音列的成分居多。[23]
小到一首歌曲,大到整个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从微观到宏观,腔音列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其音乐的地域特点与母语基因风格。作为种子的腔音列,其能量折射出人文地貌的厚度和人格特点的立体形象。
3音色、音量叠加中的数量关系与立体结构
我国有大量的传统器乐以自娱独白为主要特点,但是仍有很多注重乐队合奏、产生多种立体交响效果的音乐形式。如,隋唐时期的燕乐,其乐队编制很大,包括管乐器(笛、篪、箫、笙等)、弦乐器(琴、瑟、三弦琴、箜篌、筝、琵琶等)和打击乐器(方响、钟、铃、磬、节鼓等),除此之外,还有声乐做陪伴[24];汉代的“吹鼓乐”,以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为主演奏的器乐,鼓、排箫、横笛、笳和角等共同组成中国式交响乐的立体音效。这种立体音效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形成各种色彩性和音之外,还存在各种音色、音量的叠加现象。不仅重视对旋律的装饰,产生音高的立体感,还着眼于不同数量的多种乐器不同音色的叠加以及音量气势的渲染,从而产生音色的立体化、音量的浓厚度,这是另一种隐性立体思维——“音色、音量的拓展、叠加式立体思维”,起到一种突出、点要的效果。见谱例5。毋庸置疑,其结果依然是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
(二)单向思维与双向思维并存
我国传统音乐尽管大多数是线性旋律,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旋律仅是由一个主题发展而来,而是在感情表达的自然流露中存在类似西方音乐中(例如奏鸣曲式)对比式主、副双主题的例证。如在广东音乐《双声恨》中,第一腔句(1-45小节)与第二腔句(45-115小节)之间就构成了D商调式和G徵调式两个主题,形成类似西方属主关系的调式调性变化。整首乐曲在进入流水板之前,大部分乐句围绕着两个主题线不断衍伸发展(D商调式和G徵调式交替出现),如牛郎和织女两个形象交织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互诉衷肠,凄楚而哀婉。(见谱例6[26])
另一方面,仅从单主题音乐分析,一个完整的主题,一般都具有旋律上行、下行自带抛物线所构成的一对矛盾体,这两个矛盾体就是双向思维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如,谱例7中第1-2小节中的F-E-D的下行旋律和D-F-A的上行旋律构成一对矛盾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因此,在传统音乐中单向思维与双向思维变通并存。(见谱例7[27])
(三)严密性思维与灵活性思维并存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有许多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严谨性与严密性,在创作中需要对每个音、每个段落等进行仔细推敲、考量;还有一部分则有一定的灵活度,可以进行变化、即兴或自由发挥,体现出严密性思维与灵活性思维并存的创作思路。
我国传统音乐就各种单个腔句而言,灵活性思维主要体现在其头部、腹部,特别是腹部旋律的多变性;但是其尾部旋律,即终止,往往具有很大的传承性、可辨性、稳定性[28],即严密性。因此,刘正维学者提出传统音乐的两大终止群体:徵(Z)终止群体和羽(Y)终止群体。
戏曲中的灵活性思维体现在:同样唱腔在不同戏曲中通过板式变化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甚至差异很大,如京剧《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与《三击掌》西皮“慢板”之间的变奏,由11个音变奏成129个音,相差十多倍,产生许多新生的旋律,给创作者极大的创作自由。[29](见谱例8)
过去民间用工尺谱记谱,以“上尺工凡六五乙”代表音阶中的七个音,以板眼符号点明节拍的重音和大致的节奏。[30]这种记谱法中记录的主要骨干音及节奏轮廓是刻意为之的严密性思维的体现,而演奏者可以围绕骨干音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做即兴变奏,各个不同律制的乐器声部在结合时会产生偶然因素,形成有趣的声部配合现象。这种骨干音基础上的变化就是灵活性思维的展现。(见谱例9)
我国唐大曲也存在严密性思维与灵活性思维的创作思路。如唐大曲在段落结构上充分体现了中国音乐的三部性原则。这是程式性严密思维的体现。第一部分为散板序奏;第二部分为大曲主体,由多曲联套组合而成,通过变奏、对比手法发展音乐;第三部分为大曲的展开,引入新材料,速度渐快,情绪激昂,是大曲的高潮乐章。[31]其中为区别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再现性而采用新材料展开则是独特性思维方式的表现,同时其中大量变奏手法的使用也是灵活性思维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蛇脱壳”变奏原则,颇具特点。……A3 A2 A1 A,属逆行变奏手法,即先子曲后母曲。以《苏合香》为例,第一部分“序”十九句六段,第二部分每一帖十一二句六段,第三部分“破”“急”各为九句五段接最后“曲破”二句一段,见图1。[32]许多大曲的结构具有循环因素,即双主题循环变奏发展手法,是灵活性思维的又一大显著特点。如《春莺啭》中一系列A、B双主题的循环往复,最后再现主题A,落于主题A。[33]
结 论
在今天日益重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社会需求下,全方位调动人们的创新精神、培养大脑创造力是增强国民综合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事情。创造性思维由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组成。我国传统音乐中独具中国特色的“韵味”是聚合思维的聚焦点;在发散思维方面,我国传统音乐具有线性思维与立体思维、单向思维与双向思维以及严密性思维与灵活性思维并存的特点。这些创造性思维元素隐藏于由腔音、腔音列为核心韵味的传统乐系内,组合成多种基因密码,散放入浩如烟海的传统音乐作品里,需要我们揣摩、解密并汲取其中的养分。一言以蔽之,我国传统音乐是“深情的理性”与“逻辑的感性”之间交织而成的辩证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