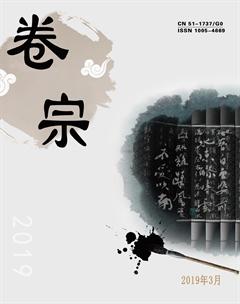试论柳宗元“文不废俳”
摘 要: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其散文在文学史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我国的寓言文学历史悠久,但直到柳宗元,才使得寓言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文不废俳”是他在散文理论上的创见,是其寓言散文一大特色,并在其寓言散文中多有体现。
关键词:寓言;幽默;文不废俳
我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各类典籍中都能够找到部分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包含着宝贵的生活经验。然而,寓言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中往往处在末流的位置,不能引起文人雅客们的重视。寓言散文的创作在先秦时期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在该时期中,寓言散文主要起着诸子们阐发个人政治理念,抨击他人观点的作用。先秦之后,寓言散文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创作,使得寓言散文成为了独立的文学样式,他提出相关寓言散文创作的理论观点,对晚唐以及之后的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寓言作品形式多样,有说、传、赋、对,还有文,其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依靠故事本身的暗示来表现主题,有的却以评论故事的形式来展现主题。然而,无论是哪种展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幽默、戏谑的特点,这种创作理念被称为文不废俳。“俳”,俳谐、戏谑、幽默的意思,《说文解字》:“戏也,从人非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戏言带有生动、幽默的特征,中国的戏剧来自于民间,看戏是市民娱乐消遣的活动。因此,一出戏中若没有生动活泼、幽默戏谑的言辞,是难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柳宗元吸取了俳的嬉笑怒骂、幽默动人的特征,并运用到寓言散文的写作当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诗文大多都强调“雅正”,对于“俳”文的写作往往表示藐视。韩愈的《毛颖传》营造了浓厚的戏谑、幽默氛围,成为了宋代俳谐文学创作的典范,但却因为违背了诗文创作的雅正要求,而遭到了指责。张籍批评“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裴度也批评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关于《毛颖传》,社会上的反映是“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阅读《毛颖传》后,郑重写下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
在文中,柳宗元首先赞扬了《毛颖传》给人“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的印象,紧接着提出“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的作文观点。柳宗元在这段话中明确提出了作文不能废弃戏谑、幽默,诙谐,进而产生“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的“奇味”。他充分肯定司马迁不同于以往的撰写史书的写作方法,从侧面反映了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中对趣味、幽默的追求。
柳宗元主张的文不废俳,文章要具有趣味。我们发现在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散文中,大部分的文章都体现出文不废俳的创作主张,有的文章在言辞中直接展现了趣味与幽默,而有的文章则是间接表达了幽默。柳宗元寓言中的趣味和幽默,并非单指文章中包含了使人酣畅大笑的元素,还有着寓言故事背后蕴含着的意味深长的启发。事实上,在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中滑稽和幽默是不能等同的,滑稽的故事情节能够带来酣畅大笑,而幽默却表现为意会的笑。二者虽都会引人发笑,但滑稽浅露,幽默则含蓄。单纯的滑稽,只是让人能一笑了之,并无余味可寻,若是在滑稽之后有可回味、可寻思之处才是幽默,也才符合了柳宗元提出的文应有“奇味”之说。西汉以来,出现了扬雄《逐贫赋》,王褒的《僮约》等调谑、讥嘲笔法写的散文,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俳谐文的写作,直到宋朝俳谐文学创作的高潮。作文为趣、文不废俳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绵绵不断的创作传统,但几乎在各个朝代,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载道、言志、缘情为中心的主流文学的排挤和批评,但它从未销声匿迹,而是潜伏在正统文学创作的边缘,最终影响了散文以及小说的创作。
文不废俳的创作理念在柳宗元的寓言写作有所体现,如何在字里行间中体现趣味、幽默,这成为他必须要处理的问题。由于受传统诗文载道、言志、缘情的影响,若寓言中是只表达了趣味与幽默,文章是难以流传至今的。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文以明道”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以往,诗歌作为载道、言志的主要载体,而散文是非主流的文学体裁,无法载道、言志,而古文运动正是要克服这个弊端,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如何使散文既能发挥出载道、言志的作用,又能生动有趣。柳宗元的文不废俳的观点为散文写作注入了蓬勃的艺术活力,使文章多了几分生动自然,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
柳宗元部分寓言的主角是动物,选取了在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有的篇章中通过不同动物的对比,颠覆了人们日常中的认知,并增添了喜剧效果。柳氏寓言中丰富的趣味性和喜剧性的背后往往蕴含着理性内涵,如《黔之驴》,驴凭借着庞大的外形,连凶猛的老虎都惧怕它。却在老虎多次的试探下,发现驴只是空有其表。当老虎对它“荡倚冲冒”时,它在“不胜怒”的情况下,却也“蹄之”而已。这一“蹄”,把它的软弱无能彻底暴露了,最后被虎“断其喉,尽其肉”。柳宗元先是颠覆了驴的日常形象,然后通过描写老虎前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比手法的运用,表现了驴的喜剧形象。“庞然大物”、“看似神”的驴表现出了虚弱无能的本性,造成了极大的不协调,颇具有滑稽意味。《黔之驴》滑稽意味的背后讽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徒有其表而又“好以技以怒强”的人,使人读了后,不仅发笑,还思考其蕴含的哲理。
类似的寓言还有《永某氏之鼠》。永州有一人,因生肖为鼠,非常崇拜鼠类,家中不允许养猫,更不允许伤害鼠类,甚至人都要吃老鼠剩下的食物。鼠类白天与人同行,夜间咬物,“其声万状”使人无法安睡。后来“永某氏”搬走了,新屋主对鼠类十分痛恨,借猫雇工,“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灭鼠在生活中十分常见,当它处在正常状态下,是无法让人发笑的。但经过柳宗元的处理,一转灭鼠为养鼠,将“永某氏”的恋鼠癖、鼠类在其纵容下对生活造成的不便得以放大,并超出了常态,便使人的笑声油然而生。尤其是群鼠先前的得意忘形、甚嚣尘上的情状,与后来它们的悲惨下场之间的对比,可以说大快人心。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當审美主体否定丑时,心中会引发审美快感。当我们依据作者的启示,进一步将它跟“窃时以肆暴”者们进行对比时,文章中的幽默会更加明显,也使得讽刺美感更加凸显。
柳宗元的寓言虽结构短小,但意味深远丰富,他使寓言成为独立的文体。柳宗元不仅学习了先秦寓言的写作方法,自己还有所创新。“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这段话,表明了作文不仅要明道,而且文要具有气、趣、幽的特点,这样的文章才不显得呆板无味。《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记言之文亦有风趣绝佳者。柳宗元主动学习的是《国语》中的“趣”,主要表现在以人物对话为主的篇章中。柳宗元巧于利用嘲谑、反语、夸张等手法,从文章的修辞手法来表现文不废俳的创作特点,使得寓言更富有趣味性。在以人物为主角的篇章中大多都是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来表现严肃的思想内容,如《乞巧文》、《愚溪对》、《李赤传》、《起废答》等等。
《愚溪对》通过柳子与愚溪对话来自我嘲讽来表现文章的幽默美。柳子(柳宗元的化身)在梦中与愚溪之神辩驳,通过两人之间一来一回的辩驳中表现出了幽默,却是自我嘲笑,既生动又无奈。愚溪之神首先为自己辩驳,认为柳子称他为愚溪是污蔑。溪神认为事物应是名副其实,如闽地的“恶溪”、西海的“弱水”、秦地的“浊泾”等都是有其实才有其名,而“清且美、能灌溉、能行舟”的溪,为何被称为愚溪?柳子回答:“你本来是不愚的,但是我愚而又偏爱你,所以你是无法摘掉‘愚的帽子”。接着柳子指出是溪神招愚者来住,而且住下后又迟迟不走。溪神听到此,无话可说只得辞别柳子。全文中围绕着“愚”,以柳子和溪神的对话展开全文,柳子一系列不同于常人的举动,实际上是作者的写照,撞跌半死而不悔,不过是知难而进,不甘屈服现实的表现。柳宗元面对永贞革新的失败与贬官的苦闷,表面上自嘲,心底却有着傲岸和不屈服。因此,溪神不愚,柳子也不愚,而柳子坚持说愚,这样倒置的自嘲使得文章的幽默美得到加强。《乞巧文》的构思方式和行文结构和《愚溪对》有相似之处。乞巧节,柳子看见妇女们向织女礼拜乞巧,希望能“驱去蹇拙,手目开利”,柳子想到自己的“方拙”,于是也向织女乞巧。在祷告词中,先是对织女颂扬,再说明自己的大拙之处。织女的使者却在梦中对他说:“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坚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失大,失不汙卑”柳子听完,“泣而欣受”决定“抱拙终身”。文中作为士大夫的柳子学妇女向织女乞巧,本身就有较浓的喜剧色彩,而更富有喜剧色彩的是随处可见的自嘲。而柳子的自嘲看起来是自贬,实际上却是对权贵们的鄙夷和怨愤。
柳宗元提出“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文章应该具备“趣”的特点,这和文不废俳的观点不谋而合。“趣”已经不再局限于学习《国语》提供的经验,而是加入了自我的理解。因此,“趣”渗透到其大多文章中,使他的文章和同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家的文章相比,有了别样的特色。虽然柳宗元借《国语》提出文章应具有趣味,却并未真正指明趣的内涵,我们可以从其文学作品中分析出趣味或者是文不废俳的主要含义。寓言的结构、修辞、语言、意象等等,都成为了“趣味”的载体,产生了异于常理却令人舒畅的艺术效果。古文运动虽高扬“文以明道”的创作理念,在散文创作中摆脱了骈偶体裁的束缚,实现了文章阐明儒道的目标,但是在理论上还忽视了古文作为独特的文学体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而柳宗元的文不废俳使文章多了几分活泼自然,少了单纯说理的生硬牵强,同时还填补了这个空白。
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中主张文不废俳,然而并非文章一昧追求戏谑、趣味,还要有说理或讽刺的作用。在柳宗元的寓言中,大部分的篇章都以戏谑、趣味、幽默为主要的表现手法,讽刺、嘲讽为主要目的,而达到说理的目的。柳氏寓言往往带着喜剧色彩,通过把对象的丑暴露出来后加以嘲讽和讥笑,随后马上否定。如果讽刺是直露的、冷酷的,是无法体现幽默的,因此柳氏寓言中的讽刺往往都是含蓄、内敛的,同时还兼具趣味,表现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使得文章不只有冷冰冰的讽刺还有奇味。柳宗元的《李赤传》可以说是一篇“奇”文,以虚构离奇的情节来创作文章,却又具有耐人寻味的含蓄美。文中的李赤自称能诗,因此自名为“赤”,意在和李白齐肩。然而,能与李白自拟之人,却被厕鬼化为的妇人迷惑,一心想与她结为夫妻。多次在茅厕中自尽,却被友人救了下来,还把友人大骂一顿,直到最后一头扎进厕坑而死去。故事的情节是离奇古怪的,具有极浓的怪诞色彩。茅房给人肮脏、臭气熏天的直观感受,李赤自拟李白,应当有着超然自得、潇洒豪放的品质,却在厕鬼迷惑后,一心要在肮脏的茅房里结束生命,两者的对比体现出了作者对李赤的态度。将李赤与现实生活中“为欲利好恶迁其神”的人进行对比时,就能感受到作者对这类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否定。《李赤传》中的怪诞美促成了幽默美的形成,而幽默的背后体现了强烈的讽刺意味。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说道:“为词章,泛滥渟蓄,如深博无涯涘”新的立意、新的构思、新的语言,在艺术上表现出多变的风格,避免平庸,使文章有滋味,这样的观点影响了晚唐的讽刺小品文的创作。不可否认的是,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对于晚唐讽刺小品文,甚至对明清的小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柳氏的寓言中,讽刺是自我表达的主要方式,突显了文章的主旨与作者的感情。如《罴说》,此文短则短矣,而内容上十分完整。楚地有一名猎者,凭借着“吹竹为百兽之音”的小技,模仿鹿鸣,想引诱鹿来捕捉,可是引来了貙,猎人急忙吹出虎声吓走了貙,却引来了虎,猎人只能吹出罴的叫声,谁料把虎吓走了而引来了罴。此时猎人再也无法吹出能够吓走罴的动物的叫声,落得“捽搏挽裂而食之”。文中所虚构的故事虽然离奇,本身就有一定的喜剧色彩。文章的幽默美在行文之间有所体现,在故事背后的深刻讽刺中也有体现。作者在文末暗示:“今天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引导着读者对寓言“谜底”的思考,却没有点明谜底。柳宗元寓言讽刺对象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关,《罴说》写于藩镇割据严重的中唐,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以藩制藩”的策略,用某个藩镇的力量制约或镇压另一个藩镇,而柳宗元对国家的制藩政策的隐患有着清楚地认识。他在这篇仅有130字的寓言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中的貙、虎、罴等分别指代了当时势力大小不同的藩镇,而猎者则是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寓言的结局是猎者最终被罴吞掉,也就预示着统治者采取的“以藩制藩”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国家的权力将会被分割,人民将会面临更加黑暗、复杂的社会现实。可见,《罴说》寓意丰富,意味深长,它将含蓄与讽刺相结合,形成了明显的讽刺性幽默美的艺术效果。
柳宗元寓言汲取了先秦诸子寓言的优秀传统,使寓言散文成为了一种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古代散文的种类。柳宗元大多数的寓言虽结构短小,但都独立成篇,并且广泛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柳氏寓言将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也就要求了社会讽刺寓言不仅在说理,而且还要具有文学性质,因此,文不废俳的观点被提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詩有别才,非关理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以纠正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端,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在散文创作中,没有相应的散文创作批评理论。柳宗元的文不废俳观的提出,为散文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持。文不废俳要求了散文写作要有趣味性和幽默感,而讽刺则通过文章的“奇味”、趣味表现出来,使得文章更具有感染力和张力,也使得讽刺意味更加深远。柳宗元的寓言兼具趣味和讽喻的双重特点,掀起了继先秦诸子之后寓言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撰.柳宗元集校注[M].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许慎撰.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3]严羽.沧浪诗话[M].普慧、孙尚勇、杨遇青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孙昌武.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5]徐英.柳宗元寓言幽默美初探[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6]康建强.试论柳宗元之文趣说——以对《国语》文趣的继承与发展为考察中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7]沈文凡、彭飞.晚唐讽刺文学对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接受[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作者简介
李春锦(1995-),女,海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