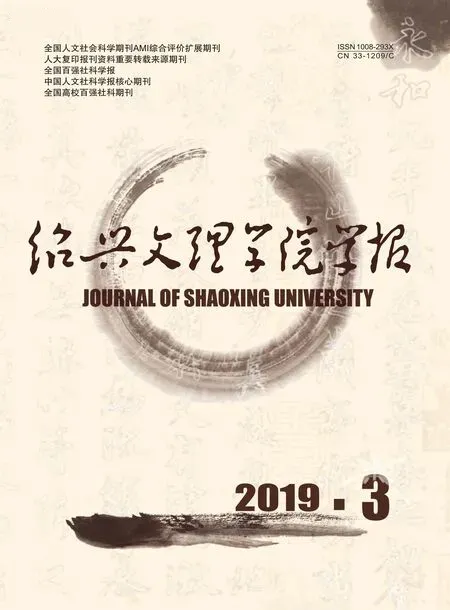近代出洋的先行者
——斌椿使团的文化旅程
柴旭林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由于长期的封闭落后,晚清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疲于应对,为西方各国所制约。外交事务上的长期停滞,给晚清政府的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使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采取措施,加强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斌椿使团的派出就是晚清政府试图初步了解欧洲国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出使缘由及使团成员
19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了解打败自己的“蛮夷”之国,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对外国事物知之甚少,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茫然无知。特别是又拘泥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封建传统思想,无法做出突破。就在这时,一个偶然性的机会使清政府迈出了对外交流的第一步。同治五年(1866),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因成亲而请辞归国,同时劝说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恭亲王奕派人随行,借此机会可以了解西方国家的概况。于是就有了斌椿使团的出行。
(一)出使缘由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兹查有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前年五月间,经总税务司赫德延请办理文案,并伊子笔帖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兹印证。”[1]2
(二)使团负责人的选定
在选定出访团负责人时,清政府所看重的并不是官衔或者才能,而是选用了“老成可靠”的卸任山西襄陵知县斌椿。“斌椿(1803—1871),字友松,监生,属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曾任江西赣县知县。道光三十年(1850),服满候补,掣得山西平阳府襄陵县知县缺。”[3]472清政府之所以选取斌椿为负责人,是为了防止同文馆的学生“少不更事,贻笑外邦”。更重要的是斌椿受赫德聘请,在海关总税务司办理文案已有两年之久,其子广英也同聘襄办,经常与洋人打交道,加之赫德对他们父子俩非常了解,所以斌椿父子得以接此差事。据《航海述奇》所记:“同治乙丑年冬,十年二月,经总理衙门奏派,前任山西襄陵知县、副护军参领衔、三品顶戴、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斌椿(友松)……前往泰西各国游历,查访风俗。”[4]1简单说,该使团的任务是:“将各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5]204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斌椿是旗人,更让清政府放心其忠诚度。对于清政府来说,汉人和洋人打交道是最不让其放心的,因此,在涉及官方性质的对外交往中,任用更多的是满族旗人。这一点,从洋务运动伊始,总理衙门官员和同文馆学生的民族构成就可以看出。加之斌椿此人好交友,一直存有海外旅行之心,其与许继畬、李善兰等人皆相识,前者更是在斌椿出访之前赠其所著《瀛寰志略》一书。故一系列综合因素决定了斌椿成为此次考察的负责人。
(三)随行人员
1866年正月,斌椿等一行十一人领旨受命,同各国使臣辞别,正式出行。该使团自大沽口出海,一路南下,途经山东、香港等地,又经南亚、东南亚等地前往欧洲,沿途风俗人情载入《乘槎笔记》,该书是中国人所著第一部旅欧游记,且是亲历者亲笔所书的第一部游记。
二、斌椿使团的旅程及见闻
斌椿自称为“东土西来第一人”,其作为传统士大夫的代表,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但却时刻怀有游历四方、增长见识的意向,实为难能可贵。斌椿使团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访问使团,虽不曾有正式的外交使团称号,但其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不容忽视,“看似无足轻重,实则这次出访西洋,在清朝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不容忽视”[7]81。
(一)斌椿使团的旅行路线
1866年3月14日,赫德一行在拜访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于天津乘轮船启行。在上海停留四天后,改乘法国轮船“拉布得内”号,而后于3月27日,抵达香港。换乘“康拔直”号,先后抵达西贡和新加坡。4月24日,他们抵达苏伊士。5月2日,使团抵达马赛。随后斌椿一行人抵达伦敦,受到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接见,在英国参观完毕之后乘火车去了柏林,这是他们访问的最后一个首都。斌椿使团于8月19日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中国。9月28日,船抵香港,使团解散。斌椿于11月13日回到北京。总理衙门表示将把《乘槎笔记》抄呈御览。
现阶段史学界对斌椿使团的访问路线已有详细梳理,故不赘述。但对其重要作用与贡献梳理稍欠,故对此着重探讨。
互联网已经深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改变了,对于传统的电视和报纸杂志等传媒方式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网络作为媒介比起传统的媒介更显得出很多优势,它打破了地域限制,更实时快捷直观地得到所要获取的信息,也使信息得以共享,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互联网上的众多网站中,新闻发布系统在各大网站中是不可或缺的系统之一,人们能够通过网站上的新闻发布系统了解更多的信息,获取社会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新闻进行检索。
(二)斌椿使团的见闻
斌椿一行人从出访开始,接触最多的便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出行所坐的“火轮船”到之后所乘“火轮车”等等,一系列先进科技产品让斌椿等人眼花缭乱。他们记录下了近代国人对于西方科技的心理感受,同时也展现出传统士大夫在东西方文明碰撞过程中的心路变化。
1.对近代化交通工具优点的介绍
斌椿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首次接触近代交通工具自然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对近代科技充满了赞叹。此次出访首先乘坐的是法国轮船“行如飞”号,斌椿等人对于此轮船的印象还好,尤其在触礁时他更是肯定了该轮船的坚固,“大雾弥漫,舟触于石。使非坚固如此舟者,则危矣”[6]93。张德彝则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该船,详细介绍了当时洋船所携带的救生艇和救生圈,以及轮船内部的客房等等。
由上海乘坐轮船转赴香港时,斌椿对此轮船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先是描述了该船的外形和大小,又紧接着详细记载了该轮船的内部构造、人员配置、住宿环境等等,这是中国人关于西方轮船的初步认识。“火轮器具居其大半,占一千二百礅,货物正容八百礅。船主一人,司船者十一人……舟之上下四旁,皆有铜铁管贯注,数百人饮食洗濯之用,无缺乏忧也。”[6]95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斌椿等人对于近代火轮船的欣赏和赞叹。
在前往麦西国(即埃及)途中,斌椿等人乘坐了火轮车:“申刻登火轮车。前车为火轮器具,烧石炭……初犹缓缓,数武后即如奔马不可遏。树木、山冈、阡陌,皆疾驰而过,不可逼视。”[6]104斌椿不仅在其笔记中记录了第一次乘坐火轮车的情景,更是在诗歌中对火轮车进行了赞叹:“轮车之制,首次载火轮器具,火燃水沸,气由管出,激轮行……前车启行,后车衔尾随之,一日夜可行三千里,然非铁路不能。”[6]163又有“宛然筑室在中途,行止随心秒转枢;列子御风形有似,长房缩地事非诬;六轮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劳八骏驱?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车辙遍寰区”[6]163。从斌椿引经据典作此诗可以看出他对火车是由衷赞美的,这与那些将近代科技称之为“奇技淫巧”之人相比,更可见其开明先进。斌椿在法国时还记载了脚踏车,“街衢游人,有只用两轮,贯以短轴,人坐轴上……驰行疾于奔马”[6]108。总体而言,斌椿等人对西方近代交通工具持比较欣赏的态度,“发达的交通工具让斌椿既新奇,又认同”[8]15。据《乘槎笔记》所载,斌椿在法国还曾让人购买了一个火轮车模具:“得火轮车式样一具,王承荣代购也。”[6]111
2.将近代机械化信息传入国内
斌椿使团每到一地,都要去参观当地的工厂生产情况,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斌椿等人见识到了西方先进科技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巨大功效,也表现出了对这些先进生产工具的赞美。“他们乘坐了轮船、火车和电梯,参观了许多大城市和名胜,看到了电报、织布机和其他机器,大开眼界。”[9]74
斌椿等人到达法国马赛时,见到了当时的电梯,“客寓楼七层,梯形如旋螺。登降苦劳,则另有小屋可容七人,用火轮转法……帐幔铺设皆华美”[6]107-108。张德彝同样对电梯作了初步描述,他称电梯为“自行屋”,“如人懒上此四百八十余步石梯,梯旁一门,内有自行屋一间……欲上第几层楼时,自能止住”[4]21。斌椿和张德彝都对电梯表露出了一定的赞赏。
随后,斌椿等人还记载了近代化的西方工厂,留下了近代中国人对近代化机械的最初印象。近代化的西方工厂分别有造船厂、纺织厂、印刷厂、铸币厂、造针厂等等。“辰初,偕新旧二总督,乘双马车四辆至造针处。层层高楼,横以铁桥;处处轮机,通以水道。男女作工各二百余名,人多而力省,盖恃火机之功也。又至造铜笔处,用小火机,一时可得数千支。又往造轮车厂,其木皆南印度产也。钉长四寸,螺蛳形。再至造田器处……其镀法将金银掷于药池,溶于清水,再系铜器浸于水内,则金银自黝于铜上,薄厚如意,极为光显。”[4]48类似参观这些工厂所留记述不胜枚举。在法国见识到电报后,张德彝也发出了赞叹:“此处随按,彼处虽千万里亦随得之,其速捷于影响。”[4]26
至欧洲,斌椿等人更加直观地见识到了近代欧洲的城市风貌,也记载了近代西方的各种事物,包括城市面貌、建筑特色等。“从《乘槎笔记》中可看出:欧洲都市的规模和繁华使斌椿大为震惊……现代化城市及其与中国传统城市的反差都让其惊讶不已。西方的机器亦使斌椿感到新鲜和刺激。”[12]22
三、斌椿使团的贡献
史学界历来对于此次出行诟病较多的地方就是该使团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起到开化民心的作用,记载更多的是浮于表面的风土人情。不可否认的是斌椿与张德彝在其所留游记中关于民俗风情的内容确实占到了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阶层来说,能在见识到外国风土人情之后,思想上产生许多启蒙性的转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并且是不容忽视的。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入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现代学者对于斌椿使团地位的肯定仅可作为参考,若想真正彰显此次出访活动在中国近代史或者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则必须从使团本身的事例出发,探索该使团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实际贡献,且在此过程中,政府对于该使团的回应也具有重要的佐证作用。
(一)使团任务的完成——以政府赋予为标准
考察该使团的成就时,不能仅从使团负责人,即斌椿回国后的个人命运出发,应综合使团成员所留文献以及他们的命运发展进行全面考量。不论是《乘槎笔记》还是《航海述奇》,都实现了记录各地风俗民情的目的。“斌椿的西行,成为清政府由闭关锁国缓慢开放国门的序幕。斌椿的出国可以说是主持对外交涉的议政王奕的一次试探。他要让斌椿现行出洋,看看外国的真实情况;同时他要让清政府的官员用出洋考察的亲身经历,向清政府和思想仍处蒙昧状态的士大夫进行‘现身说法’,道出出洋的必要性。斌椿的出国考察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15]475-476对于此点,段培龙在其文章中论道:“斌椿此行的任务须留心考察泰西诸国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并将资料带回以供朝廷参照印证之用。此处说明斌椿出行着重在游历考察,而非奉总理衙门之正式训令以从事外交及政治活动。”[31]38
从赫德其人来说,他极力促成了该使团的出行,其目的是:1.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去欧洲;2.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3.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4.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5.使斌椿一回到中国,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6.使清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和科学;7.劝导中国派遣大使出国;8.在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切合实际的基于理性的友谊[16]512-513。事实上,赫德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在未来的日子里,除了第5点以外,赫德的所有愿望都一一兑现”[17]125。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来看,斌椿使团的派出并没有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却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派出该使团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走向近代化,只是在经历一系列挫败之后想要了解自己的“对手”而已。所以,不能仅用近代化史观分析此次出行,而应从该使团的派出缘由等具体理由方面分析。
(二)近代观念的引入——使团成员的观念转变
斌椿等人在去往欧洲的途中见识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其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其对于科学观点的认知以及对西方先进科技与制度的认可上,这在其著作中也时常有所体现。
到达欧洲之后,斌椿一行人更是不断经受着近代城市及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洗礼”,传统思想观念的某些方面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一点从斌椿回答英国太子妃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6]117此外,在回答维多利亚女王时还有表现出对英国文化及见识到的英国城市风情的赞美:“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游览胜景,实为感幸。”[6]117-118从斌椿在欧洲所留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欧洲文明的认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在当时,承认欧洲的物质技术文明‘甚于中国’,欧洲的民主制度也自有‘好处’,对于一个传统文人而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同治年间的中国,并未形成学习西方的社会共识,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传统文人眼里,更是被视为‘獉狉之佐’。”[14]62
到达北欧国家荷兰后,张德彝等人见到了该国的填海造田技术,并为之惊奇,在详细描述了该工程的具体配置之后,又写道:“每日运水六千万斗,廿年来,复得肥田数万顷。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4]55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抑或说在信奉天命的中国,发出这样的感叹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在经受了西方近代科技的刺激之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虽然他们还没有萌生出完全科学的思想,但可以做出初步的改变已实属难得。
该访问团对于所见识到的绝大部分西方近代文明持认可态度,这一点从其看到近代西方机械后的感受可以看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斌椿出访伊始,就不断改变着自己原先的想法。
在欧洲见识到近代机械生产之后斌椿等人所受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一行人饶有兴致参观了近代工厂,并为之赞叹不已。如在法国参观造船厂后,张德彝道:“先见管厂官,经德善告以来意,该员大喜,乃令取其所造各种轮船轮机图式,并一小轮船长约三尺者与看,其法备臻精巧。”[4]22又如参观纺织厂时斌椿叹道:“计自木棉出包时,至纺织染成,不逾晷刻,亦神速哉。”[6]117张德彝亦道:“纺线织布,悉用火机,一时可得棉线数百斤,织染洋布数十匹。棉花以合众国产最佳,中国产次之。”[4]50从其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承认东西方的差距。斌椿对于近代机械生产的介绍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在讨论近代机械的引进问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斌椿等人的记载:“按乘槎笔记,英都织布局,楼五重,工匠三千余人,棉花至此,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13]
同样,在见到近代西方的时钟后,张德彝详细描述了该时钟的外形和配件,并感叹道:“机关巧妙,莫可名言。”[4]65在海上经历了长时间航行之后,斌椿对地球的概念也逐步确定下来,“足证地球之圆,非臆说也”[6]129。
(三)对晚清政府后续活动的影响——以对外事务为中心
斌椿使团出行后的第六年,即1872年,在容闳和李鸿章等人的倡导下,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启了中国留学事业的新时代。这一历史事实或许和斌椿等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清政府在之后的对外交往中更加开放,这与斌椿等人反馈的良好信息密切相关。换言之,假使斌椿等人在第一次出访后,有关欧洲的反馈信息十分糟糕,恐怕清政府不会更放心地走向开放。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之后志刚等人的出访,正是斌椿反馈回来的信息不算太坏,才有了后来人的继续出访。正是斌椿等人的出访,迈出了清政府看清自身与国外差距进程的第一步,“现在随通商各口,外人星罗棋布,中国情事无一不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国则未深悉,自斌椿、志刚、孙家毂出使后,至今无续往之人,窃谓宜选有才略而明大体者……”[23]可以看出斌椿等人的出访涵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斌椿使团对清政府后续的外交活动产生了影响,对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作用,“斌椿虽系游历性质……回国后,报告外情甚详。总署王大臣之观感一新,乃益视遣使为未可缓图。遂于同治六年九月致各省将军督抚论修约书,条列六项,其中即有遣使一条,另各纾己见,以便公商”[24]670。“然而有意义的是,10年之后我们能够听到在这个事件中来自斌椿使团的遥远的回应。曾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几乎可以肯定读过斌椿和张德彝的日记。”[16]465客观分析,斌椿使团的出行并没有对当时的国内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但不能因此彻底抹杀其对于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斌椿代表团在英国受到了欢迎,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此举也表现出赞赏的态度,因而也部分地打消了清廷对遣使的疑虑,初步验证了遣使的可行性,促成了清统治者思想观念的根本动摇。”[25]69从中可以看出斌椿使团对于晚清外交的推动。
(四)对西方近代政体的介绍——以使团成员的记载为重点
在游览途中,斌椿等人还记载了西欧等国的政治体制,并表达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到达英国后,斌椿等人参观了英国议会大厦,记录了国人对于西方议会的最早印象:“申刻,至公议厅。高峻闳敞,各乡公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意见不合者,听其辩论,必俟众论佥同然后施行,君若相不能强也。)”[6]114斌椿介绍了议会议政的情形,并且补充了议会制度的特点:“六百议员聚于‘公议厅’,共议政事,议员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辩论,达成共识后再施行其主张,君和相亦不能勉强之。”[14]62随后,斌椿又记述了英国地方政治制度,“英属各乡镇,皆公举一人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6]118。必须承认的是,斌椿并没有对议会制度作出评论,而且对其本质认识不清,但可以有意识地记载下来还是难能可贵的。
除斌椿外,张德彝也对英国的议会制度作出了详细记述,且详细程度甚于斌椿,并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申刻乘马车至其议事厅,楼式奇巧,皆系玉石雕刻……大概西俗好兵,贵武未免贱文,此其所短者也。虽曰富强,不足多焉。”[4]45从其论述中,可看出张德彝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并不十分认同。但张德彝对议员的选举等都作了记述。此外,张德彝还记载了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又至判断处,其承审者十二人,昂然上坐,两造立于左右四五步外。事有不平,悉听十二人评断。断之不决,另请十二人,无有刑讯。虽系武断乡曲,尚不失于公道,有时亦经官断”[4]50。由此可见,张德彝对陪审团制度持比较认可的态度。另外,他还记载了近代西方的婚姻制度和自由恋爱下的婚姻观念。
(五)使团成员的命运——以张德彝为考察对象
从斌椿本人回国后的经历来看,这次出行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自身的命运。“斌椿始终未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他虽然在北京有一些政治影响,但是似乎没有做什么事,以增扩清政府对西学的看法。根据赫德日记(1867年1月9日),斌椿于1867年初担任同文馆‘西学总管’,但是他的任命似乎只是名义上的,他最终于1871年去世。他的儿子接受该处英文馆的任命,也没有发挥持久的影响。”[16]464-465此种说法仅仅看到了斌椿个人的仕途命运,忽视了对此情况出现缘由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尚未形成学习西方的风气,加之斌椿位卑言轻,与当时的朝野大臣相比,更是差得很多。因此,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清朝臣子自然不可能在朝野政治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所以,斌椿及其儿子回国后的命运,表面上看是此次使团出行的失败,究其根本是整个中国的失败,是由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情形导致的,仅仅将其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次活动的失败,是有失公允的。简而言之,整个中国社会封闭顽固的风气造就了此次使团的命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次使团的出行是失败的。
就使团成员自身来说,其命运的发展是可以对此次出行的成功进行佐证的。斌椿使团成员中,凤仪、彦慧曾供职于清朝的海关部门,张德彝所达成就与地位最高。
张德彝回国后逐渐在晚清外交事业上有所成就,“张本人曾陪随‘马嘉理使团’,写有另一部日记,而且终于1901年成为驻英国公使。经过差不多长久的等待时期之后,蒲安臣使团中许多中国成员在国外都有杰出的外交成就”[16]465。张德彝回国后曾供职于清政府的外交机构,为晚清的外交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查其所上奏折:“奏为驻英参赞,一届三年期满,照章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出使章程内载,随使人员,三年为期,期满奏奖,如有经接办大臣留用者,仍准以期满之日请奖。又吏部保奖章程内载,凡出使人员……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26]类似奏章、电报等不胜枚举,又如《时报》所载:“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电告外务部己于去月二十九日会英国外务大臣蓝斯唐候提议收还威海卫。”[27]足以说明张德彝在晚清外交事务中的参与度。
虽说张德彝已经有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趋势,但是封建思想仍占据他的主要观念,“张德彝……成为了先行者,却没有成为领路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28]62。加之张德彝本身是同文馆的学生,并没有经过正规的科举考试,所以心中不免有遗憾。这就反映在他在晚年时教导后代还是要读书取仕,“国家以读书能文(按指八股制艺)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读传统的圣贤经书)为要务”[29]91。将张德彝与同时代的其他传统知识分子相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他所具备的进步性,其实这正是当时中国向近代化过渡所导致的社会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承认外国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拘泥于自身接受的传统教育无法自拔,从而表现出一种纠结的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的出现是情有可原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纵观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缓慢起步,在这段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中,人们的心态也必然要经历痛苦的转折。这是历史走向进步所必然带来的“阵痛”。
四、结语
历史本身是不断发展的,我们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我们不能在达到新的高度之后就否认前人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封建顽固的氛围中,斌椿等人敢为人先,勇敢地迈出了对外交往的第一步,其勇气本就值得肯定。中国的近代化历史本身就是缓慢进行的,也必然存在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斌椿使团没有对国内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是客观事实,但假若中国自该使团之后就完全认识到自身与近代化西方的差距,那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也不会如此的艰难。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亦然,在这一进程中,斌椿使团没有成为“领路人”是客观事实,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造成的。但即使如此,其作为“先行者”的贡献不可轻视,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