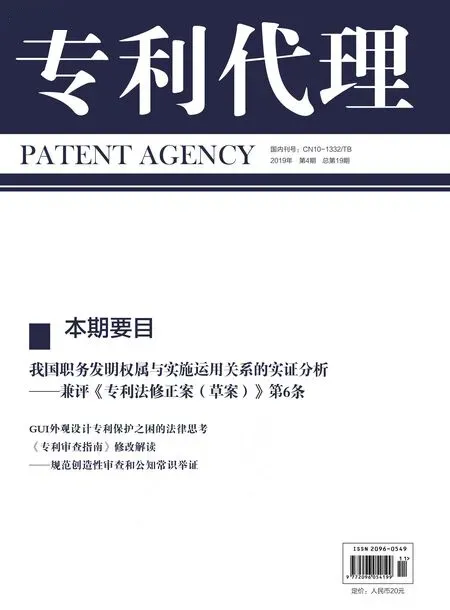浅析权利要求单侧撰写
曾红芳
一、权利要求的单侧撰写和多侧撰写
单侧撰写是相对于多侧撰写而言的,单侧撰写是指在撰写权利要求的过程中,对于方法权利要求,仅以方法交互中的一侧设备作为执行主体,来描述方法权利要求的各个步骤;对于装置权利要求,仅撰写装置设备所包括的部件和结构。多侧撰写是指在撰写权利要求的过程中,对于方法权利要求,包括了由不同执行主体所执行的多个步骤;对于装置权利要求而言,往往是包括了多个执行主体分别所对应设备的系统。
由于多侧撰写的专利权利要求涉及的执行主体众多,在确定侵权诉讼对象以及诉讼管辖法院时,较之单侧撰写的专利权利要求更为复杂。为了适应专利侵权判定使用的“全面覆盖原则”①参见《侵权责任法》(20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我们越来越强调采用单侧撰写的方式来撰写权利要求。特别是在著名的“西电捷通诉索尼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一案中,经过该案曲折的无效和诉讼程序,我们更是体会到了单侧撰写的重要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带来创新性的技术方案是在一侧设备,或者单独的设备中完成的,那么采用单侧撰写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但如果创新性的技术方案不仅仅涉及一侧设备,或者采用单独的设备是完成不了的,那么如果生硬地采用单侧撰写的方式势必也会对权利要求的保护带来不利影响。
二、权利要求单侧撰写存在问题的案例分析
【案例1】一种建立网络连接的技术方案,由终端生成用于建立网络连接的连接建立信息,并将该连接建立信息发送给网络服务器,由网络服务器对连接建立信息进行鉴权,在鉴权通过的情况下,网络服务器与终端建立网络连接,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法建立既自由又安全的网络连接的问题。在该方案中,由终端生成连接建立信息能够实现连接建立自由的效果,由网络服务器进行鉴权能够实现安全建立连接的效果。
对于终端侧的方法权利要求而言,如果仅写终端侧所执行的动作,权利要求大致是这样的。
一种网络连接建立方法,其特征在于:
终端生成用于建立网络连接的连接建立信息;
所述终端向所述网络服务器发送所述连接建立信息,并与所述网络服务器建立网络连接。
显然,这样的终端侧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是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在解决所声称的技术问题时,缺少“网络服务器对连接建立信息进行鉴权”这一必要技术特征,是无法实现安全连接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终端侧的权利要求改写成这样:
一种网络连接建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生成用于建立网络连接的连接建立信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连接建立信息发送给所述网络服务器,以使所述网络服务器对所述连接建立信息进行鉴权,并在鉴权通过的情况下,与所述终端建立网络连接。
或者,改写成如下方式。
一种网络连接建立方法,其特征在于:
终端生成用于建立网络连接的连接建立信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连接建立信息发送给所述网络服务器,其中,所述连接建立信息用于所述网络服务器对网络连接的建立进行鉴权,并在鉴权通过的情况下,与所述终端建立网络连接。
显然,这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都克服了原终端侧权利要求在撰写时所存在的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缺陷。在第一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通过“以使所述网络服务器……”的描述方式,不仅体现了网络服务器执行鉴权的技术特征,而且表面上在权利要求的步骤中也没有出现非终端侧执行主体的动作。在第二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通过“所述连接建立信息用于……”的描述方式,也不仅体现了网络服务器执行鉴权的技术特征,而且表面上在权利要求的步骤中也没有出现非终端侧执行主体的动作。
但是,这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中,虽然表面上权利要求的步骤中没有明显出现由网络服务器作为执行主体执行鉴权的动作,但实质上如果网络服务器不执行鉴权的操作,是无法真正实现技术方案,解决技术问题的。在第一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以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倾向性地记载了网络服务器会执行鉴权的动作。在第二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所述连接建立信息用于……”,其中,“用于”一词虽然不能确保网络服务器一定会执行鉴权的动作,但是如果保护的方案中包括了网络服务器不执行鉴权的动作的话,这个方案是不能解决技术问题的。只有包括的是网络服务器执行鉴权的动作的话,才能够有效解决技术问题。因此,对于第二种改写的权利要求而言,网络服务器也是执行了鉴权的动作的。
因此,对于上述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而言,其实质上还是记载了“由网络服务器执行鉴权动作”这一技术特征的,即仅仅是表面形式看起来没有记载而已。因此,这与多侧撰写的权利要求的保护实质上是一样的。
另外,对于终端侧的权利要求而言,包括了终端的部件和结构,但在终端侧的权利要求中,还包括了采用网络服务器执行鉴权的限定,这就造成了不清楚是要对终端侧进行保护,还是要对网络服务器进行保护,造成了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不清楚 。其实对于这类问题的案件在欧美专利局进行审查时,采用上述单侧撰写的装置权利要求,欧美审查员都有过提出不清楚的问题。然而,针对这样表面上是采用单侧撰写,但实质保护内容还是多侧撰写的方式,在争辩后如果审查员不同意,除了修改为多侧的系统权利要求外,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来解决。
【案例2】一种在D2D 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技术方案:在D2D 设备间进行数据传输时,为了增强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性,在传输前由D2D 发送方设备对原始数据采用了一种新的数据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得到加密数据,以及在传输后由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与该新的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对传输得到的加密数据进行解密,从而得到该原始数据,实现数据的安全可靠传输。在该方案中,实现数据的安全可靠传输是由D2D 发送方设备对原始数据采用新的数据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并且由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与该新的数据解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对数据进行解密,才能得到该原始数据,两个操作步骤来共同完成的,缺少其中一个操作步骤均无法达到数据的安全可靠传输的效果。
对于本案,采用单侧撰写的方式时,对于D2D发送方设备侧的方法权利要求而言,权利要求大致是这样的。
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D2D 发送方设备采用数据加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密,得到加密数据;
所述D2D 发送方设备将所述加密数据发送给D2D 接收方设备。
显然,D2D 发送方设备这样单侧的权利要求是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在解决所声称的技术问题时,是缺少“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的与该新的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从而得到真正要传输的原始数据”这一必要技术特征的,是无法实现原始数据的安全可靠传输的。
同样,为解决该问题,参考同行的一些建议,将D2D 发送方设备这一单侧的权利要求改写成这样。
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D2D 发送方设备采用数据加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密,得到加密数据;
所述D2D 发送方设备将所述加密数据发送给D2D 接收方设备,其中,所述D2D 接收方设备对接收到所述加密数据采用与所述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进行解密,得到所述原始数据。
或者,改写成如下方式。
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D2D 发送方设备采用数据加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密,得到加密数据;
所述D2D 发送方设备将所述加密数据发送给D2D 接收方设备,用于所述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与所述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进行解密,得到所述原始数据。
虽然这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均包括了“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的与该新的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对数据进行解密,从而得到真正要传输的原始数据”这一技术特征,均克服了之前所撰写的权利要求所存在的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缺陷。在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中,均不仅体现了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数据解密方法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得到原始数据的技术特征,而且表面上均没有出现非D2D 发送方设备作为执行主体来执行动作步骤。
但是,这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虽然表面上其步骤中没有明显出现由D2D 接收方设备作为执行主体执行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的动作,得到原始数据,但实质上如果D2D 接收方设备不执行解密的操作,是无法得到原始数据的,即是无法真正实现技术方案,解决技术问题的。在第一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其中,所述D2D 接收方设备……”虽然作为执行动作的状态进行限定,但已经较为明确地记载了D2D 接收方设备执行解密的动作,得到原始数据的特征。在第二种改写的权利要求中,“用于所述D2D 接收方设备……”,其中,“用于”一词虽然不能确保D2D 接收方设备一定会执行解密的动作,但是如果保护的方案中包括了D2D 接收方设备不执行解密的动作的话,这个方案是不能解决技术问题的。只有包括了D2D接收方设备执行解密的动作的话,才能够有效解决技术问题。因此,对于第二种改写的权利要求而言,D2D 接收方设备实质上也是要D2D 接收方设备执行解密动作的。
因此,对于上述两种改写后的权利要求而言,其实质上还是记载了“D2D 接收方设备执行解密的动作,得到原始数据”这一技术特征的,同样也仅仅是表面形式看起来没有记载而已。因此,这与多侧撰写的权利要求在实质的保护上是一样的。所以,为使得权利要求表述更为清楚、简单,可以直接将权利要求修改为:
一种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D2D 发送方设备采用数据加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密,得到加密数据;
所述D2D 发送方设备将所述加密数据发送给D2D 接收方设备;
所述D2D 接收方设备采用与所述数据加密方法对应的数据解密方法进行解密,得到所述原始数据。
以上案例的技术方案中均仅涉及的是简单的两侧,但在实际的发明创造中,往往会涉及更多侧、更多设备的参与。对于需要多侧或者更多设备参与的技术方案,在对其中一侧进行撰写时,对于其他多个执行主体的执行动作,往往采用的撰写方法是,要么作为某一动作的状语存在,要么作为某一名词的定语予以体现。由于限定存在相互交叉,因此更容易造成权利要求的不清楚。另外,考虑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了避免对执行主体的单一限定造成保护范围的缩小,在实际撰写时,有时还不明确限定执行主体。综合上述原因,在采用单侧撰写时,如果对执行主体不明确限定,还会进一步地加重权利要求不清楚的问题。
三、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办法
其实,造成上述权利要求撰写尴尬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了适应几十年前法律规定的“全面覆盖原则”侵权判定。虽然“全面覆盖原则”还是能够较好地适应一些专利的侵权判定,但技术发展了几十年,发展的侧面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化,要求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去适应一成不变的法律规定,可能是不明智的。该法律规定也许很适应当时的需要,但对于当前高速发展的新领域,例如网络领域、通信领域等,几十年前的法律规定还是很难适应发展需要的。因此,面对新领域中的问题,在我们成文法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创新型社会的转型阶段,加强专利保护已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是否可以有条件地对法律法规进行适当补充或者借鉴参考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例如,德国《专利法》第10 条有关不以直接侵权为前提的间接侵权类型,较好地解决了有效保护专利与全面覆盖原则之间的冲突),适时地出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例如,对于一些需要多侧协调完成的技术方案,采用多侧撰写时,只要被诉方实质上采用了其中一侧的技术,即可直接被认定为侵权),从而使得法律法规最大可能地促进技术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