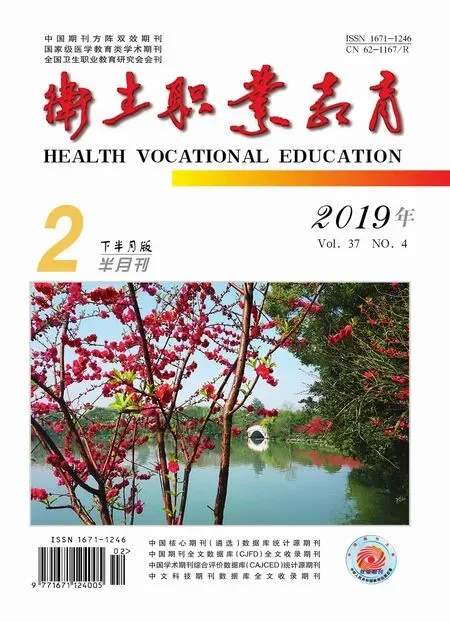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况分析及对策
王庆华,赵晓敏,刘骙骙,张 瑜,杨 忠
(滨州医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3)
2014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1]。生活满意度是个人依照自己选择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价,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生活满意度是多维概念,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经济状况、自我效能、人际关系和社会保障等[2]。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不仅物质层面需要政策保障,而且精神层面需要人文关怀[3]。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缺乏系统研究,本课题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况及对策,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8年3月1日至7月31日,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滨州市滨城区44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女性194人,男性 254人;年龄 24~39岁,平均(27.5±6.5)岁。纳入标准:(1)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2)年龄在16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3)研究对象身心健康,思维清晰,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本研究。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学资料,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家庭状况等;第二部分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问卷,包括社会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职业培训、经济收入、生活状态、身体健康、心理感受、自我效能、子女教育、法律援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共计12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非常满意(85~100分)、一般满意(65~84分)和不太满意(≤64分)3个等级,进行自评,计算满意度。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问卷调查法和焦点访谈法,以滨州市滨城区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和企业作为研究场所,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向研究对象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承诺匿名和保密,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利用周末或假期集中发放问卷和焦点访谈,自行拟订访谈提纲,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6%。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构成比和χ2检验、多元回归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等,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况
满意度=(非常满意人数+一般满意人数)/总人数×100%。包括生活状态满意度为67.86%,主观支持满意度为78.35%,经济收入满意度为55.58%,身体健康满意度为79.47%,心理感受满意度为58.71%,自我效能满意度为74.78%,总体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况[n(%)]
2.2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的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的多元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况
表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生活状态满意度为67.86%,主观支持满意度为78.35%,经济收入满意度为55.58%,身体健康满意度为79.47%,心理感受满意度为58.71%,自我效能满意度为74.78%,总体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表2显示,主观支持因素、自我效能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比较大(P<0.001),说明社会支持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来源与新朋友、互动活动、情感支持、工作成就、归属感及社会制度等有关,个体获取较多社会支持时,有助于其缓解压力、克服困难、自我效能感增强[4]。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构建以同乡关系、亲戚关系和同事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自我效能是衡量个体自信水平的重要指标,可影响其获取知识能力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对此,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互相合作交流,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使其获得个人工作成功的经验,增加自信,提高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进城务工早已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5]。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限制和小农意识影响,仅仅满足传统的消费需求,缺乏从整合好的信息中提炼自己所需知识的能力,劳动技能不高,只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客观上,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公共信息服务非均等化因素,自然就将这些信息弱势群体边缘化[6]。与城镇居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相关行业的行业环境、从业知识、劳动技能、竞争能力、驾驭市场能力都处于劣势,在信息占有和资源使用方面存在差距[7],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和职业素养有待提高。
3.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
表2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各维度及自我效能与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或P<0.001)。把社会支持及其各因素、自我效能带入逐步回归方程,对生活满意度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个体的自我效能、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判定系数为0.360,回归方程为Y(生活满意度)=57.2+0.579X1(自我效能)+0.724X2(主观支持)+1.695X3(对支持的利用度)。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有助于其更好地适应城镇生活。社会支持是系列的社会互动,包括家庭成员、朋友、老乡、同事及其他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和支持[8]。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也称实际社会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直接存在及参与,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重要资源[9]。主观支持也称领悟社会支持,即个体所体验到的情感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对支持的利用度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支持别人的同时也为别人给自己提供帮助打下基础。
4 建议与对策
4.1 城镇社区建立农民工管理中心,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环境
管理中心负责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管理,如农民工在务工地落户办法的制订及实施,居住、就医、权益保障的落实与监管,随迁子女的教育规划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问题。同时,建立健全各级农民工行业协会,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指导信息发布、法律咨询及援助、职业教育和创业培训等服务,加强各行业协会间的沟通协作,使之在劳务对接、信息共享、经验交流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双向机制加强管理、完善服务,切实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保障和实际援助。用工企业以人为本,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管理者应创造让员工感觉公平的工作环境,如公平的薪酬制度、公平的内部晋升渠道以及管理者观念上的公平。企业应多管齐下,营造更加公平的软环境,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状况,凝练企业文化内涵和团队向心力,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关心的事物主题及内容,如在社区层面推行法律援助、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讲座等服务,鼓励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社区活动,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生活,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4.2 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村生活幸福感,鼓励更多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让农民受到社会尊重与认可。大力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培训、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技能。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鼓励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组建职业农民队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加强对该群体的健康投资,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10]。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讲座以及运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强对农民工身心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状况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的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意识。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宣传及实施,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在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发挥了建设者和主力军作用,国家各级政府出台惠农政策,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思想观念发生新变化,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不断提高,积极融入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总体属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会支持因素和自我效能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