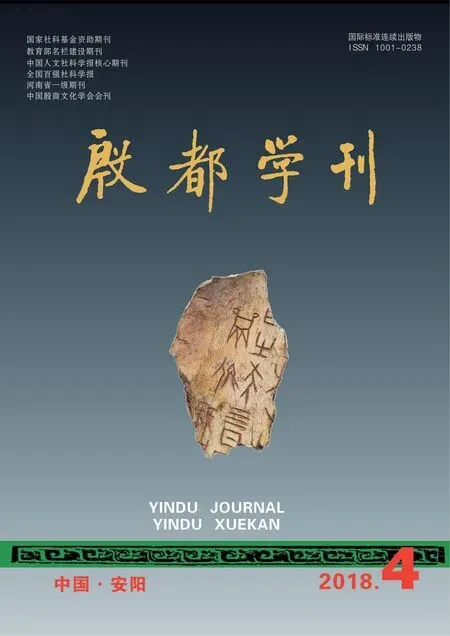全球史视域下的元代文学研究
——以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为中心
罗海燕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一、引 论
当代历史学家萧启庆先生曾指出,元朝既是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种世界性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当时跨族籍跨国境的多元文明得以互动和融通。就文学而言,元代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诗词文赋等,在西域、南方、北方和高丽作家群体的共同推动之下,形成了南北交融和东西播迁的态势,也因此具有了全球史的意义。当时众多的理学学派,“流而为文”,衍为了元代中州文派、北方文派、江西文派、新安文派与高丽文派等文学流派。注罗海燕等人《宋元时期的学术承传与诗文流派的生成》(韩国《中国语文论丛》2015年总第67辑)与《元代的儒学承传与多元一统文坛格局之形成》(《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曾指出: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儒学与文学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新儒学的理学被定为官学后,元代出现了众多的学派,这些学派“流而为文”,衍生为许多诗文流派,如中州文派、北方文派、江西文派、金华文派、新安文派、高丽文派等。这些文派之间跨越族群,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并促成了元代多元一体的文坛格局。其中,金华朱子学历来被视为朱学嫡脉,而到许谦一辈,则已由“讲学家”转而为“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许谦之后,至其弟子辈,更是均为“文章之士”。依据明晰的师门承传,金华学派流衍为金华文派。这一派成员众多,绵延百馀年,在元明文学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深远。
不过,目前对于元代金华文派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文学史的纵向发展中对其进行历史定位;二是把它与其他同时存在的诗文流派加以横向比较。由于缺乏全球史视域的观照,故在一定程度上了忽略了金华文派在海外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朝鲜半岛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即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元代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接受、认同和影响等,作一全面考察,以期在全球史视域下对元代时期金华学术与文学作出新的认知和估衡。
二、元代许谦之学与金华文派
南宋朱熹殁后,其后学派别林立。黄宗羲《宋元学案》中涉及朱子学派的学案就多达17个。其中,经由黄幹传至浙江金华何基以至许谦的一脉,朱学最为纯粹,历来被视为是朱学正统与嫡脉。清人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案语中即言:“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1](P216)何基(北山先生)、王柏(鲁斋先生)、金履祥(仁山先生)与许谦(白云先生),被世人誉为“北山四先生”或“金华四先生”。四人皆以朱熹为宗,将传承朱学作为毕生使命,使得师门兴盛,硕儒群出。及入元后,金华学派进一步传播朱子之学,维护正统,强调宗法。尤其是,许谦讲学于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学者负笈而至,门下著录者前后达千馀人。门人中叶仪、范祖干、方用、欧阳玄、揭傒斯、朱震亨、王毅等人均能弘扬师说。朱子之学由之得以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官学化。而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巩固统治、统一政教的过程中,宋濂、王袆、胡翰、章溢、苏伯衡与许元等金华朱子后学,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朱子理学嫡脉的金华学派,在元代新的社会历史环境影响之下,到许谦一辈时,发生明显变化。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曾指出:“余尝谓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2](P332)他认为,从许谦一辈到义乌籍的柳贯、黄溍等,再到宋濂(谥文宪)一代,金华(古称婺州)之学发生了三次变化。朱彝尊的评论也证实了这些衍变趋势,他说“金华承黄文献溍、柳文肃贯、吴贞文莱之后,多以古文词鸣”。[3](卷2《胡翰》)这三种趋变最终归于一途,即金华学派由朱子理学流派,转向了有着明显师承脉络且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元代金华文派。
黄百家指出:“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1](P299)四库馆臣曾评论许谦的诗文:“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4](卷166集部19《白云集四卷》)认为许谦诗作超出了前辈语涉理学的“击壤集”一路,同时其文醇古而无宋人语录之习气。最重要的是,许谦已由“讲学家”转而为“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尤其到许谦的弟子辈,他们虽然在理学上发明无多,但是在诗文方面成就显著。
金华文派成员之间主要通过师承关系等联结在一起。他们往往借助书院、私塾、乡学与家学等,形成了一种稳定且强有力的人际网络。“北山四先生”一生勤勉于传播朱子之学,其弟子柳贯与黄溍、吴莱等过从甚密。黄溍师从王炎泽,王炎泽师从徐侨门人,进而承续朱子之学,也属于朱学之后。吴莱年龄晚于黄、柳,但是因为他们同为方凤弟子,故往来密切。三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人常将三人并称,尊之为“三先生”。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等又师从“三先生”。他四人被人称为“四先生”,四先生之后,则有方孝孺等弟子。故就师承而言,“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吴莱)——四先生(宋濂、王袆、胡翰、戴良)——方孝孺,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承传主线。[注]元代科举制度时行时废,传统的“座主”与“门生”以及“同年”关系日渐趋于淡化,再加上元代学术氛围宽松,一人师从多人,乃至多门,成为当时普遍现象。金华文派中也存在某一弟子在礼本师之外,还参礼其他不同辈尊师情况,如胡翰既问学于许谦,又师从于柳贯。本文则主要从他们本人的言说及后世的一般认定两大方面加以考量与判定。同时,金华文派成员基本都生活在金华区域内,往往是同郡或者同乡。相同的地域,一样的风俗,交通的便捷,使得乡缘也成为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他们往往以“吾婺”或“吾乡”自矜。这种因乡土而产生的缘分,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无论是官居高位,还是沉沦下潦,他们都能因同乡之谊,彼此相互奖掖、荐推或颂扬。此外,各成员之间还存在相互交叉的亲缘、友缘、趣缘等关系。戴良拜祭方凤之子方樗时,曾提及金华文派成员之间的多种关联,称“某等之于先生,或以姻亲而托交,或以乡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从,或以友朋而密迩”[5](卷7《祭方寿夫先生文》)。如但就亲缘而言,吴莱为方凤孙婿,许谦有二子许元与许亨,苏友龙与苏伯衡为父子关系,而王袆与宋濂又为儿女亲家。这些关系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容性强却又界限分明的关系网络,有力促进了金华文派的生成。
金华文派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金华文派主张文学与学术、事功合和为一;二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道德重建意识,重视教化;三是形成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文风。黄百家论金华之学时尝言:“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1](P299)他指出“北山四先生”传承了朱熹的道学正脉,同时,至柳贯及弟子吴师道、戴良与宋濂等时,则又继承与发扬了朱熹的文学方面。可以说,“学髓”及“文澜”并得,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是金华文派学术与文学方面突出的特点。
金华文派前后承传了三代,绵延百馀年,在元明文学的变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初,金履祥、许谦等人授徒教学,隐居乡里,声名不显,却担任着传承朱熹之学的重任。元中后期,金华文人与吴中文人同为当时文坛最活跃的两大诗文群体。至元明之际,金华文派达于鼎盛,在全国文坛独步一时。明人胡应麟尝言:“国初文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王子充、刘伯温、方希古、苏平仲、张孟兼、唐处敬辈,诸方无抗衡者。”[6](卷1)《明史》也称“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袆、方孝孺以文雄。”[7](P4883)他们不仅以古文著称,诗歌创作亦不弱。胡应麟曾转述王世贞对宋濂与王袆的评论:“宋、王二氏,虽以文名而诗亦严整、妥切,则婺中诸君子,冠冕国初,不独其文也。”[8](P34)后来,尽管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政治打击下,方孝孺被杀,金华文人多凋谢、沦亡。但是,金华文派的文学主张及诗文创作却始终影响着有明一代,甚至馀泽惠及清代与后世。[注]明代文学流派众多,而这些社团、流派如“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等几乎都与金华文派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罗海燕《金华文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73页)此外,金华文派的影响还不止限于国内,甚至波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朱元璋曾不无骄傲地对宋濂感叹道:“方今四夷皆知卿者。”[9](P2350)
三、元代金华文派海外传播的多元路径
元代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始于元朝与高丽在政治上联姻以及“舅甥之好”关系的确立。元朝一统南北,程朱理学先是由南而北,南北交融,并由中原而东传至高丽,形成朝鲜半岛一脉。当代治学术史者一般认为,元初留居在元大都的高丽士人安珦、白颐正、权溥等,主动接受许衡一派的程朱之学,开启高丽一脉[注]许衡在元代学术界的地位被称为理学宗师。他创建的鲁斋学派覆盖了当时元朝北方学术界。所以,那时来中国元朝学习朱子学的学者深受许衡理学思想的影响。(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他们是元代高丽学派的第一代,之后则传授李齐贤(1287-1367)一辈。元中期李齐贤等人与姚燧等问学切磨,进一步昌明学术,并授之李穑等弟子。元后期李穑又灯传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理学由是大盛。但是现据留存文献可以确考,在元延祐六年(1319)左右,李齐贤曾与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许谦有过交往。李齐贤曾自述道:
延祐己未,予从于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宝陁窟。王召古杭吴寿山,令写陋容。而北村汤先生为之赞。北归为人借观,因失其所在。其后三十二年,余奉国表如京师,复得之。惊老壮之异貌,感离合之有时,题四十字为识。[10](卷4)
同时,许谦(1270-1337)又曾撰《李齐贤真赞》云:“目秀眉扬,神舒气缓。妙手描模,毫发无间。形色天性,所贵践形。人见其貎,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养内外。和顺积中,睟面盎背。朝瞻夕视,如对大宾。力行所学,无负其身。”[11](卷4)从两人的叙述可知,两人在当时已有交集,这庶几可以视作是金华文派与朝鲜半岛士人接触的可以确考的最早时间节点。之后,自高丽晚期至朝鲜王朝终结,金华文派一直藉由不同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朝鲜半岛的学术、文学与民族精神等。
(一)师友问学与私淑授受
元朝恢复科举之后,大量的高丽士人,往往“志欲仕中原,挺身归大元”[12](卷15《李公神道碑铭并序》),并逐渐由师承北方的许衡之学转为求教于南方的许谦。其中,尤其具有代表性者是高丽士人李榖与李穑父子。两人都曾在元朝中举,颇获中原士人赏识。李榖入元之后,曾直接拜访许谦,两人曾就四书问题等,共同探讨数十天。高丽学者罗继从曾为李榖画像作赞,并注解道:“元金华处士许谦,号白云先生,立学社,著《四书丛说》二十卷。公入元访之时,丛说尚未就,因讨论数旬。许谓公曰:‘幸逢有道,疑义多所辨明。’”[13](《聘君李文孝公画像赞》)从其中也可以看出,李榖对于《四书丛说》的成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李榖之子李穑曾直接师承许谦弟子中“许门四杰”之一的欧阳玄(号圭斋)。李穑曾在元朝科举中进士第二甲第二名,并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仕郞,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欧阳玄担任考官,对李穑极为赞赏,引为门生。李穑也视欧阳玄为自己的风范宗师,屡称“吾座主欧阳先生”。他在《书登科录后》中尝道:“我初偕计游中原,望洋学海穷词源。圭斋提衡翼群豪,轻重毫厘无间言。”[12](卷23《书登科录后》)并在诗中自道渊源来自,其云:“衣钵谁知海外传,圭斋一语向琅然。”[14](卷22《纪事》)朝鲜半岛士人对于李穑与欧阳玄的师友渊源尤其称道。如李縡曾道:“穑在元,从欧阳玄学古文。”[15](卷9《尊攘编》)李光靖亦云:“恭惟牧隐先祖,实为道学宗师,入乎中原则衣钵于圭斋。”[16](卷10《西山影堂上梁文》)此外,不少未能踏足中原的学者则通过金华文派的论著成为私淑弟子。如李朝学者黄景源、成韶对于许谦极力推崇之,“闻先生之风而慕其德”[17](卷6《与申成甫韶书》),并访求研读许谦著作,自任其后。
(二)同气相求诗文酬答
早在李齐贤一辈,就与金华学者陈樵等人,颇多诗文往还。陈樵《鹿皮子集》就存有多首酬赠李齐贤的诗作。后李榖在元统元年(1333)中举,并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陈旅曾道:“元统元年,天子亲策进士。旅叨掌试卷帘内,高丽李榖所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乃超置乙科。宰相遂奏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亦荣矣哉。”[18](卷4《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次年,李榖捧制书东还。“许门四杰”中的欧阳玄与揭傒斯等,都纷纷作诗送行,成为一时盛事。此外,“金华三先生”之一的黄溍也曾集陶渊明诗句题赠李榖云:“饯送倾皇朝,归子念前途。前途当几许,直至东海隅。古时功名士,事事在中都。遥遥沮溺心,君情定何如。”[19](《稼亭杂录》之《集渊明句奉题稼亭》)表达了对李榖的期许和不舍之情。也有学者读金华文派成员之书而想见其人,故有次韵追和之作。李朝学者李滉就因读黄溍文集中《秋夜观书作》一诗而有同韵之作,其《读金华集用<秋夜观书>诗韵》既表达了对黄溍的崇敬,认为他“金华发幽愤,学邃名亦隆。独登风骚坛,偏垒未易攻”。同时也对黄溍原诗中“吾将离言说,庶以观其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颇有深夜读书,独与古人相晤的意趣。[20](《退溪先生续集》卷2)
(三)购刊典籍究心研读
若不能登堂入室亲聆教诲,通过购买典籍以研读,则成为向圣贤问学的最佳途径。朝鲜半岛士人多藉助往来使者或商旅来获取金华文派成员的各种著述。李氏朝鲜王朝成宗李娎就曾欲读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而不得,故下旨访求。无名氏所辑的金訢《遗行》曾记载:“成庙欲览战国策,无内藏,下教访求,并及诸遗书。公上所藏吴师道校注战国策一部。 御书答曰:‘方观史记,须考此书。尔之进此善本,岂无意耶?’”[21](卷4)朝廷如此,士人也是如此。黄景源就曾托成韶务必访求许谦的所有论著。其云:“白云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及《春秋句读》十二卷、《仪礼句读》七卷、《诗名物钞》八卷、《书丛说》六卷、《四书丛说》二十卷,惟足下求诸四方,则他日必有得也。”[17](卷6《与申成甫韶书》)洪直弼也曾在《与申仲立》信中,嘱托购买许谦等人书籍。其云:“幸求仁山、白云两集,用作裨补世敎之资焉。”[22](卷13《与申仲立》)又曾对李子冈说:“区区所旷感于两贤(指金履祥、许谦)者,以所值之时同也,计应不言而喻也。必购两贤遗书,俾贱子获睹宗庙百官之盛,用寓高山景行之慕焉。”[22](卷8《答李子冈》)
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朝鲜半岛士人所研读的金华文学重要成员的典籍多达数十种,详见表1。
此外,他们也会重新刊刻这些文献典籍。如李朝的延平府院君李贵在中就曾道:“曾在先王朝,特令印出文天祥、方孝孺、郑梦周三家文集,颁赐中外臣僚。”[23](卷5《请印布抗义新编箚》)请令重新刊刻方孝孺的文集。
㈣ 访求画像拜祭真容
朝鲜半岛士人倾拜圣贤,除购买典籍之外,也往往访求画像,或挂于斋堂,或置诸左右,以朝夕拜祭。程朱之学东传之初,高丽士人安珦就曾在大都摹绘朱子画像,东还之后常置朱子像于近侧,以示钦慕。并且,安珦还曾资助金文鼎到中国江南画孔子和七十子像。之后,金华文派中,许谦、宋濂、方孝孺等人的画像,流入朝鲜半岛为最多。黄景源曾专门到中国访求许谦画像,并撰有《白云先生画像记》,其云:“今年冬,余入燕都,得先生画像而归,悬之堂中。……燕都人怪余来求先生像。然先生不事蒙古,凡天下学士大夫不幸遭极乱之世,皆宜以先生为法,百世之下,乌可以不传其像乎?乃为记,以示学者。”[17](卷10)方孝孺作为名臣代表,也曾被摹像崇拜。朴胤源《历代名臣像赞》还专门为方孝孺像撰赞。其云:“月沉辉,燕高飞。腕可断,诏不可草。直死为是兮,曲生为非。文章兮浑浩,道学兮正醇。又合之以节义,萃三美于一身。凡有秉彝之心者,孰不拜乎先生之真。”[24](卷22《历代名臣像赞》)

表1
㈤ 征引论著和品评人物
元代金华文派的论著和生平大节一直是朝鲜半岛士人谈学论道、著书立说以及臧否褒扬的重要对象。尤其是许谦的论著和观点,多为李朝君臣作为论学的依据。李朝学者崔璧《奎章阁内制讲义·诗传上》曾记载当时君臣围绕《诗经·鄘风》中“君子偕老”的问答:“御制条问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方说淫恶人之容貌,而疑于天与帝。恐似未安。此是古人质朴处耶?’臣璧对曰:‘许谦以为胡然天胡然帝者,是自天降耶其鬼神耶之谓,则释得好矣。而其异于后世口气,则诚如圣敎矣。”[25](卷3)如李滉曾引宋濂关于伊洛渊源的论断,并评论称“固亦天下之公论也”[20](《退溪先生续集》卷八《伊洛渊源录跋》)宋秉璿引宋濂的“积高山之善,尚未为君子;贪丝毫之利,便陷于小人”,并评论道:“此宋潜溪濂铭楹之语,可以为为士者之终身佩服也。”[26](卷17)裵龙吉则征引朱震亨关于风水方面的观点,其《风水辨》云:“善乎明儒朱彦修之言曰……此说深圣王之制矣。”[27](卷5)其他如苏伯衡《染说》、叶子奇《论元贿》、胡翰《风水问答序》以及王袆《青岩丛录》中关于“老子之道”的论断等,也广为征引。而李裕元《皇明史咏》中吟咏宋濂、方孝孺的诗歌,则是对金华文派成员生平大节的褒扬和推崇。其《宋濂》云:“学术文章一世宗,首膺征聘辅从容。佐命臣中声独卓,伟然不负弓旌踪。”[28](册3)其《方孝孺》云:“潜溪门下一书生,炯炯双眸秋水明。九食三旬独自笑,礼隆正学以庐名。”[28](册3)丁范祖《方孝孺》诗则云:“金川血雨晦三光,迎拜军前有蹇扬。纵恨书生疏庙略,能将家族死纲常。”[29](卷13)
除上述之外,朝鲜半岛士人还频繁化用金华文派成员的人事典故和诗文佳句。
四、朝鲜半岛对金华文派的认同和建构
自高丽季末到终李氏朝鲜一朝,朝鲜半岛士人对元代金华文派的接受,基于三大认同,并以“他者之眼”对其进行了本土化建构。
㈠ 对金华文派的三大认同
其一,作为朱熹之学嫡传的认同。尹锺燮在其《杂识》中曾梳理金华学派的统绪,其云:“朱子道统,一传黄勉斋,再传何北山,三传王文宪,四传金仁山,五传许白云。两贤以有宋遗民,毕生自靖于元。六传宋文宪,大明之中赞,一初之制作,猗欤其功。七传方正学,任纲常之重。为紫阳之所究竟,盖紫阳之道学正大,不绝如是。”[30](卷6)李榘在其《看史剩语》中也曾论金华道统,其云:“自朱夫子既没之后,门第弟子传相授受,以寿道脉者甚众。而胡元御世,天下荡然,无复礼义,犹幸于大贤遗化之地,儒师继起,隐居讲明,私淑诸人。如白云得之于仁山,仁山得之于鲁斋,鲁斋得之于北山,北山实得之于勉斋。的有来承,断无他惑。虽其所至有高下,所得有浅深,要不失其统绪。”[31](卷5)并将许谦一脉与北方许衡一脉及江西吴澄一脉相比,认为后两者是“屈身伸道儒名释行者”。他们都认为许谦接续朱子之学,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嫡传脉绪。这也是朝鲜半岛绝大多数士人的共同认知。
其二,人格气节的认同。前人笼统论有元一代的学术和文学,认为理学上分为三家,即许衡之学、吴澄之学与许谦之学;而文学上也分三派,即北方之文、江西之文与浙东之文,其中浙东之文即是指金华文派。[注]民国时期学者刘咸炘等,就曾依据元代的学派而将元代文派分为三家。其《宋元文派论述称》:“论元之文,当分三方”,即北方之文、江西之文与浙东之文。(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就朝鲜半岛士人的评论而言,在丽末时学者多尊崇许衡之学与北方之文,而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士人则明显地开始贬抑许衡的学术与人格,而特别推尊许谦的为学与为人。柳麟锡就曾论许衡,认为:“盖不可以有学问而掩其失身之大也。”[32](卷54)而对于入元的金履祥和许谦,他则以“完人”相许,尝云:“虽举天下夷狄而二公独中国也。举天下禽兽而二公独人类也。若二公者,真可谓完人也已。真可谓善学朱子也已。”并提出:“金仁山、许白云秉义自洁,可以法天下后世也。”[32](卷54)而洪直弼认为许谦人格之高更在金履祥之上。其云:“金仁山、许白云两贤,蒙难于铁木之世,隐居讲道,守身全节,是所云天地变化,我得其正者也。仁山曾被一命于德祐之朝,固应乃尔。而白云上不逮宋,下不及明,遗世独立,不受腥尘,卓然为赵氏遗民,视仁山又加难矣。一传而为宋潜溪,贲饰一初之制作。再传而为方正学,扶植万古之纲常。所以为紫阳世适也。”[22](卷13《与申仲立》)在他们看来,金华文派的承传也是人格精神的承传。
其三,文学成就的认同。朝鲜半岛士人对金华文派的文学创作也极其推重,多认同金华文派具有深厚的理学底蕴,注重道德人格,并在文学上成就非凡。李宜显《云阳漫录》曾称“明兴,宋潜溪、方逊志诸公以经术为文章,其文虽各有长短,犹可见先进典刑”[33](卷28)。李德懋《诗观小传·宋濂》评论了其人其诗:“濂为开国文士之冠,于诗亦用全力为之,严整安切,盖心慕韩、苏而具体者。”[34](卷24)认为宋濂的诗歌努力学习、实践了韩愈、苏轼“严整安切”的风格,从容不迫,有大儒风范。韩章锡在《明文续选序》中则专论方孝孺云:“及观其所为逊志斋集,其志远其辞宏,其气和平而其理密察,泽于道德而其言自中尺度,措之政事而其术皆可师法。”认为方孝孺是“有德者必有言”的典范,堪为“皇明三百年有真儒者出,为文章正宗”。[35](卷7)卢守慎在《逊志斋集序》中也曾论:“臣受命作先生集序,窃不胜惶恐感激。疾读未半,不觉泪落。徐而考之,得杂著、表、笺、啓、书、序、记、题跋、赞、祭文、行状、传、碑、表、志、诗总一千三百八十首并附录凡二十四卷。既而叹曰:‘醇矣哉,先生之文也!理逼周程朱子,而考亭之密、昌黎之严,合而为一。”[37](卷7)
㈡ 对元代金华文派的本土化建构
中国自元而明清,历经三代,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也实现了高丽与李氏朝鲜王朝的鼎革。尽管都处在东亚这个共同的“接触空间中”,但是由于文化生态的不尽一致和与时变迁,朝鲜半岛士人以“他者之眼”,对客观存在的元代金华文派进行了本土化的建构。
其一,梳理出了元代金华文派大致的传承谱系,并指出其主要特征。李朝学者金春泽曾在《东文问答》中论道:“朱子以后,中华道学之变,盖自何北山、王鲁斋,以及金仁山以下诸儒与元代相终始者,皆朱子之学也。明兴而宋景濂、王子充则佐文治,方希直则树臣节。又此学之余也,可谓盛矣。”[37](卷18)他在这段话中,指出了自“北山四先生”到宋濂、王袆一辈,再到方孝孺,这一脉的前后承传。同时,还指出了金华文派所包含的注重学术、推重道德节气与长于文学的三大特征。李宜显则更侧重从文学方面加以梳理,他在《陶峡丛说》中论道:“明文集行世者,几乎充栋汗牛,不可殚论,而大约有四派,姑就余家藏而言之。方逊志、刘诚意、宋潜溪,以义理、学术发为文词者也,此为一派。”强调这一派的创作是“以义理、学术发为文词”[33](卷28)。
其二,以金华文派的文学创作作为典范。这种典范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提升,二是人格砥砺,三则是诗文汲取。就第三方面而言,朝鲜士人往往以金华文派为效仿的标的。李宜显《云阳漫录》曾指出:“宋潜溪、方逊志诸公以经术为文章,其文虽各有长短,犹可见先进典型。”[33](卷27)同时,他们在文章中多引征言论作为依据,在诗歌中多追和原韵,熔铸典故,化用佳句。李瀷《贫贱生勤俭》结尾就曾引叶子奇《草木子》中“祖宗富贵自诗书中来,子孙享富贵则贱;诗书家业自勤俭中来,子孙得家业则亡勤俭”,并以为“更是亲切”。[38](卷16)宋濂曾作《静室》诗二首,李滉则次韵和之为《偶读宋潜溪静室诗次韵示儿子寯闵生应祺二首》,并示以儿子和弟子。此外,宋濂的一组以徐福出海求仙为题材的诗歌《日东曲》也深为朝鲜半岛士人关注,和者甚众。南龙翼在与朋友应和时就曾多次提及。其《次达帅富土山韵要和》后曾附原韵云:“闻昔宋濂题杰句,何时徐市没遗踪。”另一首《次柏师富山韵》后亦附原韵云:“徐福来兹踪已占,宋濂成曲世相传。”[39](卷11)洪直弼曾作《病枕闻赛皷》诗:“鼕鼕赛皷彻昏晨,南舍东邻尽祀神。安得起来西邺令,免敎狐啸惑愚民。”[22](卷3)其中最后一句即来自吴莱的《巫者降神歌》“妖狐声共叫啸”。李徳懋非常喜欢叶子奇的《隐居》一诗:“功名富贵两忘羊,且尽生前酒一觞。多种好花三百本,短篱风雨四时香。”曾书酒家土壁上。丁若镛《陪家君同韩礼安尹掌令弼秉二丈于吴承旨龙津别墅夜宴》诗更是化用其意,其云“花园种花三百本,拟弃轩裳随鹿群”[40](卷1)。韩章锡《天一亭》诗亦化用之:“更有名花三百本,江乡不断四时香。”[35](卷1)
其三,自觉接续元代金华文派谱系。元代理学东传,经由李齐贤、李榖、李穑等人推扬,极大促进了朝鲜半岛学术与文风的转变。周世鹏《金司成季珍入湖南幕赴锦山郡两行时赠行诗卷跋》就曾论道:“至丽季然后程朱之学始东,士蔚兴。及我朝,文与道大行,为士于世者,入得伊洛之渊源,上沂于洙泗,莫不以生晩为喜,于会文辅仁之道愈勤。”[41](卷6)后世在评论丽朝之际的文学史时,对于李榖、李穑师承许谦、欧阳玄等,颇多着墨。李縡《尊攘编》就指出:“穑在元,从欧阳玄学古文。朝鲜之士学古文,自穑始。”[15](卷9)安重观《文武》也曾论道:“而胡元之虞集、欧阳玄,颇以文词自著,则是或为我明开先者欤。明兴大家数如宋景濂、方希直,既皆应期而作。……稼、牧父子,特起于其垂亡。”[44](卷7)中国当代学者张学智《牧隐李穑儒学思想的渊源与特点》在论李穑的思想的渊源时,也曾指出金华学派的理学与文章之学相结合的学风对牧隐有很大的影响,此种影响也奠定了他一生基本的学术方向。[43](P66-74)
其四,主张文道合一。元代金华文派反对文与道割裂,主张文道合一,文统与道统合一,追求义理、文章兼擅。朝鲜半岛士人对此有着同样认识和主张。金春泽《论诗文》曾道:“文本于道,一而已。道莫尊于孔孟,故文亦莫盛于孔孟。自孔孟以后,则文有韩、欧。道有程、朱。文与道始分焉。此殆天地间一大欠事。”[37](卷16)曹兢燮《尧泉先生文集序》对文道两分提出批判而主张:“夫文所以明道也。古之圣贤,道充而文至,文与道为一。”[44](卷18)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丽朝鼎革之后,李朝士人受政治影响,对于元朝充满敌意,动辄云“胡元”“鞑靼”,这种情绪对元代金华文派的建构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尊许谦贬许衡、吴澄的倾向非常明显;二是对于许谦等人的不仕元朝的行为高度赞赏。这也造成元代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学术、文学与民族精神。
五、结 语
元代金华文派以区域命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超越了区域限制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流派。同时,它在朝鲜半岛也有着深远影响。就文学史意义而言,元代金华文派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认同、接受,以及本土化建构,不仅促成了文人之间的亲密交往,而且由之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诗文。这些诗文背后则是学术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生成。尤其在全球史视域下,元代金华文派所蕴含的学术、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等,在朝鲜半岛实现了互动、转化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