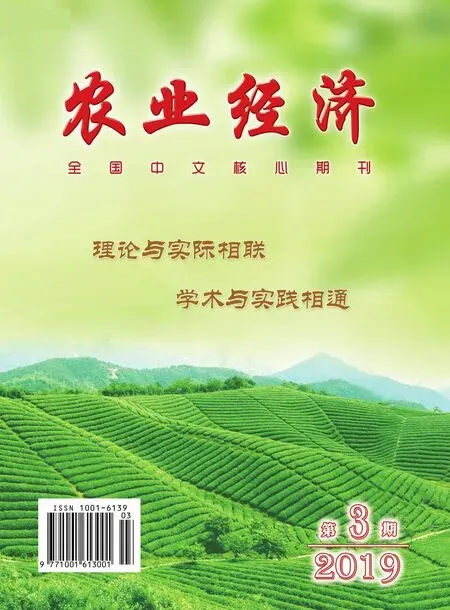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理路及其价值实现研究
◎赵 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主要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扶贫攻坚力度,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热情,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截至2017年末我国仍有3000 多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一、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扶贫工作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1]。由于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实力各不相同,社会资本在农村扶贫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也经历了较大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的计划经济时代
这一时期社会资本基本未参与我国农村扶贫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贫困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一方面,国家通过农村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以制度改革为基础,国家开始在农村地区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建立了“五保户”、特困群体救济制度,实现了对农村困难居民较低水平的保障。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国有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占比高达90%以上。民营经济不发达,社会资本实力弱小,这一时期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开展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二)改革开发至20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二是21世纪初至20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首先,自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初的十年,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包产到户改革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极大的活跃了农村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难以再对农村人口起到普惠作用,反而是因为各地区不同的资源和环境禀赋,导致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为缓解这一矛盾,国家提出了农村扶贫战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一时期社会资本开始逐步参与农村扶贫工作。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政策由农业支持工业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过渡,于2005年废除了农业税并开始实施粮食补贴政策,2007年在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理路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是促进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重要基础,而要实现农村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首先要厘清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理路。
(一)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是共同富裕
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是共同富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是先富带动后富。思考和判断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状况,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农村精准扶贫的理论依据,即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合理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对农村精准扶贫开发工作仍存在较多分歧,具体来说就是要不要、能不能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一是要不要通过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必须要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
二是能不能通过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社会资本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开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效果显著。例如,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自2017年开始担任河北省阜平县平石头村名誉村主任,为该村定下了未来五年内人均纯收入翻十倍的目标。并且京东集团已开始在全国800 多个贫困县推广电商精准扶贫,目前来看发展势头良好。另外,大连万达对贵州丹寨的帮扶、恒大集团对贵州毕节的帮扶均成效显著。
三是社会资本通过何种方式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具体方式五花八门:产业扶贫、电商扶贫,“输血”与“造血”之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外部的帮扶仅仅是困难群体脱贫的条件,困难群体自身强烈的脱贫意愿才是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前提。因此,扶贫先要扶智,必须首先激发困难群体的脱贫意愿,之后才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问题。
(二)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价值取向是体现被帮扶地区意志
体现被帮扶地区意志是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取向。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逻辑取向,即在农村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到底谁决定谁的问题。扶贫资源是按照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来分配,还是按照自下而上的困难区县的发展需求来分配,两种社会治理机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必须要搞清社会与国家间从属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决定国家。但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分析,问题却又变的复杂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逐渐消亡,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无“社会”的现象,社会组织完全成为政治意志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在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和国家谁优先的问题,理论层面仍未完全解释清楚。
其次,从实践方面来看。由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应首先从满足困难区县发展实际需求出发。所以,当前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既要尊重国家有权部门和社会资本控制人对扶贫资源的实际分配权,又要解决好如何通过满足困难地区千差万别的发展需求,进一步激发困难地区自身对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活力。但是,当前在实践方面尚未完全处理好扶贫资源分配与被帮扶地区意志之间的关系。
(三)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实现机制
扶贫工作的实现机制,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充分反映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机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矛盾。用于精准脱贫的资源有限,一方面难以实现全覆盖,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整体推进。因此,不论是从财政资金支持农村脱贫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资本支持农村脱贫的角度来看,困难区县脱贫反映的不仅是一个权力保障的问题,更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在财政资金支持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跑部进京”和贫困县不愿摘帽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扶贫资源在分配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十八大以来,政府将农村精准扶贫作为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投入了上千亿的财政资金,同时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投入。但是,在实践中,困难区县自身无力直接参与巨大增量扶贫资源的分配,而是由公共资源或社会资本的实际控制者来决定如何分配,困难区县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申请扶贫开发项目,然后由有权部门或社会资本实际控制人将扶贫资源分配给他们。因此,扶贫资源自上而下的分配机制是一种人治的方式,难以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扶贫资源自下而上的分配机制才是一种法治的方式,才能真正体现困难区县的实际需求。因此,在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平、有效,如何解决部分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恶劣的困难区县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问题,仍然是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三、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价值实现路径
“十二五”以来,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我国在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扶贫攻坚依然任重道远[2]。
(一)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加大扶贫资源投入力度
一是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首先,要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确识别。截止2018年2月,我国现有585 个国家级贫困县。但由于流动人口众多,当前每个县具体的贫困人口数字仍然不够准确。没有准确的贫困人口数据,精准扶贫更无从谈起。要解决贫困人口数据不准确的问题,必须要发挥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通过走村入户,了解困难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真正做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全部实现建档立卡,为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奠定基础。其次,部分困难群体对脱贫积极性不高。一方面,部分困难群体对脱贫工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人认为国家帮扶的钱不要白不要,抱着困难群体的身份不舍得放手。另一方面,个别困难群众好吃懒、不思进取。对于脱贫攻坚,思想上不积极,行为上不主动,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干着急。因此,要实现这部分困难群体脱贫,首先必须要转变被帮扶群体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要让他们切实树立起贫穷可耻、劳动光荣的观念,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
二是多措并举,加大扶贫资源投入力度。当前,国家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仅2017年一年,国家扶贫专项资金投入近千亿元。但相对于500 多个贫困县,3000 多万贫困人口,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力度仍显不足。农村扶贫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应负的社会责任,首先,社会资本应与国家财政资金一道,不断加大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农村精准扶贫离不开农业产业化发展,而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地区困难群众脱贫的前提。其次,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要坚持能扶则扶、能搬则搬、多措并举的原则[3]。例如,某些农村地区出现集中连片贫困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对于这类地区而言,加大扶贫资金支持力度即可。而另外一些地区的贫困,可能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极度干旱、寒冷或其他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这类地区,则应考虑通过异地搬迁安置的方式进行帮扶。例如,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的9 个贫困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已实现了精准脱贫。
(二)因地制宜设计扶贫机制,加大扶贫监督力度
一是扶贫机制设计必须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应该因地制宜的设计脱贫攻坚方案,产业帮扶应充分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首先,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可以考虑采用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帮助落后地区将鲜活农产品及时销售到城市,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可充分利用城市化进程,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向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征地,拓宽困难群体的收入渠道。其次,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资本,应协助地方基层政府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落地,切实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最后,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要突出地方特色。例如,对于东北地区的精准扶贫可以引导发展冰雪旅游的配套产业,对于其他地区的农村精准扶贫则应坚持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充分体现地方经济特色和贫困地区群众发展意志。
二是不断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建立立体化的社会监督网络。不论是社会资本还是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精准扶贫领域的资金都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一分一毫都不能贪污、挪用。但是,当前我国扶贫领域的贪腐问题仍呈高发态势。2017年以来,仅湖南一省扶贫领域立案逾4800 件。扶贫领域存在的贪腐问题,往往贪腐金额绝对值不大,但在群众当中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例如,2013年至2014年,延吉市仲坪村原村干部柳吉善,骗取国家扶贫专项资金30万元,导致该村几十名群众集体上访。柳吉善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追究刑事责任。要想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本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价值实现,就必须不断加大对社会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充分调动群众、公共舆论和国家监管部门等各方面的力量,建设立体化的监督网络,让扶贫资金贪腐人员无所遁逃。其次,政府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必须要对扶贫领域的贪腐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高压态势,切实做到对于扶贫贪腐,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绝不姑息。
(三)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增强保险对精准扶贫的保障作用
一是充分发挥扶贫资金对促进农村精准扶贫的杠杆作用。不论是社会资本,还是国家扶贫资金,相对于广大贫困地区巨量的资金需求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因此,扶贫资金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贫困地区脱贫缺乏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尚未具备满足困难地区产业发展所需全部资金的能力,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扶贫资金对促进农村精准扶贫的杠杆作用[4]。发挥扶贫资金翘杠杆的作用,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地方基层政府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扶贫资金的担保融资体制,切实帮助困难群体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把精准扶贫信贷与一般涉农贷款区分开来,通过延长信贷期限、提供优惠利率等方式,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的资金帮扶力度。
二是增强农业保险对农村精准扶贫的保障作用。农村精准扶贫,主要还是以发展农林牧渔等相关产业为主。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是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发展农业保险对于对冲农业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自然风险意义重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基层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大对涉农保险的宣传力度,使困难群体真正对农业保险的范围、补贴政策和具体参保程序等有所了解,激发困难群体参加涉农保险的积极性。其次,相关涉农保险公司要不断完善农业保险品种,努力实现保险产品对农林牧渔产业的全覆盖。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是壮大扶贫攻坚力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贫困目标的重要基础。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工作要充分吸收社会资本的加入,发挥市场的调解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完善农村扶贫相关政策,发挥好扶贫资金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