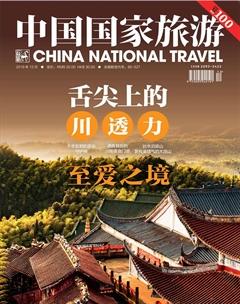金刚证寺
柳田国男
我坐上了朝熊山的缆车。缆车沿着笔直的线路向上开动后,同伴忽然颇有些伤感地说起了家事,说孩子们还都在上学,双亲年纪都很大了。我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要说起这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缆车上升的幅度很大,有些骇人。现在是雨天的下午,坐缆车的就我们两人,如果两人摔死,哪家报纸会刊载消息呢?因为内心都有点寂寞,所以我对同伴开起了这种玩笑。缆车到了终点站,那站上也只有孤零零的一个站长。一个卖东西的,在店里打着哈欠。在山下听说山上有人力车,但也不见影子。虽是秋季,但还未到赏红叶的时节,所以游人才这么少。在春光明媚的参拜神宫的季节,参拜的人们几乎没有不顺便到这座山上来的,那时的拥挤程度不难想象。这样一想,心情也随之轻松起来。实际上,在关西地区如要寻找游人稀少的游览地,那是需要特别动点脑筋的,比如露宿园边或者彻夜不睡之类,否则根本没门。所以这当儿没有游人,实属千载难逢。想到这里,心里竟有点儿飘飘然了。
人一点点多起来了,不断有三五成群的人从山上下来,下山的人除了山里的居民外,有些也许是早晨在山上参拜的人。这么多的人,简直让我对刚才无人的情形起了疑心。山路位于山岭之上,自然路面没有什么积水塘需要飞身而过,但走到树荫下时总会有水滴落下来。幸好此时的天气已在渐渐放晴。那个豆腐店不像听说的那样古朴,坐垫倒很干净,角落里还有个墙上刷着油漆的食堂。如果再下雨就需要住一宿了,但因为我们打算乘夜车回去,连手套都放在山田,所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回去。我在家时散步,总喜欢趁路上无人时出去;但旅行毕竟与散步不同,没有这个必要。虽然我们时间充裕,但并不会因此而长时间伫立一处,所以不经意间已经走到通向山门的路,来到万金丹屋跟前的一个转角。
那儿视野极好,视线越过山岭,可以看到斜斜的大片海面,山的样子也非常美。这样的美景,让我终于有了庆幸今天来游的好心情。算算日子,明天就是明治节,今天已是十一月二日。近处的树木已经渐染秋色,远处山头的树梢则已是秋色绚烂。志摩和度会郡尽收眼底,更远处是熊野一带的连绵高峰。左侧的海面上,闪烁着太阳的光辉。我在那智的妙法山前、木曾深处的三国山巅也这样眺望过,但那些地方看不到海,也没有今天的水蒸气。眼下淋湿的山景被太阳一照,一切都清楚地呈现出来,色彩有浓有淡,就像彩虹呈粉状散布在林间一样。从林后照过来的强烈阳光,在林间闪烁跃动,给人以诸景围着日轮的印象。我和同伴修行不足,对佛教的灵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但眼下还是被这个非同寻常的光与霞深深打动了。我眼睛里不禁涌出了泪水,不得不常常擦拭,因为不如此就看不清楚了。
进了金刚证寺山门,庭院很大,却空无一人。我们先拜了石阶左侧的虚空藏菩萨。这时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一只摇着尾巴的瘦瘦的小白狗。观察它的面部,可知其刚刚脱离幼儿期,是一只并非原产日本的狗。它居然登上了这么高的山顶,这让我惊讶不已,也让我感叹悲伤。有位夫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讨厌狗的人,可这只狗却不会察言观色,在夫人的裙边转来转去。夫人举起遮阳伞欲打,我赶忙止住了夫人。我对她说:“这只狗孤独得很,怪可怜的。”我心生怜爱,嘴里召唤着它,想找个店,买点儿什么给它吃。可它到了石阶下,就不肯再进一步,而那附近也没有店铺。告别了狗,我在一座座殿堂里进进出出,总算遇到了第一个参拜者。他看上去应该比我小四五岁,但也到了被称作“翁”而不会生气的年纪。他穿着白衣,系着白巾,手持旧斗笠,脚上也穿着朝奉者所穿的正规鞋子;眼神则露着朝奉者常有的温和恭谨。朝奉者默默地参拜后,很快就走往别处了。
寺院后面,是通往地藏菩萨的路,走了约200米来到一断崖处时,视野一下开阔起来。举目望去,但见祭奠死者的高大的塔形木牌,两层、三层地排列着,密密麻麻,简直像墙一样严丝合缝,其间几乎不透空隙,数量之多,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从木牌上写着的姓名、年龄看,死者中年轻男女很多,也不知是什么缘故。那些特意前来吊唁的人自不用说,即便单纯为游山而来的人们,面对这种场面而不感到震撼、不涌起哀思的,也应该只是很小一部分吧。地藏堂前有个巨大的石香炉,有两三位工作人员。香炉里浓浓的香烟袅袅上升,却并没有被风吹散,形成了一面烟霞。山冈的顶端崖边半悬着一座小茶馆。置身小茶馆里,耳鼓里隐隐传来大海的涛声,眼前则是海邊的荒滩。但见惊涛拍岸,白浪穿空,瞬间碎开散去,一刻不曾止歇。凝视这样的景象,感觉它所表现的人世无常之感,比万千说教还要深入人心。
当我举目再向志州海滨、海角方面眺望时,天空忽然出现了大片的云层,仿佛在提醒我:已到了返回的时间。是的,是得往回走了,天黑后就不好走了。这样想着,脚下用力,很快就回到了金刚证寺前。我惦记着那只小狗,目下四处寻找,却发现刚才碰到的朝奉者,在本堂那里放下了斗笠休息。而那只狗的下巴枕着老人的膝盖,享受着老人的抚摸,快活地摇着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