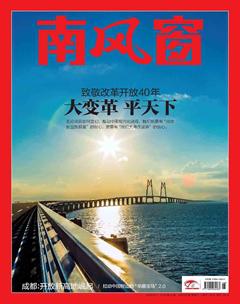中国成都:站在西部,瞭望世界
李少威

未来几年,一座名为“天府中心”的677米摩天楼,将在天府新区秦皇寺地块拔地而起。巍然挺立之日,“中国第一高楼”将从东部的上海让渡于西部的成都。
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正经历着一个东西再平衡的过程。引领着西部崛起的那座城市,就叫成都。
在中国人信仰与实用浑然一体的心理结构中,高楼永远有着独特的位置。它呈现一种向上生长的积极姿势,同时又指向“天”这一传统文化秩序的原点,因而意味深长。同时,人们不会过度忧心与摩天楼相关的需求和浪费问题,他们相信实业资本的极度冷静与理性—资本的使命就是不断繁衍,它对最佳繁衍地的嗅觉,比任何动物都要灵敏。
和“天府中心”的高度相应的,是“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所处的高度。
如今,它在瞭望世界。
“高光时代”
2018年10月18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发出了一条消息:成都计划在2020年发射一颗国产“人造月亮”,用来代替城市里的路灯。
这个消息,其实并不准确,能否发射并不确定,路灯也不会被取代,但“人造月亮”这种“黑科技”的确在成都孕育。
“人造月亮”其实是一颗卫星,通过反射太阳光,它能集中照亮直径10~80公里的区域,亮度是月光的8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技术应用。“人造月亮”出现之后,四川人苏东坡诗句“明月几时有”后面的问号将被抹去。
曾经,类似的技术应用,是发达国家令人仰望的专利;后来,在中国东部亦渐有闪烁;今天,即便是出现在西部的成都,也已不再令人惊奇。
能否容纳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注定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事实上,过去数年里,财富论坛、国际马拉松、蓉欧快铁……成都对“高光时刻”已习以为常。
久等了,但她的时代来临了。
历史上的成都,给人的主要印象是黎民富庶、人文鼎盛。10月16日,再次置身武侯祠内,“锦官城外柏森森”,耳际响起“隆中对”: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先主曰“善”。
进可攻、退可守,成都平原天险环拱,沃野千里,倘能保持和平,施行仁政,则古蜀王开明九世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信手拈来。刘备也许对别的没有信心,对仁政则相当得心应手,以成都为中心,“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事实证明,只要成都人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出数年,就将富甲天下。富庶的指征之一是金融。来到北宋—西方史家眼里的中国“近世”开端,中国第一种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足为明证。
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帮成都解決了水患,基本根除了威胁最大的天灾,把农业从自然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然而历朝历代人祸频仍,战火纷飞,成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虽欲休养生息,岂可得乎?两次“湖广填四川”,正标记着这片世外桃源遭逢的巨大劫难。
真正的长久和平时代,自共和国建立后开启。真正的民间活力释放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40年,成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属于它的时代,中国人也等到了一个被光环笼罩的成都。
或许,与“高光时刻”一字之差的“高光时代”,更适合用于描述今天的成都。
转折时刻
历史只是历史。
成都在数千年历史上的那些繁荣、辉煌,都建基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征就是按部就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外部世界了无兴趣。
今天不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彻底改造的进程,是从“酒香不怕巷子深”到“酒香也要勤吆喝”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期,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即便在观念意识里感知到了这一转变,卖力吆喝,也未必见效。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资本。
正因为资本的使命是繁衍增殖,对机会和利润极其敏感,所以资本也必然是势利的。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欢迎资本,天下一理,但资本在众多手举鲜花的欢迎者中,只亲吻了其中的少数人。它是这样选择它的联姻对象的:
造成城市与资本联姻的那些障碍性因素,在时势变迁和当地政府锐意改革的双重力量作用下,有的突破了,有的自然消失了。
1.文化趋近。文化是“社会资本”的关键部分,它让契约获得无形保障。
2.乡情润滑。如果从文化上不能求得绝对安心,那就寄托于乡情的支持。
3.成本因素。早期主要是地理位置—劳动力可以流动,但区域位置不能流动,而地理主要决定了物流成本。
4.市场机会。这才是根本问题,是资本精确制导的目标。
文化决定开放的起跑线,东部得天独厚;乡情系于原籍本地的华人华侨,沿海有历史积累;物流成本是硬性因素,它与产业链不成熟造成的额外成本之间往往互相加强;市场机会有一个梯次发掘的渐进过程,自东向西。综合而言,在改革开放早期乃至中期,西部所谓“落后”,原因一目了然: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占优势。
清华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从199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的东中西部相对差系数持续扩大,直到2004年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如果姑且把过去的40年理解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在它的中段,西部仍然持续弱势,难以被机会的追光打亮。成都在西部的重要性从未衰减,但在当时,是矮子里挑高个。
直到2004年,相对差系数达到75%的峰值,然后开始不断缩小,仅仅用了4年,2008年就缩小至60%。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比值2004年前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2004年后也发生逆转,开始不断下降。西部的经济增速、工业产出增速等指标,大体在2004年以后也进入了活跃期,并迅速超越东部,持续领先。
新世纪,西部猛然获得了成长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风水轮流转”,那么十几年前就已经转到西部了。对于成都而言,时间节点也相差不大。
所以,《南风窗》记者对西南美国商会会长王晓东、TCL成都公司总经理孙秀红、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良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成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根本性转折?
答案是多层次的。
新气象
层次在眼前展开。
王晓东提到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增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
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机会的过程。所以,刘希良回忆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市场扩大、机会出现,于是资本和人才都望向了西边。“八九十年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代,不论是工人、大学生,都往东南方向跑。成都高校很多,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大学生,但留在当地的很少。”
而在2002年、2003年,人才开始回流。四川的乡土文化本来就有强大的黏性,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回到家乡。而这些回乡的工人、大学毕业生,已经是受过现代工商业制度反复训练的熟练工和市场能手。
机会要有风向标,要有人以榜样的角色去昭示,这个风向标,这个榜样,就是英特尔(Intel)。
2003年,英特尔落户成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家在成都大规模投资的跨国公司。现任英特尔全球副总裁罗宾·马丁彼时被指派负责成都公司工厂的设立和运营,他说,那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网络上搜索“成都”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的反应很典型,成都在之前很难被大资本的追光照亮,但英特尔进来以后,世界就开始熟悉成都。
王晓东说起来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英特尔的体量够大,地位够高,所以它的现身,就是最好的示范。它的上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而它历来对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环境要求很高,這既打消了其他国际大企业的疑虑,也倒逼着成都自身的改革。“外资企业代表可以参加市长办公会,各部门的领导都被请到会上来,有什么问题现场收集,现场答复,效率非常高,给了外资企业以信心。”
刘希良说,之后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至沓来,先后在成都大规模布局。有数据可以佐证,到2018年9月,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数量达到285家。
TCL成都公司在2004年设立,2006年投产。作为一个制造业实体,TCL的经历最能反映成都经济、社会的联动性变革。成都公司总经理孙秀红说,一开始本地的产业配套环境不太好,技工、熟手工也比较紧缺,必须从无到有自己去培养。习惯了珠三角成熟的产业链和人力资源环境的TCL,初入成都感到不便是可以预想的,他们看中的,是成都作为西部中心辐射整个西部的国内消费市场,因而TCL成都的早期初衷,其实是一个便于内销的工厂。也正是像TCL这样的知名制造企业的到来,加速了对成都周边的本土人力资源的工业化训练进程。
开放不再是东部专利,而已渐渐成为一种均衡的权利。具体到成都,“一带一路”这一世界性的利好,加上信息技术的即时性,让这座西部名城突破了所有空间屏障。
2008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这一年,汶川地震发生。这两件举世皆知的坏事都有一个正向的次生效应:前者凸显了西部,后者让世界再一次看到了成都。王晓东说,在金融危机中,西部所遭受的冲击远比东部微弱,因此它相当于敞开了一个市场;而2008年应对各种重大挑战的中国人所展现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汹涌的慈悲之心,则让全世界对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好感,而成都是众目的焦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扩大内需投资中的大部分投向了中西部地区的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并带动地方和社会巨额资金跟进。
高速公路、地铁、财富论坛……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在不断升级。王晓东说,2008年至2017年,美资企业对中国大陆城市营商环境的打分,成都连续8年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一。美资企业运营成本,成都总体上比沿海低20%左右。“一开始是只有大企业敢来,中小企业承受不了风险,现在中小企业也可以很放心地到成都投资。”
人们发现,造成城市与资本联姻的那些障碍性因素,在时势变迁和当地政府锐意改革的双重力量作用下,有的突破了,有的自然消失了。
“蜀道艰难”曾经拱卫了农业时代的成都,而在工业化时代则变成一种劣势。
现在,蜀道无妨,四面通衢。
后来居上
刘希良所执掌的新川创新科技园,是一个合资企业,由新加坡企业和成都企业共同投资,于2012年设立。
在国外投资工业园或科技园,是新加坡的一个传统,因为它有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等待转化,而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缺少向实业转化所需的土地。在过去新加坡和中国合作的园区项目,都分布在苏州、天津、广州等东部城市,新川创新科技园是西部的第一个。
为什么在东部以外选择了成都?刘希良的答案是,成都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人才基础、科技基础、市场基础。
如果以新川科技园成立时间为基准,把时钟拨回10年前,即2002年,这个回答是不可想象的。前面的梳理中已经示意,工业基础、人才基础、科技基础、市场基础等,正是过去西部缺乏的工业化资源。也就在短短10年左右,一切都逆转了。正如孙秀红的感受,从一开始技工、熟手工稀缺,到人力资源素质、产业配套和市场氛围都迅速成长了起来。

刘希良特别强调一点,因为中国有足够大的人口基数,所以各种科研成果都能找到现实的应用场景,而不是只能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新加坡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无人驾驶出租车牌照,但在成都则可以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方,专门用于无人驾驶的场景实验。
新川创新科技园定位于两大产业品类: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乍一看,这几乎是国内各大城市最近十几年里争相发展的方向,并无特别的新意。
不过刘希良是理性的,比如对生物制药,他就清晰地梳理了成都的优势:华西医院是国内著名的高水平医院,有大量的病例资源;“什么都见过”,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病例倒逼科研,医院还有自己的试验用猴子培育基地;医院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并且已经搭建平台,与社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四川生物种类丰富,是一个范围广阔、品种齐全的原材料产地。
从刘希良的举例中可以勾勒出他所说的优势,主要包括两点:历史悠久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背靠天府山川的内陆地理环境。然而在过去,这两点不但不是优势,前者代表包袱,后者象征闭塞。
在今天,越来越多曾经迅猛发展的东部新生城市感受到了继续前进的强大“风阻”,原因正在于缺乏历史积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东部制造业名城,也许可以拥有和成都旗鼓相当的经济体量,但当中国社会来到一个渐趋稳态的时期,就会发现一旦形势变化、资本异动,自己能用以支持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非常有限—比如,刘希良说的病例资源和生物资源。
所以人们必须思考,是什么让“历史包袱”和内陆环境倏然转化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动力来源?拓展性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回答了为何今天成都迎来了它的时代。
答案就是开放。
开放不再是东部专利,而已渐渐成为一种均衡的权利。具体到成都,“一带一路”这一世界性的利好,加上信息技术的即时性,让这座西部名城突破了所有空间屏障。过去,成都的技术、人才、劳动力、原材料、制成品都向东部涌流,因为产能、市场和海外连接点都在东部,人们无法想象成都会成为一个中心,形成全面逆流。
然而今天,现实正是如此。火车从成都出发,开往俄罗斯,开往西欧。中欧班列蓉欧快铁2013年试运行,到今年6月28日已累计达到2000列,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根据TCL提供的数据,使用铁路往西欧市场发货,成本与从东部出发的海运差不多,但时间上节省将近两个星期,这珍贵的两个星期,为货款回流、汇率预期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贡献了效率。因为同一个理由,东部的货物也通过铁路源源而来,在成都集成以后發往欧洲。
对于TCL成都公司而言,这是一个从未料想的结果,原本在成都布局的目的只是为了照顾西部内销市场,2016年开始使用蓉欧快铁以后,这家企业就从一个内向型基地变身为一个外向型基地,可以说颇具戏剧性。
河东河西的变化,甚至用不了30年。
现在,很多成都人还体验着城市生活的慢节奏,享受着深厚的市井文化带来的幸福感,但他们的观念意识,已经不是传统印象中的样子。刘希良现在是新川创新科技园的总经理,过去曾在政府任职,对此体会殊深。他说,过去提到东部,中西部的目标是追赶,而现在则放眼于超越,成都人很清楚,想要超越,观念至关重要。
“怎么超越?只有更开放,更大胆,更突破,更超前。现在全国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很多新科技—如AI、大数据,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谁能抢得先机,实现应用突破,就会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对于站位更高的成都主政者而言,眼前风起云涌,江山如此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