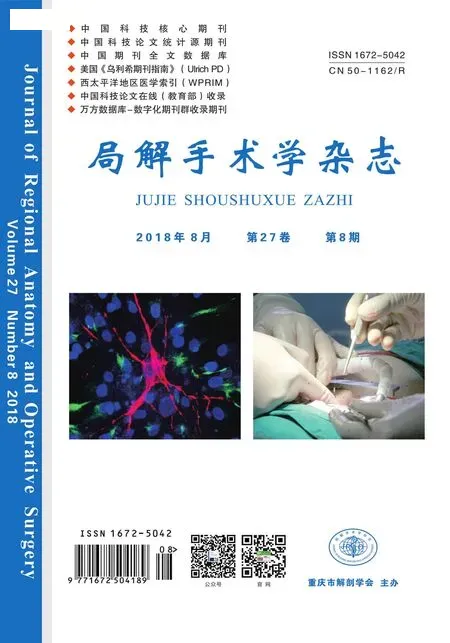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心脏瓣膜病变合并房颤的疗效观察
,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湖北 武汉 430030)
心房颤动即房颤(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不仅影响心房内血流且直接影响心功能,易形成血栓,造成心脑血管及肺部栓塞,威胁生命[1]。房颤多由心脏瓣膜病变引起,而风湿性心脏病是心脏瓣膜病变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2]。在临床上,瓣膜病变合并房颤的发病率可高达5.5%~10%[3]。心脏二尖瓣变病患者房颤发病率最高,保守治疗效果差,心脏瓣膜置换术是目前治疗重度心脏瓣膜疾病的主要方法[4],可将病变瓣膜替换为人工健康瓣膜。但对于合并房颤的患者,单纯置换瓣膜对于心律转复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开展了心脏手术同期双极射频消融术,对于纠正心律失常发挥了较好的作用[5]。另有研究发现,炎症在房颤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除了早期发现的IL-6、hsCRP,一种新发现的趋化因子CX3CL-1(FKN)也被认为与房颤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作为预测疾病的危险因素[6]。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心脏瓣膜疾病合并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对患者心功能及血清IL-6、hsCRP、CX3CL-1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4年9月至2017年9月于我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心脏瓣膜病变合并房颤患者共120例,将其按治疗方式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0例。观察组男39例,女21例;平均年龄(57.82±10.17)岁;平均病程(3.48±1.04)年;二尖瓣病变31例,主动脉瓣病变16例,二尖瓣合并主动脉瓣病变13例。对照组男34例,女26例;平均年龄(55.46±9.32)岁;平均病程(3.64±1.17)年;二尖瓣病变29例,主动脉瓣病变14例,二尖瓣合并主动脉瓣病变17例。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瓣膜病变部位等一般资料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心脏瓣膜病变合并心房颤动;②心功能分级≥Ⅲ级;③左室舒张末内径≥60 mm,心脏射血分数≤0.40;④首次行心脏手术,符合心脏瓣膜置换术的手术适应证;⑤能完成随访;⑥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妊娠及哺乳期患者;②合并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感染性心内膜炎等其他心脏疾病;③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合并精神障碍者。④不能坚持随访者。
1.2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先行射频消融术,阻断升主动脉,使心脏停搏,停搏前采用常规电复率评价窦房结状态。切断Marshall韧带,行右上肺-左上肺静脉连线、右下肺静脉-左下肺静脉、左上肺静脉和左心耳残端之间消融,每条线路消融5次,持续时间为10~20 min,术毕前放置心外临时起搏线[7],之后按照常规方法行瓣膜置换术[8]。对照组仅进行瓣膜置换术,2组患者术后予以心电监护,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抗凝抗感染补充血容量,并予以胺碘酮持续泵入,待患者可以进食时,改为胺碘酮口服,根据心律情况调整用量及决定是否停药,随访3个月。
1.3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①窦性转复率,包括手术结束时及术后1个月、2个月、3个月复查一次24 h动态心电图,均未发现房颤者视为成功窦性转复;②心功能指标,检测术前及术后3个月左心房内径、左心室舒张末容积、射血分数以评价心功能;③血清IL-6、hsCRP、CX3CL-1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术前及术后3个月患者血清IL-6、hsCRP、CX3CL-1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百分率(%)比较采用χ2检验,2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差异有极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患者手术结束时及术后3个月窦性转复率
手术结束时及术后3个月,观察组转复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2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3个月心功能指标
2组患者术前心功能指标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后3个月,观察组左心房内径、左心室舒张末容积均低于对照组,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2组患者术前及术后3个月血清IL-6、hsCRP、CX3CL-1水平
2组患者术前血清IL-6、hsCRP、CX3CL-1水平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术后3个月血清IL-6、hsCRP、CX3CL-1水平均低于手术前,且术后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2组患者手术结束时及术后3个月窦性转复率[n=60,例(%)]

组别 手术结束时转复术后3个月转复观察组51(85.00)49(81.67)对照组37(67.67)18(30.00)χ2 11.34150.784P <0.05<0.01

表2 2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3个月心功能指标(n=60)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论
人工瓣膜置换术是治疗严重瓣膜病变的有效手段,但对于合并房颤患者而言,单纯瓣膜置换后窦性转复率不高,大部分患者房颤将持续存在。射频消融术则能有效促进窦性转复,而恢复窦性心律也可以改善心房收缩功能,防止心室重构[9-10],有效降低心律失常风险,改善患者预后[11],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射频能量产生热量使相应的心房组织透壁性坏死,消除异位局灶,阻断异常传导路线[12]。伴随微创外科技术的提升,现多采用Cox-Maze Ⅳ迷宫术,与传统的MazeⅢ术疗效相当,但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13]。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在解决原发病患者瓣膜病变基础上,也解决了因房颤带来的心悸、气促、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但在术中一定要避免损害房室结,手术结束时应在心外膜留置临时起搏线,确保消融线互连,降低风险。
提高心功能及窦性转复率是治疗心脏瓣膜病合并AF的主要目标。Joshibayev等[14]研究显示,采用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可以提高患者窦性心律恢复率,降低病死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李岑等[15]研究显示70例AF患者行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使大多数患者恢复窦性心律,术后随访3~40个月无死亡病例,疗效显著且安全性好。熊敏等[16]研究认为风心病合并房颤患者行二尖瓣机械瓣置换手术同期进行射频消融治疗会增加手术难度及对患者的创伤程度,但是术后患者的窦性心律转复律更高、术后左心房内径恢复更好。目前研究多为小样本,缺乏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因此,射频消融术联合瓣膜置换术的疗效尚未获得绝对的肯定。本研究中,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瓣膜病变合并房颤的患者相比于单纯运用于瓣膜置换术的患者窦性转复率显著提升,左心房内径、左心室舒张末容积降低,射血分数升高,对改善心室重构,提高心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炎症在房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选取了IL-6、hsCRP、CX3CL-1三项炎性指标,一方面探讨炎症因子与房颤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借以评价术后疗效。本研究显示术前患者IL-6、hsCRP、CX3CL-1水平是显著上升的,治疗后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术后各指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IL-6是由单核细胞合成的促炎因子,可诱导CRP合成,引起心肌细胞炎性损害,加重房室重构[17]。hs-CRP是反应炎症水平的常用指标,可诱导心肌细胞凋亡,加重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促进心肌纤维化[18]。CX3CL-1是CX3C家族中唯一成员,可通过驱使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NK细胞到达炎症部位而加重炎症反应。有研究显示,房颤的发生和维持与CRP、IL-6等炎性反应因子相关,且是房颤血栓前状态指标独立相关[19],房颤患者血清IL-6、hsCRP水平显著上升,在经过治疗后水平可下降[20],风湿病患者中CX3CL-1水平显著上升,可反应炎症水平和程度[21]。
综上所述,瓣膜置换术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心脏瓣膜病变合并房颤具有良后的效果,可提高患者心功能和窦性心律转复率,且我们推测该疗法可以降低患者血清炎症指标,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减少心肌损害,降低血栓发生率,实现结构到功能的良性循环,促进疾病恢复。但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随访时间局限于术后中期,后续我们将设计更大规模的临床对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