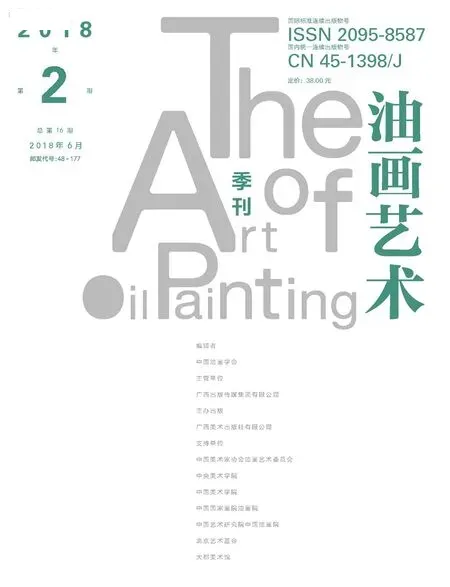观宋人石头的经验
焦小健
杭州吴山顶上有许多散落的石碑,这个印象很早就存于我脑中。这些刻碑的石头始于宋代,在南宋皇宫的御园内作为石山被安置山上。历朝历代的修建与损毁,石碑形成的崖石在荒野的山中早已残缺不全,成为一堆石头。但是,我从大学时代就忘不了这些景象。
在我的意识里,自己愈加熟悉西方艺术传统,吴山那堆石头总是要挡住我的视线。美术史提到中国人学习西画的历史是一百年,曾经在此的南宋画史和吴山那些石头已经存在了近800年。两组数字不仅有时间文化的差距,它还提供了一个现存的观石头体验,即自己与遥远的历史传统相处在今天同一个时代。
南宋御山当年的外貌在岁月中早已经消失殆尽,吴山下的民居烟火味蔓延到山上,此山已经成为普通的景山。许多年间,我翻山步走其间,在杂乱树丛的山路上常常会设想当年宋代的模样和布局。在我看来,时间消磨不了那些初始的地形和痕迹。这里的山景、树林、碑石、城隍阁、缠绕的紫藤,尽管它们不断地被改造,但那种神秘性仍旧存在。这些藏匿在历史尘埃背后的气息提示着它们曾经在此,不是消失了。北宋人范宽那幅《溪山行旅图》里的某些局部在这里依稀可寻,虽然那是一幅描写北方风景的大山水,但其图画前景下角的石山和树林就在吴山中可以找到相似的地方。诗人苏轼诗里有记载“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从,吴山多故态,转侧为君容”,这是当时诗人眼睛看到的吴山。几百年后的今天,四周现代化高楼林立地朝吴山挤压过来,吴山缩成了一小块萧瑟荒野的山景。即便如此,你仍然觉得宋代山水画里原本就有着这种荒凉。
吴山下山的道四通八达,顺着石阶下山,不小心弯进了居民区严官巷,六部桥,再往前行就是南宋太庙遗址。这些巷名地点保存了宋王朝户部、吏部的曾在,尽管再也找不到数百年前皇家的威严。“文革”前保留至今的老杭州居民悠闲的生活方式依然存有,小院树枝伸出墙头,门边小铺卖的老酒,阳台晒着腌制的板鸭,还有修伞、做木桶的店铺,不久这些也将成为逝去时代的遗迹。顺着墙角边的小路上山,一路有烧香供佛的石洞烛火。等你爬到吴山顶上“江湖汇观”亭时,从那里看西湖,又能感觉到皇家选景的气度了。这种气势让你依稀觉察历史和中国山水画的辽阔。曾经有历史传说:南宋亡国时,有位挥军到此的金人将军看到连绵的湖山和十里桂树,无限感慨,从此下马不再征战。

焦小健 《宋人的石头系列——古道》 布面油画 112cm×292cm 2016年
带着西方的绘画经验看吴山,这里有中国特色。此山靠近西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座城市的中心开窗见山,况且是有历史的山。
2002年我的工作室搬到山边,自己想过画山里的石头,有一些成功和不成功的体验。吴山的石头是中国式的,错落有致,适合水墨画的散点构图和造型。石头树林布局既是变化多端的,也 是凌乱的。白色的石头和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的白色石山有的比较,但是吴山的石头属于奇石,参照西方模式画石是无趣的。况且西方的传统有眼见为实的意识,让你觉得面对吴山真景构图缺少整体感和远近层次。脑中的西画模式和中国实景意识有冲突,中西绘画两条并列的路数没有融合。所以我总结那次的经验是要转换对传统的再认识。
这方面西方画家不同。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他在自传中说到绘画的时候,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地很自然,因为西方文化和欧洲传统是他们土地和文化的根,所以他从古代说到现在没有麻烦。但是,他在北京办展与讲座谈中国传统水墨画里的构图布局,中国人听了未必觉得他说的都在理,因为我们有众所周知的评判标准。相同,我们谈西方传统也有这样的尴尬,除了借鉴外来西方传统,还有本真的中国传统。一旦这些都涌进大脑成为意识,两种不同性质的固有性越强,结果越可能会相互抵消。当然,看你个人怎么消化这个问题。

焦小健 《力之中心》 布面油画 150cm ×150cm 2017年
我曾经见过乾隆皇帝喜欢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创作的一幅竖条幅中国山水画,他在树木的背景上涂了一片深蓝的天空,画面看起来不协调,蓝色有点僵死。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中国水墨画里带进意大利人的空间和色彩意识,哪怕他的水墨画语言不地道。中国油画家谈传统语言,追求绘画的地道并当作本体语言。油画家们会追到14世纪威尼斯画派、17世纪尼德兰画派或者是20世纪塞尚、德兰的现代主义那里。欧洲不同艺术历史时期许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大师作品,看多了都成为后代人借鉴传统的尺度。比如:文艺复兴的威尼斯画派提香、丁托列托他们画教皇牧师深红色的丝绒长袍很有表现力,他们直接用线在色彩未干时勾勒衣纹,效果非常提神。到了20世纪现代画家德郎画的一幅深背景金发女的时候,他画丝绒长裙的方法依然复古了威尼斯人的技法,只是线条更加潇洒。艺术史上的繁荣和黄金时代影响到后代的每一位画家,技术性的掌握会成为绘画的语言,画家会被这些描绘感动。问题是西方的油画技术语言横跨万水千山变成我们的本体意识,本体就是本质性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看风景的绘画意识和方法。合适的方面会融合得很好,不合适的方面是连你看真山水风景都有距离,你会觉得有些中国风景不入画。因为这些景物没有被西方历史上的画家画过,没有让你眼睛一亮的先例。特别是传统的绘画语言变成意识里的本体语言,自己完全陷进去的时候,你看其他都觉得是非本体非语言而拒绝。那就是你掉到西方复古中去了。
曾经有人和我说过,竹不可以画成油画。因为我们习惯了西方画法,画什么都眼见为实,一看具体的竹叶比较凌乱,肯定觉得很不入画。但我以为,竹是中国艺术传统表现的重要形象,竹在中国既是植物也是观念。中国传统国画看竹的方法是胸有成竹,不看具体性的,所以它非常合适为水墨画笔墨的语言。传统历史已经有过许多伟大的画作,但是这些不构成我们不能再去画油画的理由。如果我不去将竹当对象画,换一种角度去体会这个植物的复杂性,体会竹的节高心空的禅意和佛境,规避中国画模式,那完全可以用今天语言去重新感觉的。因此,不要什么都眼见为实,要多表现运动,表现物的生命转换。这是我这些年实践的结果。无论如何,总不该油画只能够画西方传统里画过的景,中国传统水墨只能画古人和有烟云的山。这样的执守传统语言肯定是僵化的。
任何传统,包括西方传统或者中国传统都有当下性,它们都殊途同归,况且艺术是层层叠叠的高峰和多条真理小径,其他的学科都是纳入统一性中区分局部问题,唯独艺术总是要将局部问题放大,逃离统一性。正因为如此,历史传统常常在鲜为人知处和今天的人共同相处于一个时空。好像吴山那堆石头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曾经,我们这些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断层。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都往西方现代性上走,习惯了西方文化思维,对中国石林和历史的湖山陌生,中国古代传统不被看好。这种成见影响着对中国山水历史的认识。但是,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已经将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历史改变了曾经的定位,认识传统和学习西方都回不到过去了。我们唯有汲取古代经验在今天的有用性,思考面对艺术和绘画我们能够再给今天的世界提供些什么。
我看吴山石头的经验中,那些从宋朝开始累积在山上的石头仍旧透露着曾经的意识形态。历朝历代的文人一旦刻字在这些自然的石头上,那些“忠”“孝”“天下第一山”的大字将儒家道德意识醒目地融进天地山水和石头间。这些放置山里的石头在今天属于户外雕塑或者一种环境装置艺术。石头以大面积的模式安置山中,雕刻文字,起着与山水融为一体的教化效用。这个方式和宋画中描绘的庭院石头,甚至和以后的文人画中的石头不同。宋画里的一块石头是道家角度,没有说教。画中平和宁静于荒野中的石头只作为自然山川的微小版,只用墨迹和水纹呈现山水世界。那些刻在吴山石头上的表现中国伦理道德观、家国天下观的文字,和宋画以水墨画石头表现自然的境界,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线。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某些看起来对立而实际上又无碍的两种认识在中国传统审美中是并行的,它让我想到中国经验里本质上的虚空可以包容对立 、转化对立的说法。

焦小健 《农耕时代》 布面油画 146cm×112cm 2017年

焦小健 《不依不饶》 布面油画 200cm×150cm 2017年
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经验,18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德里弗里希创作过一幅《云端漫步者》的油画,画中主人站在山顶的石头上,从中心背对着观众,他朝着一片云海般的世界低头沉思。这种自我沉思是一种典型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思考。画面充满哲思。他沉思着自我内部如何通向神秘的外部世界。神秘主义者诗人诺瓦利斯说过:“神秘莫测的道路通向内部,谁在此停留,仅成功一半。第二步必须是朝向外部的有效目光——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和有分寸地观察”。这幅画不大,有一种主体者内在的神秘性和西方二元论的思维。13世纪南宋画家梁楷也画过一幅行游诗人图,这幅图尺寸更小。画中占三分之二的是块空空的巨石,那块空石如巨大的世界一般,此外是溪水和小径,大量的留空和云气渲染。右下角梁楷画了一个只有石头十分之一大小的微小人物——一个云游诗人。这两幅绘画相差五百年,却在表达主题上相同,而且两幅作品都具有某种神秘性,区别是《云端漫步者》要进入这个神秘世界,让世界风起云涌。而云游诗人在太虚幻境中,是世界云淡风清的神秘。前者朝向外部世界的深思是主体性意识的有效介入,后者只能够是非主体性地在世界中云游的状态。
14世纪中国元代画家王蒙也画过一泉石,画中只有石头没有人,但是表现了某种不在场性,画家题了四句诗:“去随流水远,归与云相随,无心任玄化,泊然齐始终”。这些题跋透露着画家比喻石头的太虚空境和面对自然泊然始终的态度。但是,我们从宋朝到元朝的转换中,看到山水画已经从大空间中逐渐聚焦到单独的物的描绘上,文人画的写意开始登场。如果用西方的经验,这些转换意识就是主体性表现的介入。
即使是主体性表现的迹象,从宋朝到元朝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传统中保持的与世界同化的态度没有变,水墨画追求气韵流动,古代画家感受到流动性是自然万物神秘的灵动,好比石头既是集天地精华的太虚幻境,又是一种始于生与死的自然循环。随着中国山水画在以后的世纪中一次次被推向顶峰,中国绘画已经慢慢呈现保守状态。现在的中国画丢失了曾经对自然的神秘感悟,虚空剩下的是模式持守和自我重复。这种重复来自画家的主观设想。许多国画家谈起西方绘画,认为人家只是客观地描摹,不懂西方绘画对自然的反思和理性的求索从古至今丝毫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整个西方技术理性思维的突飞猛进中,西方人对自然求逻辑、求建构、求几何构成、求真理的主体性认识道路一直推动着艺术往前走。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出现使他们走到了主体性的黄昏,但是这些不影响他们反思主体性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画过一块石头悬置在空中,背后白云缭绕,蓝天上一轮明月升起,他称为“真实的感觉”。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用石头做过最恰当的概括:即使将石头砸成碎片,其内部仍然幽暗;世界依然神秘莫测。
如果我们仅以18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德里弗里希之后的艺术来看这个国家的绘画发展。经过了20世纪初的老表现主义到世纪末的新表现主义,这些艺术家的思想和创作继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神秘性,但是新表现主义和德里弗里希时代和老表现主义不同的是没有了理性的主体性思路。他们表现的是世界不停息的生死轮回的运动现象,这个运动一直秉承着从古老神话、玄妙的诗歌、神秘的宗教哲学那里接过来的灵感。这些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喜欢的是中国宋代的绘画。因为宋画里有中国古人在10世纪左右创作的神秘虚幻空境的自然山水和不生不灭的佛家观念。
十几年后我又重新找回画吴山石头的主题。它们在我的宋人石头系列里作为一种无言之石。我同时将中国石山作为曾在的历史图像和一个现存的世界来观看,重要的不是具体对着石头画。那些过去了的模式有没有指向现实意义,或许它就是一个气韵生动的小世界。石头成为一种视野,它们存在于吴山,表象在历史长河中。我的创作是将与历史感悟的生命释放到画布上。
意识保存着作品从初步形成到完成经过无数次观看,有时候它们来历可疑地只在一朝一夕中完成。在宇宙的空间里,历史、现实、那些像陨石一样从天而降的石头,它们运行的光年何止是丛宋代到今天的千年周期。行星碰撞撒落的陨石碎片,没有先兆地袭来,它们保持着运行,保持着燃烧。燃烧,发光,燃烧……最后消失在黑暗里。重要的是这点。

焦小健 《大众娱乐》 布面油画 150cm×200cm 2017年

焦小健 《中国风景》 布面油画 100cm×240cm 2017年
那堆躺在枝叶草丛中的古代石头,它们被风化地千疮百孔,每一个孔洞都是紫色的血浆,撒落在石孔间的金色落叶是死亡的花瓣,随之被风化,与时间一起苍老,四散在黑暗的林中,光从树丛缝隙中射进来,在刺眼的光中穿越,这是我有次路过一个树林中获得的直观意象。当时光线强烈地射向我的双眼,恍如白昼与黑夜的交替。我想到了吴山被强光照亮的满地碎石和穿透时间的历史,在光线和碎石的交错中,宝石般通透的顽石,缠绕的藤蔓,被照亮的残缺碑文。
光照的空白,为我接下去的绘画意向留出余地,一个非现实看起来很真的空地隐隐约约在那里。

焦小健 《向倪瓒致敬》 布面油画 150cm×400cm 2017年


焦小健 《水的线条 我的笑容》 布面油画 200cm×110cm 2017年

焦小健 《地上的火球》 布面油画 150cm×200cm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