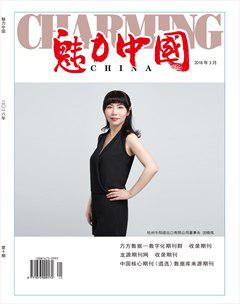宋代官僚宗族发展阶段性略论
摘要:两宋时期的官僚宗族从发展历程上看,大体可以划分为宋初宗族重建、北宋中后期宗族有限发展以及南宋宗族体系化和制度化三个时期。宋代官僚宗族自建立之始,即秉承为王权服务、巩固统治的观念,其后的宗族建设也多凭一些官僚士大夫的责任忧患意识,实为“敬宗收族”,却也有自助自救之意。官僚宗族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制度化,反映了宗族建设的逐渐成熟,士大夫在宗族建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又折射出宋代宗族对王权的依附性关系。
关键词: 宋代;官僚宗族;中央王权
一、宗族重建时期
北宋立国之初,统治者为耕植垦荒、发展农业,曾下诏:“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这是对自由垦荒、土地私有的默认。此政虽一时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更为财力雄厚的地主阶级予以方便,他们兼并土地、广置田产,使得贫富严重不均。加之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豪门望族经唐一代的打压和唐末五代的战乱更替转而凋零,社会向来信仰、推崇的仁、义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宋代新型的士大夫有识之士首先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理学家们建立了一套“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是有理”的以“理”为世界万物本原的学说,并致力于将“理”物化为道德观念。以此为理论基础,士大夫们投身于基层社会建设,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理想,整合家族与社会资源,呼吁宗族重建,以稳定基层,达到安邦定国的目标。
二、宗族有限发展时期
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士大夫加入到了宗族建设的大军中。他们的实践活动涉及到了建祠堂、修族谱、置义田、设义庄等各个方面。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宗族的数量和建设规模仍非常有限,因为“宋代社会,一般只有精英阶层才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和社会权威修谱以收族”。北宋时代修谱家族虽不时见诸记载,但数目毕竟有限。迨至两宋之际,战乱频仍,多数家族无心修谱,亦无力修谱:“世遇乱离,人不自保,遂使子孙不得尽知先世之所以来。”《宋代宗族义田建置情况一览表》尽数列举了两宋的义田数量,其实也不过80家。
政府并非完全忽视地方宗族的发展,对基层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非常重视,并积极打压,而对利于社会建设的宗族才放任其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其时并没有给予基层宗族建设太多的正面支持。同时,宋代恢复重建的宗族力量尚弱小,体系不完善,制度也不够成熟,缺少与政府和王权相抗衡的条件,宗族势力的发展只有与王权保持统一性方能长久。
三、宗族建设体系化时期
南宋理学家朱熹作《家礼》,使得宋代宗族建设开始有例可循、有制可依,宗族建设始得以体系化。之所以将朱熹作为转折点,是因为他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對宋代宗族组织制度和原则作了系统说明,且被后世沿袭传承。朱熹主要在祠堂规制、祭祀礼仪、设立族产三个方面影响了以后的宗族制度。
因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经济文化繁荣,宗族社会得以繁衍,朱熹《家礼》问世后,也主要于东南沿海一带传播。受到影响的首先是朱熹所在的福建地区,有学者认为“《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宗族组织化。”徽州宗族也多承载《家礼》的体系,认为“《家礼》是一部新的‘典常,是宗族礼仪活动的指南,‘若衣服饮食,不可一日离焉”。南宋的宗族建设因《家礼》从而逐渐走向体系化、制度化建设时期。
四、宋代官僚宗族与王权
纵观宋代宗族建设的三个阶段,宗族与王权自下而上始终维持着政府调控、社会秩序的一元化。士大夫在宗族建设进程中的一系列举措更指明了宗族是向王权靠拢、依附于王权的,这也是宋代官僚宗族发展的显著特点,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其一,重视教育。在集权统治的社会,国家的政令措施必定深刻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在宋代国家重视科举制度的大背景下,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官本位思想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走上了科举的道路,士大夫们读书入仕皆以服务政权为要,也体现了政权对士人、宗族的控制。
其二,族长由官僚担任。在宋代宗族重建之时,理学家们就提出了新的立“宗子”法——由官僚担任一族族长,而不是严格按照传统,取嫡长子为宗子。
其三,家族婚姻上的“门当户对”。对于魏晋世族来说,谱系就是身份的象征。谱系不仅有排斥寒门、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政治功能,而且是婚姻的纽带,对于血脉传承具有重大作用。
其四,等级制与伦理教化。宋代祠堂建置的兴起使宗族内部逐渐走向等级制。自古以来施行的家庙制度是上层官僚的特权,即便宋代重新修订家庙制度,也只有寥寥数人享有家庙祭祀的权力,“本朝(理宗朝)大臣賜家庙:文彦博、蔡京、郑居中……凡十四人”。然而由于官僚数量的庞大、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家庙制度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祠堂应运而生。
司马光在《影堂杂仪》中规定祭祀的礼仪:“每旦子孙谒影堂前,唱喏出外,归亦然,出外再宿上,归则入影堂,每位各再拜。将远谪及迁官,大事则盥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拜。”司马光要求宗族子弟在家族生活中要以“孝”为先,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礼仪约束,每当出、入家门或仕途有变,都要告知祖先。朱熹《家礼》对其稍加损益,万世传承。真宗朝宰相贾昌朝《戒子孙》,“今诲汝等,居家孝,事忠君,与人谦和,临下慈爱……”;《欧阳永叔集·与十二侄》中,欧阳修告诫子侄:“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世。至于临难死节,也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也自佑汝,慎不可避思事也”,即作为官僚要一心为国尽忠,哪怕是面临生死,也要维持操守。
宋代士大夫官僚通过宗族建设一方面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通过对宗族子弟的教导与规范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族内部的伦理教化为王权统治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在基层社会加强人伦、巩固尊亲,作为王权统治利器的以官僚宗族为主体的宋代宗族,逐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时代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治安.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2]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此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16CLSJ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玉双,女,汉族,1993年10月生,籍贯山东淄博,青岛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