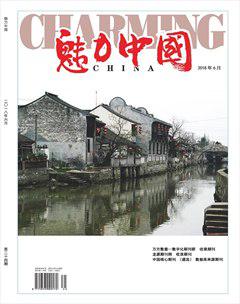从《浮士德》看歌德的生态矛盾思想
王亚楠
摘要:《浮士德》作为歌德晚年最成功的文学巨著,其中蕴含了歌德在生态学层面的矛盾思想。他一方面将浮士德塑造为一个不断进取的探索者并对这种精神予以肯定,但同时由于浮士德在进行精神探索时只考虑自身欲望和需求,置他人于不顾,因此歌德在另一方面又对浮士德的反生态行为进行了批判。歌德的批判态度体现在浮士德前四个阶段的追求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阶段中看似成功的浮士德最终却被“忧愁”吹瞎了眼睛。
关键词:浮士德;歌德;生态矛盾思想
《浮士德》耗费了歌德近60年的心血,是他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并称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书中塑造的浮士德形象和浮士德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于浮士德的探索,一方面要肯定其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还要从生态批评视域对其中的反生态思想进行反思。从生态学层面来看,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体现了歌德强烈的生态矛盾思想。他一方面对浮士德不断追求探索的精神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对其探索造成的后果予以否定。
一、追求情欲的浮士德
浮士德第一次從镜子中看见玛格莉特的时候就发狂的爱上了她,于是他强硬的对靡菲斯托说:“听着,你必须把这姑娘给我弄来!”“如果这甜蜜可爱的人儿,今夜我不能搂她在怀里,咱俩到子夜就各奔东西。”[1]在与玛格莉特偷会时,因为担心碰到玛格莉特的妈妈,浮士德便让玛格莉特把安眠药放进妈妈的水里,不料因用量过大造成了妈妈的死亡。又因玛格莉特的哥哥阻止二人约会,浮士德在靡菲斯托的帮助下竟一剑刺死了瓦伦廷,使得玛格莉特从一位原本笃信宗教、清白无邪、拥有许多美好品性的天使被迫害成一个背上杀母和不洁的罪名、被众人鄙弃、在狱中几近癫狂的阶下因。
从一个侧面来看,浮士德这种为了自己的愿望而不言放弃的作为正是浮士德精神中所宣扬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浮士德的行为最终酿成了一个悲剧。他不但杀害了玛格莉特的两个亲人,还使得玛格莉特在极端痛苦之下无意识地溺死了她与浮士德的孩子,犯下了弑婴罪,最终身陷囹圄。
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2]生态批评家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文化危机、文明危机。浮士德的种种行为都折射出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与玛格莉特的交往中,他并没有将玛格莉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只把她当作是英雄的陪衬,是实现个人爱情理想的媒介,是奋斗途中一个偶然的失误。他为了一己私欲,不惜残害他人生命。歌德对浮士德人类中心主义行为的否定可从这一阶段的结果中窥见一斑,他以一场悲剧结束了浮士德追求爱情的阶段:玛格莉特发疯,浮士德也陷入深深的恐惧中。当浮士德看到狱中的玛格莉特时,他发出了深深地忏悔“真希望世上没我这个人!”歌德在赞美浮士德执着追求的精神的同时警示人们逾越生态底线的执着追求是不可取的。
二、渴望古典美的浮士德
浮士德在追求宫延生活失败后转而追求古典美的化身——海伦。然而,想要找到海伦绝非易事,她存在于那“入无人涉足之途,不可涉足;临人所不求之境,不可祈求。没锁须开启,没闩须拔掉”[3]的连足音也听不到、没有实地可以立足的虚无之境。董问樵先生指出,“‘浮士德精神主要指‘永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的现代精神。”[4]一个连魔力广大的靡菲斯托都怯以进入的地方,浮士德却敢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勇敢前行。这一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所在,更是歌德对浮士德的肯定之所在。然而,在其追求海伦的过程中,浮士德身上表现出来的欲望极端化的精神是应受谴责的。当海伦的丈夫墨涅拉斯要来攻打浮士德以夺回妻子海伦时,浮士德召集起自己的军队与之抗衡,拒绝归还海伦。毋庸置疑,这一欲望极端化导致的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应受到批判。于是,歌德将最后的结局安排为:浮士德与海伦所生之子欧福良在出生后不久便如彗星般陨落,海伦也意识到“幸福和美貌不能长久结合为一,生命与爱情的纽带已同时扯断。”[5]终于离开了浮士德。浮士德对古典美的追求也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结局安排流露出歌德对浮士德欲望极端化的生态反思。
三、围海造田的浮士德
在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探索时,浮士德眼中的地球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完成伟业提供阔土的地方,它不但自身贫瘠而且还将贫瘠播撒,于是,他下定决心“把狂暴的潮水从岸边驱走,让无垠的大海便成为有垠,甚至逼它退回去老远老远。”[6]为了达成围海造田的愿望,浮士德凭借卓越的战绩从国王那里得到了封地——大海,而这战绩的背后却是无辜的大自然遭受的灭顶之灾,“地平线渐渐变得昏暗,只有这儿那儿见得着神秘的红光一闪一闪;刀剑已经被映得血红;山峰、森林和整个天空全部笼罩在红光里面”。[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而浮士德使自然为己所用——围海造田的做法无疑严重违背了这一理念。
浮士德为满足自身欲望和需求,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行径再次彰显了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不顾百姓疾苦让他们夜以继日的劳作,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竟通过利诱、恐吓、逼迫等手段来达到目的。当他面对阻碍其疆土扩张的菩提树和影响他视线的老人的房子,他说“快让那边俩老家伙迁移,我希望在菩提树下安居;这几株树如果不归我所有,纵然统治世界仍觉难受。我渴望在那儿开阔眼界,在扶疏的枝间搭建高台,从高台上纵目远望大地,好把我的成就尽收眼底。"[8]正是浮士德的这一欲望最终导致了老夫妇在火中惨死的结局,而最终实现了理想的他却被“忧愁”吹瞎了眼睛,这一细节可看作歌德对浮士德无限扩张的征服意识和欲望的终极讽刺。
浮士德在围海造田时置后代生存于不顾,肆意地消费地球资源,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在浮士德眼中,他的行为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种造福于千万人的劳动,因此,他才能从中感到快乐满足。浮士德在临终前对自己的一生追求进行了总结:“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施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浮士德式生存叫做“积极的奋斗的、征服的生存”,而这一点也正是歌德所赞扬的。
参考文献:
[1][3][5][6][7][8]歌德.浮士德[M].杨武能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5:130-131,327,516,530,547,579.
[2]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4]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