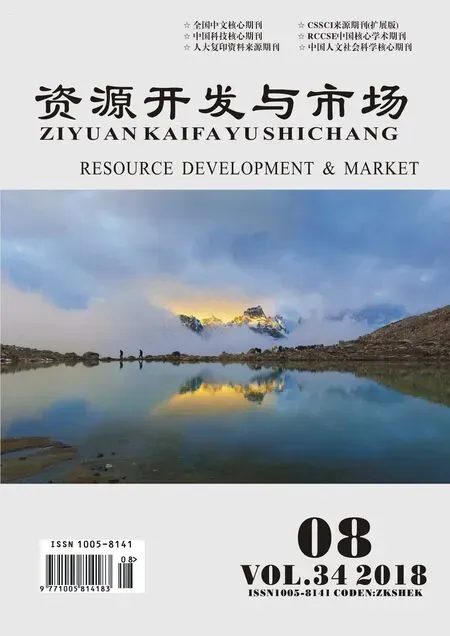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淮河流域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处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之间,流域总面积约27万km2,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5省、40个地级市、181个县,总人口约1.7亿人,平均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倍,居各江河流域人口密度之首。2016年,淮河流域人均GDP为4.39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条件优越,主要作物有水稻、小麦、大豆等,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基地;工业矿产资源丰富,以食品、轻纺工业为主,近年来煤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等轻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一大批大中型工业城市崛起。由于工农业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大规模增加,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远远超过水环境容量,对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使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难以协调发展。此外,淮河流域存在严重的水质性缺水问题。根据《治淮汇刊》和《淮河流域水资源公报》有关水质数据,2001—2010年流域Ⅲ类以上的水质比例不足整体评价河长的1/2,但“十二五”期间流域水质达标率缓慢上升,废污水排放量有所减少。总体上,淮河流域水环境形势严峻,水环境状况脆弱,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近年,众多学者对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系列研究[1,2]。郑旭等[3]采用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模型对水环境污染和社会经济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研究,描述了工业废水、COD排放量和生活污水等污染排放指标和人均GDP的不同曲线特征。在此基础上,揣小伟等[4]比较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江苏水环境的影响,认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削减重点污染行业有利于保护水环境。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水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冫工明峰等[5-7]应用模加和方法评价了不同地区水环境承载力现状,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姜大川等[8]运用混合模型计算了武汉城市圈水环境承载力状况,表明水环境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陈自娟等[9]分析了水环境承载力和流域生态补偿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有效调节流域内利益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来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等。同时,对淮河流域水污染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Peng X[10]基于EKC曲线理论分析得到淮河流域五省经济增长导致工业“三废”排放量增加,只有走循环经济道路才能实现淮河流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YT Guo等利用模糊物元理论[11]、TOPSIS模型[12]评价了淮河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识别出了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陈岩[13]、刘倩倩[14,15]等认为水质、水量、洪涝、旱灾会影响流域水资源的脆弱性,影响区域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徐娜[16]从气候变化角度分析了珠江流域水资源的脆弱性;童国平[17]从水量角度论述了流域水量和社会经济之间的脱钩关系,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来增强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①评价社会经济与水环境的协调发展模型多集中于EKC曲线和环境承载力指标,方法较单一。②研究大多讨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单独从水污染角度判断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值得重视,如了解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各自的作用,有利于更清晰地分辨出社会经济状况对水环境的影响力大小,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③对淮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讨论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较多,从水污染问题出发的水环境质量、水环境与流域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有待深化。
本文把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看成三个复合子系统,将淮河流域各省区域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内容,通过构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来了解系统的整体协调性和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首先采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科学评估淮河流域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各系统及其系统整体发展状况和协调发展水平,然后利用耦合模型测度四省区域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淮河流域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突变理论
突变理论由法国数学家Rene Thom创立,是主要利用动态系统的拓扑理论构造自然现象与社会活动中不连续变化现象的数学模型,并用来描述和预测事物连续性中断的质变过程[18]。突变理论适用于系统内部作用尚不明确的研究,而流域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理解为流域系统内部各指标的逐渐变化导致整体流域系统的水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发生质变,其中每一个指标数据变化都可引起突变现象,因此本文应用突变理论来评价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1 常见突变模型的势函数、分叉集和归一公式
1.2 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突变级数法首先是对系统的评价目标进行多层次矛盾分解,然后利用突变理论与模糊数学理论相结合得到突变模糊隶属函数,由此函数得到初等突变模型和分歧方程,在此基础之上推到出归一化公式,再进行综合量化计算,最终归一为一个参数。该参数即为总隶属函数,它可实现对系统的综合评价[19](表1)。其中,总隶属函数可计算出区域的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实现对流域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合理评价。
改进的突变级数法主要体现在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确定指标排序,即:①熵权法。在运用突变级数法对目标进行综合评估的过程中,必须对各指标按重要性程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利用熵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确定各指标的重要性,权重越大,重要性越大,这样避免了指标排序的主观性,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准确[14]。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具体步骤可参照文献[14]。②常见突变模型。如果1个指标(系统状态变量)包括2个对应的下级指标(系统控制变量)可视为尖点突变系统;同理,当一个指标分布含有1、3、4个下级指标,分别视为折叠突变、燕尾突变和蝴蝶突变模型[19],其势函数、分叉集和归一公式见表1。③突变系统的综合评价选择原则。结合多目标模糊决策理论和实际情况确定评价原则:如果各指标为相互联系、相互补足的关系,采用“互补”的原则,即状态变量取各控制变量的平均值;如果各指标是相互独立的,采用“非互补”的原则,即状态变量利用“大中取小”的准则在各控制变量中取值。④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划分。由突变级数法得到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反映系统的综合发展状况,对其进行等距划分,得到五个协调发展水平阶段,见表2。

表2 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划分
1.3 基于耦合模型的系统相互关系研究
突变级数法评价得到的系统综合值可反映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了进一步确定水环境分别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引入耦合度模型来说明两两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从水污染问题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会直接影响水环境状况,为了更加明确社会和经济系统对水环境的影响大小,分别计算水环境和社会系统、水环境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度(C),表达式为:
(1)
式中,U1、U2分别为水环境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当C=0时,耦合度最小,表示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处于无关联状态并向无序方向发展;当C=1时,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达到最佳的有序发展状态。根据耦合度的变化特征,采用中值分段法将耦合度划分为4个区间,见表3。

表3 耦合度和耦合阶段划分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水环境系统评价指标选取
依据指标体系建立原则,从水污染和污水治理两个方面构建水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5个评价指标,分别为:A1(万元GDP废污水排放量)、A2(万元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A3(万元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A4(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A5(废污水处理费用)。其中,选取万元GDP废污水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来衡量工业发展产生的污染物对水环境的影响,选取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废污水处理费用来衡量水污染的治理水平和资金投入。
2.2 社会系统评价指标选取
从人口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选取4个评价指标对淮河流域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分别为:B1(人口自然增长率)、B2(城镇化率)、B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B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中,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来衡量人口的增长状况和城市化发展;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角度,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人们生活发展水平。

表4 淮河流域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指标熵权值
2.3 经济系统评价指标选取
从经济活力和经济结构方面选取4个评价指标对流域经济增长状况进行评价,分别为C1(人均GDP)、C2(第三产业产值)、C3(第一产业比重)、C4(第三产业比重)。其中,从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来衡量整体经济状况和产业发展活力,以第一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流域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体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可了解产业发展份额和发展趋势。运用熵权法得到淮河流域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熵权,见表4。
从表4可见,各系统的指标熵权值可判断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用I表示),即IA2>IA3>IA1、IA5>IA4,得到I水污染>I污水治理;IB1>IB2、IB3>IB4,得到I生活水平>I人口发展;IC2>IC1、IC3>IC4,得到I经济结构>I经济活力;将指标从左至右排列来确定各系统指标重要性,得到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图1。

图1 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到的初等突变模型类型主要是尖点突变系统(如污水治理、生活水平、人口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等)和燕尾突变系统(如水污染),然后采用各系统下的归一公式和指标“互补”原则得到水环境、社会、经济各系统评价值,最后遵循各系统之间“非互补”原则,得到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并对整体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3 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3.1 地域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析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时期淮河流域整体地域的协调性分别处于较高和高水平状态,内部差距小。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区域内部协调性水平差距,对各省区域的综合值进行排序(图2)。
由图2(a)可见,淮河流域河南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综合值最小,其次是江苏省和安徽省,山东省最大。 “十一五”期间,淮河流域上游协调性相对较差,中游状况一般,山东区域水系协调发展水平最优。由图2(b)可见,“十二五”时期的系统发展综合值提高,系统协调性水平上升,空间协调性也发生了变化。安徽省的系统发展综合值排名下降,协调水平在流域整体中最差;河南省和江苏省区域的系统综合值排名上升,区域协调状况在流域整体中逐步改善;山东省区域的协调性一直保持整体的最高水平。总之,淮河流域西部地区协调水平较差,东北部协调水平最优,流域南部(安徽省)的协调状况在整体中地位下降,所以需要关注流域南部经济水平的发展,寻找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实力,做到经济状况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达到流域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图2 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性时空变化
3.2 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分析
淮河流域内河南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性结果分析:河南省区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各系统的评价值、综合评价值、水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耦合度C1、水环境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度C2等结果见表5、图3。

表5 河南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图3 河南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变化
具体分析为:①水环境、社会和经济各系统评价。从图3可见,2005—2011年水环境系统评价值一直处于小幅增长的状况,随后4年状况则逐渐趋于稳定,说明河南省区域在“十一五”期间水环境状况得到逐渐改善,并在“十二五”期间保持良好状态。由于河南省大力发展工业,导致河流污染严重。随着节能环保意识的提高,当地水资源环境状况逐渐改善。在研究期间,河南省社会系统评价值不断增长,说明流域人口数量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系统评价值呈先陡后缓的走势,表明河南省前期经济发展迅速,后期逐渐回归平稳,经济状况稳定良好。②系统的综合评价。由表5可知,河南省区域的系统综合评价值波动增加,系统整体协调状态呈“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状况逐步改善。其中,2005年系统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十一五”期间则过渡到较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十二五”期间发展到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③系统耦合度。河南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耦合阶段为拮抗,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较大,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影响到水环境状况,但两者的相互作用保持不变。河南省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度为0.8—1并不断下降,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很大,但两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小,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水环境质量为代价,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强脱钩,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淮河流域内安徽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性结果分析:安徽省区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各系统评价值、综合评价值、水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耦合度C1、水环境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度C2等结果见表6、图4。

表6 安徽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图4 安徽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变化
具体分析为:①对水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评价。从图4可见,水环境系统评价值不断增加,说明安徽省区域经历“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阶段,水环境状况逐步改善,水资源质量稳步提高。社会系统评价值在逐渐增加,说明安徽省区域的社会生活稳步发展。经济系统评价值呈现先增后缓的增长趋势,说明安徽省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迅速,而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逐渐下降到10%以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②系统综合评价。由表6可知,整体协调状态呈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安徽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发展状况逐步改善。其中,2005年系统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发展状态,“十一五”前期的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后期及“十二五”期间已发展并保持在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③从系统耦合度情况。与河南省相同,安徽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系统的耦合阶段为拮抗,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较大,但两者的相互作用保持不变。安徽省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度由高水平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很大但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安徽省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经济方式的转变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淮河流域内江苏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性结果分析:江苏省区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各系统评价值、综合评价值、水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耦合度C1、水环境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度C2等结果见表7、图5。

表7 江苏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图5 江苏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变化
具体分析为:①水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评价。从图5可见,水环境系统评价值缓慢增加,但在2010年评价值出现凹点,表明江苏省在“十一五”前期注重发展经济,随着规划的完成,人们开始保护水环境,减少工业废水废物的排放,使江苏省水资源质量缓慢提高。2010年由于江苏省万元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达37.46t/a/万元,工业废水效益低,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的同时损害了水环境效益。社会系统评价值逐步增长,说明流域内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经济系统评价值出现先增后缓的增加趋势,主要是“十一五”期间过度追求经济增速,经济增速达15%以上,“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质量提高。②系统综合评价。由表7可知,江苏省区域的系统整体状态呈“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状况逐步改善,但期间略有波动。其中,2005年系统整体为低水平协调,在“十一五”前两年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后期已保持在高水平协调状态。其中,2010年系统协调状况受到水环境的影响,工业产值上升导致废水废物大量排放,环境状况短期恶化。③系统耦合度。江苏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保持不变,而水环境和经济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越来越弱,得益于该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淮河流域内山东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性结果分析:山东省区域水环境、社会、经济各系统评价值、综合评价值、水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耦合度C1、水环境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度C2等结果见表8、图6。

表8 山东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图6 山东省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变化
具体分析为:①从水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评价情况。从图6可见,水环境系统评价值在“十一五”期间上升幅度大,而“十二五”期间增加缓慢。由于山东省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保护环境的政策与环保意识提高,水环境状况不断改善。社会系统评价值呈波动式逐渐增加,其中2010年和2013年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大幅度增加,导致区域内水环境压力增大,水环境状况出现短期恶化。经济系统评价值呈现先增后缓的增长状态,表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变好。②系统综合评价。由表8可知,山东省区域的系统整体协调状态呈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中,2005年系统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在“十一五”期间,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由较高发展水平到高水平协调状态;在“十二五”期间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整体仍保持在高水平协调发展状态,其中2010年系统综合状况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当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造成水环境压力陡增。③系统耦合度。与其他区域相同,山东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系统的耦合阶段为拮抗且不变。山东省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度为由高水平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虽然经济发展比社会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更大,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力逐渐减小,两者相互关系变弱。同时,需要重视社会系统的发展,积极转变社会生活方式达到节约用水,实现水环境和社会耦合度下降。
4 结论
主要结论为:①从流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变化特征看,从“十一五”发展到“十二五”阶段,流域整体协调性从较高水平上升到高水平,而流域南部地区(安徽省)的协调状况下降,因此安徽省急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域整体的综合协调状况。总体来说,流域内部协调性差距较小,其中西部地区协调水平较差,东北部协调水平保持最优。②从淮河流域各省区域水资源—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发展状况看,水环境和社会、经济三大系统评价值整体呈增长趋势,但经济系统评价值变化状态为先增后缓,水环境和社会系统评价值波动上升,说明淮河流域内各省份的社会经济越来越好,水环境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十一五”期间,由于淮河流域各省注重经济发展,经济增速普遍达到10%以上,使水环境质量变差。随着“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节水技术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等使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水环境质量也逐步提高,呈可持续发展状态。③从系统的综合状况和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淮河流域各省区域的整体协调状态呈低水平—较低—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状况逐步提高。此外,由于受到突变级数法法的影响,使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三个系统的最小评价值决定,所以淮河流域的经济系统主要影响系统的综合评价,要想流域未来水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再得到提高,经济发展需要尽快走出过渡期和发展期,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活力来保证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稳定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水环境系统协调健康发展。④从系统之间耦合度看,淮河流域各省区域水环境和社会系统耦合为拮抗阶段,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较大,但两者的相互作用基本保持不变。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是由高水平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很大,但经济对水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小,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经济方式转变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