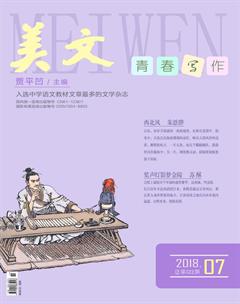北京!北京!
一
北京是什么?“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用得很多很俗,但似乎确实找不到比这句话更好的形容,我相信每个人给北京的定义都不一样。用最官方的表达来说,它是共和国的首都,坐落于东经116°、北纬40°。每个人说起北京来似乎都如数家珍。那有天安门、故宫、长城……爱吃的人会告诉你,它还有北京烤鸭,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当然也少不了一些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这里有足够包容的空间给你创作。还有一群“北漂”,他们怀揣着各式各样的梦想来到这里,期待这座城市可以给予他们一点回应。当然还有“引领”全国的房价,能让人们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
这只是一个世人都知道的北京,每个在北京待过的人都有另一个北京。
对于想南方延绵青山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北京是在我十八岁前尚未踏足的北方,所有印刷在教科书上的有关北京的标签,是我对它的所有印象,当然还有家长、老师从小在耳边提及的清华、北大。北京太过遥远,也太过繁华,我的绝大多数活动范围在从小长大的县城,在北京面前我没有任何优越感,除了在自嘲时候会笑着说道,我们最起码有新鲜空气,这个时候刚好是在“雾霾”这两个字眼频繁出现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算是我幸运的一年,入围了一个比赛去到上海,我被南京路上的繁华震慑,外滩对面的浦东摩天大楼高耸,巨大的广告牌下打着“我 上海”,街道干净整洁到难以置信。令我一直称道的是公共厕所,我曾经在《意林》亦或是《读者》之类的杂志上看过讲道,日本的公共厕所马桶里面的水可以饮用,也许这是个野鸡新闻,或者过度美化。直到我到上海后,发现文章形容的就是上海呀。
大家都井然有序安静的排队,丝毫没有小县城那种稍微五六个人就闹哄哄乃至插队更是常事。手足无措第一次乘坐地铁在城市里穿梭,在上海地铁是我在这个城市第一次接触的公共交通工具,我极力装成娴熟的样子,来掩饰我第一次乘坐地铁不想让别人看出来的不安。
从见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便把它列为我最爱的城市
高考完后因为参加考试原因,我相继去了武汉还有北京。那时候关于北京空气差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柴静《穹顶之下》的纪录片放出来后达到顶峰。在高三的冬天,整个北方确实笼罩在雾霾之下,隐隐有跨江的趋势。
“北方都是空气不好的吧。”我在心里暗下定论。
当然武汉不算是北方,可是在出火车的一个小时内,因为和来接我的学长聊天,嗓子就因为空气原因,刺痛得讲不出话。这是我第一次真确感受到空气污染对我嗓子的伤害,以至于我对接下来北京之旅没有任何期待。
二
高铁呼啸穿过中原大地,五个小时把我从武汉送到北京。华北平原上留下的是收割完后的麦茬,平原上没有任何遮挡物挡住视线,偶尔有几个突兀的小土坡,上面稀稀落落长着几棵树。此刻在地理书的写过的地貌出现在眼前,而我不得不感慨,华北平原真平啊。我的家乡是在群山包围的小县城,一眼望去,是走不出的群山,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最后离开。
就在我以为一路上平原望不到的尽头的时候,天黑下来,在夜色笼盖下的北京西站下车,大厅里仍旧熙熙攘攘,与专门来到北京陪我考试的姑姑会面后,没来得及打量这个城市,便在夜色中赶到了连锁酒店。
第二天天亮后又赶着去位于郊区昌平的某所大学考试,我只有透过公交打量这个城市,六月上旬,北京城是灰蒙蒙一片,当然不可避免我嗓子又痛了。车上一瞥,初下定论,我不喜欢这个城市,剩下的三个小时车程在昏睡中过去,我本以为这是我做过最长时间一次的公交,而返程的时候因为遇上传说中的北京堵车,在公车上的时间远远不止是三个小时。
姑姑行程只剩下一天,她和姑父在我来之前在北京故宫天安门等地,我考试那天,他们去了昌平附件的八达岭长城。因为姑姑的记错上班日期,以为我们在北京只剩下一天游玩的时间。她和姑父继续去北京经典景点,问我是否需要一起,我拒绝了,因为要去赴约与一个朋友见面。
我们约定的行程是去逛清华北大,可以说基本上绝大多少国人都对清北有一种微妙的情怀,虽然高考后得知自己绝对无缘这两个学校,仍然想要一瞥中国最高学府的风采。幸运的是当初非节假日,与朋友无需排队就进入北大校园,误打误撞从一条小路七弯八绕进入清华园,和朋友吐槽,清华比北大漂亮。确实是啊在我那时候看来,北大园子里的花草无精打采,园林缺乏管理杂草丛生,还有干涸的小池塘。
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北大东门前的报刊亭没有文学类杂志,我却在它物理实验室的门口前买到了《人民文学》《收获》和《萌芽》,两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在路过北京的报刊亭都没有发现文学杂志的情况下,我就是坚信,北大物理实验室门口的报刊亭一定有,事实确实如此。
第一次来北京,我们没有看过天安门故宫和长城,匆匆忙忙结束。
三
两年后的六月,我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来北京上暑假课,同样从北京西站坐地铁出发去三里屯一个姐姐家居住,因为到达的时候是周六早上,恰好错过早上人流高峰上班的场景。乘坐电梯出地铁口,电梯缓缓上升,通过透明的天窗,我看到矗立在道路旁的中国作家出版社,那里有中国顶级文学期刊社的总部。似惊又喜,自己还是一个能因为遇到与文学相关的东西而雀跃的女生。
我居住的三里屯的片区,这儿的房子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然而就在一个街区之隔,是三里屯的中心地带。上完课晚上回来后,路过那篇繁华,灯火通明,透过三里屯soho的窗户,还有很多人在加班奋战。当然喧闹是商业中心,来来去去一批又一批的人。
难以想象到回到租住的房子,安靜到可以听到蟋蟀声,又隐约可以听到商业区那边传来音乐沸腾的声音,总感觉有巨大的不真实感笼罩着我,从而生出巨大的恐慌。
早上上课时候从三里屯出发,我逆着人流出发,穿过从四面八方往这边来上班步履匆匆的人员,昨天晚上街区便上稀稀疏疏的几辆共享单车,如今这边又整齐排列占尽街道位置,是那些工人深夜工作的结果。
北京的炎夏真正到来,我打槐树下走过,槐树开出细碎的花,浅黄色,小小的米团状,小巧可爱,难以想象北京这座城市,还拥有如此小家碧玉的东西。
记得这次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姐姐问我,两个月在北京除了上课外,你还想去那些地方看看嘛?
我有些羞赧,反而不好意思开口,犹豫说道:“虽然之前来过北京,我还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有去过故宫,我想先要去那看看。”因为这些年城市兴起“网红”地点,想去太被全民知道拥护的故宫天安门,反而怕会被取笑,为了避免尴尬,我还说了一句,“我想去的地方会不会太俗气了”。她说不会啊,这是经典呀。
当然几天后,在北京一个朋友的陪同下,终于去到天安门,37°C的高温炙烤下,丝毫没有打击我的热情,但我也知道,自己并没有想象中激动。好像去实现一个必然的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持续太久了,等到真正要完成那刻,反而只是轻松。只是那个时候我会想起一年级坐在深山乡村的我,读着关于北京的那篇课文,里面写着,北京是共和国的首都,那里有故宫和天安门。
四
待在北京两个月的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太过深入。我在配钥匙时候被小贩坑骗过在反映过来一腔热血找回坑我的钱的钱。同样我也遇到过热情有责任感的朝阳区大妈,在我没来得及看清红绿灯的时候提醒我。误打误撞走入过北京胡同,遇到热情的本地人给我指路。
姐姐是一名程序员,经常加班,晚上偶尔将近十一二点回来,那时我已经在床上睡得正熟。
和她的交谈中,她和我说,再过一年她就辞职离开北京,大四实习时候来到北京,工作一两年后被她的爸妈要求回到家乡的小城,那时候家乡的互联网发展不好,工作机会少,浪费半年时间后又回到北京。她说感谢北京给她工作机会,然而在付出七八年青春后,还是要离开这儿。因为北京除开这辈子有难以企及的房价,更多是没有归属感。
有趣的是,寒假里我又再去上海,住在一个同学家。她初中中考成绩不理想,选择辍学,来到上海打工已经有了快七年。后来她意识到自己选择辍学是个失败的选择,参加了成人高考,读了大专。她和我说18年夏天就要毕业,等毕业好就要离开这儿去个更小的城市。她选择要离开的理由,与我在北京的姐姐有异常的相似,她说我在上海没有归属感,感觉不到我是被需要的。我们从外滩乘坐地铁回到她居住的地方,兜兜转转将近两三个小时,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疲倦感,突然就让我对城市太大产生恐惧,从高三见到大城市繁华后便把留在这变成目标,也让我对这个目标开始怀疑。
归属感是什么?我开始思考。
是在城市中被需要?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或者在城市中取得成功吗?或者兼而有之。我承认我是有乡土情怀,然而我知道乡村俨然是远去的骊歌,田园牧歌式的情怀在农村是找不到的。我回不去了,只能停留在我的回忆情怀里面,享受城市的便捷后,便会难以忍受乡村鼻塞的交通,更难忍受的是旱厕。
可是人又是贪心的,既想要城市的便捷,在城市的冰冷巨大水泥包围后,又会忍不住想要乡村生活的人情味。
曾经第一次见到大城市,处处优越于乡村的环境,会让人忍不住把大城市变为自己以后想要留下的地方,然而这个因果链太过于脆弱,一旦受到冲击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城市到底是因何而在?特别是乡村长大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选择城市。這些困惑,往往集中在从乡村长大后来步入城市的年轻人身上。深入思考,往往会有一种被割裂的无力感。
我去过的城市越来越多,而我也越来越频繁思考我与城市的关系,以期寻找到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