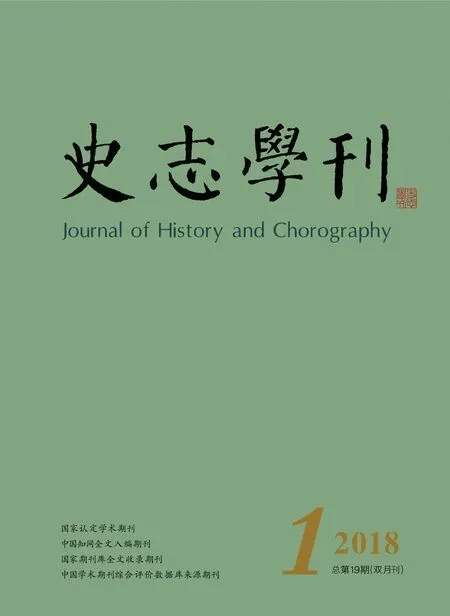汉末流寓交州士人考析
张寅潇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州510631)
东汉末年,中土动乱,中原人士为避战乱,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外地。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认为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到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间,中原人士大概有四次比较大的迁移[1]葛剑雄主编.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P271-273),贺昌群先生在《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之传播》一文中也指出“自桓灵以来数十年间,天灾人祸频仍,中原人士转徙四方者,大抵可分四个区域:(一)自三辅入汉中、巴蜀,(二)青、徐之人或北走幽、冀,或远渡辽东,(三)或入扬州,或南渡江左,(四)充、豫士庶,或入荆州,南转交阯。”[2]贺昌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之传播.文史杂志,1941,(5).后收入氏著.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学术专著).商务印书馆,2003.(P166)这些举家迁徙的流民中不乏饱读诗书的士人学子,他们的流寓无疑推动了当地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原文明向边地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学界对流寓到巴蜀、辽东、江左包括荆州等地士人的迁徙情况和影响多有研究,而对交州地区的关注则相对较少[3]关于士人流寓交州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宋超.东汉末年中原士民迁徙扬荆交三州考——兼论永嘉迁徙前客家先民的早期形态.齐鲁学刊,2000,(6);秦佳.两汉交州官吏及相关人物研究.郑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陈国保.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4);王小丽.秦汉时期岭南移民问题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严伟.魏晋时期交广地区若干问题探讨.华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间或有之,亦疏于简略,或失于阙漏,这与中原士人迁移此地者较少、文献记载有限不无关系,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对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流寓到交州的士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考证,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斧正。
一、交州沿革及汉末交州概况
交州,原称交阯,又作交趾,《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4](唐)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卷 12)·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P1338),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广西、广东和越南的中北部一带。交州在先秦时称南越,是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秦统一六国后,在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1](汉)司马迁.史记(卷 113)·南越列传.中华书局,2014.(P3593),将其正式纳入中原版图。但到了秦二世时,赵佗趁乱“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又隔绝在外,脱离了中央的管辖。这种独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元鼎六年(公元114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2](汉)班固.汉书(卷 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P188),后以九郡为交阯刺史。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 15)·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P464-465)交州之名始定。
东汉末年,王纲解纽,交阯太守士燮趁乱占据交州,“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4](晋)陈寿.三国志(卷 49).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1982.(P1191),交州自此俨然成为士燮等人的独立王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即赵佗)不足踰也。”[4](P1192)
鉴于交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丰饶的物产资源和突出的战略地位,除士燮外,汉末的其他诸侯如北方的曹操、荆州刘表以及江东孙权均欲在交州分一杯羹,于是,围绕着交州归属权的争斗在东汉末年频频上演[5]胡守为.士燮家族及其在交州的统治.学术研究,1996,(11);凌文超.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朱子彦,王光乾.论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和攻守形势.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4](P1192),建安末年,士燮又遣子廞入质,以示臣服,但其实交州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吴黄武五年(226年)士燮离世,之后,孙权逐步翦除士燮子嗣,彻底取代士氏,确立了对交州的统治,汉末关于交州的争夺战也以孙权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终结。
从士燮割据到并入孙吴的这二三十年间,交州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史载“交阯士府君(士燮)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4](P1191)。加之士燮本人又“体器宽厚,谦虚下士”,故而“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正是交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士燮爱贤敬士的态度,使交州在东汉末年成为中原士人理想的避难所,他们不惜远渡重洋,举家迁徙,对交州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二、汉末流寓交州的主要人物
笔者据《后汉书》、《三国志》等诸多史料整理出汉末流寓交州的士人主要有刘熙、许慈、程秉、薛综、许靖、袁沛、邓子孝、徐元贤、桓晔、袁忠、桓邵、袁徽和刘巴等13人[6]士燮先祖早在王莽时便已迁到交州,不宜将其归入汉末流寓交州士人之中,故而本文未将其纳入讨论范围内。与士燮类似的还有牟子,据《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序可知牟子亦为汉末流寓交趾之隐士,因其家本在苍梧,苍梧郡亦属交州,牟子只是从苍梧郡迁到交趾郡,严格来讲,牟子也不能称作流寓到交州的士人,故本文也未将其包括在内。。
1.刘熙。刘熙,史书无传,其事迹散见于《三国志》等书中,只知其为汉末名士,博通五经,在其所著《释名》序中有“汉北海刘熙成国撰”[7](东汉)刘熙撰.(清)毕阮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1.但也有学者怀疑《释名》的作者不是刘熙,而是刘珍,抑或不是在交州的刘熙,而是另外一个同名姓的刘熙。对该问题,周祖谟、宦荣卿、张华清等人在其论文中都对刘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证,认为《释名》确系汉末在交州之刘熙所作,分别见于周祖谟.释名校释序.辞书研究,1984,(4),宦荣卿.《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复旦学报,1985,(5).和张华清.再论《释名》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目.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另外,陈建初.《释名》考论.通过各种考证认为“刘熙字成国,青州北海人,曾避乱交州(今两广一带),生活在汉灵帝至献帝年间,是当时名儒,可能曾受征辟而不就,故号为‘征士’,确是今所传《释名》一书的作者”(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相对全面而可信的。之语,北海国(今山东昌乐县一带)在东汉时属青州,《世说新语·言语》注引伏滔《滔集》亦曰:“后汉时……刘成国……青士有才德者也”[1](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上册)·言语(第二).余嘉锡著作集.中华书局,2007.(P157)。而且,从当时流寓到交州的其他士人资料来看,他们或多或少均与刘熙有所来往,史载许慈、薛综皆从刘熙学,士燮、程秉亦与之“考论大义”,故刘熙应为汉末中原人士流寓交州之先行者。
《隋书·经籍志》载刘熙著《释名》八卷、《孟子注》七卷、《谥法》三卷,说明其博通数经,当为汉末硕儒。尤其《释名》一书从词语间的语音联系出发,对世间万物的名称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声训学专著,成书后受到学界的广泛推崇,吴国韦曜“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2](晋)陈寿.三国志(卷 65).吴书·韦曜传.中华书局,1982.(P1463)。这样一位精通五经的大儒隐居交州,不问世事,教授子弟,不仅开交州风气先,其弟子又将所学精华传播到蜀、吴等地,对当时学术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许慈。《三国志·许慈传》载“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3](晋)陈寿.三国志(卷 42).蜀书·许慈传.中华书局,1982.(P1022-1023)。
许慈于建安年间与许靖俱入蜀,而其何时入交则不可知。作为蜀汉政权为数不多博通数经的硕儒,许慈在恢复蜀地经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3](P1023)既然许慈能在蜀地重建儒学,那么其在交州之时应当也会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程秉、薛综。《三国志·程秉传》载“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孙)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病卒官。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4](晋)陈寿.三国志(卷 53).吴书·程秉传.中华书局,1982.(P1248)。
《三国志·薛综传》载“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今江苏宿州北)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赤乌)五年,为太子少傅……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5](晋)陈寿.三国志(卷 53).吴书·薛综传.中华书局,1982.(P1250-1254)
程秉、薛综二人经历颇为相近,皆于汉末避乱交州,并与刘熙考论大义,后又前往东吴为官,且均作过太子的老师。历朝历代对太子之师有严格要求,非学识过人、品行高洁者不能为之,程、薛二人能够当此大任,足见其学识之渊博、品德之高尚。由于许慈、程秉和薛综三人后来或入蜀、或至吴,故而他们对交州的影响不如刘熙那样广泛。
4.许靖、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国志·许靖传》载:“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6](晋)陈寿.三国志(卷 38).蜀书·许靖传.中华书局,1982.(P963)。后为尚书郎,董卓秉政时与吏部尚书周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关东兵起,许靖恐卓诛杀,往“依扬州刺史陈祎。祎死,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6](P963-964)。
许靖等人的交州之行并不顺利,他在给曹操的书信中写道:“会稽倾覆,景兴(王朗字)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欧、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6](P964),茫茫无际的汪洋,看不到汉朝的一寸国土,粮食吃完了只好以草充饥,不断有人因为饥饿死去,情形何其悲惨、凄凉,“当时见者莫不叹息”。许靖历尽艰辛来到南海郡(今广东中东部)后,听闻曹操已迎天子都许,他又“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夷、越蜂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元贤被害,老弱并杀。”听到天子安定的消息后,许靖准备取道荆州返回中原,却不想在路途中遭遇盗匪,同行的徐元贤等人惨遭杀害。许靖不得不继续颠沛流离,史载“靖寻循渚岸五千余里,复遇疾疠,伯母殒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侍,前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岂可具陈哉!”[1](晋)陈寿.三国志(卷 38).蜀书·许靖传.中华书局,1982.(P964-965)许靖等人经历几番坎坷凄楚后,终于来到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暂时告别了流亡的生涯。后来,益州的刘璋遣使招许靖,靖遂入蜀,“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1](P966)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许靖在交州的活动情况,但从他雅好人伦的特点来看,“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1](P967),其应该也会对当地的人物进行品评,“沙汰秽浊,显拔幽滞”[1](P963),进而对交州的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与许靖同行的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人未见其具体事迹,无法详察。据王朗写给许靖的书信推测,他们应当是许靖的学生。“往者随军到荆州,见邓子孝、桓元将,粗闻足下动静,云夫子既在益州,执职领郡”[1](P967),邓子孝、桓元将称许靖为夫子,则二人应为许靖弟子,而许靖在书信中将袁沛、徐元贤和邓子孝并称,那么袁、徐二人亦当为受学于许靖。古代学生跟随老师流亡是很常见的现象,孔子周游列国时便有诸多弟子相随,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人共同追随恩师流寓交州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徐元贤在去往荆州的路上被害,邓子孝去了荆州,袁沛不知所踪。袁、邓、徐三人的事迹虽不详,但其作为许靖的学生,当也是修习儒术的士人学子,也对交州的文化普及以及儒学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5.桓晔。桓晔,沛郡龙亢(今安徽蒙城东南)人,《后汉书·桓荣传》载:“晔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37)·桓荣传.注引《东观记》.中华书局,1965.(P1259-1260)
东汉沛郡桓氏世传《欧阳尚书》,家族繁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至卿相,显乎当世”[2](P1261)。桓晔父亲桓鸾“少立操行……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2](P1259)。后征拜为议郎,上陈五事,因为触及宦官们的利益,桓鸾的上表并没有得到重视,“书奏御,牾内竖,故不省。”
桓晔深受父亲影响,特别注重培养志向节操,桓晔的姑姑为司空杨赐的夫人,父亲去世时,姑姑回家赴丧,先在驿站把随从人员安顿妥当后才回家,桓晔很是不满。“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杨赐派遣官吏供奉祠庙,在当地调取祭祀用具,桓晔也不接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忮若此。”[2](P1259)
初平年间,为避战乱,桓晔远赴吴会,危难之时仍不忘修习品性,史载“礹到吴郡,扬州刺史刘繇振给谷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后东适会稽,住止山阴县故鲁相钟离意舍,太守王朗饷给粮食、布帛、牛羊,一无所留……每当危亡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皆肃其行”[2](P1260)。后来,桓晔又“浮海客交阯”,他这种高洁的节操对交州的风俗也产生了影响,越人被他的品性所感动,邻居之间互不争讼,可见其对交州文明程度的提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6.袁忠、桓邵。袁忠,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人,《后汉书·袁安传》载:“忠字正甫,与同郡范滂为友,俱证党事得释……初平中,为沛相,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及天下大乱,忠弃官客会稽上虞。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献帝都许,征为卫尉,未到,卒。”[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45)·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P1526)
汝南袁氏较之沛郡桓氏,在东汉时更为显赫,“自安至宏四世三公,贵倾天下”[1](晋)袁宏.后汉纪(卷 22)·孝桓皇帝纪下.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2002.(P420)。先祖袁良,习《孟氏易》,举为明经;良孙袁安,少传良学,为人威严,治理楚狱,不避权贵,名重朝廷;安子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45)·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P1522);京子袁彭,少传父业,“有清絜之美”;彭弟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2](P1523);汤长子成,左中郎将;次子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优号三老,尊崇无二;逢弟袁隗,少历显官,献帝初,为太傅;成子袁绍、逢子袁术,汉末群雄,割据一方,并重于时。
与袁汤一支的隆盛相比,袁忠所在的袁彭一支则显得冷清许多。袁忠父贺,仅为彭城相;兄长袁闳,“玄静履真,不慕荣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州府辟召,州郡礼命,皆不就”[1](P420)。忠弟袁弘亦“耻其门族贵执,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终于家”[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5)·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1526.关于汝南袁氏,可参看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与兄长、弟弟淡泊名利不同的是,袁忠选择了入仕,并与名列“八顾”的范滂为友,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党锢事发,忠与范滂俱入牢狱。“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 67)·范滂传.中华书局,1965.(P2205)。据此可知,袁忠虽节操亚于宏,但他心系天下的拳拳爱国之情昭然显著。
关于袁忠避难交州的原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5](晋)陈寿.三国志(卷 1).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中华书局,1982.(P55)据此而论,袁忠避难交州是为躲避曹操的迫害。曹操擅杀名士边让,在当时的确引起兖州诸多士人的不满,陈宫、张邈等人更是趁曹操东征徐州之际,迎吕布为兖州牧,郡县皆应。袁忠作为天下名士,又曾得罪过曹操,担心曹操伺机报复,故而远走交趾,以避其锋,倒也符合情理。至于后来说曹操遣使令士燮“尽族之”则未必是事实,鉴于擅杀名士引起的严重后果,曹操随后便调整了对待士人的政策,转敌视为拉拢,且袁忠对己统治已无威胁可言,没有必要赶尽杀绝。《曹瞒传》本为吴人所作,重点突出的就是曹操“酷虐变诈”的个性特征,“难免在其中添加、增饰、虚构,从而折射、投影出一个他(指作者)所需要的曹操”[6]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P146),故而《曹瞒传》的记载不能完全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关于袁忠的死因,笔者认为还应以《袁安传》所述“征辟未至而卒”为是。
桓邵,沛国人,事迹不详,只知其与袁忠俱避难于交州。据桓邵对曹操以及边让事件的态度,我们大约可以推测出他应与袁忠、边让等人同属当世名士,但于学术有无建树则不可知。值得注意的是,桓晔、桓邵俱为沛国人氏似可推测二者同属沛国桓氏,如此则桓邵亦当有家学渊源。根据《曹瞒传》的记载,桓邵到交州后,曹操仍遣使令士燮尽族之,后又云“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5](P55)据此看来,桓邵应该是被曹操当面处死的,与前令士燮尽族之自相矛盾,这也进一步印证该条记载的确存在有不实之处。袁忠、桓邵确有可能因为躲避曹操迫害而避难交州,但曹操应当没有遣使下令士燮尽族之,桓邵何时、因何卒,史书并没有交代,只有暂且存疑。
7.袁徽。袁徽,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西)人,“以儒素称。遭天下乱,避难交州。司徒辟,不至。”[7](晋)陈寿.三国志(卷 11).魏书·袁涣传.中华书局,1982.(P336)据《国三老袁良碑》:“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8](宋)洪适.隶释(卷 6)·隶续·国三老袁良碑.中华书局,1986.(P70)之语,可知陈郡袁氏与汝南袁氏应同出一脉,良生昌、璋,昌生安,璋生滂,滂生涣[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74 下)·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P3164-3165),徽,涣从弟也。
袁徽从兄袁涣虽出身名门,却“躬履清蹈,进退以道”[2](晋)陈寿.三国志(卷 11).魏书·袁涣传.中华书局,1982.(P366)。《三国志·袁涣传》载:“袁涣字曜卿,陈郡扶乐人也。父滂,为汉司徒。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2](P333)。刘备为豫州牧,举涣茂才,后涣为吕布所拘,“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后归曹操,历任梁相、郎中令等职,多有良言进谏,“居官数年卒”。
汉末大乱,袁涣认为一味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能够守节秉义,或许可以安身。“初,天下将乱,涣慨然叹曰:‘汉室陵迟,乱无日矣。苟天下扰攘,逃将安之?若天未丧道,民以义存,唯强而有礼,可以庇身乎!’”[2](P336)
袁徽却不同意兄长的观点,他认为汉室衰微已成定局,即便有匡扶社稷之功,却又不免惹祸上身,为名利所累,倒不如远遁山林,以求免身。“徽曰:‘古人有言,‘知机其神乎’!见机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汉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识,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兴,外患必众,徽将远迹山海,以求免身。’”[3](晋)陈寿.三国志(卷11).魏书·袁涣传.注引袁闳.汉纪.中华书局,1982.336.《后汉纪》作“袁微”,见(晋)袁宏撰.后汉纪(卷29)·孝献皇帝纪.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2002.554.与袁涣投身大义的精神相比,袁徽明哲保身的想法似乎有些自私,但倒也符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理念,我们不能说孰对孰错,人各有志而已,“及乱作,各行其志”。
另外,袁徽的学术成就可从他写给荀彧的书信中略知一二,“交趾士府君(士燮)……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4](晋)陈寿.三国志(卷 49).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1982.(P1191-1192)由此可知,袁徽不仅研习《左传》,而且对《尚书》也有所精研,加之世传《孟氏易》,则其兼通数经明矣。
8.刘巴。《三国志·刘巴传》载“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今湖南邵东东南)人也。少知名,荆州牧刘表连辟,及举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阯”[5](晋)陈寿.三国志(卷 39).蜀书·刘巴传.中华书局,1982.(P980)。
刘巴出身官宦世家,史载“巴祖父曜,苍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6](晋)陈寿.三国志(卷 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1982.(P980),年少知名,游学荆北,时人谓之高士,州牧刘表连辟,不至。后来曹操南征荆州,刘巴前往投靠,被派往招纳荆南三郡,却被刘备隔绝在南,不得已只得远赴交州。
刘巴本不欲前往交州,又与士燮不和,很快他便转投益州。《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云:“巴入交阯,更姓为张。与交阯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杀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杀也。’主簿请自送至州,见益州牧刘璋,璋父焉为巴父祥举孝廉,见巴惊喜,每大事辄以咨访。”[6](P981)
由于刘巴在交州的时间相当短暂,且与士燮不和,故其对交州的影响只能说是微乎其微。刘璋准备遣法正迎刘备入川时,刘巴曾进谏说:“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6](P981)。刘备入川始于建安十六年(211),而其夺取荆南三郡是在建安十四年(209),从刘巴被刘备隔绝归路不得已入交至其前往益州,刘巴在交州停留不过两年左右时间,虽为当世高士,但其影响实在有限,无法与刘熙等人相比。
从流寓交州士人的身份来看,其中刘熙、许慈、程秉、薛综四人均为学识渊博的经师硕儒;桓晔、袁忠、袁徽三人出身名门望族,世传家学;许靖、刘巴、桓邵三人则属知名高士;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人资料不详。
从流寓的原因来看,士人们主要还是为躲避战乱,具体而言,许靖是为躲避董卓诛杀;袁忠、桓邵或为躲避曹操迫害;刘巴则为刘备隔绝;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人为追随夫子许靖;程秉、薛综、桓晔、袁徽四人为避乱;刘熙、许慈二人原因不详。
从流寓的路径来看,士人们大多选择的是海路,如许靖、袁沛、邓子孝、徐元贤、袁忠、桓晔六人皆从会稽郡浮海入交,只有刘巴或从荆南入交,其余六人入交路径不详。
从流寓士人的籍贯层面来考察,我们发现这13人中以豫州最多,有7人。另外,荆州有2人、青州1人(袁沛、邓子孝、徐元贤三人资料不详,无法统计)。具体而言,青州北海国1人;荆州零陵郡1人、南阳郡1人;豫州有陈郡1人、沛郡(国)3人、汝南郡3人(详见下表)。这也与汉末学术人才在全国的分布大致相吻合,“东汉时期,文化重心从西汉时的齐鲁及其周围地区逐渐西移至洛阳周围的南阳、颍川、汝南、河南、陈留一带。”[1]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P88)
从流寓士人的归宿来看,许慈、许靖、刘巴三人入蜀地为官;程秉、薛综往吴国任职;邓子孝转到荆州;徐元贤、桓晔死于交州;袁忠或死于交州,或死于返回中原途中;桓邵或死于交州,或死于许都;刘熙、袁徽、袁沛三人去向不明,很可能一直留在交州。

流寓交州士人籍贯表
三、结语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富庶的中原之地成了哀嚎遍野的废墟,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于是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向边缘地区移民的小高潮,其西如益州、其东如扬州、其南如荆州以及北疆的辽东和南陲的交州都有中原人士的身影。在这股举家迁徙的移民浪潮中,那些深谙礼仪的社会精英们俨然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将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带到各个偏远闭塞之地,对当地的文明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而流寓交州的许靖、刘熙等十三位士人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化精英或出身名门望族、或博通五经、或品行高洁,他们为避战乱,不远万里,举家迁徙,来到交州以后,或授学乡里,或研习学问,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传播开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也使当地的文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相对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来讲,交州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一旦中原稍为安定,他们又都回到中原或扬州、益州等发展程度更高的地方,很少就此定居。故汉末流寓交州之士人虽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影响亦不可估计过高,毕竟他们的停留时间都不长。交州或者越南的真正崛起,实是宋朝陈氏建国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汉魏之际的影响只能说是前奏而已,这点也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