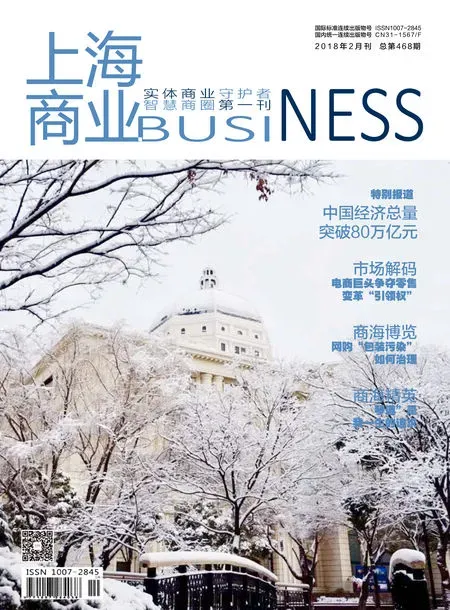“琴道”是我一生的追求
—— 记“幽篁里古琴研发中心”创始人杨致俭
文/吴赛华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2003年,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琴艺术继昆曲之后,第二批入选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上海,有一位古琴演奏家、制作家,他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斫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任上海七弦古琴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专家委员、“幽篁里古琴研发中心”创始人,他就是2017年获得“上海工匠”称号的杨致俭。
结缘古琴 顺其自然
杨致俭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学习琴棋书画。尤其是古琴,师从当代两位古琴泰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南龚北李”,即中国琴会前会长龚一先生和琴会荣誉会长李祥霆教授,深入学习广陵派、虞山派经典曲目和古琴斫制技艺,此外,他师从著名洞箫演奏家、“江南箫王”戴树红教授,潜心钻研琴箫演奏艺术。
“我没有想过会专业从事古琴教育和传播,至少小时候没有想过。”杨致俭直言。在他30岁前,他一直认为,琴棋书画是个人的修养,弹琴给自己听,做琴给自己弹。随着年龄的增长,想多做点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想改变在乎的世界,或至少影响在乎的领域。”杨致俭说,“对艺术家或者学艺术的人来说,学习是一生的,小时候可能学习一些技术性、专业性的知识,长大后更多的是源于对生活、人生的热爱,促使自己不断改变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学什么不重要,不停地学习最重要,最后通过某一技术表现出来才是对琴棋书画最好的表达方式。”四十不惑,就是不再迷惑自己是谁,能成为谁,能做什么,而想明白这些是他35岁以后。
古琴上有七根弦,13个徽,所以它也叫七弦琴,杨致俭出生于7月13日,“我是为琴而生的。”他笑着说。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但一个人能弹琴、做琴、讲琴,又爱艺术、爱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且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年纪正合适,杨致俭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少数人之一。从古琴演奏家到制作家,到从事相关教学工作,杨致俭说这三者对他来说没有切割那么明显,一切都切换得很自如。“当觉得做这些事情的时机到了,也就自然而然去做了。只要觉得当下做这些是最合适的,是喜欢的、不计较任何得失的。”
2005年底,杨致俭创立了“天下古琴”传习中心,2011年成立了上海七弦古琴文化发展基金会,是中国第一个以古琴文化之传承、保护和发展为目的的基金会。2011年,基金会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保护单位。2013年,基金会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制作)保护单位。2014年,杨致俭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斫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些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没有刻意要成为什么。”杨致俭说。
科学量化地看待古琴制作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更严谨,偏理性;音乐偏感性,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现了艺术的高水平。从宏观角度讲,建筑讲究美、对称、和谐与统一,古琴也不例外。”因大学里学过建筑学,杨致俭对建筑与古琴的关系自有一套理论。
任何非遗项目的创新都要尊重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杨致俭认为古琴制作的创新不是任意新造一个造型,而是用科学量化的态度和眼光去看待最传统的古琴制作。比如打磨光滑,什么叫光滑,用几号砂纸,打磨多少次。又如琴面制作,对面板曲率的合理性、平整性有非常高的要求,1米24的长度,要刚好在某个点,正好下凹1.3毫米,木头有一点点变形,就会对演奏产生影响。将数据变成理论,变成实现作品功能的基础和依据,达到质和量的要求。“中国古人留下很多精神和物质财富,包括古琴,但这些能工巧匠没有写一本书教你什么是好的古琴,怎样制作一张传世好琴。”杨致俭结合大学学过的现代材料学、结构学、声学等知识,科学量化地看待古琴制作,通过内在原理实现其外在功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古琴制作领域的数字化研究机构,制定行业规范,将古琴制作的各个环节,全面实现标准化制作。




做琴,杨致俭沿用古人的方法,从头至尾,全部由个人手工完成。一张琴从木材选料、外观造型、槽腹结构、木胚装配、木胚裱布等十多道工序,每一道都很有讲究,制作需要至少两年时间。“制琴很重要一点要学会等待。用时间堆出作品,用等待换出作品。”杨致俭说。为了学习古琴制作,他曾辗转于福州、山西等地学习大漆制作,去日本研究莳绘技艺。“之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天南地北地学习,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从民间、典籍里挖掘出来,以达到古琴的使用价值、音响学效果和工艺要求。”正是这样的追求,杨致俭先后修复了多张唐、宋、元、明等历代名琴,恢复了一千年前的唐代传统制琴工艺,并与师傅李祥霆教授合作,成功研发了“醉琴斋”丝弦。
追求“琴道” 注重传播
古琴不但是一种音乐,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道”。书法有书道,茶有茶道,古琴也有琴道。“所谓‘琴道’,就是学琴、弹琴的人,通过古琴的演奏去了解这个世界。”杨致俭解释道,他的最终追求就是“道”。古琴面圆底平,象征天圆地方。琴长3尺6寸6,象征一年有366天。古琴上有13个用贝壳做的叫‘徽’的圆点,就是音阶,它代表一年有12个月加1个闰月。“由此看出中国古人弹奏古琴的根本目的是跟自然沟通,跟古人对话,琴是弹给自己听的。”
面对非遗传承的难点,杨致俭直言:“古琴制作最难的地方在于把艺术和技术相融合。我之所以琴做得好,因为我弹琴弹得好。枪械的制造者,未必是神枪手,因为社会分工已经很细化了,古琴领域还没有细分到这个程度。我用一个专业演奏家的要求,去指导如何做出一张最顶尖的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艺术和技术兼掌握的人毕竟是少数,是否会影响传承呢?杨致俭不这么认为,“成为大师要符合三个条件,即学术上承上启下,行业内开一代先锋,个人人品成为楷模。每个时代真正的大师是很少的。从传承角度来讲,这一代或下一代只有部分古琴制作技艺被传承,到再下一代可能大师就出现了。量变引起质变,总会有一代出现从事或奉献给琴道的人。”
2017年9月,杨致俭获得“上海工匠”称号。11月,在浦东唐镇成立了上海首个工匠创新工作室(古琴制作技艺)。工作室既是古法制琴工艺的展示,又是一个传习、交流的场所,设有木工房、漆工房、荫房、沉淀房等,重现了一整套复杂的古琴斫制工艺。除了工作室带几个徒弟外,杨致俭注重非遗的社会传播。“天下古琴”传习中心走进上海包玉刚学校、复旦大学、上海大世界等地开展古琴文化讲座;将古琴与书法、昆曲、钢琴相结合,创新古琴艺术传播方式;设计古琴书签、环保袋、文件夹等各种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开放古琴工作室,做一回“木工”,让人们对“匠心”有更深刻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