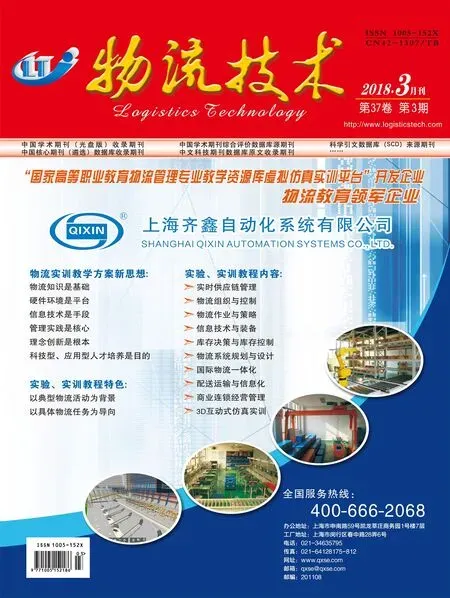芬兰的责任物流发展与启示
李菽林,范毅强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1 引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会后,供给侧改革成为改革政策、建议中的高频词,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供给侧改革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2017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等问题,统筹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全面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和创新被认为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两个根本任务,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有效方式。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行业,不仅受各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还能够支撑、推动、服务产业改革,宏观经济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为物流行业带来了挑战,物流产业的内部结构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例如,2017年二季度,进口货物物流总额6.1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1个百分点,增速的变化反映了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为物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参考。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物流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在拉动和推动的角色中转换。二次大战后,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围绕质量,芬兰先后经历了质量设定、质量保障、质量增长、质量创新四个发展阶段,芬兰的经济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物流发展特征为我国物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2 芬兰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特点及对责任物流的培育
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和德国的引领下,大规模生产在欧洲开始扩散。战争时期长期的物资匮乏,大规模生产迎合了个体在战后对物质的心理需求,随之,社会、经济与科技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改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R M Solow(1956)[2]论述了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生产力之间的函数关系,认为科技的发展不仅推动着产业链的重塑和变革,甚至成为了左右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交融,以及社会、经济对科技的依赖,科学与技术在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职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对物流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有了多方位的要求,传统物流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物流应运而生。芬兰作为北欧多民族国家,包括了芬兰、瑞典、罗马尼亚、萨米、鞑靼族,2017年是芬兰结束沙俄统治宣告独立后的第100年,在这一百年时间里,芬兰从农业、资源(森林,铜、锌、银矿)利用型国家逐步转型为科技、教育强国,特别是1991-1993年和2012-2014年两个时间段内GDP的负增长所映射出的产业改革,以及产业改革过程中围绕质量的四个阶段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物流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与中国强调从提升供给质量推动供给侧改革一样,芬兰的产业转型与质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围绕质量的四个发展阶段可划分为质量设定、质量保障、质量增长以及质量创新。
2.1 质量设定时期
质量设定时期发生在芬兰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邻国、联盟中质量体制的学习、复制和参照。二战结束后,芬兰开始了由农业和资源型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至六十年代,芬兰的工业依然高度依赖着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并不具备优势。虽然在1960年芬兰的人均GDP已经赶超英国和瑞典,但是芬兰并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首批成员国,时至1961年,芬兰才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的准成员国。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由于过度采伐,芬兰高度依赖的森林资源持续减少,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要点,随着六十年代政府限制采伐的政策出台,科技成为社会和政府认可的引领芬兰持续发展的新引擎。1963年芬兰效仿瑞典设立了科技政策委员会,尝试用政策的方式规划、引导科技,协调各级之间的科技活动。1967年,隶属于芬兰央行下的芬兰国家基金成立,负责支持工业项目的研究和发展。1969年,芬兰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准入让芬兰感受到了科技领域上的差距,也为芬兰科学与技术的学习和提升提供了场所。受Brooks在1971年巴黎OECD会议上报告的影响,芬兰中央研究委员会、科技政策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3年制订了科学与技术政策,它可视为芬兰第一部推行科技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方案[3]。科技政策委员会的设立以及科技政策的颁布展现了芬兰对科技的重视,不仅推动、鼓励科学研究,也为芬兰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科技的进步对物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助推了物流服务的发展。
在二战结束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里,芬兰的经济以投资驱动型经济为主,据芬兰统计局数据显示,七十年代芬兰的研究和发展(R&D)投入实现了每年15%以上的增长,即便是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以及1975年-1977年期间接近1%的GDP低速增长时期,芬兰的R&D投入也保持高位增长,其中制造业的R&D投入经费占总投入费用的比例比较稳定,从1971年至1979年一直维持在44%左右,高等教育的R&D投入经费也一直维持在20%左右,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为战后婴儿潮的教育提供了支持,更为以后科技的应用提供了基础和支撑。虽然该时期内并未催生高新技术产业,但在该时间段内,依赖科技政策的推动以及资源、劳动力优势,实现了GDP年平均增长4%以上,高等教育培育出的科技人才也为芬兰的再发展提供了支撑,缩小了芬兰在科技上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质量设定时期的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征非常类似。
2.2 质量保障时期
七十年代后期,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成功为OECD成员国提供了参考,特别是日本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结合方面,大部分OECD成员国开始模仿日本相关的机构设置模式,并着力资助和策划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研究[3]。1983年芬兰国家技术局成立,专注于规划和执行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隔年出台的《芬兰国家技术发展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的13个技术方向,包括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化、陶瓷材料、粉末冶金、金属成型加工、激光技术、基因技术等,其中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研发经费占据了总经费的47%。“1985年9月12日,芬兰政府向议会提出了新的科技政策的工作报告,决定要把今后科技工作的重点放到进一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技研究相结合,以及鼓励企业进行应用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三个方面[4]。到八十年代中期,芬兰大型生产商的信息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例如生产造纸机械的Raute公司,虽然只有1 280名员工,但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已经非常高,1985年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近1亿美元。
在质量保障时期,芬兰的R&D投入依然保持着每年15%以上的增长,但是有关质量的管理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有清晰目标的质量设定时期向质量保障时期转换,该时期的质量保障体现在三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优势工业的科技保障,提倡科技与应用的结合,增强竞争力,如大学与企业签订了价值1.05亿芬兰马克的合同;第二方面体现在对新技术研发投入的保障,并积极促成研发与应用之间的转换;第三方面表现在制度上的保障,除机构的设置、发展计划的实施之外,还从1984年开始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减免税收。八十年代,制造业的R&D投入经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44%左右上升至48%左右,特别是制造业之外的工商业R&D投入经费从1981年的8.4%上升至1989年的13.6%,可见芬兰政府在保障优势领域的同时,大力推动着新技术研发及其应用。八十年代对质量的保障让芬兰的经济从石油危机中恢复,获得了年平均3%的GDP增长,也为芬兰的科技发展培育出了社会基础和知识基础。依据芬兰交通部的统计报告,在质量保障时期,物流成本所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从70年代的近15%提升至80年的近16%,如1990年,物流成本占到GDP比重的近18%,其中运输费用占物流成本中的44%,仓储费用占28%,资金费用占22%,管理成本26%,但是物流周期从70年代的25天左右缩短至80年代的8.5天左右[5]。
2.3 质量增长时期
八十年代关于科学与技术的质量保障培育了芬兰的持续发展,依照芬兰统计局对能源消耗的统计,七十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核能减少了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芬兰1971年的出口额,1990年的出口额增长了2.38倍,可是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出口额一直维持在低位[6]。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传统制造业和工业的衰落,以及非劳动力人口增加后为社会福利带来的压力,芬兰经济开始衰退,特别是作为芬兰主要贸易国苏联的解体和德国马克的升值对芬兰的经济影响巨大,1991年至1993年芬兰的GDP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直到1994年经济才逐渐开始复苏。
在经济的衰退和复苏时期,芬兰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采取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增长方式,整个九十年代,R&D投入依然保持了年15%的增长,高新技术进口占技术总进口量的比例也实现了年平均6.7%的增长(见表1),电子领域的专利应用数实现了年平均50%的增长,从1990年的228,增长到了1998年的659。在1990年GSM规范说明的完成和1991年GSM系统开通的契机下,芬兰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例如,九十年代初诺基亚公司便开始了转型,剥离了造纸、橡胶、电缆等传统业务,向计算机、电子消费品、通讯产品业务转型。在保证研发投入,利用高新技术推动产业改革的基础上,芬兰政府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保证高校前沿科研经费的同时,在九十年代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做出了巨大革新,开始了从职业教育向技术教育的转型,如1991年《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法》颁布,1995年《多科技术学院法》颁布,2003年和2005年对《多科技术学院法》的修订,为多科技术学院增加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技术应用型大学的设立为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基础,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表1 1991-2005年芬兰高新区技术出口与进口占技术总出口量与进口量的比较
2.4 质量创新时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依据芬兰交通局的统计,芬兰生产和贸易公司的物流相关花费与公司的营收额比持续增长,特别是交通运输费用保持高位增长,从2000年的4.5%增长到2008年的6.3%,到2008年时,与物流相关的总花费已达到生产和贸易公司营收额的14.3%[7]。2000年之后,芬兰制造业所占R&D投入的比例持续增长,在2008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59.1%,相反高等教育的R&D投入比例却持续走低,2008年时只占据了总R&D投入的17%,依据芬兰统计局的创新活动发生率(Prevalence of innovation activity)数据,2000年至2008年,在制造业R&D投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未能激发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仅制造业产品的创新活动发生率并未增长,还发生了接近年千分之6的下浮,在人数为10至49,50至249,250以上的三种规模的制造业公司里,中型(人数50至249)公司的过程创新和创新活动仅为小型(10至49人)公司的1.3倍不到,并且在2000年至2008年里,优势逐渐缩小。依据芬兰产品创新数据显示,大型(人数250以上)公司在2000年投放的创新型新产品占大型公司产品总量的28%,可是该数据在2004年下滑至20.2%[9]。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第三代通讯技术的应用,芬兰逐渐丧失了在通讯技术上的统治地位,相关产品的出口也大幅下降,显而易见,高增长的制造业R&D投入并未保证技术上的优势,也并未孕育出适合创新和研究的环境,甚至阻碍了创新的自由发展。在缺乏特定的参照目标后,创新成为了支撑增长的唯一途径,过分强调制造业的研发,增加制造业的R&D投入并不能快速地实现创新任务,也让研发人员过分的注重创新活动和创新产品,却忽视了创新过程。依据芬兰产品创新数据显示,2000年小型(10至49人)公司强调创新过程的创新活动发生率只有24.5%,中型(人数50至249)公司为28.2%,大型(人数250以上)公司为58.7%[10]。虽然2004年后,创新过程的发生率逐步得到提升,可是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和创新研究的源头,相关的R&D投入却持续减少,投入比例从2004年的19.7%下降至2008年的17%。从2009年起,芬兰R&D投入的偏重开始发生变化,更加注重均衡发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便一直持续增长的制造业R&D经费比例,从2008年的59.1%下降至2015年的44.7%,高等教育机构所占R&D经费的比例从2008年的17%提升至2015年的24%,而且从注重单一领域的提升向注重多领域协同发展转移,制造业之外的其它工商业所获得的R&D经费比例由2009年的14%提升至2015年的22%。
3 质量创新时期芬兰责任物流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对芬兰质量创新时期宏观经济的数据分析能够清楚获悉,发展是需要阶梯、需要步骤的,质量设定、质量保障、质量增长时期为芬兰的质量创新时期提供了支持,实现了各方位的均衡,为质量创新时期提供了协同发展的可能。协同发展是质量创新时期展现出的重要特征,在该时期,质量增长时期中的优势企业、优势产业不再凸显,甚至有的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在这种局面下,其它工商业获得了政府更多的关注。从R&D研发费用的分配和芬兰产业结构转型中能够清晰可见,在质量创新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对物流服务需求的变化,让芬兰物流行业迎来了挑战和机遇,2011年至2013年,芬兰物流成本的构成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相应的物流服务效率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11]。2011年至2013年,物流运输费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可是物流的仓储费、库存管理费出现了巨大的上升,可见在质量创新时期,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过剩成为了很多企业的症结,企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发生明显的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提升物流服务的效率成为芬兰物流公司在质量创新时期的难题,也孕育了芬兰物流发展的新方向。
基于芬兰的地理和环境因素、经济转型特征、欧盟对碳排放的要求以及欧盟对逆向物流的要求(如欧盟规定2020年废旧易拉罐回收率必须在80%以上,依据欧洲铝业协会统计,2012年芬兰废旧易拉罐回收率已超过97%),芬兰的物流业需要在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的基础上可持续性的发展物流,甚至还要利用物流业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监督、控制产业的发展,在质量创新时期,芬兰的物流展现了创新、协同和责任三个特征。
3.1 数据创新
短短70年,芬兰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科技强国,在苏联解体、能源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围绕质量,芬兰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转型。质量创新是芬兰成功的秘诀,甚至这种创新式的质量文化已经融入了芬兰的教育、社会和文化之中。在物流创新方面,数据平台的创新是最为明显的。2000年时,一个物流系统内部的各物流点都只能查阅自己的相关数据[12]。近年来,物流数据的全面性、快速性、完整性为芬兰物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支持,不仅包括了芬兰交通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物流方面提供了详尽的数据支持,还包括专业的数据公司(如Cusham&Waklefield、KTI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公开发布与物流相关的数据(不止包括了宏观数据,还包括非常多的微观数据,如芬兰各地区的仓储空置率等),物流数据的发布为物流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指向,更为物流研究提供了支持,各种完整、快速的数据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为芬兰物流业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3.2 协同
协同是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只依据第一、第二产业的需求提供物流服务,不仅不会使企业加速转型,而且会减缓整个宏观经济转型的速度,只有在真实的数据、创新发展趋势指引下,才能让物流服务把握准确的方向。近年来,芬兰的协同不仅表现在区域集中和公司集中后所触发的协同活动,更强调区域内知识、教育、技术、公司、基础设施之间的协同[13]。区域内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公司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物流服务的格局。全面、快速、完整的数据推动了芬兰物流业的协同性发展,虽然,在地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芬兰物流业同样存在分布不均的现象,依据芬兰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芬兰乌西马地区的物流业占到了全国的28%,可是全芬兰的仓储空置率差距非常小,赫尔辛基都市区的空置率为6.2%,于韦斯屈莱地区为2.3%。此外,随着国家政策向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倾斜,芬兰物流业的业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物流服务的业务量逐步增多,这不仅为很多起步阶段的小型企业提供了方便,也缓解了大型公司因为经济转型增长的库存压力。
3.3 责任
芬兰一直非常重视碳排放量问题,自2003年开始,就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有着严格的控制,依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芬兰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低于1985年的排放总量[14]。在长时间的要求下,芬兰物流业已经将该要求转换成了一种责任,并将这种责任转化为一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在欧盟国家中,芬兰的人口密度最低,而且离欧洲中心的平均距离为2 000km左右,人口大多集中在芬兰的南部,这都为物流服务增添了难度。在二氧化碳排放、反向物流的要求下,面对人口分布不均所造成的物流服务需求不均,芬兰物流不能随意根据个体的需求去扩大物流服务范围,而是在服务效率、服务范围、服务成本、服务责任等方面调整。围绕公路运输,芬兰相关的负责任发展策略主要有:
(1)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人口分布的不均,因此按照人口密度将区域分成了五类,制定相关策略;
(2)从税收和商业的设置上改变个体的消费习惯。利用税收严格控制、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在商业设置上,增加市区的便利店、零售店,减少郊区、城市周围大型商场的开设,大大减小了个体购物的路程,减少了个体购物过程中对汽车的依赖;
(3)提升分销汽车的效率。优化公路法,允许更大运输能力的车辆上路,最大化的使用运输车辆的功效,例如,发展双向物流及路线优化,提升运输车辆的运输能力,例如,34m长的节能卡车已在芬兰大量投入使用;
(4)在非优势区域发展工业,降低分销成本,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限制物流费用在生产附加值中的占比。芬兰大部分工业都是出口型,发展地方市场,能够减小对外部的依赖,地方市场因为辐射范围更小,有利于物流服务的优化,而且细分市场后的产品更贴合区域内个体的需求。
4 经济转型时期芬兰责任物流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对外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倡导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经济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已成为培育我国新优势的主要发展方向。纵观全球,依据康奈尔大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指标》所示,2008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都大幅减少了R&D投入,虽然在2010年,R&D投入有过短暂的恢复性提升,但在2010年至2015年的5年时间里,R&D投入持续减少,并且极有可能在今后的长时间内维持低位。在研究经费减少,研究人员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全球进入了创新发展时期,一时间,创新中心、科创中心、智库在政策的支持下飞速发展。面对经济增长方向的不确定性,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之间不仅需要深度具身融合,更需要负责任发展。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在创新发展期,芬兰物流业选择的创新、协同与责任的发展之路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从芬兰的几个发展时期来看,自二十世纪开始,科技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科技的发展主导着经济的变革,科技的质量直接反映经济的竞争力。芬兰对科技的投入和指引从四个时期映射出了科技质量的变化和要求,虽然通过质量的设定、质量的保障能够快速弥补科技上的差距,也能催生出领域内部的质量增长,可是单一领域内科技的快速增长并不利于科技质量的长期增长,并不能培育出推动长期增长的创新环境。在质量创新时期,不需要政府政策的直接干预,更注重教育、信息、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环境的持续改善[16]。从芬兰转型期的经验来看,只注重制造业的R&D投入和产品的创新并不能持续激发出高质量的创新发展,不能培育出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创新、协同、责任同样需要足够的重视。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对环境、诚信、可持续性发展越来越重视,负责任式的高质量发展会成为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芬兰物流业在质量创新时期展现出的创新、协同、责任特征,在创新基础条件、创新过程和创新管理模式三个方面为我国的物流发展提供了启示。创新基础条件方面,科技、基础设施、信息化水平是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在质量设定、质量保障、质量增长时期,芬兰实现了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赶超,可是信息化水平是质量创新时期的关键,芬兰对物流行业各种数据的搜集和比较为我国的物流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我国的物流协会、商会和为物流服务的第四方物流提出了要求,只有全面、快速、完整的数据才能够为物流服务的发展提供指引;创新过程方面,与质量保障时期推行的质量管理不同,例如,日本从六十年代从美国引进了质量管理小组,日本垄断资本认为,以往的经营管理是侧重于赋予职工正确的工作方法,而质量管理小组则侧重于赋予职工正确的工作动机[17]。质量管理小组的设立,弥补了顶层、中层,甚至各部门之间对质量理解和认识的鸿沟,小组不止专注于保证质量,将质量与生产、服务相融合,甚至最终实现保障质量、提升质量的效果。创新过程更注重协同能力,基础设施、科技、信息化、教育、企业文化、发展策略等,每一项都是发展的重要环节,任何一处短板都会造成协同的失效,服务质量的下降。创新管理是对决策层在成本、业务、服务质量等层面之外负责任的发展,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生命线,纯粹以利润、市场份额为目标的发展,势必会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在利润、市场份额与责任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5 结语
围绕质量,芬兰的发展展现出了四个发展范式。在现今全球创新时代,科技水平的差异已日益缩小,而且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芬兰创新发展时期的物流发展特征为我国物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物流与个人工作、生活的融合,物流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行业的发展问题,已经逐步转换为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物流活动的社会化也推动着物流企业、行业的责任化,单纯的依赖质量管理程序和科技带来的发展,虽然获得了高额的利润,扩大了市场份额,可是相应的环境、生态问题接踵而至,例如,在个体需求的驱动下,第三方物流发展空前,可是相应的反向物流发展并未跟上,这无疑为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埋下了隐患。负责任的发展是创新管理模式下的管理技术,由上而下地建立负责任发展的创新质量管理文化,使质量、成本、利润、责任成为创新发展中的四条并行准则,才能推进我国物流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权威人士再论当前经济形势,阐释如何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6-01-04.
[2]RM 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9-81.
[3]T Lemola.Convergenc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the case of Finland[J].Research Policy,2002,31(8-9):1 481-1 490.
[4]李凡.芬兰科技政策动向[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86,(6).
[5]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Finland.Finland State of Logistics 2006[EB/OL].https://www.lvm.fi/documents/20181/819315/Julkaisuja+45_2006.pdf/41603e16-f2d3-4823-bba6-407148a7401d?version=1.0,2017-10-20.
[6]Statistics Finland.Energy consumption[EB/OL].http://www.findikaattori.fi/en/25,2017-03-23.
[7]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Finland.Finland State of Logistics 2014[EB/OL].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9978218.pdf.
[8]Statistics Finland.Prevalence of innovation activity by size category of personnel and industry[EB/OL].http://pxnet2.stat.fi/PXWeb/pxweb/en/StatFin/StatFin__ttt__inn/010_inn_tau_010.px/table/tableViewLayout1/?rxid=3072525f-7920-4080-a819-e88bfe0ef60f,2017-03-23.
[9]Statistics Finland.Proportions of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unchanged products of turnover by size category of personnel and industry 2000-2014 by Group,Industry,Year,Size category of personnel and Contents[EB/OL].http://pxnet2.stat.fi/PXWeb/pxweb/en/StatFin/StatFin__ttt__inn/060_inn_tau_060.px/table/tableViewLayout1/?rxid=3072525f-7920-4080-a819-e88bfe0ef60f,2016-02-06.
[10]Statistics Finland.Proportions of product innovations and unchanged products of turnover by size category of personnel and industry 2000-2014 by Group,Industry,Year,Size category of personnel and Contents[EB/OL].http://pxnet2.stat.fi/PXWeb/pxweb/en/StatFin/StatFin__ttt__inn/060_inn_tau_060.px/table/tableViewLayout1/?rxid=3072525f-7920-4080-a819-e88bfe0ef60f,2016-02-06.
[11]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Finland.Finland State of Logistics 2014[EB/OL].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9978218.pdf.2014:13.
[12]Simchi-Levi,Kaminsky,Simchi-Levi.Designing and 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M].Boston:Irwin McGraw-Hill Published,2000.
[13]T Makkonen,T Inkinen.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Finland[J].Fennia,2015,193(1):134-137.
[14]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CO2emissions(kt)[EB/OL].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contextual=emissions-by-gas&locations=FI&order=wbapi_data_value_2007+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desc.2017.
[15]熊鸿儒.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J].学习与探索,2015,(9).
[16]张锁柱.增强日本企业活力的“质量管理小组”[J].日本问题研究,1992,(3):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