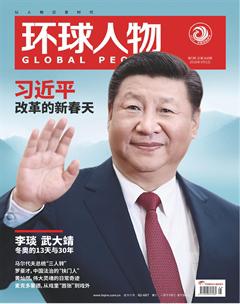黄灿然 伟大灵魂的日常奇迹
陈娟
黄灿然
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集《我的灵魂》《奇迹集》等。主要译著有《小于一》《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和希尼的《开垦地:詩选1966—1996》。

2018年2月5日,黄灿然在深圳洞背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黄灿然的这个春节是在奔波中度过的。除夕之夜,为陪伴女友,他留在深圳洞背村,和几个友邻到诗人孙文波家中吃年夜饭,守岁迎新。第二日一大早,他赶回香港,与亲人团聚。因母亲生病,他连续几日都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
洞背村的春节格外安静,正在建设的大楼停止施工,外来务工的人大都回乡。留下来的,要么是村民,要么是像黄灿然这样“定居”此地的外来户,“好似又回到我刚来时的样子,干净而安静,能听清鸟叫声。唯一不同的是,村口起了几栋高楼,灰秃秃的。”黄灿然说,“但能身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对于诗人来说也很难得。”
4年前,黄灿然第一次来到洞背村。当时高楼的所在地还是两个小山头,从山谷间往前看是一片海,晴时蓝阴时灰,偶有货船开来。几个月后,他便辞去香港《大公报》的工作,搬到洞背村,租了一个三居室住了下来。之后的日子, “村民”黄灿然一直默默地做着两件事:一边专注于翻译诗集和文学评论,将布罗茨基(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阿巴斯(伊朗著名导演、诗人)、希尼(爱尔兰诗人)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一边把细微的日常写成诗。

年轻的黄灿然在香港。他当时在《大公报》工作,常常利用闲余时间翻译和写诗。(摄于1992年)
从香港到洞背村
采访黄灿然那天,正赶上大风。他下楼来接,裹得很严实,黑衣黑帽黑鞋,甚至还有一个自制的黑绑腿,“因为怕冷,最近脊椎又有了问题。”他家在五楼,从客厅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角小小的海平面。地上、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一个书架靠墙而立,一壁的书,大都是外文的。我们围着电磁炉取暖,他背窗而坐,点燃一支烟,“喝完咖啡,我们下山去喝下午茶。”
山下葵涌(音同冲)镇上的茶餐厅,是黄灿然常去的地方——搬离香港时,他唯一怀念的就是茶餐厅。至今再忆当年旧事,他仍觉得自己是被老天“安排”到洞背村的。
2013年,在《大公报》工作的第二十三个年头,黄灿然和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卖掉房子分了家产之后,他和女儿黄钟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一个月开销很大,房租1万港元,抽烟花去2000港元。我一个月工资也就2万港元,还要上夜班。有时入不敷出,就想着离职。”
第二年初,黄灿然到深圳与诗人陈东东相聚。有朋友提议到海边的一个村子看看,于是一帮诗友,包括黄灿然、陈东东、孙文波、凌越等,浩浩荡荡开到洞背村,“村子不似其他农村,倒像是一个社区,安静、干净,当时就有了住下来的念头”。
回香港后,他决定辞职。到2014年6月份,算是在洞背安顿下来。洞背是深圳葵涌下的一座小山村,整个村子不大,仅数十户人家。黄灿然对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他生于乡村,离福建泉州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按当时的称呼叫“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那里四面环山,“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外面的世界就意味着下面的世界。”1978年,全家移居香港和祖母团聚。那一年,黄灿然15岁。

黄灿然在洞背村山下的葵涌镇街头。他很喜欢到镇上的茶餐厅喝下午茶。
他是在睡梦中抵达香港的。彼时香港制造业正红火,工人供不应求,黄灿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了一名制衣厂工人。上班第一年,他住在马路边的铁皮屋里,好多人挤一间,连像样的床都没有。上午10点开工,下班时间不定,有时会熬通宵,“给牛仔衣打枣,就是钉扣子,不难,一学就会。”
流水线的工作,枯燥而沉闷。但在香港,黄灿然接触到了文艺电影、新文学,进而接触到外国文学。在各种文艺形式中,他偏爱外国文学,尤其爱叶芝和加缪。读的越多,思考就越多,受加缪等人影响,他开始思考: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越想越觉得无意义、荒谬,也试图反抗,但怀疑反抗也是浪费。”黄灿然说,那时的他和很多青年一样,孤独而茫然。后来在舅舅的建议下准备考大学,读夜校、学英语;26岁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上世纪90年代初,入职香港《大公报》,每日翻译国际新闻,二十多年如一日。
“现在像是兜了一个圈回来。”他笑着说。他开始重新关注乡村里曾经熟悉的一切,比如臭屁虫何时产卵,壁虎藏在哪个角落,如何让脾气不好的土狗停止狂吠,辨认山中的植物叫什么名字……这些都一一被黄灿然写入诗中,成为《洞背集》的一个篇章。
黄灿然渐渐发现,自己好像是在和诗谈恋爱,以前总是追它、讨好它,现在不为所动,只需静静地等待,诗会自己找上门来。
把日常的奇迹写成诗
黄灿然在洞背村过着简单安静的生活,很少参与文艺圈内的活动,除了诗歌朗诵会。但实际上,他拥有一批与整个诗歌及翻译圈的冷清氛围不相称的热情拥趸, 诗歌节上,众多诗人齐聚一堂,大家总爱开黄灿然的玩笑,羡慕他招读者喜欢。
今年1月,他来了一趟北京。单向街书店将“年度致敬奖”颁给他,还为他的诗集《奇迹集》再版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是“世界全是诗”。

从上到下依次是:黄灿然的个人诗集《奇迹集》和最新译著《一只狼在放哨 阿巴斯诗集》。
朗诵会那一晚,台下聚了很多人,站着的人群一直蜿蜒到场子外的书架之间,每个人都可以上台朗诵一首诗。诗人蓝蓝是黄灿然的朋友,她读完其中的一首《城市之神》后说:“他(黄灿然)有一种崭新的目光,在最普通人中间、最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奇迹。”
《奇迹集》收录的诗写于2006—2009年。当时黄灿然还在《大公报》上班,工作间隙,他会到报社附近的茶餐厅喝下午茶,观察周边的一切。2006年夏,黄灿然一口气写了八九十首。最初他只复印装订了10多本,在朋友间传阅。
3年后,恰逢民间刊物《新诗》的编辑蒋浩约稿,他又加了一些新写的诗交出,以《新诗·奇迹集》的专刊形式出版,主要是在淘宝上出售,半年后即重印,深受读者喜爱。《奇迹集》真正公开出版是在2012年,2018年1月再版时又增添了几十首集外诗,也都写于那一时期。
在《奇迹集》里,黄灿然揭示的“日常的奇迹”比比皆是。比如《微光》,写凌晨两点时,看见两个年轻人在长凳上促膝谈心,“他们正不自觉地领受着贫穷馈赠的幸福”,也“正创造着将来要领受的美好回忆”。在《裁缝店》,看到一个老人独自在熨衣服,他又写道:“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如今回看,黄灿然觉得“那是自己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 。
《奇迹集》的写作不同于之前,改变源自一场大病,持续有10年之久。那时走在路上,他会突然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恐高症也加剧,去医院却检查不出确切病因。最严重的一次,他站在家里,感到灵魂出窍,往楼外飞去,“但意识告诉我要自救,身体使劲往后仰,几乎贴在地板上。”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名字叫《来自黑暗》。说到这儿,他拿出手机翻出那首诗,轻轻地读了起来:我来自黑暗、郁闷和疾病/不是我如今享受到黎明的黑暗,也不是到郊外散散心/就能消除的郁闷,或吃了药/休息几天就痊愈的疾病/对生活在光明中、欢愉中/和健康中的人们,我的向往/是无保留的,我走在他们中间/经过他们身边,坐在他们对面/欣赏他们,内心赞美他们……
病好之后,黄灿然整个人都彻底变了。
“从消极变得积极,也从探索自我内心开始向外延展,将目光放在外部世界的一切上。”另一个改变是,他开始注意身体,并总结出了一套可能只适用于自己的养生法则,像是吃牛排、喝热水,夏天也穿着厚毛袜。直到现在,他还常常把自己的“养生经”灌输给所有他关心的人。
翻译,为别人服务
在洞背村邻居、村民以及朋友的眼中,黄灿然是一个生活规律的人。写诗之外,他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翻译。“他为自己建了一个翻译日程表,每天的工作量都按计划来。即便有朋友过来,他也会腾出时间工作。”孙文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比黄灿然早半年定居于此,两人是故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就因为写诗相识。
两人也经常相约一起走山(山中徒步),哪条路好走,哪条路风景最美,黄灿然都摸得清清楚楚。 “有时我们也会下山到海滩,坐坐、逛逛、打打望,经常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孙文波说。
在这种简单而自律的生活下,黄灿然收获颇丰。2014年,他翻译的布罗茨基最重要的随笔集《小于一》出版,被誉为“完美之书”,上市两个月重印5次,在年底更是横扫各大“年度好书榜”。2017年,几又成为黄灿然的爆发年,他翻译的《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希尼三十年文选》和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陆续出版。
“在诗人和翻译家这两个身份之间,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可以闲着,一年到头只生产那么一点点;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黄灿然说,他称翻译是“衣食父母”——这是他从未预料到的。刚到香港时,他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只懂得一个英文单词“peasant(农民)”。后来为考大学,他读夜校学英语,等到被《大公报》录用,才真正以此为生。
在《大公报》,黄灿然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日复一日,常常身心俱疲。有一日,他站在阳台上思考,觉得活著实在太累,“但安逸对我也毫无吸引力,既然这样,那么我何不多做翻译,把下半生用来服务别人?”有了这个方向,黄灿然下班之后继续挑灯到天亮,翻译一些诗或文论。
当时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新闻署在金钟设有一个图书馆,距黄灿然的住处不远,坐电车只需十来分钟。他就天天往那里跑,读书、看杂志、复印英文资料,有时也从书店买英文书。遇到喜欢的,他就翻译出来,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就这样一直译了20多年,每天译几百字,苏珊·桑塔格、里尔克到米沃什(美籍波兰诗人)、布罗茨基、库切(南非小说家)等,这些世界文学史有名的知识分子和诗人,都和他的名字有了联系。
“他很会选择翻译的对象,能找到真正优秀的诗人与文字。”诗人凌越是他译著的忠实读者,每出版一本就买一本。很多年后,黄灿然到台湾拜访作家林贤治,在他家中发现一本《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是自己1999年出版的译文集,书边都翻烂了,“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白翻译,还是影响了一些人的。”
靠着微薄的翻译稿费,黄灿然一直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有时稿费不到位,还需要朋友救济或卖书,但他本人乐在其中,从未想过改变。“黄老师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很多人自惭形秽的样本:原来我们可以这样自足而奉献地度过一生。”刘宽说。前些日子,他到洞背村跟了黄灿然3天,拍摄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用镜头记录黄灿然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他在一个看似狭窄的世界里,过着一种如何真正的开阔的生活。
4年前,黄灿然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每日发布自己的创作、翻译及评论,推荐他欣赏的经典作品和好诗文。公众号的欢迎词上写有三条,其中一条是一段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诗人)的文字:睡得少,又在醒来的全部时间里努力工作,然后承认整件事情是一个笑话——此中含有一种真正的精神严肃性。
黄灿然很看重这段话,“你很认真地工作,觉得它根本没意义,但你做,是个笑话,你还是继续做。我就是这样的。”很显然,他所做的不是笑话,比如翻译,他很早就确定是要用它来服务别人的。至于写诗,他在诗里写过,“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