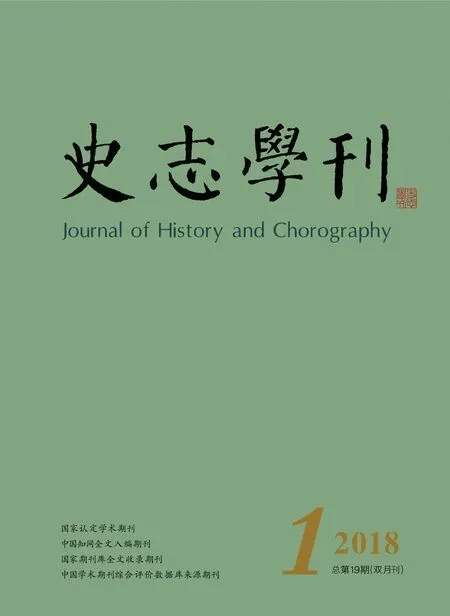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史略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近年来,方志学学科的建设备受关注,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1]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J].广西地方志,2013,(2).(P4)而充分、成熟的方志史研究是构建完整学科体系的必备要素。梅森《中国方志史的研究方法及思路》指出:“背景、节点法是史学研究的必要方法,节点,就是历史阶段。”[2]梅森.中国方志史的研究方法及思路[J].中国地方志,2015,(6).(P8)魏晋隋唐方志处于中国方志发展史的初级阶段,李绍钦、文成章《从方志源流看史志关系》(1982)称“魏晋至隋唐为方志的创建期”[3]李绍钦,文成章.从方志源流勘史志关系[J].中国地方史志,1982,(5).,黄苇《方志学》(1993)称“魏晋隋唐方志出现雏形”[4]黄苇.方志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P88-212),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方志)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5]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P1)魏晋隋唐方志的兴起和发展对后世方志的定型、完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1935)指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会要会典等书固无论矣,即现存之档案,传志,金石文字,以及诗文集,笔记等类,已莫不有人搜罗,条分件系作精密之研究。独于方志则仍多屏而弗采,采而弗详。”[6]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A].李泽主.朱士嘉方志文集[C].燕山出版社,1991.(P1)因此这部分文献的利用为魏晋隋唐正史研究、方言研究、文学地理研究及自然、社会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古代的整理与研究
(一)方志辑佚
方志辑佚可追溯至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其中涵芬楼一百卷本《说郛》辑有魏晋隋唐方志四十种,但该书经明人窜改,已“非宗仪之旧矣”[1](清)永瑢等撰.傅卜棠点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P510)。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辑晋陆翙《邺中记》等魏晋隋唐方志五种,董斯张辑刘宋山谦之《吴兴记》一卷,由此开方志辑佚之风。
清代,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汉唐地理书一百八十五种,今中华书局仅刊印七十种,其中魏晋隋唐方志十四种。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辑魏晋隋唐方志四种,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魏晋隋唐湖南地区方志六十六种,这些均是学界目前利用较多的辑佚著作。
此外,张澍《二酉堂丛书》辑《凉州记》等魏晋方志五种;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辑《三齐略记》等魏晋方志九种;杜文澜《曼陀罗华阁丛书》辑《会稽记》等魏晋方志六种;孙诒让辑《永嘉郡记》、严可均辑《南越志》《阳羡风土记》、洪颐煊辑《临海记》、曾钊辑《交州记》、劳格辑《钱塘记》、缪荃孙辑《吴兴记》、曹元忠辑《荆州记》等。虽属断简残编,但零圭断璧,弥足珍贵。
(二)方志提要
综上,古代魏晋隋唐方志的整理研究以清代成果最为突出,虽然研究角度与形式相对单一,但几部较系统的辑佚成果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民国时期的整理与研究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东方杂志》,1924)首次提出“方志学”概念,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研究走向了新的层面。这一时期魏晋隋唐方志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方志目录
魏晋隋唐方志散佚严重,系统考证存目者,首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禹贡》,1935—1936)[3]1935-1936年,《禹贡》第4卷3、4、5、7、9期及第5卷1期连载了张国淦《中国地方志考》,后经作者整理,改题《中国古方志考》,1962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仿朱彝尊《经义考》体例,对秦汉至元代方志(其中魏晋隋唐方志三百种)凡有名可稽者进行考证。除摘录和归纳旧著的分析及论断外,还间抒己见附于案语中。《中国古方志考》不仅为考录性方志目录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也为后代学者研究宋以前方志提供了极大参考。但该书著录范围过广,“凡古代所谓郡国之书及属于方志之一体者,并加收录”[4]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M].中华书局,1963.,因此也将不少总志、专志收录在内。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区域性方志考录体目录,张维《陇右方志录》[5]1932年《陇右方志录》首次刊印于兰州,后经标点题名为《甘宁青方志考》(上、下).新西北月刊,1940,(第3卷第3、4期).(1932)及《陇右方志录补》(北平大学书局铅印本,1934)收今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志书,其中魏晋隋唐方志共七种。以时代为序,详考志书撰人、纂修年代、卷次、存佚等情况,并详录内容纲领,叙述纂修源流,是我国较早的区域性方志目录。他如萨士武《福建方志考略》(乌山图书馆排印本,1935)、童振藻《云南方志考》(杭州图书馆整理本,1936)、庄为玑《泉州方志考》(《厦门大学学报》,1936)等,但涉及魏晋隋唐方志甚少。
域外学者对魏晋隋唐方志也有所研究,(日本)青山定雄撰《六朝之地记》(颐安译,《中和》1943,2-5)系列文章,其中第2期是对六朝方志撰者、体裁与内容的介绍,3至5期对百余种六朝方志的著录情况进行细致考证,推阐精详,极为赅洽。
(二)方志辑佚
民国时期辑佚成果较零散,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绍兴刊行木刻版,1915)辑录方志四种,包括《会稽土地记》《会稽地志》及两种《会稽记》;叶昌炽《毄淡庐丛稿》(民国稿本)辑《徐州记》《寿阳记》等魏晋方志十五种。他如陈蜚声辑《齐地记》(《十笏园丛刊》潍县海岱文社,1920)、冯国瑞辑《秦州记》(《说文月刊》,1944)等。
此外,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1]张国淦先生此项工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开始,遗稿直至2004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辑录了《永乐大典》中的方志佚文,其中魏晋隋唐时期方志二十种,对了解该时期方志有极大价值。
(三)方志整理
魏晋隋唐方志的整理主要围绕敦煌方志写卷及《华阳国志》展开。
1.方志写卷整理。
敦煌写卷的研究在民国大热,国内外学者相继投身西陲地方志的整理与考校中,讨论对象主要有五种文献(研究成果已有译名者采用译名,无译名者用外文原名)。
(1)《沙州伊州地志》(S367)的研究。如(法国)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亚洲报》,1916)、(英国)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21)、(英国)翟理斯《A Chinese Geograghical Text ofthe Ninthcentury》(《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1932)、(日本)羽田亨《唐光启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弘文堂,1929)等。
(2)《寿昌县地境》(王目[2]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商务印书馆,1962.1700)的研究。如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图书季刊》,1944)、(日本)森鹿三《关于新出敦煌石室遗书——尤其是〈寿昌县地境〉》(《东洋史研究》,1948)等。
(3)《敦煌录》(S5448)的研究。如(英国)翟理斯《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等。
(4)《沙州志》(S788v)的研究。如(英国)翟理斯《敦煌发现的一件地志残卷》(《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1934)等。
(5)《沙州都督府图经》(P5034)的研究。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北平图书馆刊印,1936)等。
2.《华阳国志》考校。
《华阳国志》是魏晋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性方志。朱士嘉《〈华阳国志〉版本考略》(《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4)对《华阳国志》十九种版本的源流和传承关系做了详细论述,是首篇系统研究《华阳国志》版本的专文。他如姚师濂《〈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禹贡》,1934)、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成于抗战时,收入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53年)。
综上,民国时期方志辑佚成果虽相对零散,但方志考录体目录及方志的考校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经典论著。敦煌方志写卷研究也在民国兴起,为后世形成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整理与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由于缺少修志实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方志研究力度大减,魏晋隋唐方志研究更显沉寂,成果缺乏系统性。
1.方志目录与方志辑佚。
该时期方志目录及方志辑佚均属断域研究,尚未见到全国性的整理成果。代表性的如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科学出版社,1958)对浙江地区方志进行编目考证,其中魏晋隋唐时期方志十六种。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辑录魏晋隋唐方志七种。
域外成果有(日本)新美宽编、铃木隆一补《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正/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该书辑有魏晋隋唐方志如东晋喻归《西河记》等。
2.方志写卷专题研究。
敦煌方志写卷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尚有余温,国内研究以王重民为代表,他的《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分别对《沙州都督府图经》(P5034)、《西州图经》(P2009)、《寿昌县地境》(王目[1]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商务印书馆,1962.1700)作了校勘和研究。
域外研究以日本学者成果最突出,波利贞《千佛岩莫高窟与敦煌文书》(《西域文化研究》,1959)对《敦煌录》(S5448)进行了录文和研究,推断其撰成于晚唐僖宗年间(847—888)。松田寿男《段国〈沙州记〉集注》(《游牧社会史探》第10册,1961)主要以张澍所辑《沙州记》二十条为蓝本,考证佚文的编排顺序及出处,校注张氏辑本的讹误。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暦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4)首次汇集《沙州图经》S2593v、P2005、P2695、P5034 四种抄本,并整理出可靠文本。
3.专书整理与研究。
国内专书整理与研究的专著有2部。《蛮书》的整理有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该书对《蛮书》十卷作了精审的校勘和注释,尤其注意到前人忽略的材料,如《太平御览》所引《南夷志》即是《蛮书》的文字,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蛮书》面貌。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除对文本进行校勘外,还对以前未考证清楚的山川郡国作了充分考订,是继向达著作后又一部系统研究《蛮书》的成果。
《华阳国志》的研究,刘琳《〈华阳国志〉简论》(《四川大学学报》,1978)全面介绍《华阳国志》在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史料价值及版本,为此后的《华阳国志》研究提供了借鉴。
日本学者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有专著2部,专文2篇,专著有船木胜马《华阳国志译注稿》(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1974)、满志煊《华阳国志校注》(中国文化学院文史研究所,1980)。专文有狩野直祯《华阳国志的成书》(圣心女子大学论丛,1963)、久村因《论华阳国志的版本》(名大教养部记要人文社会科学,1973)等。
综上,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以域外成果居多,国内研究相较前代鲜有超越,是魏晋隋唐方志研究最低沉的时期。
(二)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1]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A].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当代中国地方志重要文献汇编[C].1990.(P21)全国群起响应,而方志编纂中实际问题的出现,又迫切地要求有成熟的方志理论进行解决。因此从80年代开始,方志的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对魏晋隋唐方志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方面。
1.通论性研究。
魏晋隋唐方志通论性研究多见于各方志史、方志学著作专章,较著者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二章第一节“汉魏隋唐时期的方志”,林衍经《方志史话》(中州书画社,1983)第四章第一节“官修志书的出现及其成就”,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中第二章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的地记”、第二节“隋唐的图经”,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二章第三节“魏晋隋唐方志出现雏形”,(台湾)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5)第二章“方志的起源与发展”等,对魏晋隋唐方志的形成、发展及代表性方志进行了介绍。
2.方志辑佚与辑本整理。
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是20世纪80年代方志辑佚的重要著作,内容虽仅限于一省,但无论从辑佚种类或字数来看都超越前代,该书收录魏晋隋唐山西方志十一种。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是古方志辑佚的集大成者,共辑录汉唐方志四百三十九种,凡该时期地记、图经、耆旧传、风土记、异物志及旧事杂记之类,只要有关某一地域或州县的专书,具备方志性质者,概予收录,可谓“麟光片羽,亦所不遗”[2]傅振伦.《汉唐方志辑佚》序[J].中国地方志,1996,(3-4).(P99)。但该书仍存缺憾,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中国地方志》,2006)指出:“刘书优长之处为广辑汉唐地志,且备注出处,便于引用和复核,不足之处为未充分吸取前人成绩,阙漏较多,处理也颇多失当处,读者利用时应有所注意。今后有条件,仍有重作辑录的必要。”[3]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J].中国地方志,2006,(7).(P29)此外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附辑录《南雍州记》三种,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许作民《邺都佚志辑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也辑有少量魏晋隋唐方志。
辑佚专文7篇,包括骆伟《〈齐记〉〈齐地记〉〈三齐记〉〈三齐略记〉〈齐记补〉辑佚》(《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刘纬毅《〈上党记〉辑佚》(《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太原事迹记〉辑佚四则》(《山西大学学报》,1983)、冯君实《〈邺中记〉辑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沙铭璞《辑佚唐代卢求〈成都记〉》(《成都文物》,1984)、韩格平《〈京口记〉残句辑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曹剑《〈邠志〉辑释》(《公刘豳国考》三秦出版社,1993)等。
辑本目录的整理最著者为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辑佚书专题目录,收先秦至南北朝佚书辑本及现存书佚文辑本,凡属1949年前版本均予以著录,对此后的方志辑本整理有较大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前代辑佚书的整理著作。王晶波点校《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将《凉州记》《西河记》《西河旧事》《沙州记》的张澍辑本、陶宗仪辑本、汤球辑本进行比勘,有纠误增补之功。
3.方志目录。
陈光贻《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附于《稀见地方志提要》,齐鲁书社,1987)对《古今图书集成》所收清以前佚志进行编目,注明志书名称、卷数、修纂者、修纂年代及存佚;并有备考,注明该地简略的沿革和志书见于何种目录。其中包含魏晋隋唐方志百余种。
区域性考录体目录九种,孙继民《六朝时期两湖方志的流传和辑佚》(《江汉论坛》,1986)综合前人成果,整理出《见于书目著录的六朝两湖方志一览表》,包含六朝时期两湖方志五十三种。黎传记、易平《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社,1989)考索明代以前江西佚志三百余种,后删除佚文、核定增补存目,又成《江西方志通考》(黄山书社,1998)。龚立新《江西早期方志考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二十六种江西方志进行了考订,弥补了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这一部分的遗漏。刘永之《河南方志佚书目录》(《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2)对清以前河南佚志进行编目,当中也列有不少魏晋隋唐方志。黄燕生系列论文《〈永乐大典〉杭州方志辑考》(《浙江方志》,1989)、《〈永乐大典〉常州方志辑考》(《常州方志》,1989)、《〈永乐大典〉溧阳方志辑考》(《常州方志》,1989)、《〈永乐大典〉绍兴方志辑考(上)》(《浙江方志》,1991)、《〈永乐大典〉绍兴方志辑考(下)》(《浙江方志》,1992)及罗新《〈永乐大典〉所录湖北方志考》(《湖北方志》,1988)分别对《永乐大典》中的江苏、浙江、湖北方志进行了辑录考证,当中也涉及少量魏晋隋唐方志。
此外还有对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进行补正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的为周振鹏《古方志存目研究例说》(《复旦学报》,1987),该文补张书未收之古方志二十六例。他如张崇根《〈中国古方志考〉一勘》(《文献》,1980)、黎传纪《〈中国古方志考〉江西佚志辑补》(《江西方志》,1989)、娄雨亭《〈中国古方志考〉补正三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等。
4.方志写卷专题研究。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敦煌方志写卷的研究以域外成果居多,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相继投入此项研究,研究范围虽未扩大,但研究深度超越前代,产生了一些专题研究成果。
专著主要有三部,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对《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兴平县志》(S6014)等作了辑录和校注。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分别对《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沙州志》(S788v)、《沙州伊州地志》(S367)、《寿昌县地境》(王目[1]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商务印书馆,1962.1700)进行逐条考释。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社,1998)对《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等八种唐代方志作了笺释和考证。专文有李并成《我省现存最早的方志档案——敦煌遗书地志书卷》(《档案》,1990)、刘纬毅《敦煌遗书方志叙录》(《中国地方志》,1993),两文均对现存九种敦煌方志写卷进行了介绍。
此外,针对某一种写卷进行的专文探讨共12篇,主要围绕《沙州图经》(P2005)、《西州图经》(P2009)、《寿昌县地境》(王目[1]1700)、《沙州伊州地志》(S367)、《沙州志》(S788v)、《敦煌录》(S5448)六种方志展开。
5.专书整理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专书整理研究,包括专著3部,专文48篇。
(1)《华阳国志》整理研究。
这一时期,成就特别突出的是《华阳国志》的整理与研究,有专著3部,专文39篇。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6)是首部《华阳国志》校注本,该书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参校其他九种版本,纠谬存疑,校勘审慎。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亦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并以三十余种版本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是整理研究《华阳国志》集大成者。刘重来《常璩与〈华阳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对作者生平、史学思想及《华阳国志》的地位、史料价值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这一时期探讨《华阳国志》的专文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有吕淑梅《〈华阳国志〉版本集说——兼谈云南省图书馆所藏版本》(《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该文首先梳理朱士嘉、刘琳所举《华阳国志》版本共24种,其次将云南省图书馆所藏《华阳国志》版本与朱、刘所举相较,其中15种为二人所未见,对《华阳国志》版本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其他如刘重来《说〈华阳国志〉》(《史学史研究》,1984)、刘固盛《〈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复印报刊资料》,1997)、赵俊芳《〈华阳国志〉汉魏丛书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等。
(2)其他专书的整理研究。
其他专书的整理研究著作有石洪运、洪承越《〈荆州记〉九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该书汇辑晋范汪《荆州记》、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刘宋庾仲雍《荆州记》、刘宋郭仲产《荆州记》、南齐刘澄之《荆州记》的不同辑本共九种,并对此进行了整理点校。其他专书的整理研究专文9篇,涉及方志有《邺中记》《吴地记》《闽中记》《九江寿春记》《荆州记》五种。
综上,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产生了较系统、全面的辑佚书及多种通论性研究,敦煌方志写卷研究形成专题,专书的整理与考证成果渐多,标志着魏晋隋唐方志的研究进入繁荣阶段。
(三)21世纪以来的整理与研究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方志的整理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局面。魏晋隋唐方志的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通论性研究。
魏晋隋唐方志通论性的探讨一部分以方志学著作专章形式出现,如黄道立《中国方志学》(巴蜀书社,2005)第四章第二节“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节“隋唐”,陆振岳《方志学研究》(齐鲁书社,2013)第二章第三节“魏晋南北朝”、第四节“隋唐”,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三章“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等,均对魏晋隋唐方志的形成、发展及代表性方志等进行了介绍。
通论性的专文有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4),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方志兴盛的原因、分布、种类及作者籍贯等进行了论述。但该文将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如《十三州志》、专志如耆旧传、异物志等均纳入方志范畴,缺少方志范围的基本界定。
2.方志辑佚与辑佚成果补正。
(1)辑佚专书。
马蓉、陈抗、钟文《〈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是迄今辑佚《永乐大典》方志成果最丰硕的著作,该书采取对已有辑本者不辑的原则,补充了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中华书局,2004)中遗漏的部分,辑录魏晋隋唐方志十一种。以区域为单位的辑佚著作有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辑录魏晋隋唐岭南方志十一种;王文才、王炎《蜀志类钞》(巴蜀书社,2010)辑录魏晋隋唐时期蜀地方志八种;陈晓捷《关中佚志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辑录魏晋隋唐陕西方志十七种。
此外(日本)福田俊昭《敦煌类书の研究》第二部《敦煌类书にみえる辑佚书》(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3)从敦煌文书中辑有《西河旧事》等方志。
(2)辑佚专文。
国内辑佚专文较著者为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该文对88种隋唐图经进行了存目考证及佚文辑录,对魏晋隋唐方志研究有极大参考价值。
单书辑佚专文有20篇,如骆伟《〈南越志〉辑录》(《广东史志》,2000)、陈庆元、陈炜《林谞〈闽中记〉辑考》(《闽江学院学报》,2004)、鲍远航《庾仲雍〈湘州记〉考证与辑补》(《湘潭大学学报》,2008)等。另外,李广龙《〈汉书〉颜师古注引方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鲍远航《〈水经注〉所引两种晋宋巴蜀地记考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水经注〉所引三种汉晋河北地记考述》(《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水经注〉所引〈汉中记〉考述》(《安康学院学报》,2014)等从注文的引文入手对方志材料进行了辑佚。
此外,还有针对辑佚书进行补正的成果,如熊清元《〈汉唐方志辑佚〉举误》(《古籍研究》,2000)、卞东波《〈汉唐方志辑佚〉纠误》(《中国史研究》,2003)、何九盈《〈汉唐方志辑佚〉标点商榷》(《湖北大学学报》,2004)、李鳯玲《〈汉唐方志辑佚〉纠谬》(《古典文献研究》,2005)、屈直敏《〈汉唐方志辑佚〉补正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王勇《〈汉唐地理书钞〉讹误考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王驰《敦煌类书扩充〈汉唐方志辑佚〉三则》(《黑龙江史志》,2014)等。
3.区域性方志研究。
区域性方志的研究主要涉及甘肃、山西、湖南几省。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7)、《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图书与情报》,2007)、《武威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青海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系列文章先后考查了二十余种魏晋隋唐时期甘肃地区的方志,其中十七种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遗书。刘益龄《隋唐、宋元时期山西方志编纂述略》(《中国地方志》,2008)叙述了隋唐、宋元时期山西方志“数量增加”“体例臻于定型”“专志的出现”的发展概貌。周建刚、毛健《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方志史书考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对宋以前湖南方志起源、发展和演变情况进行了论述。
4.专书整理与研究。
(1)方志写卷研究。
敦煌方志写卷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热,产生了不少专题研究成果。二十一世纪敦煌方志写卷的研究热度骤减,仅李并成《敦煌本唐代图经再考》(《中国地方志》,2016)对敦煌图经进行较系统的介绍。此外成果主要是《沙州图经》《兴平县志》两书的专文探讨。《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的研究有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2003)、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等;《兴平县志》(S6014)的研究有李并成《唐〈始平县图经〉残卷(S6014)研究》(《敦煌研究》,2005)等。
(2)《华阳国志》的整理与研究。
新世纪以后对《华阳国志》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专著有三种,汪启明、赵静《〈华阳国志〉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首次对《华阳国志》进行全书注释和翻译;刘重来《〈华阳国志〉研究》(巴蜀书社,2008)对常璩思想及史料价值进行了探讨。唐春生《〈华阳国志〉白话插图全本》(重庆出版社,2008)以刘琳、任乃强校注本为依据,将全书翻译成白话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这一时期《华阳国志》研究专文共84篇,其中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期刊论文16篇,学位论文4篇。
(3)其他专书整理与研究。
其他专书整理研究著作2部,研究文章25篇。姜川、赵德科《〈武昌记〉辑考》(鄂州星光印刷厂,2001),该书对三种《武昌记》的版本、流传进行了梳理,并对佚文进行了整理;孙琪华《〈益州记〉辑注及校勘》(巴蜀书社,2014)对历史上所引《益州记》各版本做了辑录和注释,对各种版本的源流做了梳理,使《益州记》终得以完本重见天日。其他专书研究文章涉及方志有《蛮书》《荆州记》《交州记》《吴地记》《永嘉记》《上党记》等16种。
综上,21世纪以来魏晋隋唐方志综合探讨、区域性方志研究、专书整理考证及前代成果补正之作增多,研究较前代学术视野更开阔、研究角度增多,不断将研究引向系统而深入的层面。
四、现有研究的基本特征及不足
1.学界对方志的认识差异较大,研究对象不统一。许多研究在进行文献整理前并未对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进行严格界定,研究对象选取的标准无法统一,产生了一些误辑、误补的研究。
2.成果零散、研究薄弱。魏晋隋唐方志存目数量较大,历代辑佚、校勘、考证成果丰硕,但多数成果以单书为对象,成果分散、系统性较弱。
3.重复性整理较多。通过整理存目及辑本情况可以发现,不少方志已有多种辑本,如魏晋佚名《巴汉志》有清代王谟辑本、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辑本,后陈晓捷《关中佚志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与王文才《蜀志类钞》(巴蜀书社,2010)亦辑录《巴汉志》,然并未参考前代辑本;另一部分方志如《上饶记》仅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一种辑本,且该辑本今不传。除方志流传程度存在差异外,更主要是缺乏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导致出现重复性整理。
4.对经典成果的过度依赖。就古方志存目研究而言,多数成果仍全赖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很少发明。张国淦之书事属首创,功不可没,但也存在网罗不全、考订未周之处。单就《太平御览》所引方志而言,张书就有《陕县图经》《邺县图经》《故安图经》《宜春图经》等书未录,表明古方志存目研究大有可为。
5.缺乏对材料的发掘利用。目前学界整理方志存目、进行方志辑佚主要利用历代目录书、《舆地志》《太平寰宇记》一类地理总志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唐宋类书,一些材料尚未被发掘利用。如宋代晏殊所编大型类书《类要》,原书七十六卷,今存三十七卷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从现存文本看,引书达七百余种,当中保存不少魏晋隋唐佚志,实为辑佚之渊薮,考订之新材。而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却未引《类要》,今知至少可补《陇右记》《庐江记》《道州记》《河州记》《兴城记》《黔中记》等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