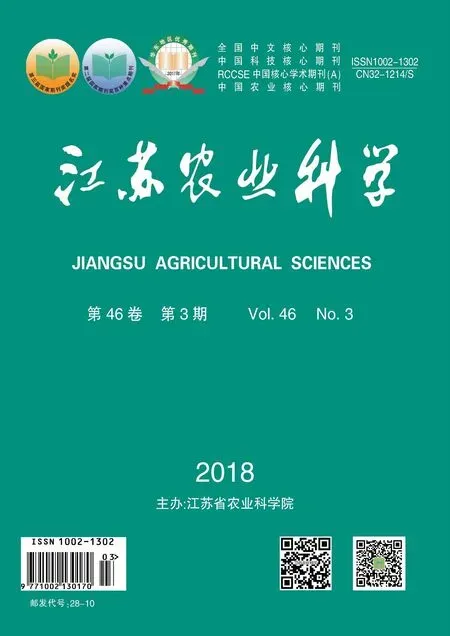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的效果评价
姜申未, 杨朝现, 孙小峰
(1.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 2.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通信作者:杨朝现,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方面的研究。E-mail:yangcx@swu.edu.cn。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纵深推进,人地矛盾进一步显现,农村耕地细碎化、劳动力外流、农业技术落后等因素使得农业发展受到限制[1],这在客观上要求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其从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户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农户,从而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2-3]。事实上,当前我国农村存在土地经营分散、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村资本注入缺乏、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已造成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呈现结构性扭曲[4]。因此有必要疏通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流动的路径,实现农村资源价值的整合与显化已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关键。而农地流转恰是整合农业资源的有效途径,是破解农业资源低效利用和农村发展障碍问题的关键[5],借此可以最大化地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各要素的增殖效益[6]。
农地流转已日益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从流转动因、模式、困境、评价等到与之相关的农户参与意愿、劳动力转移、机制优化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而将资源整合视角应用到农地流转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有部分学者尝试以要素组合理论[7-8]、资源配置理论[9]以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的联动[10]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乃至农村发展的影响。马晓河等认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11]。刘卫柏等认为土地流转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12]。冒佩华等通过平均处理效应方法论证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积极影响[13]。这些其实都是对于农地流转与农业资源整合的具体研究。
那么农地流转如何带动农业资源整合,农村各类资源整合的效果如何,不同流转模式的整合过程有什么差异?目前,国内土地科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多是从流转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进行考量,缺少系统论的动态评价,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源整合视角去评价农地流转的效果。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东北侧,龙泉山西麓,境内地势平坦,以平坝为主,平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兼有丘陵,丘陵分布在松林镇和连山镇,地势东高西低。幅员面积538 km2,辖18个乡镇,183个行政村,总人口60余万。截至2014年,广汉市实现农业总产值53.37亿元,其中粮食播种面积4.76万hm2,新增1 hm2以上规模流转面积1 560 hm2,累计流转农用地面积3 436 hm2,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4.60%。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调研小组2015年在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兴隆镇、和兴镇、松林镇、西外乡5个乡镇对经营大户与农户展开实地调研,主要方法为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等形式。经统计,调研共发放问卷626份,收回626份,有效问卷586份,有效率为94%。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农业资源整合过程中,农地流转无疑是最为基础的资源流动路径[14],它是指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15]。梳理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关系发现,土地流转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整合过程[16]。它能打破传统的农业资源组织结构,有效促进农业农村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重组。笔者调查后发现,研究区普遍存在农业资源利用粗放、信息和市场渠道不流畅等现象,使得农业资源僵化浪费,农村经济持续低迷。近年来,广汉市通过积极开展农地流转,吸引外资注入,培植了一批有特色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激活农村各类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由于农地流转带动农业资源整合这一耦合关系,笔者不得不从资源整合视角去研究农地流转。因此,本研究以土地流转为“引擎”,农业资源和整合过程为“双轨”,建立“农业资源—整合过程—流转模式—整合差异”分析框架,进而评价土地流转带动下的资源整合效果(图1)。

2.1 资源整合过程分析
资源整合是一项系统复杂的过程,多见于人力资源管理、科技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在研究土地资源管理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指主体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配置和有机融合,并对原有的资源体系进行重构,以形成新的核心资源体系[16]。Ge等给出了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内外部行为,主要指面向外部的资源识取行为(包括资源识别与资源获取)和内在的资源配用行为(包括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17-18]。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资源整合过程分为资源识别→资源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利用4个步骤:(1)资源识别是起点。经营者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依据产业和市场定位来选择资源,由此决定农地流转后的农村产业发展,如传统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2)资源获取是重要过程,其方式可分为内部培育和外部获取。农地流转中资源的获取分为购买和合作,购入有形资源(劳力、土地、农资、机械等)、无形资源(技术经验与管理技能等),与合作社或大户合作。(3)资源配置是中心环节。农地流转的资源配置主要是对识取后的资源围绕市场定位进行合理安排。(4)资源利用是最后步骤,利用得当便是资源价值显化、农地流转效果提升的关键。
2.2 农业资源梳理与指标体系构建
农地流转所涉及的资源属于农业资源。农业资源是指农业在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15]。梳理农业资源的构成发现,多数学者虽然研究资源指标略有不同,但主要集中于“二分法”观点。一般来讲,农业自然资源分为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等,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和产品销售市场等[19]。也有从资源整合视角依据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对资源分类。董保宝等认为,资源既可以是来自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已有资源,通过将内外部资源整合之后可以提升资源的动态能力和经营者的竞争优势[20]。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思路,在资源整合视角下将主要农业要素划分为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农业生产基本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后者是随着社会进步所追加的新型要素,如科学技术、管理和产品销售市场等。
农业资源整合的效果评价需要构建指标体系,结合相关研究[21-22],笔者从6个方面——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管理资源、科技资源、产品销售市场资源细分15项指标,构建了农业资源整合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2.3 农地流转模式确定
农地流转带动下的资源整合对象主要是流入农地的经营者,其经营行为对各类型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农地流转效应的提升[11]。但是,不同的流转模式对资源整合过程不同,最终的效应也不同。学者们从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特征等视角总结了农地流转的多种模式。本研究以研究区不同经营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优势作为划分依据将流转分为传统小农型、市场主导型和多元合作型3种农地流转模式。其中,传统小农型是指农户之间由于生计的简单而小规模的流转;市场主导型是在市场需求刺激下的以大户为主的自发性流转;多元合作型是政府通过政策、管理、信息等资源优势并将农户的土地资源、市场的资金资源等整合起来的一种流转方式。通过分析各流转模式所识取和配用过程的特征,有利于为农地流转的资源整合路径提供微观层面的分析思路,从而找出不同流转模式对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优势。
2.4 评价方法及过程
由于农地流转受多种因素制约,很难精确描述影响因子的作用[23]。目前评价方法多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24]为基础,主观判断的不确定性导致评价结果失真。资源整合是典型的灰色系统,其内部规律客观存在却难以认知,灰色评价法可将土地流转带动下的资源整合内部机制看作一个“黑匣子”,从外部获取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0]。因此本研究在厘清农地流转不同模式的特征基础上,引入灰色理论来减少不确定性,运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26]对农业资源整合效应进行评价,从而寻求各类农业资源要素合理高效流动的路径。
其灰色评价算法如下:首先,依据影响农业资源整合的重要指标,邀请专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打分。各农业资源Ci的评价指标权重为U=(α1,α2,…,α6),二级评价指标C1j的权重为U1=(α11,α12,α13),同理可得劳动力资源U2、资金资源U3、管理资源U4、科技资源U5、产品销售市场资源U6的最终指标权重。然后,根据农业资源实际整合情况,结合专家打分构建评价样本矩阵D=[dijk](n1+n2+n3)×m。将评价灰度e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借鉴冯伟等的表示方法[26],计算灰色评价系数及权矩阵。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对各农业资源进行评价,其一级灰色综合评价结果为Oi=Ui·Ri,由此可知总灰色评价权阵R=(O1,O2,O3,O4,O5,O6),进一步求出二级综合评价结果为O=U·R。对O进行单值化处理,对各灰度进行“灰水平”赋值,设ω=(100,75,50,25),据此求出农业资源整合的综合评价值Y=O·ωT并划分“优、良、中、差”4个评价等级(表2)。

表1 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注:指标层中“指数”类从1~10标度,趋近于10的为正向;比率(重)以百分比标度;变化量以年平均值标度。

表2 农地流转对资源整合效应评价等级分类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流转模式的资源整合效果
经上述评价过程,最终计算得传统小农型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的综合评价值为Y1=O·ωT=59.93。对照评价等级分类表可知其得分区间属于“良”等级,因此资源得到一定整合,效果较好。同理求得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的综合评价值为Y2=74.82,整合效果趋近于“优”等级;多元合作型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的综合评价值为Y3=89.16,属于“优”等级,资源得到充分整合,整合效果好。通过对586份有效问卷的整理,得出评价体系中指标层的均值,对3种农地流转模式的各项资源进行统计评价。
3.2 结果分析
3.2.1 资源禀赋决定资源整合轨迹 资源禀赋决定资源整合轨迹,从而影响着农地流转的效果。传统小农型流转模式资源整合过程较为粗简,主要表现在对内部资源的依赖,经营者普遍缺乏对外部资源的识别能力,获取形式单一,对资源的配置格局较为简单,利用较为粗放。市场主导型流转模式经营者受市场利益驱动,产业目标较明确,具备资本、技术等资源禀赋上的优势,并对这些内外部资源有一定认识和获取渠道,其配置中以市场为导向,资源利用较为集约。多元合作型流转模式经营主体有公司、农户和非农人员,整合过程涉及资源更多,过程更为全面、复杂;经营者注重与政府、村社、专业合作社等合作,资源识别能力更强,能够清晰地认识内部资源禀赋优势和外部资源的提升作用,在产业定位上有着更多的选择,比如观光、休闲等;对资源的配置更有规划性,利用更加高效。
3.2.2 流转模式决定资源整合优势 流转带动下的各项农业资源价值得以显化,并且总体呈现多元合作型>市场主导型>传统小农型。由于3种农地流转模式存在特征差异,因此从整合的综合效果(表3)来看,多元合作型最优(89.16),市场主导型次之(74.82),传统小农型最差(59.93)。结合表2评价等级来看,3种农地流转模式都处在“良”以上等级,资源整合整体效果好,这说明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具有优势。同时,同一项资源在不同流转模式中具有不同的整合效果。传统小农型侧重于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类内生资源的整合;由于流转主体为农户,自身所拥有的土地资源(79.35)整合效果较好,但是由于对资金、科技、管理方面的资源禀赋;优势较差,因此在这些方面的整合效果不佳;市场主导型的资金资源整合优势突出。由于利益驱使的大量融资,资金资源(90.45)整合效果最优,其他资源的整合效果略优于传统小农型(表4)。多元合作型对各类农业资源的整合效果都有优势。由于优势集聚,加之政府的参与,各项资源都得到更优的整合效果,管理资源和科技资源的大量投入使得就业岗位增多,因此劳动力资源整合效果优势明显(89.64)。通过调查整理和统计评价,用“+”的数量给出不同流转模式对各项农业资源的整合优势(表5)。

表3 3种农地流转模式的各项资源整合评价统计

表4 不同农地流转模式对资源整合轨迹差异

表5 不同流转模式下的资源优势比较
3.2.3 整合强度决定资源整合效果 研究发现,资源整合强度(或者说资源投入效率)与资源整合效果整体上呈现正比趋势。研究区地势平坦,道路通达,在土地资源方面便于实现规模经营,相较于其他2种流转模式而言,多元合作型的规模经营程度最高,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资源投入的集约利用,单位土地产出率较高,平均为1万元/(hm2·年);在劳动力、资金、管理资源方面,较其他流转模式具备劳动力密集、投入产出比高、管理方式优、信息渠道广等优势;在产品销售市场资源方面,借助多方经营主体,利用网络平台和政府资源,具有很广的销售渠道,农产品商品化率高达81%;科技资源方面,便于机械作业,农业机械化率达到72%,同时由于政府对资源意识和获取的优越性,技术和受培训人员比例逐渐增大至71%,大强度整合使资源迅速集聚,有利于特色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模式以效益为导向,除了资金优势明显外,其余各项资源指标都不如多元合作型,受利益驱动和技术缺乏影响,多种植经济作物且少有机械配套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一般,为39%;由于管理程度不够,自身意识缺乏,因此基础建设比重较小,为13%,技术及受培训人员比例为23%,管理综合指数一般。对于传统小农型流转模式,因为较少有基础设施、办公用房等占用,垦殖系数很高,平均为94%;其他方面均差于其他2种流转模式,单位耕地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较高,因此农业产出较低;劳动力投入平均减少0.21人,有效劳动时间仅比非流转模式减少 0.54 h,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几乎为0,技术及受培训人员比例仅为5%,管理方式落后,经济效益差,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240元;流转多靠亲戚关系维系,农产品商品化率为21%,整合意识低,资源禀赋弱,整合强度小,多以维持水稻、红苕、蔬菜等家户种植为主(图2)。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传统小农型对于资源整合的认识和支持不足,无法识取和配置更多资源;市场主导型基于市场导向,对资源的识别和获取非常重视;多元合作型由于经营主体较多,对资源的识取和配置掌握更多优势,利用效率最高。

地流转首先是带动了农业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不同流转模式下的资源整合综合效果不同。本研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传统小农型、市场主导型和多元合作型3种农地流转模式,对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管理资源、科技资源、产品销售市场资源六大类的15项指标的整合效应通过多层次灰色评价法进行评价,最终得出3种流转模式综合效应呈现出多元合作型>市场主导型>传统小农型。
4.1.2 同一流转模式中单一资源的整合优势表现各异 每一种流转模式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差异,因此整合效应会表现出一定不同。在传统小农型流转模式中,土地资源占据较大优势;市场主导型流转模式中,资金资源占据最主要的优势,其他资源优势处在高于传统小农型低于多元合作型之间;多元合作型流转模式中,除了土地资源整合优势一般外,其余资源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资源,从而带动整体的资源整合效应。
4.2 讨论
要提高农地流转效应,可以在资源整合视角下逐步优化整合轨迹,并依据不同的整合优势判定流转模式的适用性。传统小农型模式整合意识及手段落后,资源优势较少,整合效应较差,但其对耕地保护和粮食供应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流转模式依靠“地缘”关系操作,具有手续简便、投入少、流转快、稳定农村环境的优势,因此适用于在流转难度大的地区以种植主要粮食作物为产业导向。市场主导型模式资金资源优势明显,在投资、管理、市场方面具有很大空间,经营者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寻求效益,因此经济落后区可以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推广此流转模式以种植特色经济作物为产业导向。多元合作型模式资源整合手段丰富,集约化程度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经营主体较多,合作协约难,投资额巨大,管理复杂,甚至出现非农化现象,适宜在区域特色中挖掘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为产业导向。
参考文献:
[1]张仕超,魏朝富,邵景安,等. 丘陵区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J]. 农业工程学报,2014,30(12):1-17.
[2]Jin S,Deininger K.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9,37(4):629-646.
[3]黄 枫,孙世龙. 让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J]. 管理世界,2015(7):71-81.
[4]楚晓琳,贾宪威. 影响农业资源整合的相关因素与对策[J]. 商业时代,2009(19):99-100.
[5]游和远,吴次芳. 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 管理世界,2010(3):65-75.
[6]靳 桥,邢 忠,汤西子. 生态整合目标导向下的城市开放空间资源利用与关联建设用地布局[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5(6):68-74.
[7]王茂爱. 论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组合[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6):18-22.
[8]龙登高. 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J]. 经济研究,2009(2):146-156.
[9]陈训波. 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愿景[J]. 改革,2012(8):82-90.
[10]张仕超,李治猛,魏朝富. 乡村土地资源整合模式:土地流转与整治[J]. 广东农业科学,2014,41(9):229-236.
[11]马晓河,崔红志. 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J]. 管理世界,2002(11):63-77.
[12]刘卫柏,李 中.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运行绩效与对策[J]. 经济地理,2011,31(2):300-304.
[13]冒佩华,徐 骥.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 管理世界,2015(5):63-74,88.
[14]崔慧霞.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 农业经济,2014(11):7-9.
[15]刘书楷. 农业资源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J]. 自然资源学报,1987(2):310-320.
[16]Michael A H,Bierman L,Shimizu K,et al.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on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in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1):13-28.
[17]Ge B S,Dong B B. Resourc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venture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contingency model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y[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Long Beach,2008.
[18]马鸿佳. 创业环境、资源整合能力与过程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08.
[19]陈印军,卢 布,杨瑞珍,等. 农业资源管理研究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7,28(6):21-25.
[20]董保宝,葛宝山,王 侃. 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J]. 管理世界,2011(3):92-101.
[21]孙小峰. 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效应的评价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5.
[22]李迎迎. 不同产业模式下农业生产要素整合效应评价[D]. 重庆:西南大学,2015.
[23]程令国,张 晔,刘志彪.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J]. 管理世界,2016(1):88-98.
[24]符学葳.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研究和应用[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
[25]宋晓丽,樊俊华. 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在土地评价中的应用[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6(1):106-109.
[26]冯 伟,王修来,马宁玲,等. 基于多层次灰色理论的科技资源整合效果评价模型[J]. 技术经济,2009,28(5):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