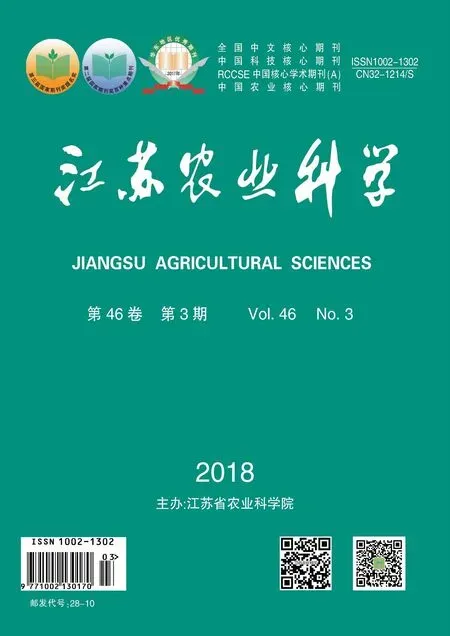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固氮菌在其修复中的作用
刘 晨, 贾凤安, 吕 睿
(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43)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及城镇的加速建设,排放到环境中的工业废料及有毒污染物也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由于重金属在自然环境中代谢慢,还会转移并累积到植物中,对动物和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因此会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许多重金属即使在很低的浓度下,毒性仍然很大。砷(As)、镉(Cd)、铬(Cr)、铜(Cu)、铅(Pb)、汞(Hg)、镍(Ni)等重金属不仅对细胞有毒害作用,还会致癌以及导致突变[1]。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仍然是我国的发展重点,因此对环境的修复就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以及酶活性与土壤养分含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固氮菌可有效改善土壤环境,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植物根系对氮元素的吸收,提高土壤微生物的酶活性,活化土壤中的矿质养分[2]。本研究以固氮菌为研究对象,在总结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及近期对固氮菌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作用的基础上,探讨固氮菌修复重金属土壤的可行性。
1 重金属污染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指比重大于5或4[主要包括铜、锌(Zn)、镉、铅、汞(Hg)、铬、砷、镍、钴(Co)]的金属或其化合物在土壤环境中所造成的污染[3]。
1.1 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
2011年11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称,全球25%的耕地严重退化,其中来自污染方面的退化原因不可忽视[4]。 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1.1%,其中重金属污染问题比较突出[5]。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利益和健康利益的双重损害。目前,我国受Cd、As、Cr、Pb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 000万hm2,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粮食减产超过1×107t,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6];与常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相比,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见性和隐蔽性。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导致土壤肥力退化、农作物产量降低和品质下降,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威胁到人们的食品安全[7]。据统计,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发生的重大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几十余起,已经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8-9]。
1.2 污染来源
土壤中的重金属来源较多,除内源污染外其余都是与人类工业生产、农业活动等相关的外源污染(表1)。其中,以工业来源及农业来源的污染对耕地的土质影响最为严重[10]。工业废弃物是土壤重金属的主要成因,主要来源于采矿业、化工业、金属加工等。将工业废水用于农田灌溉成为我国农业的普遍现象,结果导致耕地中重金属的富集,最终这些重金属会从污染的耕地中转移到农作物中[11]。
1.2.1 工业来源 土壤中有70%重金属来源于矿山开采和冶炼矿石开采[12]。尾矿是矿石开采的副产物,是矿石经磨细,选取有用成分后形成的废弃物,其中包含的部分元素是重要的二次矿产资源,但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仍无法有效利用。由尾矿形成的固体矿物废料,是固体工业废料的主要成分。尾矿已成为全球范围的难题,遍布墨西哥、美国、智利、秘鲁、南非、印度、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国家[13-14]。全世界每年排弃的尾矿和废石约达300亿t,裸露的尾矿堆通过风和水的传播将污染扩散至周围数万公顷范围,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和全球生态环境[15-16]。我国现有2 700多座矿山尾矿库,堆积尾矿约50亿t[17],其中每年排弃的尾矿约3亿t,占用土地约20 km2[18],严重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平衡,危及人体健康和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尾矿还是产生酸性矿山废水(acid mine drainage,AMD)的重要源头之一[19],AMD的pH值一般在4以下,而且富含重金属[Pb、Zn、Cu、Cd、Mn、Ni、As等],这些生物毒性极高的酸性废水是采矿业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直接排放可对下游的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表1 我国重金属污染来源分类[5,9]
1.2.2 农业来源
1.2.2.1 污水灌溉 污水灌溉作为一种农业灌溉措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机污水灌溉除了提供水源和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其污水中的有害成分也会影响土壤质量和农作物品质[20]。我国污水灌溉污染的农田面积为 330万hm2,平均污水灌溉农田每年接纳工业污水6 645 t/hm2。据我国农业部对全国污水灌区进行的调查,在约140万hm2的污水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水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的占 46.7%,中度污染的占9.7%,严重污染的占8.4%[21]。
1.2.2.2 化肥滥用 为了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投入过量的含有铅、镉、汞、砷等重金属的化肥。如磷肥的主要生产原料是磷矿石,天然伴生Cd,Cd的含量在0.10~571.00 mg/kg之间,平均含量为0.98 mg/kg[5]。由于每年都施用磷肥,而磷肥被植物利用的比例只有10%~20%,造成大部分Cd在土壤中不断累积。不同种类重金属的主要来源见表2。

表2 不同种类重金属的主要来源
1.3 污染源的控制
对于污水灌溉带来的重金属污染早已有研究,如我国甘肃省白银地区使用含As废水灌溉农田导致全市16.3%的土壤As超过当地临界值(25 mg/kg),最高达149 mg/kg[22],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但污水灌溉由来已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用水的巨大缺口,立即禁止并不现实,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化肥是目前农作物增产的重要手段,我国以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的人口,与化肥的施用密不可分,目前还没有更加绿色高效的替代物来取代化肥。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可以预见一定时期内重金属等污染物排放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形势将越发严峻。因此,重金属污染问题仅通过源头“防”是不现实的,应着重从修复方面入手,控制及减轻污染范围和程度。
2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
各种重金属存在形态非常复杂。水溶态、交换态对植物最有效,活性最大,毒性最强,称为可给态,将这2种形态转变为稳定性更强的形态是降低其毒性的有效途径之一[23]。
传统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通常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如排土填埋法、稀释法、淋洗法、物理分离法和电化学法等。其原理主要是通过减少土壤表层污染物的浓度,或增强土壤中污染物的稳定性使其水溶性、扩散性和生物有效性降低,从而减轻其危害。这些传统的修复方法虽然治理效果较好、历时短,但也有许多缺陷如成本高、难于管理、易造成二次污染、对环境扰动大[6],同时这些技术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即当重金属浓度低于100 mg/L时,很难被有效去除[24]。此外,大多数的重金属盐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当这些重金属以工业废水的形式被排放时,很难用物理方法进行分离[25]。生物修复在这方面就显示出了优势,如利用微生物或植物进行生物吸附或利用生物体内累积等方法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不仅能去除重金属,还可以重建土壤的生态系统、恢复土壤活力(表3)。
3 固氮菌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作用
氮素是植物生长必需的矿质元素,也是需求量最大的矿质元素[26],重金属污染区一般缺乏氮素,通过固氮菌可以方便、低成本地为污染地区土壤补充氮源,促进该地区的植株生长,使土壤环境进入良性循环,降低污染度,甚至使土壤趋于无污染。
3.1 作为污染/修复的重要指标
鉴于固氮菌在天然生态系统氮素循环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污染物胁迫对自生固氮菌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此外,由于植物生长周期比较长, 研究重金属胁迫下的共生或联合固氮作用往往所需时间较长而固氮菌受到胁迫后固氮作用迅速受到影响,便于及时监测。因此,土壤中固氮菌群数量、固氮酶活性的变化可作为土壤污染/修复的监测指标,建立有效的污染预警指标体系,为环境质量评价提供有益的参考[27]。

表3 不同土壤修复方法优劣势比较
3.2 氮源补充
有研究表明[28],三大微生物以及各生理类群对重金属污染的敏感性大小分别表现为放线菌>细菌>真菌、自生固氮菌>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纤维分解菌。可见在重金属污染土壤生态环境条件下,参与氮素转化的细菌生理类群往往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在重金属胁迫下固氮菌数量的下降及固氮酶活性下降往往会导致该地区氮素缺乏,这也是土壤肥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恢复土壤活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对其进行氮源补充。目前,针对氮素缺乏的普遍做法是加大尿素等氮类化肥的施加。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土壤状况陷入恶性循环。通过添加固氮菌类生物肥实现修复土壤的目的,才能起到从本质上改善土壤肥力,并实现整个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3.3 参与修复
微生物修复中的固氮菌修复重金属土壤最近备受重视,该方法不仅能发挥微生物修复数量众多、比表面积大、带电、代谢活动旺盛等优势,还具有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土壤重金属的活性等特点[29],还能缓解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的土壤氮素减少、肥力下降问题。
3.4 固氮菌抵抗重金属作用机制
(1)细胞表面吸附。由于微生物对重金属具有很强的亲和吸附性能,有毒金属离子可以沉积在细胞的不同部位或结合到胞外基质上,或被轻度鳌合在可溶性或不溶性生物多聚物上。(2)重金属的转化作用。微生物能通过氧化还原、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作用转化重金属,将有毒物质转化成无毒或低毒物质。(3)输出系统对重金属的作用。其中有3种系统(RND、CDF和P-ATPase)介导二价金属阳离子排出细胞[30],目前这种输出机制主要用于抗镉和抗铜系统。(4)通过形成金属硫化物及金属磷化物达到抗重金属的目的。(5)微生物是土壤中腐殖质形成的根源,而二价金属离子可以与腐殖质络合(图1),形成低毒的络合态。一些固氮蓝细菌和某些藻类能产生胞外聚合物如多糖、糖蛋白、脂多搪等,这些物质具有大量的阴离子基团,与重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而解毒。如在藻类中发现一种被称为“植物鳌合蛋白”的多肽能与Cd、Cu、Zn等重金属结合。在蓝细菌中发现一种可以与重金属强力鳌合的金属硫蛋白(MT),可通过其残基上的硫基与金属离子结合形成无毒或低毒络合物。Vasundhara等发现,随着培养基中重金属(Cu、Ni)离子浓度的升高,圆褐固氮菌(Azotobacterchroococcum)对重金属的吸收量也增加,并产生一种诱导物质——硫醇,该物质是一种重金属结合缩氨酸,与环境中的重金属离子结合,从而降低其对细胞的毒性[31]。

4 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现状及生物修复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总结下来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现状可以概括为:(1)以Cd、As、Pb、Cu、Cr、Hg等元素为主;(2)多种重金属元素复合污染;(3)不同区域间因来源不同、污染程度不同又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正是由于污染面积广、污染源复杂、差异性明显的现状,使固氮菌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大打折扣。
4.1 重金属污染程度及种类
固氮菌对重金属的修复和耐受能力与其浓度有很大关系,一般在低浓度下固氮菌的生长及固氮作用还会被促进,但在高浓度下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二者一般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这种相关性还与重金属的种类有关[32]。有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土壤中Cd、As、Pb、Cu含量的增加,固氮菌的固氮活性降低,而且4种重金属元素的毒性大小为Cd>As>Cu>Pb。 El-Enany 等研究了2种蓝细菌在含低浓度、中等浓度重金属(Zn、Cd)污水处理下,它们的固氮活性均增加,但在高浓度下其代谢则受到抑制[33]。然而,Brookes等研究发现,即使是很低浓度的重金属[乙二胺四乙酸(EDTA)浸提,Zn 30 mg/kg、Cu 15 mg/kg、Ni 2 mg/kg、Cd 2 mg/kg]试验中的蓝绿藻固氮强度降低了50%[34]。不同种类的固氮菌对不同重金属甚至同一重金属的敏感程度不一,不能同一定论。
4.2 土壤类型不同、pH值不同对固氮菌活性影响较大
重金属离子对固氮菌的毒性与土壤的pH值密切相关。Obbard等利用温室栽培白三叶草评价较低重金属(Zn、Cd、Cu、Ni、Mn)含量的污泥对其根瘤菌数量及固氮效率的影响,发现土壤pH值为6.0左右时,污泥中一定浓度范围内的重金属离子对根瘤菌影响较小,但当pH值(5.0)较低时,根瘤菌对重金属毒害的忍耐度降低,其数量及固氮活性均明显下降[35-36]。一般来说,这几种重金属离子在酸性土壤中的有效性较大,在水溶液中其离子浓度随pH值降低而增加。
4.3 复合污染
在土壤环境中,由单个污染物质构成的环境污染虽时有发生,但实际上绝对意义的单一污染是不存在的,污染多具伴生性和综合性,即多种污染物形成复合污染[37]。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同样浓度下,固氮菌对复合污染更为敏感[38-39]。
5 解决方法
5.1 增强固氮菌重金属耐受性——菌种筛选
从各类重金属污染环境筛选固氮菌的研究如胡佳频等从钾长石矿区中分离固氮菌,该研究从吉首钾长石矿区共分离出自生固氮菌28株,所有固氮菌株均具有一定的解钾活性[40]。其中活性最高的根瘤菌L13发酵液中有效钾(K)含量达到 71.22 mg/L,有效氮(N)含量可达10.71 mg/L。李雯等从铁尾矿植被恢复区筛选分离出48株具有固氮能力的菌株,其中固氮酶活力最高的Ec1固氮比活力可达到307.23 nmol/(mg·h),再将Ec1接种到紫花苜蓿上,结果显示磷酸酶、脲酶、土壤酶活性均有明显增加,土壤养分含量均高于对照组[2]。
5.2 与其他菌群或介质、植物联合使用
固氮菌只是微生物体系中一个很小的分支(图2),还有许多非固氮菌的微生物,虽然不能为重金属污染土壤直接提供氮源,但对重金属的吸附以及价态的改变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如对重金属抗性最强的真菌类[40]。

利用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生物修复手段之一,因为它与微生物修复一样具有环境友好及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特点。但单纯依靠植物去除重金属污染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植物生长慢、生物量低、对金属有选择性、不适宜复合污染修复。研究表明,氮素是植物必需的生命元素和生长限制元素[42]。通过增施肥料可提高修复植物生长速度、生物量及重金属积累量[43],植物-固氮菌联合修复是在植物修复的基础上,与微生物形成互惠互利的联合体来提高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效率[44]。许多植物都具有重金属富集作用,如Sriprang等利用豆科植物与基因工程根瘤菌的共生关系,来修复土壤Cd的污染取得了成功[45]。李廷强等通过研究不同重金属浓度下东南景天的根际微生物发现,Zn超积累的东南景天的根际微生物细菌数量、主要生理类群数量及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显著高于非超积累生态型,说明在重金属超积累型植物联合作用下,细菌对重金属抗性更强,对污染土壤的修复能力也更强[46]。目前已发现的具有重金属超积累能力的植物已有700余种,广泛分布于50个科(表4)[47-53]。和固氮菌之间如何联合,和哪种固氮菌进行联合已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发掘空间的研究方向。
5.3 “一区一策”的治理理念(根据重金属种类、pH值、种植作物不同给出具体方案)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区域特征明显,土壤属性差异大,相应的重金属污染物类型多样,污染治理技术与模式在不同区域、 不同污染物类型及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上实用效果差异显著。重金属污染治理必须考虑区域特点,在修复治理中充分体现“一区一策”的治理理念[54]。不同种类的固氮菌对不同重金属敏感程度不一;不同重金属复合,2种或几种重金属之间是互相拮抗还是强强联合;固氮菌的抗性程度都须进一步研究。要固氮菌发挥固氮甚至是对重金属土壤的修复作用,前提是保证固氮菌的活性,因此应以不同地区的不同污染类型、pH值、种植作物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前期从各种极端条件下筛选或遗传学改造得到的固氮菌库,给出适合当地生境的固氮菌,进一步与其他菌群、植物甚至介质相结合,最终实现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及土壤的活化作用。

表4 已报道的有重金属修复能力的植物(中国)[48-53]
5.4 基因工程菌
基因工程菌(GEM)是指其遗传物质经由DNA重组技术改造,增强或扩大某种菌对土壤水污泥等环境中化学物质的降解作用,使其获得修复污染土壤的能力[55]。将重金属抗性基因通过遗传学手段整合进高效固氮菌或其他菌中,使其具有重金属抗性,达到污染土壤生物学修复的目的。运用遗传学手段获得具有耐/抗重金属的工程菌与大规模的菌株筛选相比成本较高,但是可降低盲目性,减少工作量。
重组菌可以在较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在多种复杂的环境条件下用作生物修复剂。表5列出了近期报道的一些对重金属有修复作用的基因工程菌。基因工程菌也推动了“微生物传感器”的发展,它可快速准确地测量污染地的污染程度。多种微生物传感器一般设计出来用于检测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如Hg、Cd、Ni、Cu、As[56-57]。目前,基因工程技术被认为是土壤重金属修复中最有希望的研究方向(表5)[58]。

表5 有重金属修复能力的基因工程菌[59-70]
6 结论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活力退化[71-72]。固氮菌可有效改善土壤环境,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植物根系对氮元素的吸收,能增强宿主植物的抗病性和抗逆性。因此,以固氮菌为修复剂用于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成为生物修复中的一个新兴方向。但这一方法也存在限制,即固氮菌本质上是细菌,所以对重金属的耐受力存在上限,同时重金属污染土壤多为复合污染且污染情况千差万别,仅仅依靠目前从自然生境中分离得到的固氮菌完成生物修复存在一定难度。
因此,固氮菌和超积累植物及其他高效降解微生物的筛选、合理搭配、修复机制的探索和基于植物与微生物联合修复的根际圈效应、以广义生物修复为核心的联合修复以及修复强化措施的研究将成为污染土壤生态修复研究的核心内容[73]。此外通过对固氮菌进行遗传学改造,提高它对重金属的耐受力甚至赋予它本身并不具备的对重金属的吸附、转运、分解等能力来完成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也将成为今后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学修复的研究重点。我国约有 0.1亿hm2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地域上大部分分布于南方亚热带水热资源丰富地区,修复治理后的土壤具有巨大的利用潜力。中度和轻度污染的土壤修复后,单位面积粮食(水稻)产量可以提高10%以上,种植业还可得到发展;重度污染的土壤修复治理后,土壤生态功能得到恢复,通过适当利用,农田每年有15 000元/hm2左右的产值[54]。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不仅可以为国家增加粮食产量,同时有助于改善和维护污染区域民众健康。土壤污染是事关农业、农村、全民健康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其修复治理可形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
[1]Salem H M,Eweida E A,Farag A . Heavy metals in drinking water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human health[C]//ICEHM. Egypt:Cairo University,2000:542-556.
[2]李 雯,阎爱华,黄秋娴,等. 尾矿区不同植被恢复模式下高效固氮菌的筛选及Biolog鉴定[J]. 生态学报,2014,34(9):2329-2337.
[3]Adriano D C. Heavy metals release in soils[J]. Soil Science,2002,167(11):771-779.
[4]陈 浩,杨达源,金晓斌. 石河子垦区耕地土壤污染问题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2):186-192.
[5]蔡美芳,李开明,谢丹平,等. 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与防治对策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14,37(120):223-230.
[6]曾学云,吴群河. 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基本机理及其发展方向[J]. 环境污染与防治,2004,8(4):76-81.
[7]林 强. 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其防治对策[J]. 福建水土保持,2004,16(1):25-28.
[8]Jiang N. Hazard highlight of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s[J]. Enviromental Economy,2011,10:10-14.
[9]张 艳,邓扬悟,罗仙平,等. 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微生物修复技术探讨[J]. 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2,3(1):63-66.
[10]Athar R,Ahmad M. Heavy metal toxicity:effect on plant growth and metal uptake by wheat,and on free living azotobacter[J]. Water Air & Soil Pollution,2002,138(1/2/3/4):165-180.
[11]Ramteke S,Sahu B L,Dahariya N S,et al.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vegetabl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16,7(7):996-1004.
[12]杜 鹃. 重金属污染七成重金属源于开采矿[N]. 广州日报,2015-09-18(08).
[13]Gulsen T. Inhibition of acid mine drainage and immobiliza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copper flotation tailings using a marble cutting was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Metallurgy,and Materials,2016,23(1):1-6.
[14]Tordoff G M,Baker A J M,Willis A J.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reveget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metalliferous mine wastes[J]. Chemosphere,2000,41(1):219-228.
[15]Hun-Dorris T. Groundwater problems spring to the surface[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04,112(3):159.
[16]González R C,González-Chávez M C A. Metal accumulation in wild plants surrounding mining wast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6,144(1):84-92.
[17]许宝健. 危险的隐患沉寂的金山[N]. 中国环境报,2009-03-06(06).
[18]祝玉学. 关于尾矿库工程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 金属矿山,1998(10):7-10.
[19]Johnson D B. Acidophilic microbial communities:candidates for bioremediation of acidic mine effluents[J].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 Biodegradation,1995,35(1/2/3):41-58.
[20]Chen Y,Wang C X,Wang Z J. Residues of source identification of persisi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farmland soil irrigated by effluents from biological treatment plants[J]. Environ Internat,2005,31(6):778- 783.
[21]丁真真. 中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与其植物修复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2007,14(3):19-20.
[22]徐红宁,许嘉林. 我国砷异常区的成因及分布[J]. 土壤,1996,28(2):80-84.
[23]申进玲,陈 蕾,李晓蕙,等. 固氮菌及其共生体系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J]. 中国农村小康科技,2006(6):68-69.
[24]Ahluwalia S S,Goyal D. Microbial and plant derived biomass for removal of heavy metals from wastewater[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07,98(12):2243-2257.
[25]Hussein H,Farag S,Moawad H.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Pseudomonasresistant to heavy metals contaminants[J]. Arab J Biotechnol,2004,7:13-22.
[26]Souza E M,Leda S C,Luciano F H,et al. Use of nitrogen-fixing bacteria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J]. BMC Proceedings,2014,8(4):23-31.
[27]廖瑞章,金荔枝,申淑玲. 利用固氮菌为指标确定土壤重金属毒性研究[J]. 农业环境保护,1989,8(4):5-9.
[28]滕 应,黄昌勇,龙 健,等. 铅锌银尾矿污染区土壤微生物区系及主要生理类群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3,22(4):408-411.
[29]Guo X J,Huang Q Y,Chen W L. Effect of microorganisms on the mo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environments[J]. China Appl Environ Biol,2001,8(1):105-110.
[30]Nies D H. Efflux-mediated heavy metal resistance in prokaryotes[J].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2003,27(2/3):313-339.
[31]Vasundhara G,Jayashree G,Kurup G M. Sequestration of nickel and copper byAzotobacterchroococcumSB1[J].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04,72(6):1122-1127.
[32]王淑芳,胡连生,纪有海,等. 重金属污染黑土中固氮菌及反硝化菌作用强度的测定[J]. 应用生态学报,1991,2(2):174-177.
[33]El-Enany A E,Issa A A. Cyanobacteria as a biosorbent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water[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2000,8(2):95-101.
[34]Brookes P C. The use of microbial parameters in monitoring soil pollution by heavy metals[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1995,19(4):269-279.
[35]Obbard J P. Ecotoxicological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sewage sludge amended soils[J]. Applied Geochemistry,2001,16(11):1405-1411.
[36]宣 瑛. 镉和乙草胺复合污染对早地土壤自生固氮菌种群和生物活性的影响[D]. 杭州:浙江大学,2006:6-16.
[37]周东美,王慎强,陈怀满.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复合污染的交互作用[J]. 土壤与环境,2000,9(2):143-145.
[38]贾会娟,祝 惠,袁 星,等. 克百威与镉单一及复合污染对土壤好气性自生固氮菌数量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7,26(10):529-532.
[39]黄 铮. 铜单一污染与铜镉复合污染对稻田土攘微生态的影响及抗性菌株的分离与特征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6:4-7.
[40]胡佳频,汤 鹏,易浪波,等. 钾长石矿区土壤固氮菌的多样性分析[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5,27(10):1127-1130.
[41]唐凤灶. 安徽铜陵铜尾矿原生演替过程中的土壤固氮菌研究[D]. 广州:中山大学,2010:2-3.
[42]Vitousek P M,Porder S,Houlton B Z,et al. Terrestrial phosphorus limitation:mechanisms,implications,and nitrogen-phosphorus interactions[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2010,20(1):5-15.
[43]杨容孑,刘柿良,宋会兴,等. 不同氮形态对龙葵镉积累、抗氧化系统和氮同化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2016,25(4):715-723.
[44]Epelde L,Becerril J M,Barrutia O,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lant and rhizosphere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 metalliferous soil[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0,158(5):1576-1583.
[45]Sriprang R,Hayashi M,Yamashita M,et al. A novel bioremediation system for heavy metals using the symbiosis between leguminous plant and genetically engineered rhizobia[J].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2002,99(3):279-293.
[46]李廷强,舒钦红,杨肖娥. 不同程度重金属污染土壤对东南景天根际土壤微生物特征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8,34(6):692-698.
[47]陈一萍. 重金属超积累植物的研究进展[J]. 环境科学与管理,2008,33(3):20-24.
[48]张学洪,罗亚平,黄海涛,等. 一种新发现的湿生铬超积累植物——李氏禾[J]. 生态学报,2006,3(26):950-953.
[49]祝鹏飞,宁 平,曾向东,等. 有色冶炼污染区土壤污染及重金属超积累植物的研究[J]. 安全与环境工程,2006,1(13):48-52.
[50]魏树和,周启星,王 新. 超积累植物龙葵及其对镉的富集特征[J]. 环境科学,2005,3(26):167-170.
[51]魏正贵,张惠娟,李辉信,等. 稀土元素超积累植物研究进展[J]. 中国稀土学报,2006,24(1):1-4.
[52]吴双桃,吴晓芙,胡曰利,等. 铅锌冶炼厂土壤污染及重金属富集植物的研究[J]. 生态环境,2004,13(2):156-167.
[53]魏树和,周启星,王 新,等. 某铅锌矿坑口周围具有重金属超积累特征植物的研究[J].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4,5(3):33-39.
[54]周建军,周 桔,冯仁国.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治理战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29(3):315-320.
[55]Sayler G S,Ripp S. Field application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roorganisms for bioremediation processes[J]. 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2000,11(3):286-289.
[56]Verma N,Singh M. Biosensors for heavy metals[J]. Biometals,2005,18(2):121-129.
[57]Bruschi M,Goulhen F. New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to remove heavy metals and radionuclides using Fe (Ⅲ)-,sulfate-and sulfur-reducing bacteria[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Environmental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ies,2007:35-55.
[58]Divya B,Kumar M D.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 with enhanced bioremediation[J]. Research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2011,6(4):72-79.
[59]Kostal J,Yang R,Wu C H,et al. Enhanced arsenic accumulation in engineered bacterial cells expressing ArsR[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4,70(8):4582-4587.
[60]Kang S H,Singh S,Kim J Y,et al. Bacteria metabolically engineered for enhanced phytochelatin production and cadmium accumulation[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7,73(19):6317-6320.
[61]Hasin A A,Gurman S J,Murphy L M,et al. Remediation of chromium(Ⅵ) by a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um[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09,44(1):400-405.
[62]Ackerley D F,Gonzalez C F,Keyhan M,et al. Mechanism of chromate reduction by theEscherichiacoliprotein,NfsA,and the role of different chromate reductases in minimizing oxidative stress during chromate reduction[J].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4,6(8):851-860.
[63]Valls M,Atrian S,de Lorenzo V,et al. Engineering a mouse metallothionein on the cell surface ofRalstoniaeutrophaCH34 for immobiliz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J]. Nat Biotechnol,2000,18(6):661-665.
[64]Brim H,McFarlan S C,Fredrickson J K,et al. Engineering deinococcus radiodurans for metal remediation in radioactive mixed waste environments[J]. Nature Biotechnology,2000,18(1):85-90.
[65]Murtaza I,Dutt A,Ali A.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ofEscherichiacoliorgano-mercurial lyase gene and its expression[J]. Indi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2002,1(1):117-120.
[66]Zhao X W,Zhou M H,Li Q B,et al. Simultaneous mercury bioaccumulation and cell propagation by genetically engineeredEscherichiacoli[J]. Process Biochemistry,2005,40(5):1611-1616.
[67]Kiyono M,Pan-Hou H. Genetic engineering of bacteria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of mercury[J].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2006,52(3):199-204.
[68]Mrinal B,Palombo E A,Belinda D,et al. A Tn5051-like mer-containing transposon identified in a heavy metal tolerant strainAchromobactersp. AO22[J]. Bmc Research Notes,2009,2(1):1-7.
[69]López A,Lázaro N,Morales S,et al. Nickel biosorption by free and immobilized cells ofPseudomonasfluorescens,4F39:a comparative study[J]. Water Air & Soil Pollution,2002,135(1/2/3/4):157-172.
[70]Sriprang R,Hayashi M,Ono H,et al. Enhanced accumulation of Cd2+by aMesorhizobiumsp. transformed with a gene fromArabidopsisthalianacoding for phytochelatin synthase.[J]. Appl Environ Microbiol,2003,69(3):1791-1796.
[71]贾昌梅,牛显春,钟华文,等. 珠江三角洲湿地污泥重金属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5):442-447.
[72]郭李凯,任珊珊,毕 斌,等. 煤矸山下农田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8):467-470.
[73]周启星,魏树和,刁春燕. 污染土壤生态修复基本原理及研究进展[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7,26(2):41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