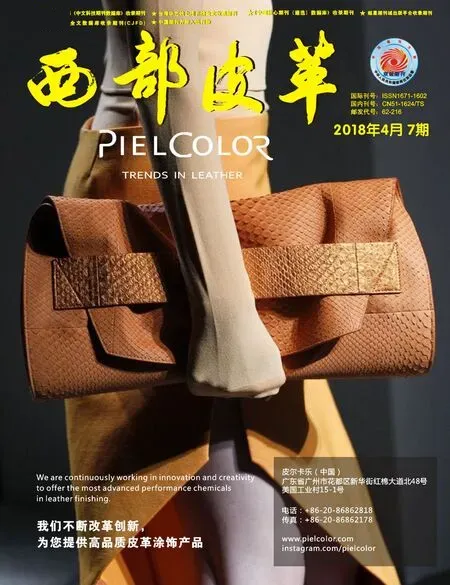浅析汉墓壁画与画像石区别之处
甘 琴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0000)
整个汉朝有着丰富多样的墓葬遗址,不仅遗址的数量多,而且有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汉代墓葬艺术研究的重点对象是画像石墓,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很多汉墓壁画遗址被挖掘出来,汉墓壁画才逐渐变成汉代墓葬遗址的热点研究。如贺林西在《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1]一书中,重点对汉墓壁画形成的思想背景与观念形态、图像及风格传统、艺术成就及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黄佩贤的《汉代墓室壁画研究》[2]一书中主要研究了两汉时期墓葬遗址中的壁画内容。现今研究汉代墓室壁画的资料很少而且很不完善。导致近代许多学者仅从壁画墓的本身去研究,鲜少将画像石墓和壁画墓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将汉墓壁画与汉墓画像石之间混为一谈。因此,本文从搜集、分析和整理相关的墓室遗址的资料入手,着重从汉代墓葬分布、墓葬画面内容、墓主身份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汉代壁画墓和画像石墓的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两种墓葬形式之间存在的巨大不同,更加完善了汉代壁画墓的研究。
1 从墓葬遗址分布区别汉画像石与汉墓壁画
根据贺西林《古墓丹青—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提到以墓室壁画为依据,按布局、风格变化和内容所做出的排纪年分析,有人主张将汉壁画墓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汉前期:以洛阳秋墓作为代表,壁画墓图画的重点在于墓顶,主要画了墓主人升仙和驱邪两个独立的壁画,这类图像受到当时阴阳学说影响较深;第二阶段是西汉的后期,包括曲江池、烧沟61号墓、洛阳八里墓和西交大墓,墓顶的图画不再绘制升仙和驱邪,而是绘制日月星象等图像,或者绘制新出现的历史故事作为绘画题材;第三阶段王莽时代至东汉的前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第四阶段是东汉的后期到三国汉魏之际,分布的范围大面积扩宽,中原、内蒙古、辽阳、甘肃四个地区广泛的出现了汉代墓室壁画遗址[3]。”这些地区汉代壁画墓的共同之处是大多都以传统的农业生活题材为主,主要描绘墓主人在去世前的工作、出行、游历等,而原本出现在壁画中的神怪则由其他的祥瑞所取代。“在这一时期,壁画墓的图像的重心也随之下移,各个墓室的壁画内容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主墓室画出行的车马和平时的家庭生活还有宴饮客人等、耳墓室则画上厨师或者仆人的劳作和农田庄园的活动等。”同时通过对以上这些汉代壁画墓遗址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西汉的前期有2座壁画墓都分布在洛阳;西汉的后期有6座壁画墓主要也是分布在河南境内;王莽至东汉的前期有11座壁画墓,则分布在山东、安徽、山西、广东、海南和洛阳;东汉后期至三国汉魏之际有30多座壁画墓,大多数分布在山东、海南、内蒙古、洛阳、甘肃、辽阳、江浙、安徽。从以上汉壁画墓的遗址分布区域来看,洛阳地区的壁画墓遗址和其他地区相比,不仅有数量多的特点,而且还存有汉代各个不同时期的壁画墓遗址。“洛阳诸墓是迄今已发现的汉壁画墓中分量最多、也是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部分[4]。”
根据墓葬遗址分布资料显示,汉壁画墓遗址在西汉时期出现在广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这三个省,东汉时期则又在此三地之外又出现了辽阳、江浙、晋西、山东、蒙古等其他的地方,遗址的范围跟西汉时期这三个省市而言,涉及面积有所扩大了些。而从西汉壁画墓的遗址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省发掘的壁画墓的存在似乎是个特例。长安和洛阳在整个汉代都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现在这两个地方就是河南省和陕西省。东汉时期壁画墓出现的地区,在西汉时期的三个地区的基础上,多增加了十一个地区,虽然这个增加的数量不多,还是可以说明,两汉时期的壁画墓虽然已经在全国都有遗址出现,但壁画墓依然不具有地域分布的普遍性。从以上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汉壁画墓的特点不光是在全国分布范围面积小,而且还没有连贯性和辐射关联性。
汉墓画像石是汉代最广泛的墓葬形式。根据汉代墓葬遗址发掘材料显示:“汉画像石墓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汉画像石墓的地域分布面积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汉墓画像石遗址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5]根据墓室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统计,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发掘的画像石墓大约有两百多座。江苏省有大约三十余座,河南省有大约五十四余座(南阳占四十座),陕西省有二十余座,山东省有三十余座,江西省约有十座。在我国天津市、云南省、湖北省、陕西省、浙江省、贵州省等地也相继发掘出了汉画像石墓或画像石刻的遗址。“四川省、重庆市的汉画像石墓葬遗址主要则是以崖墓、石棺、石函等遗址为主。”[6]随着汉代画像石遗址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全国现在的汉代画像石墓的数量多达有一万以上。
2 从墓葬画面内容区别汉墓壁画与石像画
墓葬在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它不仅具有政治要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内容,还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样也是各种封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作为墓葬艺术形式的存在,其中自然就会包含着许多两汉时期的人对自然和对生死的看法。根据许多墓室的图像绘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墓室绘画更倾向于对于未知的世界的想象,而墓室中的绘画则不光包含了他们对生命的是怎样延续和转化的思考还存在着对长生不死的期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墓壁画与画像石有着一样的死即长生的墓葬思想。“壁画、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总体说是表现墓主人的起居、生平事迹的,反映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7]。”
在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的题材研究和划分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从西汉经新莽时期至东汉壁画墓与画像石墓不同的发展脉络。第一为西汉时期。墓葬的图像几乎全是神仙信仰为主。以洛阳地区的壁画墓室绘画图像为例。该墓壁画图像几乎全是龙蛇神怪、伏羲和女娲等神仙类图像等。墓主人驾驶着龙凤车撵愉快地奔向安乐祥和的仙界,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楚帛画《人物御龙图》中的场景。第二是新莽至东汉初期。虽然此期的主题仍以神仙信仰为主,但是凡人的形象已经摆脱了神仙的影子,成为独立的艺术形象。第三是东汉时期。东汉时期的壁画墓的图像内容越来越具有世俗化的倾向。与画像石不同,神仙怪兽之图像突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墓主人在帷幔下安享美食的图像。图像中,仆人侍从恭顺地各司其职,各种乐舞和百戏表演频繁出现,流露出与同时期画像石、陶俑不相似的题材。在同一时期的画像石墓中,伏羲、女娲很多时候都是单独出现,相比之下西王母的出现在画中的情况较多,而且庄园图画的内容越来越少,楼堂建筑变得与未来月简朴和抽象,历史人物也很少出现在图像上。而在壁画墓的画像中,伏羲女娲很多时候都会尾部交缠在一起的出现,而且还会出现多种生产的大庄园、在田间耕作的农民;很多套车马出行的现实生活的图像。
3 从墓主身份来区别汉墓壁画和画像石
“发掘遗址的过程中发现了两座西汉前期的汉壁画墓,一座是位于广州象郡的南越王公墓,另一座是位于河南芒山的梁王侯墓,两座汉壁画墓都属于王公相侯坟的大墓。至今为止我国汉壁画墓发掘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河南洛阳,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许多的洛阳汉壁画墓墓主人身份和地位都相对较高。”[8]根据洛阳古墓博物馆统计出的古墓资料显示:“西汉的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而这个墓的墓主人生前是一个获两千石级别俸禄的武官;洛阳的西汉卜千秋大墓,这个墓主人卜千秋生前是汉代一个郡级的县官;洛阳的偃师杏村壁画墓中发现车马出行的壁画,墓主人则是在汉代可以享受九乘安车待遇的大官员,《汉书·武帝纪》记大鲁申公出征时是“遣使者安车加蒲轮,束帛满锦加壁,征为鲁申公[9]。”可见在汉代这个安车待遇的规格等级之高。王莽时期的洛阳有一座描绘着日月星象图像的壁画墓被发掘出来,而这个墓的男性墓主人生前是汉代的一名武官;“洛阳谷园东汉壁画墓和河南塔山壁画墓的墓室中都有描绘着日月天象和神兽的壁画,而这两个墓的墓主人,他们也都是享有很多门卒守卫和女仆奴隶的贵族群体。”“内蒙古的壁画墓是我国现今发现的壁画墓遗址中壁画分布的面积最大,绘画的种类数量也最多,同样也还是绘画构图形式最为复杂的壁画墓遗址,“格林尔的墓主人生前就是通过汉代察举孝廉后担任过“都尉行上郡属国”、“繁阳令”、“河西长史”、“护乌桓校尉使持节”等官职,可谓的确是仕途显达。”
各个分布区域的画像石墓的内容题材各有侧重,雕刻艺术也各有不同:“山东区域汉画像石以质朴厚重、古风盎然见长,表现的是儒家道德观为主的齐鲁文化;河南区域汉画像石则灵动流畅、端庄雄伟,表现的是中华民族一直流传的正统的中原文化;四川区域的汉画像石活泼俊秀、精巧唯美,表现的是巴蜀文化的活泼多样性;陕北区域汉画像石以淳朴自然、简练绚烂的风格体现出了陕北文化的边郡特色。”
按照众多的汉画像石墓遗址的考古资料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画像石墓兴起于西汉晚期,源于石椁墓,石椁墓在西汉墓中属于小型墓葬,说明画像石墓最初源于社会下层。这种下层社会因地取材的葬俗是很难被囿于传统礼制的汉代统治阶级接受的,所以在画像石墓墓主人身份大多是封爵在列侯以下,俸禄在二千石以下的中下层官员,地方商贾、富绅以及平民百姓,相反大多数统治阶级的上层如诸侯王公、列侯将相、或者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基本上都不会选择使用画像石墓来安葬。”就壁画墓和画像石墓者两种墓葬形式而言,统治者更加喜欢用壁画墓这种墓葬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很多的墓葬遗址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从壁画墓和画像石墓的墓主人身份来看,壁画墓的墓主人属于中上贵族,而画像石墓的墓主人则大多数是中下贵族和平民百姓等,这是可以初步定下结论的了。
4 结语
在汉代,虽然汉壁画墓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汉墓壁画确实是与汉墓画像石极其不同的墓葬形式。可以说汉墓壁画是汉代墓葬遗址中的珍宝。但由于墓室壁画一般有工匠直接绘制在墓室壁画上,不易保存,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在本文中,从墓葬遗址分布看,壁画墓的遗址分布比较集中且没有辐射性,而画像石墓的遗址分布范围则更为广泛和连贯;从墓葬画面内容来看,壁画墓反映的的图像画面内容是以神话世界主,而画像石墓的画面内容表现的是以现实生活为主;我们从墓葬遗址来看,壁画墓墓主人的是属于王公贵族等级,但是画像石墓的主人大多是中下的贵族和平民百姓。通过汉画像石墓和壁画墓两种墓葬之间的比较研究,发现汉壁画墓的研究资料还是很少,导致壁画墓的研究方向和深度都有限。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不断研究考古资料的去反复验证结论的真实性,同时也需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认真的研究态度去完善我们对汉代墓葬绘画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36.
[2]黄佩贤.汉代墓室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58.
[3]夏超雄.汉墓壁画、画象石题材内容试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64-77.
[4]汪小洋.汉壁画墓墓主人阶层探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1):30-33.
[5]沈伟棠.图像的两端——汪小洋教授《汉墓壁画的宗教思想与图像表现》述评[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2):49-52.
[6]李银德.徐州汉画像石墓墓主身份考[J].中原文物,1993(2):38-41.
[7]冯军平,郝慧芬.离石汉代画像石区域分布及墓葬形制 [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2(3):135-136.
[8]汪小洋.汉画像石宗教思想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4.
[9]郝利荣.汉代石椁画像与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从汉代墓葬建筑的“象生环境”和“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谈起[J].文物世界,2013(5):15-21.
[10]刘茜.汉代生死信仰的变迁与汉画像石的兴盛[J].学术月刊,2014(6):10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