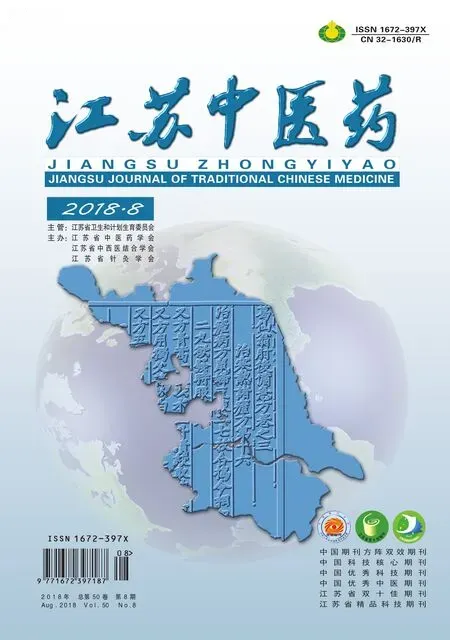从肾积奔豚角度认识惊恐障碍
曾 亮 范宇鹏 杨志敏
(广东省中医院,广东广州510000)
惊恐障碍是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恐体验,表现为严重的窒息感、濒死感和精神失控感,伴有植物神经症状,如:感觉异常、心悸、头晕、震颤等,症状可迅速发展到高峰,持续时间很短便可自行缓解,间歇期除有预期焦虑恐惧外,可无任何不适,反复发作。惊恐障碍的主要症状与中医奔豚的描述甚为相似,奔豚亦表现为一种发作性疾病,患者常有逼真的感觉异常,如“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令人喘逆……少气”,“发作欲死,复还止”等。
中医无“惊恐障碍”的病名,多根据其临床表现归属于“惊悸”“卑惵”“奔豚”等范畴,认为与心、肝、胆、肾、脾功能失调关系密切[1]。笔者在临床上从《难经》肾积奔豚的角度来理解和治疗惊恐障碍,在临床实践中佐证了肾积奔豚理论在惊恐障碍中的运用,疗效确切,现探讨于下。
1 肾与惊恐的关系
肾在志为恐,肾虚不能主志,志弱不能制恐,故如《灵枢·经脉》云:“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心如悬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七情之一的惊亦与肾联系密切,《素问·示从容论》中云:“时惊……是肾不足也。”
古代部分医家认为惊恐有相似之处,应将惊、恐视为同一种情绪,如《丹溪心法》云:“惊者恐怖之谓。”《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云:“恐则善惊之谓。”现代医家亦提出了“肾藏志,应惊恐”,“惊恐伤肾”的观点[2]。可见,肾与惊恐障碍的核心情绪联系密切,互为影响。
2 肾积奔豚与惊恐障碍
奔豚一词,始见于《灵枢·邪气藏腑病形》:“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难经》中作“肾之积名曰贲豚”,《金匮要略》作“奔豚气”。后世医家对惊恐障碍的认识多不离《金匮要略》中有关“奔豚气”肝气郁结化火上冲、阳虚感寒、水饮内动的描述,忽略了对《难经》肾积奔豚的进一步认识。
笔者在临床上观察到,惊恐障碍的患者常伴见口干,喜饮热饮,饮不解渴,腰膝酸软,性功能下降,舌淡胖、苔白腻或润,尺脉沉紧,寸关浮等症状。追问病史,患者常在年幼时有惊吓史,男性常有手淫过度、过子时而不眠,女性则常有反复流产或产后调理欠佳等肾精耗损病史,部分合并有肝囊肿、肾囊肿、肾结石、前列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病史。提示惊恐障碍与《难经》肾积奔豚肾气虚寒,阴寒成积,虚气反逆密切相关。
3 肾积奔豚的病机
张志聪在《灵枢集注》为奔豚注解:“肾为生气之原,正气虚寒则为沉厥,虚气反逆故为奔豚。阴寒在下,故足不收。肾开窍于二阴,气虚不化,故不得前后也。”肾积奔豚中的“积”,《灵枢·百病始生》指出“积”其形成的病因病机为“卒然外中御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难经·五十五难》认为“积者,阴气也”。
从《内经》和《难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肾积奔豚与寒邪和情志的变化相关,产生有形之阴邪互结于腹中,这些有形之邪可以包括水湿、痰饮、瘀血等,影响气机通畅而导致奔豚。这亦与《金匮要略》中论述奔豚气的病因“皆从惊恐得之”和发汗后阳虚,复感外寒或引动水饮有共通之处。究肾积奔豚之病机,诚如《灵素节注类编·诊脉辨脏腑病证》云:“皆下焦阳虚,阴邪郁闭故也。”
4 温氏奔豚汤之方解
笔者立足于肾积奔豚“下焦阳虚,阴邪郁闭”的病机,临床上选择温氏奔豚汤加减治疗惊恐障碍。温氏奔豚汤以熟附子和肉桂温补肾阳,破沉寒痼冷,温中降逆;人参“补五脏”和“安精神”;炙甘草以国老之名,坐镇中州,一可固护脾胃后天之本,生化有源,二可制附子和肉桂之火热峻猛;《本草经疏》言砂仁为“开脾胃之要药,和中气之正品,若兼肾虚,气不归元,非此为向导不济”;以沉香“坚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泻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 (《医林纂要》);牛膝引虚阳下行;茯苓、泽泻祛湿以恢复中焦升降之枢机;李可老中医认为,于大队辛热燥药之中,重用性润之山药,健脾和胃益肺,补肾强精益阴,滋阴配阳,益火之原,以消阴翳[3]。诸药合用,补肾逐寒,引火归原,阳回则阴寒自消,气机升降有序,制伏奔豚。
考历代医家治疗奔豚的方药,温氏奔豚汤组成有迹可循,它的渊源与桂枝加桂汤、苓桂草枣汤、奔豚丸、理中汤联系密切,如:《金匮要略》以桂枝加桂汤治疗汗后伤阳,复感寒邪,阴寒上凌之“气从少腹上至心”者;以苓桂草枣汤治疗汗后伤阳,水饮内动,“脐下悸,欲作奔豚”者;《活人方》有奔豚丸,以人参、茯苓、泽泻、沉香、肉桂、附子等炼蜜为丸,治疗积聚奔豚;《伤寒全生集》中用理中汤去白术加肉桂治“气在脐下筑筑然而动”之“欲作奔豚”。
5 温氏奔豚汤之运用
李可老中医[3]认为,本方运用要点当属肾阳虚衰,肝寒凝滞,寒饮内停,冲脉挟饮邪上冲,以“厥气上攻”为主症,即方名“奔豚”之取意。
临床上一部分病人虚阳浮于上,可能出现咽痛、心烦、反复口腔溃疡等“上火”的表现,此时不应受病家言语和症状影响,而投以清热寒凉之品,只要辨证精准,即可投以温氏奔豚汤。除了用淮山、牛膝和李可老中医所言“上有假热,热药冷服,偷渡上焦”之外,还可如扶阳名家祝味菊谓之“虚人而躁甚者,气怯于内,阳浮于上……甘凉之剂,可令小安,缓和之效也,因其小效,而频服之,则气愈怯则阳愈浮矣,此非亢阳之有余,乃阳衰不能自秘也,此时予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原,导龙入海,则可矣”。临床上加龙骨、牡蛎、磁石潜降其虚亢之阳。
6 病案举隅
蔡某,男,39岁。2017年8月24日诊。
患者因“反复发作头晕和气上冲感2年”来诊。患者2年前因体检发现高血压病,思及家中父母亦有高血压病史,担忧恐惧,遂发作头晕,伴呼吸不畅,气从胃部上冲至胸,至胸闷心悸,严重时有濒死感,常自测血压正常值范围,症状持续约2~5min后可缓解,反复至内科、急诊科就诊而症状反复,由内科医生劝导至心理睡眠科就诊,接诊时见患者形胖,对症状紧张关注,既往有熬夜史,纳可,大便烂,眠易早醒,少气,性生活减少,舌淡胖红、苔白腻浊,脉尺沉,余弦滑。辨证属脾肾阳虚,湿浊内蕴。治以温补脾肾,化湿降逆。选方温氏奔豚汤加减。处方:
熟附子10g(先煎),肉桂5g(后下),茯苓30g,泽泻30g,怀牛膝20g,炙甘草30g,山药30g,人参10g(先煎),砂仁10g(打碎后下),沉香5g(后下),山萸肉30g,生黄芪30g,石菖蒲10g,龙骨30g(先煎),牡蛎30(先煎)。7剂。并告知患者及家属对此疾病的应对措施,调整好心态。
8月31日二诊:服药后气上逆感明显好转,头晕发作频率和程度减轻,无濒死感,焦虑紧张减轻,遂在原方的基础上继续加减,共服药20余剂,未再发作头晕和气上冲感,后期以四逆汤加减巩固疗效。患者定期于门诊取降压药物,随访诉症状未再发作。
笔者运用温氏奔豚汤治疗惊恐障碍,临证加减变通,并不拘泥肾积奔豚的典型症状,只要围绕“下焦阳虚,阴邪郁闭”核心病机,起病见突发突止和有咽、胸、胃的感觉异常,均可选用温氏奔豚汤加减。惊恐障碍的患者,心理层面包含了不安全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笔者在治疗的过程中,遵《灵枢·师传》的“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的观点,常告知患者本病的特点和发病后怎样应对,家属如何陪伴,调整患者对疾病的错误认知,建立患者对疾病的信心,更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康复和防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