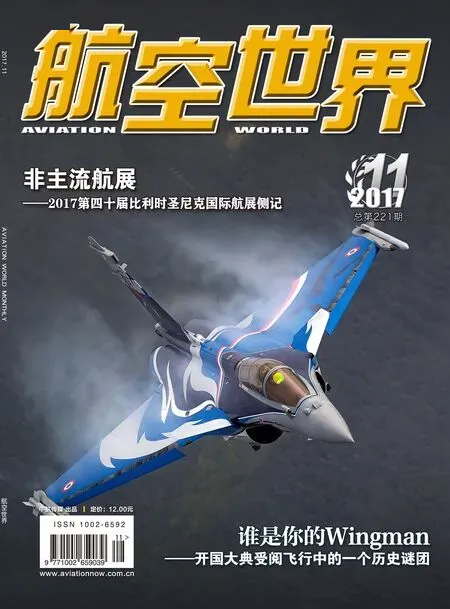谁是你的Wingman
--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中的一个历史谜团
文/肖邦振

1950年中国空军C-46运输机的涂装。小图为开国大典时C-46的涂装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中,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紧接着为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最后是1架L-5通信联络机、两架PT-19教练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共计有5种机型17架飞机。由邢海帆为带队长机的飞行员们驾驶这些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检阅。其中16架飞机的飞行员已有定论,唯有3架运输机中的左僚机冒出来两个机组(徐骏英、姚峻机组与邹耀坤、王恩泽机组)。时至今日,到底是哪个机组参加历了受阅飞行仍然是一个谜。
笔者花费多年多时间寻访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员及军委航空局老前辈,并且撰写了《飞过天安门》一书,仍未就该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正当笔者为此苦恼之时,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邓亦兵女士告诉笔者一个新名词叫“口述史学”,说这是近些年从西方传入的新型学科。她说笔者通过采访撰写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由当年参与此事的人员,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从中得出见证开国大典的一个综合历史情况,就属于口述史学的范畴。由于每个人的经历,看问题的角度,个人记忆力都不一样,所以对同一件事的说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正是口述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
受此启发,笔者在这里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出来,供感兴趣的朋友研究参考和批评指正。
事情的提起
1986年3月1日,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该校纪念委员会专门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并绘制了受阅飞行编队序列图,首次公开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的飞机和人员配备情况。这个图中,左僚机机组标注为徐骏英和姚峻,同时图下括号注明“同乘的飞行员还有邹耀坤和王恩泽”。

开国大典C-46涂装

2010年3月26日,笔者在广州拜访邹耀坤

《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绘制了受阅飞行编队序列图,首次公开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的飞机和人员配备情况(右图)
2003年10月16日,为撰写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一书,笔者在广州拜访了邹耀坤老人。邹老简要地向笔者讲述了1949年1月15日,他和刘焕统、宋宏儒一起驾机起义的情况。之后,却重点讲述了开国大典时他作为刘善本左僚机飞越天安门的事情经过。邹老当时气愤地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左僚机位置被别人取代了,希望你这个作者能够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还‘左僚机’的真实面貌。”为此, 邹老还是笔者提供了一些论证资料。
其中,1987年10月20日,空军司令部军校部刘兴军给邹老的信引人注目。信中谈到:“关于《东北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中记载参加开国大典飞行人员名单的问题,王恩泽同志于8月22日又向空军林虎副司令作了反映。林副司令员阅后批示,编辑组同志认真查一下,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您和王老提出的问题,在纪念册印前我们已经得知,但是当时由于送稿时间紧迫,我们只找了在京和知道地址的当事人作了调查,都没有说全人员名单。历史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只好按油江(当时的地面指挥)写的回忆录和当代中国军事卷中的名单写了上去,但考虑到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特意在名单后注明:您和王恩泽同志‘同乘’参加了阅兵。”笔者查阅1987年2月空军司令部编写的《中国空军史料》第四辑。其中,油江在《回忆华北航空处》一文(纪念册编辑时还只是一篇征文稿)中确实谈到受阅飞行编队的“左僚机”是徐骏英和姚峻,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军事》则没有相关资料。
为此,邹耀坤曾写信询问同一个机组的副驾驶王恩泽。时为空军某军副政委的王恩泽于1987年6月27日复信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件事,我想并非是疏忽,很可能是有人反映了不真实的情况。”

王恩泽

徐骏英
由于受阅飞行中运输机“左僚机”的位置存在着争议,使得此事成为了邹耀坤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他多次撰写文章和上广州电视台发表讲话澄清事实。同时,邹耀坤还留心报刊上有关开国大典的文章,凡是与此有误的他都要写信说明情况,得到《人民日报》和航空博物馆等多家媒体的回信。比如,《人民日报》曾发表过《1949年受阅飞机空中阵形图》,邹耀坤一看仍然没有他“左僚机”的位置,便立即去信说明情况。《人民日报》委托华南分社总编室给他回信说:“由于我们编辑人员缺乏对史料的详细了解,以致对开国大典的飞机编队没有搞准确,误写了人名。作为史料本应该准确,所以先向您老表示歉意。”
199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来临的时候,空军政治部写给邹耀坤同志的慰问信中说:“您曾作为共和国第一代飞行员,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神圣使命,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空军的发展壮大凝聚着您的心血。共和国不会忘记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人民空军更不会忘记您。”这封信充分肯定了邹耀坤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令他十分欣慰!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受阅飞行运输机“左僚机”一事未能涉及,可见澄清事实并不是一封信所能承担的。笔者查阅上世纪末空军司令部出版的《空军飞行人员名录》,也明确邹耀坤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
事情的难点
1989年10月,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作序的《当代中国空军》一书,没有再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中“左僚机”飞行员一事。
1992年6月,空军政治部编写并出版的《蓝天之路》,正式收入前述油江撰写的那篇回忆录时,删除了“左僚机”之说,仅谈到“第5分队长机是刘善本,参加的受阅飞行员有谢派芬等”。
1996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空军大辞典》一书,其中“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条目也只撰写了编队飞行情况,没有涉及飞行员名单。
2007年8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空史(第二版)》说到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也只列出了分队长的名字。
陆续出版的空军大部头历史著作,对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编队“左僚机”采用回避的办法。可见,邹耀坤等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空军领导机关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开国大典的参加者、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将军。他说:“由于当时参加受阅的飞行中队刚刚组建,人来人往,各人都把精力放在自己的飞行上,加之时间又短,大多数人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当时,军委航空局从接受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任务到具体实施,仅一个月时间进行训练,据总领队邢海帆写的受阅飞行总结,各分队长机于10月2、23、28日在天安门进行过预演,10月8、24日仅两次全体到天安门演练,其余时间都在南苑机场训练,加之参训飞行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个人精力都在自己的驾驶杆,对别人、别的分队印象不深是正常的。这也是纪念册编写组在京调查,谁都“没有说全人员名单”的原因。

2003年4月11日,笔者在成都采访杨宝庆

2004年7月1日,笔者拜访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
为此,笔者到解放军和空军档案馆查阅有关开国大典的档案资料,也只见到各个受阅分队长的名字,没有查到各架飞机飞行员完整的档案资料。笔者还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报刊关于开国大典的报道,《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到飞行员时,仅点了 “一个姓王的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特别是运输机分队的分队长刘善本,右僚机飞行员谢派芬,飞行员徐骏英、王洪智、王恩泽等人过早的去世,也增加了查对的难度。
笔者了解情况时,运输机分队健在的仅有邹耀坤、姚峻、杨宝庆3人,由于邹耀坤与姚峻同为“左僚机”的当事人,杨宝庆则成为唯一的公证人。2003年12月,杨宝庆(受阅飞行时为刘善本的副驾驶)给阎磊(受阅飞行的参加者,曾著有《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组建始末》一文)的回信说:“关于邹耀坤同志提出受阅异议之事,以前您曾提过此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吗?我看他提的事,不合乎实情,我敢肯定徐和姚参加了受阅,因为徐一直在飞C-46运输机,而邹没有飞过C-46飞机,我的印象他在哈尔滨飞苏式双发飞机。而王恩泽曾是飞过C-46的学员,怎么能搞到一起吗?老徐和我一直在齐齐哈尔第一大队飞C-46飞机,当过教员,国庆节前调北京飞行队……对邹在飞行队怎么没有印象呢?”2004年12月12日,杨宝庆曾就笔者提出的问题回信说:“国庆50周年,我与同住成都的徐骏英一起到成空机关领取空军政治部的慰问信和纪念品。怎么能在他逝世后就说不呢?”
笔者的分析
2009年9月17日,《空军报》第4版刊登署名文章:《“开国大典,我是左僚机”——记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第2梯队(应该是第3梯队,以下同——笔者注)飞行员邹耀坤》一文,该报编者按指出:“近日,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第2梯队飞行员、原空军某航校飞行顾问邹耀坤老人致信本报,反映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宣传报道中,有些媒体因所引史料失实,误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第2梯队左僚机飞行员写成他人。最近,有地方媒体仍沿用错误史料。为还历史以真实,邹耀坤老人特请本报予以澄清。”
这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姚峻的夫人周素雯给笔者打电话说,这个编者按推翻了空军领导认可的“纪念册”的名单。笔者表示姚副参谋长可直接同报社联系,周大姐说姚已患病住院,好在前些年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可见,该报编者按并不能一锤定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各方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能随便否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左僚机”仍然一个“谜”。
综合起来,笔者有以下观点。

参加受阅的部分老飞行员(左起阎磊、林虎、方槐、邢海帆、姚峻),于35年后见面合影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空中阅兵的P-51野马战斗机涂装
(一)笔者比较尊重杨宝庆的话:“我敢肯定徐和姚参加了受阅。”“徐一直在飞C-46运输机,而邹没有飞过C-46飞机”。这里,杨宝庆所说的“徐”即徐骏英,1945年8月28日,他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曾见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以后国共谈判时还驾机运送过周恩来代表,1949年2月19日驾机起义后,分配到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个人分析刘善本作为分队长,在邹耀坤和徐骏英两人中肯定会选择飞运输机的徐骏英为“左僚机”。此外,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员,35年后见面合影,其中就有姚峻。据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地面指挥员李裕介绍,这张照片是在空军大雅宝招待所拍摄的。当时摄影师招呼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合影留念,林虎、方槐、邢海帆、姚峻、阎磊等才从人群中走出来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受阅飞行带队长机邢海帆握着姚峻的手。根据这张相片,很难否定姚峻参加过受阅飞行。
(二)邹耀坤证据确实,难以否定其“左僚机”的位置。笔者采访邹老时,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按照C-46运输机的座舱设计,前面有正、副驾驶两个座位,正驾驶飞行员一般坐在左座位,副驾驶则在右边。在飞行编队训练讲评时,刘善本机长曾批评邹耀坤编队间隔距离过大。邹耀坤分析认为:自己在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时,常常坐在右座带飞新飞行员,对右座驾驶比较熟悉;运输机3机编队飞行时,邹耀坤作为正驾驶按规定在左座就坐,这个位置限制了他向右观察的视线,进而影响了对编队间隔的正确判断。邹耀坤找到原因后,报请长机飞行员刘善本批准,在受阅编队飞行时,与副驾驶王恩泽对调了座位,正驾驶邹耀坤坐在右座位,王恩泽则坐在左座位。由于坐在右座位比较容易观察前面的长机和与自己平行的右僚机,就便于保持同前面长机、右僚机飞行编队的队形,按规定的间隔、距离驾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受阅飞行的当天,按规定除机组人员外,飞机上不准其他人员上机观看,只批准几位记者来采访,并进行空中摄影。起飞前,由于邹耀坤所在左僚机有摄影记者,机组人员得到方便单独在飞机前留影,连飞机机号8003也拍摄下来了——这是邹耀坤等驾机通过天安门留下的重要纪念。同时,邹耀坤还提供了运输机飞向天安门的珍贵照片。以上细节体现了真实性,其中的照片更有说服力。

2003年4月11日,笔者在成都采访杨宝庆

2004年7月1日,笔者拜访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
历史事件有时会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难以展现它真实的面目,在给当事人和读史者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吸引了感兴趣的人们去探寻真相。虽然探寻之下真相往往仍旧掩藏在谜团中,但也许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