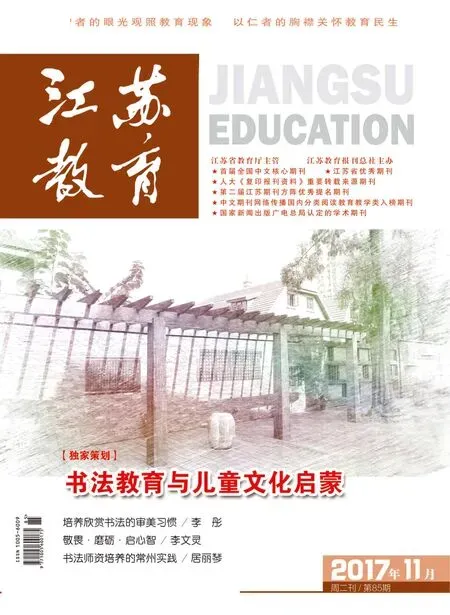篆刻艺术中的“非秩序”
篆刻艺术中的“非秩序”
陈慧清
视觉上“秩序感”的发展是中国篆刻艺术从初创到兴盛的重要原因,过于秩序化,也会阻碍篆刻艺术的发展,走上穷途末路,如明代时期的“九叠篆”印。美是秩序与变化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历代篆刻家们采取了多种使视觉“秩序”变化的方法。试从先秦文字入印、锈涩与糜烂、取法急就章三方面探讨篆刻艺术中的“非秩序”。
篆刻;非秩序;运动感官
秩序的意思是有条理地、有组织地安排各构成部分,多是人理性思考后的结果。中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从先秦古玺、汉印到明清以降的文人篆刻,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构成、风格丰富多彩,令人心旷神怡!汉印是我国篆刻史上的高峰,最主要的贡献是汉印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秩序”的处理方法,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摹印篆字体,专门用于布置方寸印面,其特点为外形方正,笔画多为横平竖直、粗细基本相等、间距基本均匀,等等(图1)。那平稳均匀和其顾盼呼应的视觉化秩序处理历来是后学者的楷模。这种处理技法做得最极致者为近代陈巨来。还有对称、均衡等秩序处理方式已于本人拙作《篆刻中的秩序》〔发表于《江苏教育》(书法教育)2016年第9期〕介绍过。美是秩序与变化的统一。此文将介绍一下使之“变化”的“非秩序”处理方法。

图1
一、先秦文字入印

图2

图3
高度秩序化的汉印体系出现之后,在唐代出现了以先秦文字入印的现象,现今发现最早的是五代杨凝式在《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中的用印“凝式”,宋代以先秦文字入印多出于文人用印,如贾似道的用印“似道”(图2)等。先秦文字,还未到秦统一文字的时候,属于大篆时期,字法杂乱多变(图3为高明、涂白奎著《古文字类编》增订本第366页“易”字的古文字写法,前三排为秦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写法,最后一排为秦统一文字后的小篆写法),使用此类文字入印,应该就是为了改变长期统治印坛的汉印式秩序感,使印面加以变化,出奇制胜,到明清乃至当今成为篆刻创作的主要流派之一。以宋代贾似道的用印“似道”为例,明显打破了汉印以“笔画多为横平竖直,笔画粗细基本相等”的秩序,改为以弧线为主,笔画粗细变化有致。古玺,是先秦时期以先秦文字为载体的印章,但出土后时人并不知道其为先秦之物。明代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是第一部以秦汉原印拓的古玺印谱,真实地保存了古玺印本来的艺术风貌,对推动明代以来古玺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氏集古印谱》中收录古玺一百余方,混杂于秦汉印之间,尽管未能明确断代,但它的艺术价值已被篆刻家所发觉。其后的朱简(明代篆刻家,字修能,号畸臣,后改名闻)是模仿古玺形式进行篆刻创作的代表。他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八年(1597-1610),花了14年时间所完成的《印品》一书,从考证玺印到匡正时谬,多方探索了印章艺术规律,见解超群。其判断“玺”为“商周迨先秦”之印,尤属当时的先进见解。(注:《中国古代印论史》,黄惇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古玺在业界被辨识、欣赏及推动,为先秦文字入印的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朱简又在其《印经》中判断当时无人认识的战国玺印曰:“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又说:“先秦以上印全有字法,故汉、晋莫及。”他明确提出古玺印的字法汉晋不及,想必就是指它的“变化”和天然趣味,也就是“非秩序”的凸显。看一下他自刻的自用印“朱简”“修能”就知道了,两印全仿先秦朱文小玺,“朱简”一印(图4),门字旁里面“日”部重心尽力往上提,留出大部分空间,造成疏密对比。“修能”一印(图5),两字一正一欹,“能”字右部上紧下松,避免平行线。

图4

图5

图6
再如明代中晚期的汪关刻的“东阳”印(图6),运用先秦古玺文字,打破笔画之间距离基本均匀的秩序感,大疏大密,但显得朴素自然,不假修饰,“阳”字其笔画长短、粗细、曲直均能随势所安,水到渠成。清中后期至今,以先秦文字入印成为篆刻创作的主要流派,晚清各大家无不好于此。以黄牧甫(1849-1908,晚清篆刻大家。安徽黟县人,原名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后以字行。)为例,他的学生李尹桑曾评价他说:“悲庵(赵之谦)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此话说的就是黄牧甫善于用三代(夏、商、周)吉金(金文)入印。黄牧甫甚至还把金文自然错落的布白精神引入到原本秩序感就很强的小篆印创作中,使之变化。如自己谦虚地在其印“颐山”印款中说:“小篆中兼有古金气味,惟龙泓老人能之,此未得其万一……”(图7为“颐山”印蜕及边款)

图7
二、锈涩与糜烂
先秦、秦、汉印章是我们学习篆刻的主要途径,因这些印章均为铜制,又因年代久远,难免会出现一些金属特有的锈涩与糜烂,锈涩是指金属印材发生氧化反应的结果,多表现为金属杂质在线条间堆积粘连,使原本清晰明确的笔画转为模糊朦胧。
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图8)以原印蘸印泥钤拓而成。体例仿元人《杨氏集古印谱》,但其中收入古玉印160余方,铜印1600余方,在数量上远甚前代。虽然当时只以原印拓成20部,但由于真实地反映了秦汉印的神采,却在以吴门为中心的文人篆刻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许多著名的印人得以茅塞顿开。三年后的万历三年(1575),顾氏因这20部钤拓本悉为好事者竞相购去,无以广播,故又将其再作补充后以木刻本行世,改名《印薮》。(注:《中国古代印论史》,黄惇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由于《印薮》的大量印行,及随后出土及收藏古印的越来越多,各类印谱也层出不穷,直至如今出版印刷技术质的飞跃,这些古印不止藏家或其朋友能欣赏到,更广大的人群也能欣赏到。原印因时间而产生的锈涩及糜烂,不仅没有致其落选印谱,反而带来了新的审美特征,为业界及社会形成共识。

图8

图9
锈涩的白文印表现为线条变细或湮没。如《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30页的这方“长平乡印”(图9),秦印惯用的强化秩序感的“田”字格把四字框住,“平”字右侧由于锈涩致使格框线条渐渐变细直至湮没,整个左侧边框也被锈涩得断断续续,这样正好使整个印章的气氛不被过于规整的“田”字框框住而显得过于呆板。后代文人篆刻家们为表现这种锈涩之迹,故意留刀不刻或薄削浅刻,来模拟这种天然生成的痕迹。近代篆刻巨匠吴昌硕深谙其理,其印作“缶庐”(图10)“缶”字右上方边栏的处理方法,与以上所讲同出一辙。锈涩的朱文印则表现为线条加粗或再生点画,如《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1页“东昜洢泽王卩鍴”印(图11),锈涩所产生的多余残点块面填补了一些空白,使这方多字印各字之间更加紧凑,产生一种贯气的效果。明代篆刻家苏宣的“张灏私印”(图 12),“弓”旁与“口”相粘连,“禾”旁与边栏粘连,“印”字下部与边栏粘连,包括线与线个别交叉点的粘连等,都是运用了锈涩之法,起到两个作用:其一,使字与字、字与边栏团得拢,打成一片。其二,在全是线造型的印里加上了块面造型,丰富了印面效果。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糜烂则与锈涩的效果正好相反,是一种损之又损的状态,糜烂的白文印如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44页中“阳周仆印”(图 13),整方印糜烂严重,四周留红少之又少,线条与线条之间粘连严重。朱文印则如《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4页“线梁公玺”(图14),整印由于糜烂,线条极细,并且已有多处线条烂得断断续续。这种现象肯定是古代工匠制印时极力避免的自然损害,但从明代文人治印的伊始,文人们就偏爱上了这种自然的、非秩序的审美。甚至历代篆刻大家还刻意用各种手段去达到这种效果。如明代印学家沈野《印谈》中提到:“文国博(文彭,文人印鼻祖)刻印章完后,必置之椟中,命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守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当代学者黄惇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印论史》中也说:“传说近代大师吴昌硕,每作印,即以糙纸或软皮擦其印面,去其火气,却不与人晓。”这种效果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这种残破是人为造出来的天然,很容易显得不天然,这就要求篆刻家的高超手段,造出“有意的天然”。正如沈野又在《印谈》中提到:“墙壁破损处,往往有绝类画、类书者,即良工不易及也。只以其出之天然,不用人力耳。故古人作书,求之鸟迹。然人力不尽,鲜获天然。王长公谓:诗雕琢极处,亦自天然。绝有得之语。”
上文提到“然人力不尽,鲜获天然”。换句话说就是“人力尽,获天然”。即“有意的天然”,其实这个“天然”已经把“有意”也包含进来了,就绝对不仅仅是“墙壁破损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当篆刻家在刻一方具体的印时,他会碰到各种矛盾的关系,如指定的文字内容排在印里看起来特别不舒服,他就要想办法。如吴昌硕印作“沈伯云”(图15),“沈”字上方有五个竖画,加上左侧“伯”的竖划,排列起来特别难看,过重,故他用了糜烂之法,把“水”旁上端三竖细化;“沈”字下端笔画少,有大量空间,故他又用锈涩之法把“水”旁下端的其中两竖变粗,使印的重心趋于平稳,但变粗的竖线又与旁边“云”字竖划靠得过紧,故他又把“云”字最右侧坚划用“糜烂”之法弱化,致使全印各个部位不突兀。这也就是把这种天然的“非秩序”手段用在本来就“非秩序”的组合中,达到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的趋向平衡的效果,正是这种趋向平衡,而不是完全平衡,也不是像汉印的摹印篆或宋明时期的九叠篆一样人为地改变字型去迎合印面,才更有意味。这是不是“有意”与“天然”融合后的“天然”?正如庄子所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

图15
三、取法急就章
急就章,又称将军印,是在铸制好的铜印胚上直接用刀凿刻而成,主要流行于魏晋六朝时期。其艺术风格成熟也在魏晋六朝时期。这一时期军中战乱频繁,军中急于封拜,印章多短时间内直接凿刻而成,用刀如笔,笔画方折挺拔,结构章法自然错落。(图16)正如甘旸在《印章集说》中所述:“凿印锤凿成文,亦日镌,成之甚速。其文繁难有神,不加润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图20

图21

图22
从以上论述可知急就章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印材坚硬,需用锤凿,刻制困难。其二,须急就,时间短。这两点足以导致印人不能像制汉印一样,有条不紊地控制好布局、点画,使之充满“秩序”。篆刻大家丁敬(1695-1765)、齐白石(1864─1957)等都从其中收益。因为材质的坚硬,锤凿时不能慢慢修整,材质的自然属性已大于理性的控制,所以刻出的线条多变,粗细长短较难精确控制,经常是一根线条随着势刻长了或刻短了,在刻下一线条时即时配合刚刚所刻成的环境,如此再生发下去。如我们看同是“凌江将军章”五个字的七方汉魏六朝时的急就章(图17~23),居然没有一方有雷同的布局,例如图17,“凌”字刻短了,第二个“江”字右边大面积留空处就填上两个方形结构,见招拆招,丰富多彩。这样就产生了意外的空间效果。如明代沈野在《印谈》中说:“余刻印章,每得鱼冻石,有筋瑕人所不能刻者,殊以为喜,因用力随其险、易、深、浅作之,锈涩糜烂,大有古色。”这是引发出的一种审美观,但还属于视觉范畴的。还有引发出的另一种审美观,它不属于视觉范畴的,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对自己的用刀刻印有这样的文字:“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我的刻法,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回一刀,纵横来回各一刀,要有四个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我刻时,随着字的笔势,顺刻下去,并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才去下刀。我的刻印,比较有劲,等于写字有笔力,就在这一点。常见他人刻石,来回盘旋,费了很多时间,就算学得这一家那一家的,但只学到了形似,把神韵都弄没了,貌合神离,仅能欺骗外行而已。他们这种刀法,只能说是蚀削,何尝是刻印。我常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图24为齐白石篆刻作品)

图23

图24

图25
这种刻法我们可以通过一方尚未完成的三国急就章“魏屠各率善佰长”(图25,根据同时期印章文字结构分析推算印文)看出。图中“魏”“屠”“各”三字已完成,但是剩下的四字皆刻制了橫画,而竖画没有刻。这种刻法,与齐白石上述的刻印方法极为类似。急就章因时间急促而不能修饰,因材质坚硬而能最大限度地纯粹体现人与材料自然属性对抗的状态,这些都很不容易被印人用以往理性的、秩序感的、经典的视觉化“图式”所修改掉,急就章不得不以客观原因保留了下来。而齐白石则主观地保留了这份“真”。正如齐白石所说的“贵痛快”。“痛快”一词常是指运动后使人产生的快感。朱光潜先生说:“近代美学日渐重视筋肉活动,于五官之外还添上运动感官或筋肉感官(kineticsense),并且倾向于把筋肉感看作美感的一个重要因素。”篆刻亦然。特别是齐白石的篆刻,观者可通过“内模仿”感知筋肉运动,从而窥探出作者当时的运动状态,感受到美。从此分析一下齐白石的篆刻:他的单刀法,即线条的一次性完成,能比其他的繁琐的刀法更能给欣赏者暗示作印时的运动,而他的“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不事先在石上描字形”,恰好通过纯粹的人的本能与石头自然属性对抗(与刻急就章类似)的方式,来体现人共有的“痛快”的运动感!沙孟海在其《印学史》中讲到齐白石时说:“治印常用单刀切石,大刀阔斧,比吴俊卿更猛利,更彪悍。”齐白石自己也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从这些评语可看出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欣赏者,都会对治印时的运动感给予较大的关注。至于视觉上的审美,就退而求其次了。
J292.1
A
1005-6009(2017)85-0063-05
陈慧清,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215000)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