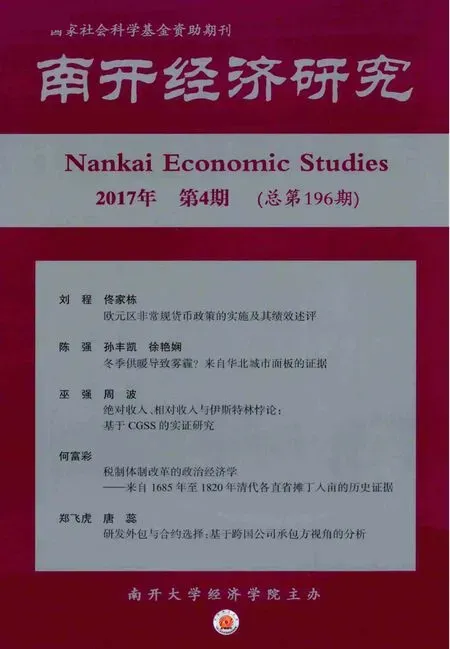研发外包与合约选择:基于跨国公司承包方视角的分析
郑飞虎 唐 蕊
研发外包与合约选择:基于跨国公司承包方视角的分析
郑飞虎 唐 蕊∗

本文结合外向式开放创新与外包交易的分析框架,基于承包方视角对国内新型的研发外包活动——“在岸逆向外包”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对不同合约的选择考虑。利用一家领先的中外合资承包方在2006—2011年间699份合约交易数据分析后发现,项目特征(诸如项目规模、持续时间)与交易双方的关联特性(包括客户类别、客户经验,谈判能力以及合作频次)等因素对承包方合约选择具有明显影响。对于不确定性高、资产专用性强的项目,承包方倾向于选择可变合约;而对项目合作频次高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交易伙伴,承包方则愿意接受固定价格合约。
研发外包;承包方;合约选择;外向式开放创新
一、引 言
就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外包的上述三种模式来看,前两种模式得到了较多学者的研究关注,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外包过程中受益的方式与途径比较清晰。运用开放式创新理论分析,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离岸外包,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走出去的离岸逆向外包,其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由外及内”(outside-in)获取外部知识这样一种过程②在传统离岸外包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受益于接包过程中发包方跨国公司对R&D项目相关技术标准流程要求与规范的执行;而在离岸逆向外包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则直接受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接包时的技术外溢与转移。。相比之下,第三种外包模式涉及大量跨国公司来到发展中国家本土接包,从事的是“由内及外”(inside-out)向外部环境转移技术的这一过程。目前研究者对这种外向式开放创新关注并不多(West and Bogers,2014;高良谋和马文甲,2014),而且就外向式开放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意见也不一致。早先学者们肯定了正面效应的存在(Chesbrough,2006),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从事外向式开放创新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泄露公司与竞争相关的技术)可能会限制公司外向式开放创新的潜在收益,进而影响其绩效(Kline,2003;Ulrich,2015)。
本文的研究聚焦第三种外包模式。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首次关注了研发外包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实践(中国模式),而且利用中国的这一独特情境,本文选取跨国公司作为承包方这一视角(inside-out)对外包过程中的合约选择行为展开深入分析。考虑到三种外包模式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事实上是在逐步加大③传统离岸外包中,跨国公司只是对外发包,对承包方的监督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离岸逆向外包中,跨国公司在本土接包,面临更多的是同行的竞争;而“在岸逆向外包”中,跨国公司需要深入发包方市场接包,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这一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跨国公司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背景下,作为接包方在选择研发外包合约时是如何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为此,我们选取了一家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开展软件研发合作的中外合资承包方,基于其699份合约交易数据展开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工作将传统外包研究从企业层面拓展到了更为微观的项目层面(Namkuk et al.,2015),这就有可能揭示外包过程中更为细致的影响机理(比如,在同一承包方的业务合作中,我们可以针对不同性质的发包合约,观察项目层面的差异对外包行为的选择乃至对外包绩效的不同影响)。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综合看到来自项目层面与交易双方关系层面(Zheng Feihu et al.,2017)的不同特征因素对于合约选择的影响效应。
二、研究框架
在一个信息完全的理想世界中,不存在合约的选择问题。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合约参数计算可以达成使双方满意度最大化的合约。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情况却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等的(Hart,1988),软件外包合同也不例外。合同定制双方不可能在合同定制时预测到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一个风险厌恶者会希望定制一个能为自己完全规避风险的合同,而不希望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导致签订了一份使自身承担大量风险的合同。合同双方专业领域、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如何通过合约安排与外包关系管理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从承包方的视角来看,针对不同类型的发包方和不同的项目,需要把伙伴关系管理因素与项目因素同时考虑在内。
基于研发外包的行为动机,我们发现在软件外包业务中,普遍被接受的主要有两类合同:固定价格合同(fixed-price contract)和可变合同(time-and-materials contract)。固定价格合同是指合同签订前便拟好价格并一次性支付,可变价格则是分期支付。两种合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风险界定不同——固定价格合同主要风险承担者是承包方,可变合同中则是发包方。一个风险中性的承包方对合同类型的选择并不关心,一个风险厌恶的发包方会倾向于固定价格合同;而在不确定性增加时,一个风险厌恶的承包方会更偏向选择可变合同。在本文设计的研究方案中,我们假定客户与承包方都是风险厌恶型。中国市场庞大的IT需求以及跨国公司纷纷抢滩国内IT研发市场外包活动都表明,交易合约的终止与不成功对于双方的声誉、时间等方面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使得任何一方都尽可能避免这一不利结果。
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在外向式开放创新的视角上引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模型(Williamson,1975、1985),运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进一步刻画软件外包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影响条件,从而形成得自项目层面与交易关系层面的不同影响因素结构图(见图1),在这一结构图基础上,我们展开相关的研究假设与分析。

图1 软件外包的影响因素结构图——基于外向式开放创新与外包交易框架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分析
(一)数据
本文研究的数据源于一家主要为金融行业提供应用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于2007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其核心业务是将最新的软件产品和技术服务提供给国内金融客户。公司总部在北京,现有员工5000多名,且在十余个城市设立了分子公司和代表处,是中国金融IT行业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之一。我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市技术与市场办公室(BTMO)的R&D合约交易数据库,包含了2005年12月到2011年6月期间所有在BTMO登记申报的在京跨国公司在计算机软件领域的R&D合约交易,共计1772个有效样本。论文研究的承包方企业属于其中交易量最大、最具特点的金融软件外包领域的龙头企业,该公司6年间登记申报了701个项目,本文从中选取699个有效样本(即该公司与233家企业定制的699份软件外包合约)。这些合同持续时间从29天到2386天不等,平均持续时间是515天,技术交易额度从7 500元到20 900 000元。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从上至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重新优化、细化、,改善企业内部各项业务流程。例如:企业可以将风险管理作为一项长期阶段性的管理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再例如:由于各企业所处的相关风险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选取真正适合企业自身长期发展的风险管理形式和工具,不断提升企业的风险防范水平。另外,风险防范与管理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企业拥有长期的、高效的管理制度。
(二)模型与变量假设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因变量(合同支付类型,Contract)是个二元虚拟变量,即承包方选择固定价格合同还是可变合同。

当合同类型是可变合同时,C等于1;当其为固定价格合同时,C取0。根据前述设定的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了软件合同外包过程中项目层面与交易关系层面两个维度共计6个自变量,具体含义与预期影响符号见表1。由于技术交易额度和持续时间是区间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比数值过大。因此,本文对技术交易额度和持续时间取对数。合同类型是因变量,因而没有预期符号。

表1 外资企业在华软件外包合同类型的影响因素:变量含义与预期影响
1.项目层面变量与相关假设
(1)软件开发风险(Duration)。软件开发是一个天然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企业往往很难准确了解研发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Barki等(1993)认为,项目规模大小是衡量软件项目风险非常重要的变量。项目规模越大,涉及层面越广,遇到的困难问题越复杂,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高,风险厌恶的承包方会更倾向于选择可变合同。与小规模项目相比,大规模项目由于交易双方要处理的事务多且复杂,从项目开始到完成所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因此,本文选用项目从签订到完成的持续天数作为软件项目风险的替代变量。
假设1:大规模项目(持续时间长)导致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承包方更倾向于选择可变合同。
(2)合同属性(Servcon)。就合同属性来说,是否涉及资产专用性投入对于交易双方合约选择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专用性资产指的是仅能用于特定项目开发并在研发完成后无法用于其他项目的资产。专用性资产强的技术合同,客户转换承包方更不容易,对其依赖性也更大。本文数据中将合同类型分为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两类。技术服务合同是指承包方以技术知识为客户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其客体是尚不存在的有待开发的技术成果。本文用合同类型衡量资产专用性,相比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开发合同需要承包方投入更多专用性资产,由于客户对承包方更依赖,因此承包方占据了更多谈判优势,有更大几率争取可变合同。
假设2:对于资产专用性更强的技术开发合同,承包方更倾向于选择可变合同。
(3)合同金额(Money)。除了合同类型,合同标明的技术交易金额也能衡量资产专用性。本文分析的承包方是一家主要为金融行业提供应用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从产业的角度划分,交易标的都属于计算机服务业,因此研发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不会受到不同产业固定效应的影响,这方便了度量特定项目研发中需要的专用性资产大小。在项目过程中,承包方会将准备专用性资产的支出计入成本中,从而导致技术交易额升高。同时,合同金额越高,项目对客户越重要,承包方因其提供更多复杂技术也占据了更多谈判优势,因此我们得到假设3。
假设3:技术交易额越高,承包方更倾向于选择可变合同。
2.交易关系层面变量与相关假设
(1)客户经验(Buyerexp)。在外包项目中,客户作为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拥有的处理外包合约的相关知识与过往经验,往往会对承包方合同类型选择产生影响。Williamson(1979)曾指出,拥有对未来或然性的预见能力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提高合同效力。拥有丰富外包经验的客户通常能更准确详细地制定合同条款,合同能较为全面地涵盖项目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规章制度也更明确与简洁,交易双方沟通与交流更通畅,不仅有助于客户更有效地监控项目的进展,对于承包方来说也能有效减少不确定性与风险。因此,面对拥有丰富外包经验并可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承包方会愿意接受甚至主动提出选择固定价格合同。本文选取同一发包方在2006—2011年间签订的软件外包合同的总数量,衡量客户在该领域的外包经验是否丰富。
假设4:拥有丰富外包经验的客户能减少风险与不确定性,承包方更倾向于选择固定价格合同。
(2)合作频次(Frequency)。在软件外包市场上,更多的客户参与业务委托竞逐时,承包方就拥有更多选择权,反之亦然。此外,交易双方如果之前已经完成了好几个项目并建立了友好关系,一旦更换承包方,客户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寻找合格的替代者,这会增加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承包方就处于较有利地位,更有可能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可变合同。同时,交易双方已经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双方信任增强,客户也会愿意接受可变合同。本文数据显示,233家客户与同一承包方之前签订的合同次数从零次到几十次不等。
假设5:交易双方之前合作频次越高,承包方更倾向于选择可变合同。
(3)谈判能力(Bank)。从商务谈判角度分析,合同的选择还依赖于谈判能力。假设交易双方皆为风险厌恶者,他们都偏好能降低自己承担风险的合同。在本文环境下,客户希望签订固定价格合同将风险转移给承包方,承包方则希望争取可变价格合同将风险转移给客户。谈判能力削弱了任务不确定性与合同选择的关系。谈判能力强的承包方(客户)有能力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可变合同(固定合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双方的谈判能力纳入变量中。通常,衡量谈判能力的因素包括交易双方的信誉、未来业务潜力以及自身规模等。
本文研究的承包方在2006—2011年间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银行和非银行类企业。从图2可以看出,非银行类客户的外包经历远不如银行类客户丰富,大多数只有1次经历,最多也只有9次。银行类客户合作频次从1次到70次不等。从与该承包方之前完成的项目来看,非银行类客户大多没有与该承包方合作的经历,而该承包方主要与银行金融业打交道,与银行类企业合作经验丰富。因此,我们引进是否是银行这一控制变量。银行类客户大多属于国有控股银行,信誉较高,支付与谈判能力较强,所以面对这类信誉高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客户,承包方愿意接受固定价格合同,由此得出假设6。

图2 非银行类外包信誉
假设6:面对银行这类信誉良好并具有发展前景的客户,承包商更倾向于选择固定价格合同。

表2 样本数据情况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从表3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除了Frequency 和Buyerexp两个变量相关系数为0.80,其余变量相关系数很小,不足以导致严重的完全共线性。这样我们将它们的交叉项Fre_buyerexp作为单独变量进行考虑,得出以下模型: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除了Servcon 和Bank两项变量以外①客户类型的变量符号与我们假设一致,但不显著,可能与数据结构特征有关,承包方签订更多是可变合同,尽管在参与交易的客户中银行占了多数;此外,合同类型中技术服务合同占比过多,这一现象也可能影响到合同属性变量的显著性。,Frequency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Lduration、Lmoney 和 Buyerex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实际测准确率为97.28%,,模型对应ROC曲线如图3,可以认为模型拟合度很好,实证分析结果与本文之前假设基本相符:从不确定性层面来看,本文假设承包方和客户都是风险厌恶者,都期望签订风险最低而对自己有利的合同。实证结果发现(Lduration=0.511**),面对持续时间长的大规模项目,随着不确定性增加,承包方更愿意采取可变合同。与拥有丰富外包经验的客户(Buyerexp=-0.020,9**)进行交易,往往意味着合同的不确定性风险减少,因此承包方会愿意接受固定价格合同。从交易频率来看(Frequency=0.183*),交易双方之间合作次数多,双方之间信任度增强,再加上替换承包方会使成本增加,客户愿意承担风险,承包方更有机会争取到可变合同。在资产专用性方面,投入大量专用性资产的项目一般交易金额也较大(Lmoney=0.359**),因此承包方偏好选择可变合同。

表4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图3 模型的ROC曲线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一类新型的研发外包——中国情境下的“在岸逆向外包”,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承包方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基于相关因素的考虑来选择不同合约的支付类型。利用一家领先的跨国软件厂商与233家中国客户达成的699份软件外包合约,我们分析了承包方在面对两类主要的软件支付合同——固定价格合同与可变合同时的不同择决及其影响因素。理论上,作为风险厌恶型的承包方一般会偏好可变合同,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愿意接受固定价格合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其最终目标,因此承包方会尽可能降低在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本文在外向式开放创新的视角下引入了外包交易理论,分别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结合软件外包的特征进行了多因素的分解与分析,最终确定了从项目特征与交易关系特征两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存在大量不确定性、风险较高的项目,比如合同持续时间长的项目,承包方更倾向选择可变合同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当面对具有丰富软件外包经验的客户时,由于客户制定的合同能够更有效地规避部分风险,再加上有发展长期合作伙伴的意愿,承包方则会选择接受固定价格合同。此外,交易双方若是拥有长期合作关系并已建立基本信任,为了减少更换承包方的成本,客户会接受承包方提出的可变合同。对于需要投入大量专用性资产的技术开发类项目,由于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无法被重复利用,相应的补偿会反映在技术交易额中。对于这类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项目,承包方一般会倾向选择可变合同。
(二)研究价值
“在岸逆向外包”是近十多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外包出现的新现象,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我国大陆接包的各种影响因素与机理尚待探索,本文的研究工作在理论贡献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立足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实践,对现有研发外包理论和观点提出了挑战。传统研发外包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交易分工观点界定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低附加值的承包方角色,新兴的逆向外包理论更多关注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到发达国家获取所需的技术与技能,上述研究更多提示的是知识怎样由外向内(outside-in)流动。本文实证分析的中国市场上的“在岸逆向外包”现象,则揭示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如何扮演承包方角色,在中国本土完成技术由内向外(inside-out)的扩散。这一研究工作为ITO领域提供了国内软件业R&D 集聚事实上已经从国际承接方地位转变为国际发包方地位的证据,对现有以发达国家发包为主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挑战,丰富了基于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逆向外包理论的应用范围。
其二,在传统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引进了外向式开放创新的理论应用,不仅扩充了主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模式,而且运用跨国公司承包方角色,基于外包交易关系层面与项目层面因素的架构设计,在微观视角上拓展了我们理解跨国公司合约选择与技术扩散背后的影响因素与机理。
其三,从本文数据时段(2006—2011年)统计的结果发现,跨国公司来华进行研发接包更多选择的是可变合同,而实证分析提示了可变合同的选择与资产专用性、合作关系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将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放在一个更大的国内宏观环境中考察(2006年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等),那么本文微观数据展示的一个结论便是:2006年以来中国市场在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下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以ITO市场R&D交易来看,来自中国企业的客户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发包要求(导致合约资产专用性加大),中方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价值链程度更深入(签署了更长时间的研发合约,因此中方客户也不愿轻易转换跨国承包方)。这些微观实证结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06年以来中国国内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的确在发挥作用。
虽然本文研究的视角是“在岸逆向外包”活动中的跨国公司承包方,但是研究结果也可应用于国内企业充当软件外包承包方的情境。本文基于跨国公司承包方地位所得结论运用于国内接包企业的相关建议包括:在针对外包活动具体选择两种不同类型的支付合约时,承包方应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适当取舍。一方面,可变合同能为承包方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承包方可以借用固定合同提高自身竞争力,吸引更多长期合作客户。因此,在签订合同之前,应充分了解客户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损失出现。承包方可以基于战略需要进行调整,如果有意愿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风险能够承担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承担一些风险,选择固定价格合同。
目前,中国本土的软件外包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中(据统计,2001年中国软件企业来自软件外包的收入为2亿美元,而在2015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达到128.7亿美金),国内不少地区也有许多新成立的软件外包承包方(参与接包的国内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和技术密集的内陆城市,比如北京、西安、成都、沈阳、深圳等)。这些公司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一般由几十人组成,交易额度不高,外包经验远不如那些外资或者合资的大企业丰富(比如大连有超过100家的软件公司承接外包业务,但是每个公司员工都只有3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100人,承接项目交易金额都不大;而从同行业对手企业分析,美国软件企业平均人数是300人,印度是145人)。对于国内这些中小型承包方,在一些资产专用性不高、时间较短的项目中,可以选择固定价格合同,以吸引更多客户;当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随着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增加,技术交易额度变大,项目持续时间变长,然后再选择可变合同。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尽管本文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数据的时间跨度不长,只包含了2006—2011年6年间一家典型跨国承包方的交易数据;同时,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北京地区,地方特色比较鲜明(主要考虑到“在岸逆向外包”这一现象在北京最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实证结论的普遍性。未来需要强化对国内更多地区、更多跨国承包方交易数据的收集与对比分析,以提高研究的精确性与全面性。其次,支付合同的选择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但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并未涉及更多因素。此外,本文所关注的这两种主要软件外包支付合同类型并不能包括所有的合同,许多由这两类合同衍生出来的支付合同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比如,有些合同虽然是固定价格合同,但根据项目的进程和质量会设立一些惩罚或奖励机制,目前国内尚缺乏对这些合同类型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分析。最后,成本往往是驱使外包交易的主要动力,在分析成本优势的决定因素时,研究它们是怎样通过不同的合同支付类型最终达到不同目的和取得不同效果的,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
[1]高良谋,马文甲.开放式创新:内涵、框架与中国情境[J].管理世界,2014(6):157-169.
[2]刘丹鹭,岳忠刚.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的案例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44-52.
[3]张千军,刘 益,王 良.基于权变视角的知识利用、知识开发以及双元性对外包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3(7):1065-1071.
[4]郑飞虎,常 磊.跨国公司研发外包活动的研究:中国的实证与新发现[J].南开经济研究,2016(4):99-114.
[5]Ambos B.,Ambos T.Location Choice,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R&D Investment in Peripheral Econom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9,48(1):24-41.
[6]Barki H.,Rivard S.,Talbot J.Toward an Assessment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Risk[J].Management Inform.Systems,1993,10(2):203-25.
[7]Chanda R.,Bangalore I.Global Sourcing of Services:The Case of Indian[R].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2006,October 9.
[8]Florida R.The Globalization of R&D:Results of a Survey of Foreign-Affiliated R&D Laboratories in the USA [J].Research Policy,1997,26(1):85-103.
[9]Hart O.D.,Moore J.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J].Econometrica,1988,56:755-85.
[10]Henry Chesbrough.Open Business Models:How to Thrive in the New Innovation Landscape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6.
[11]Henry Chesbroug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12]Hsuan J.,Mahnke V.Outsourcing R&D:A Review,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 [J].R&D Management,2011,41(1):1-7.
[13]Kim Namkuk,Kim Dong-Jae,Lee Sungjoo.Antecedents of Open Innovation at the Project Level:Empirical Analysis of Korean Firms [J].R&D Management,2015,45(5):411-39.
[14]Kline D.Sharing the Corporate Crown Jewels [J].MIT Slone Management Review,2003,44:89-93.
[15]Kuemmerle W.The Driv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9,30(March):1-24.
[16]Rugman A.A Test of Internalization Theory[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1981,2(4):211-19.
[17]Ulrich Lichtenthaler.A Note on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R&D Management,2015,45(5):606-08.
[18]West J.,Bogers M.Leveraging External Sources of Innovation:A Review of Research on Open Innovation [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4):814-31.
[19]Williamson O.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M].New York:Free Press,MacMillan,1975.
[20]Williamson O.E.The Economics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Free Press,MacMillan,1985.
[21]Williamson O.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233-61.
[22]Zheng Feihu,Jiao Hao,Cai Hongbo.Reappraisal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under the Policy of China′s ″Market for Technology″[J].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17,forthcoming.
R&D Outsourcing and Choice of Contracts:Analysis from MNCs as the Vendors
Zheng Feihu1and Tang Ru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2.Tilbur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ilburg 5037 AB,Holland)
Based on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outsourcing transaction framework,we study the determinants of contract choice of payment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which is also called ″On-Shore Reverse Outsourcing″)by MNCs.Using data of 699 outsourcing projects during 2006 to 2011 from a leading foreign software vendor in China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financial and bank industry,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project-related and transacting partnerspecific features such as project size,duration,client′s type,experience,bargaining power and frequency significantly explains contract choice in these projects.Vendors will prefer timeand-materials contract in a project with high uncertainty and asset specificity,while vendo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fixed-price contract when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several projects with clients and hope to sustai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R&D Outsourcing;Vendor;Contract Choice;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10.14116/j.nkes.2017.04.006
∗ 郑飞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编:100875),E-mail:zfh@bnu.edu.cn;唐 蕊,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与商业管理系(邮编:5037 AB),E-mail:candylyly886@163.com。本文受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创新集群、治理规则与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14JGB04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KZZY2015018)资助。
JEL Classification:F23 L24 O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