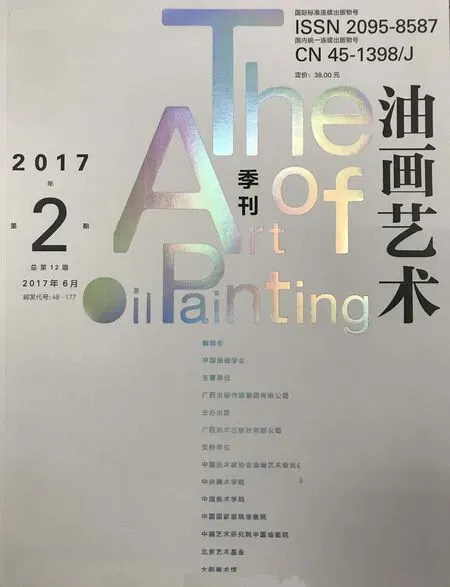西南油画述要
一、西南油画概念
在中国油画艺术生态中,西南油画群体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强盛的生命力。西南油画之所以蓬勃兴旺、独树一帜、香火代传,方兴未艾,得益于以下几个重要原因:其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主要艺术院校和重要的油画家迁徙西南。油画本来是舶来艺术形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靠从东洋西洋留学回来的油画艺术家,这些油画家大多是艺术院校的教授讲师。抗战期间,全国各地艺术院校大多迁徙至以成渝两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的美术教育和油画艺术生长因兹得天独厚。抗战期间的艺术院校和艺术教育给西南油画奠定了艺术人才、艺术形态和学科传承的基础。其二,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和人文性格,形成了西南油画独特的创作空间、创作方式和风格语言。中国的西南地区,资源丰厚,大山大水,生存条件艰难但生活形态丰富。民性勤劳,乐观诙谐,注重现实,不擅玄思,达观知命。故西南艺术家极善生活体验、现实承担。现实主义泛觞并持续于西南,是必然顺理的现象。其三,相对自由的空间与艺术市场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四川美术学院(后文简称“川美”)油画及云贵川油画得益于“山高皇帝远”的区域优势,艺术家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得以释放心灵自由,群体崛起。四川油画家的作品最先得到港台藏家收购,部分画家率先小康殷裕,后趋之若鹜,市场诱惑,天价神话,油画行道遂成产业。
西南油画概念,特指有艺术发生地域和连带关系的重庆、成都(原四川省)、云南、贵州的油画现象。广西在地域版图属西南,但因其艺术发生关系不同,故其艺术不在此脉属。西南油画是以重庆为艺术发生中心,扩延至成都及云南、贵州并相互关联。
西南油画,画迹丰厚,画家众多,形态多端,风格各异,代有人出。且与社会时代多具关联,故仅以线性历时叙事,或仅以共时空间叙事,都莫可诠释尽达。通常史家贯以潮流及时期命名的阶段划分,如“伤痕”阶段、“乡土”阶段、“生命流”阶段、“都市人格”阶段……都未必准确,难免疏缺。西南油画丰饶多姿,时空交错,多元杂错。欲治其史,不易先入为主,概念格致。而宜洞察其发生机制、族群性格、创作能力、流变轨迹,方可识其万变不移之宗,辨其一树成林之盛。
艺术史的书写,通常以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事件为表述,这三者的核心灵魂其实都是人,艺术史是关于人性和人的命运的形象历史。故艺术史叙事的真实,在于人的命运节点和人性展示的空间。在这层意义上,注意阅读、记录那些代表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画家,以及其相互关联,是探寻艺术史的门径。
二、西南油画的整体叙事
以下是西南油画历史上几次殊关命运的事件节点,以及由之发生的群体性叙事:
第一个重要事件节点是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艺术院校西迁,以陪都重庆为中心,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油画家。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艺专、正则艺专、南虹艺专、武昌艺专……战时西南大后方众多艺术院校培养了众多优秀画家。徐悲鸿、林风眠、李宗津、吴作人、唐一禾、李有行、张忠宇等中国第一代油家执教于西南,董希文、倪贻德、吴冠中、赵无极、艾中信、冯法祀、刘艺斯、刘一层、刘国枢、叶正昌等第二代油画家都于西南出道。由兹为西南油画奠定了教育和创作的基础。
第二个重要事件节点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苏联现实主义油画创作方式和苏派油画风格对川美油画的影响,川美油画系教师到著名的“马训班”培训,马克西莫夫亲临川美油画系,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川美形成比较严谨完备的苏派油画教学模式,在西南地区形成相对严谨规范的油画学统。同时,西南地区产生相当规模的意识形态主题油画,如刘国枢《县委书记》、邓绍义《唱支山歌给党听》、古月《田间抽水站》、潘迎华《我们的首都北京》、李自由《敢教山河换新装》等,这些作品充满理想主义,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宣教多于审美。
第三个重要事件节点是1977年到1984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川美油画系师生所形成的油画运动。1979年至1984年,以川美为代表的西南油画作品,在数次全国展览中异军突起,频频获奖,其势汹涌,至今全国油画界仍羡目生畏。1979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全国82件获奖作品中,川美油画获奖颇众:《1968年×月×日雪》(程丛林)、《雨过天情》(王大同)、《为什么》(高小华)、《春》(王亥)、《我爱油田》(高小华)、《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夏培耀、简崇民)。1980年3月,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父亲》(罗中立)、《藏族新一代》(周春芽)、《父与子》(朱毅勇)、《生命之光》(王嘉陵)、《再见吧小路》(王川)、《手》(杨谦)。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基石》(龙泉)、《山村小店》(朱毅勇)、《朝阳》(刘虹)、《乡村艺术家》(马一平)、《游行的队伍》(秦明)、《码头的台阶》(程丛林)……其中大多数油画作品,为在读本科学生所创作,数量之众,内涵所蕴,魅力所具,潜力之巨,客观上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后新时代以油画表达的文艺复兴,形成了在现实主义、社会承载意义上的油画艺术家群体。时任中国美协主席江丰、副主席华君武亲临川美,召开全国艺术院校油画创作现场研讨会。会上,江丰主席的一句发言集中表达了时代的变革与观念的冲突:“如果有一天,资产阶级的艺术潮流复辟侵略,我就到川美招募一支现实主义艺术大军去抵抗捍卫。”(见《1982全国艺术院校创作研讨会纪要》)
这一时期,西南的油画呈现高度群体运动特征和共性风格取向。虽然引领潮流,实则仍以体制化生存,依循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路数。以此同步的群体事件和叙事脉络,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野草画展”、“黑牛画展”、“新具象画展”、“生命潮流群体”、“川美学生自选画展”、成都“红黄蓝画会”,一直到1989年“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为表述的非体制化的油画观念、油画形式。
体制内外的油画阵营,各自标榜,相互渗透,画家们甚至脚踏两阵,是非彼此,西南油画群体革命运动持续了十年之久。1989年后,西南油画乃至中国油画,戛然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群体革命运动,艺术创作开始成为个体劳动。油画家们要面对革命结束后的生存困境,开始离开组织的江湖游走形式。至此,所谓西南油画的概念,已非创作方式与风格的群体概念,而只是地域意义和艺术生存方式的现象。
关于西南油画整体叙事,1989年前后发生较大的风格殊异,其背书基底,乃是画家个人观察与图式的确立,由先前共性模式转变为个人主体介入。人的命运节点和人性展示空间发生变化,这个核心因素使西南油画既产生了多姿各异的语言风格,又始终保持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持续关怀。如果说西南油画有独到的特性与学统,恰在于此,一直贯穿。至于题材上从农村到城市,风格上从乡土到卡通,都只是时态变化而已。有些画家画面很当代,实质还是乡土语境;有的画家画面很乡土,实质很当代,故不宜以时态表象为判别依据。真正使之发生变化的是文化的演变与虚无导致人性的改变,导致油画精神和语言的变化,当下这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1何多苓《青春》150 cm×186 cm布面油画1984年
西南油画家的整体能力,不擅观念方式与表现主义,更多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存在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承担忧患责任,充当社会的先知、启蒙和拥有居高临下的拯救情怀,表现“文化大革命”后的“伤痕”“乡土”并派生于各类生活景观油画。程丛林早期大幅度作品、罗中立的《父亲》亦不出其左。存在现实主义则以现实生活的无奈无聊来承担虚无与荒诞,表现生存、生态的烦恼、欲望、抗逆、孤独与痛苦,张晓刚的早期作品,龙泉的《红线》《夜行中巴》,陈卫闽、忻海洲的早期作品,郭晋、沈晓彤、何森的作品,以及奉正杰、奉家丽的艳俗形态油画,钟飚的穿越拼撞悬浮图式,乃至新生代熊丽均、熊宇诸家,大都出于这一脉统。其中因人而异,有的偏于浪漫、魔幻,如任小林、贾鹃丽。有的画家则偏于个人审美趣境,如莫也。有些画家更倾心绘画本体,作品更具个人图式与语言意义,如周春芽的《绿狗》《湖石》《桃花》。心理现实主义则趋于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哲思,高寒孤芳,追求精妙超逸的画境,在油画语言上也更富诗意、哲理和悲剧的蕴藏,因之也就更具经典性,何多苓的早、中期绘画是这层脉统的典范。《小翟》一画,成为中国油画心理现实主义的丰碑,后人以至画家本人都无法超越。张晓刚《血缘家庭》系列绘画也具有这一脉统的特质。

2毛旭辉《 靠背椅上的家长》90 cm×80 cm布面油画1989年

3罗群《欲》60 cm×90 cm布面油画1979年
西南油画现实主义主流中,有一个富于生命激情和表现主义趋向的群体,他们就是与云南这块热土相关联的画家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马祥生、潘德海等。高原的阳光蓝天和空气,亚热带的自由气息和生命激情,与重庆工业城市的炎热尘霾格格不入,让人易产生压抑抗逆情绪。叶永青、张晓刚等在川美率先以表现风格进入现实叙事,并影响着四川画风的变化。周春芽早期作品,程丛林、陈卫闽的作品都带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主义因素。另类和先锋也始终存在,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油画初成气候之际,刘沛沛即画出《我们在社会中》这幅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存在主义基调,又具现实社会景观的作品,过于前卫,生不逢时,多年后“85美术新潮”,方见有此类作品出现。海内外艺术潮流、资讯也促使西南油画具有时代开放性和内充生命力。如“星星画展”黄锐、马德声的入川宣讲,超级现实主义画家修克洛斯巨幅肖像风格对罗中立创作《父亲》的影响。
20世纪末中国进入消费时代,混乱的艺术市场颠覆西南油画的精神场景,尤其21世纪初少数西南油画家成为“天价标杆”后,后学趋之若鹜,而大部分油画家为保持自己的画价而固守既定的画风,西南油画普遍消解、背弃自身批判反思的精神家底,喜大普奔于庸浅的风月和形式的卖相,都是钱惹出的祸。

4熊莉钧《明星》160 cm×200 cm布面油彩与丙烯2009年
西南油画,代表了倔强而坚韧的奇特文化生命体,自生自灭,与时俱进,既守旧又维新,既开放又保守,既慕新追风,又深固难陡。西南油画史人才代出,四世同堂,各具风姿,诸如张仁强的热土激情,薛明德的形上先锋,何工的实体绘画,孟涛的魔幻景观,刘沛沛的古战沙场,张杰的油画山水,扬述的抽象世界,刘宇的残酷物语,李强的惠风香草,刘虹的女性处境,翁凯旋的田园牧歌,罗发辉的美艳溃疡,陈安健的底层生态,张奇开的太极熊猫,钟飚的众生悬浮,郭晋的命运失衡,何森的城市焦虑,熊莉均的卡通青春,沈娜的情色幻象,邱光平的魔兽狂驹,熊宇的虛拟生存,韦嘉的梦境现实,赵晓东的新农村生态,王娅的变焦错视……收览莫及,蔚为大观。

6叶永青《阿斯玛》65 cm×50 cm布面油画1989年

5忻海洲《白·哪儿来的榔头?》200 cm×200 cm布面丙烯2006年
纵观西南油画,我们看到实力强盛、自生自灭、多元多姿、薪火代传的油画生态,生存的体验与生活的激情,以及在中国油画史中重要的意义、价值与地位;也看到几近散珠的江湖机制、学统的流失与学术的缺位、杂芜的观念与生态……当油画这种相对完备的舶来艺术物种遇到西南地域文化深固难徙的本土特性,产生蓬勃、激情而荒诞的生命魅力,也产生学术的误读与基因的变异。由于审美价值的差异、艺术教育的粗放和市场功利的影响,在油画语言层面的研究和油画精神的寻绎方面,则乏善可陈。客观评价,也未出现在全球主流油画圈层具有业界学术影响和学界普遍认可的杰出油画家。这不仅仅是西南油画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油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