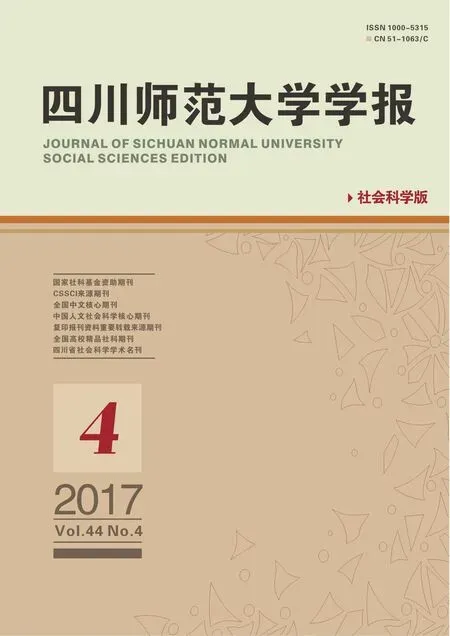清代巴县的食盐贸易与盐法变迁
黄 凯 凯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清代巴县的食盐贸易与盐法变迁
黄 凯 凯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清代盐政问题的实质是专卖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专卖制度将食盐贸易截然两分为官、私盐市场,但定额化的盐税征收体系难以根据市场状况及时做出调整,造成的结果是专卖制的崩溃与私盐市场的逐渐发育。“私盐”这一标签,成为盐商、士绅等既得利益者攻击商业对手的有力工具,而因时因势变革的地方盐法制度只不过是各市场主体之间博弈平衡后的结果。作为清代川盐外销集散中心的巴县,保存着十分丰富的档案材料,为深入探讨这一地区较长时间内食盐贸易与盐法制度变迁的互动过程提供了可能。
清代;巴县;食盐贸易;川盐外销;盐法变迁
食盐贸易是传统时期商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之处在于与王朝国家的专卖制度紧密相连。食盐专卖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清代食盐贸易存在两套相互层叠又互相排斥的市场网络,即政府建立的官盐运销网和与之相对的私盐市场。既有研究或强调官盐的销区划分缺乏市场合理性,或着重分析私盐的种类及其对官盐贸易的破坏性影响①。这为我们理解清代食盐贸易的整体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但是,官方文本中的“私盐”、“私贩”不过是政府对控制之外的食盐及其贩运者强加的标签,而地方各类人群如何运用这一标签、实际的食盐贸易到底处于何种状态等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更多地关注到清代盐法在时间、空间上存在的较大差别。在川盐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清代川盐大致有票盐制、引岸制、官运商销制三种运销体制②。然而,食盐贸易中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多方博弈往往促成地方盐法制度的不断变迁,看似“静态”的专卖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显得更为灵活和复杂。本文关注的清代巴县是四川井盐转运贵州、湖广等市场的集散中心,从康熙朝至光绪年间,聚集在重庆的盐商、私贩、官员、士绅、普通民众乃至天主教势力都广泛参与到川盐贸易当中,因时因势变革的地方盐法制度也正是他们博弈均衡后的结果。本文借助四川省档案馆出版、馆藏的《巴县档案》中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的盐法档案③,结合四川盐法志、地方志、文集等资料,试图回应的是清代某特定区域内食盐贸易与盐法制度如何互动变迁的问题。
一 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川盐贸易网
清代巴县为川东道重庆府首县,在行政区划上今已不复存在,其地理范围囊括今重庆市主城区的大部分,在文献中巴县与重庆经常交替使用。邱彭生指出,随着16至18世纪全国市场的发展,重庆城逐渐成为四川全省货物的转运中心[1]277-278。井盐运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乾隆《巴县志》称:“渝州为三江总汇,商贾辐辏之区,川西、川北各井盐,一水舟车,鳞集江岸,盐之薮也。”[2]卷三《赋役》既有盐史研究多将川盐大规模扩张的节点置于咸丰朝“川盐济楚”之后,而对清前中期川盐在贵州和湖广市场的开拓、发展与嬗变过程着墨不多。笔者认为,康雍乾时期,经重庆转运的井盐,在贵州、湖广市场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至少到乾隆中叶,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川盐贸易网络格局最终形成。
川盐对贵州市场的开拓,是在康熙中叶以后。由于川盐在价格、运输、税额等方面的优势,淮盐、滇盐逐渐被排挤出贵州市场[3]27-31。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贵州省除黎平一府仍消费淮盐外,全省市场几乎被川盐垄断[4]33。这一时期贩运入黔的川盐,大部分来自川北潼川、射洪、蓬溪、中江四县,沿涪江、嘉陵江顺流直下汇集重庆盐码头后,或由四川客商“自运黔省”,或由贵州“流商、土商每年轮流前往四川所属之重庆府买盐”[5]卷十《转运》。这一时期川盐自由贩运和贵州市场的开发,可能直接促成了康熙年间巴县盐行的成立。从事食盐贸易的商人在川北购盐后,“运至千斯门外,设立盐行,任民买食”[2]卷三《赋役》,巴县盐行成为本地居民和贵州流商、土商主要的食盐交易场所。由于史料阙如,盐行的具体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我们难知其详。范金民指出,“清代重庆各行各业均须承应官府的公事差事”[6]59,并以承差为名垄断经营、把持价格。张渝也认为,“清代重庆的部分行帮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的差务派摊有很大关系”[7]64。或可猜测,此时组织盐行的商人可能也是通过承担官府差役,把持了本地和运黔的食盐贸易。由于康熙朝数据的缺乏,我们尚不清楚此时从重庆贩运至贵州的食盐总量。根据雍正朝“计口授盐案”内的数据,四川每年额行贵州的官盐总量达3,720余万斤,其中必须经过重庆转运的官盐比重约占48%④。或可猜测,这一数据很大程度是对康熙中叶以来逐渐发育成熟的运销格局加以承认与制度化的结果。
乾隆中期以后,聚集在巴县盐码头的井盐越来越少流入贵州,代之而起的是湖广私盐市场。乾隆初年,湖广行省只有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七州县,配行川东夔州府云安县等地井盐[8]卷十四《盐法》。但自乾隆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川北、川南盐开始进入湖广。据称,此时“蜀中私盐船只偷行下楚者,不可胜计”:一方面,在巴县从事“贵州边岸”转运贸易的商人,冲破引岸的限制大规模走私湖广,“至渝赴本地发卖者十之三,贩运下楚者十之七”;另一方面,本省计岸各州县的商人也因陆路运输成本高昂,纷纷改配川南盐厂,沿川江顺流而下向湖广透漏,“计口之发卖无多,下楚之私贩实伙”[2]卷三《赋役》。笔者认为,这一转变大致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是四川盐产中心由川北向川南的转移[9]4-13,主要配行川北盐的贵州不得不更加依赖产盐旺盛的川南犍为、富顺、荣昌等地,加之乾隆十四年(1749)“贵州巡抚爱必达咨四川,议以黔商改赴犍(为)厂纳课领引配盐,至永宁缴引换票”[5]卷十《转运》。如此一来,黔商直接在川南犍为县等地配盐、在永宁县完成交易,大部分井盐可不经过嘉陵江运道和重庆直接转运贵州。二是“改配”制度的滥用。井盐生产格局的变化,瓦解了雍正年间确立的“定厂配盐”制度,产区与销区的对应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大量盐引并没有因原厂无盐可配而被户部豁除,地方政府为顾考成遂不得不默许大批商人持川北盐引到产盐旺盛的川南地方“改配”[10]卷九《山货》。三是川江(长江宜昌到宜宾段)运道的疏通。乾隆五年(1740)至十三年(1748)间,云南巡抚张允随为滇铜京运整顿川江河道,几乎将整段长江上游河道打通[11]86-91。在有利运输条件的助力下,许多盐商借用行“边引”的名义,从重庆顺流而下大规模向湖广透漏,湖广边远地区的食盐市场大部分为川私盐所占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据湖广总督舒常称,淮、川盐分界线在“宜昌府属巴东归州一带界卡”[12]卷一三〇二。直至咸丰以后,“川盐济楚”才打破了这一长期以来基本相安无事的格局。
综上所述,随着清前中期川盐对贵州、湖广市场的相继开拓,拥有优越水文条件的重庆逐渐成为川盐贸易网络的集散中心,这一局面使巴县盐码头始终充斥着大量食盐。尽管专卖制度对官、私盐有着严格的区分,但在食盐转运贸易繁荣的重庆,官与私的界限实际上十分模糊,政府对食盐市场的控制除税收手段之外显得极为有限,而更多的是通过改变制度来承认食盐市场的既有格局。在介绍完清前中期川盐贸易网络的形成过程后,接下来笔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处在网络中心的巴县,继续探讨盐法制度与食盐市场的互动过程。
二 清代巴县县域内官盐贸易网的建立与崩溃
清代巴县的食盐供应主要来自川北盐产区。在雍正年间全面整顿四川盐政的背景之下,巴县于雍正八年(1730)“禁革盐行,计口招商”,在千斯门外签商六名(称“老埠商”);乾隆五年(1740),又在临江门外新增盐商六名(称“新埠商”),认销射洪、蓬溪、三台县水引共526道,每年缴纳定额盐课银4,570.59两[2]卷三《赋役》。专商引岸制度确立后,原来“盐行”中资本较多的部分商人成为领引纳课的“专商”,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合法的食盐贸易之外。盐商不再以“承差”的形式垄断食盐市场,而是通过缴纳定额盐课获得本销区食盐贸易的独占权。然而,在地处川盐集散中心的巴县,官盐贸易网建立不久便在与私盐的竞争中趋于崩溃,地方盐法制度也相应地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多次改变。
雍正年间建立起来的巴县官盐市场运作模式,是由盐商持引到指定盐厂配盐,运至巴县盐码头,除满足县城需求外,于“四乡分立子店十二处”[2]卷三《赋役》。“四乡”指巴县城外的西城里、居义里、怀石里、江北里,子盐店设在其中的12个“场镇”⑤中,或由盐商直接经营,或由盐商雇佣他人经营。各场盐店将部分官盐就地零售,部分转运到其他没有设立盐店的基层市场,各地居民必须买食官盐。与两淮等地盐商动辄由一人垄断数十州县的食盐贸易不同,巴县由12名商人“朋领盐引”的方式直接触发了盐商对县域内部销售地盘的争夺,新老埠商之间围绕“争界争岸”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至乾隆四十年(1775)裁新埠商,而老埠商仍争执如故,致酿命案。嘉庆初减盐商额,归并一姓纳税”[13]卷四《赋役》。其中细节已无从查考。不过,根据《巴县档案》可知,嘉庆朝以后,官商由“原籍射洪”的秦姓世代担任[14]6-6-9987。
在施坚雅建构的农村市场结构模型中,商人分为在“中心集镇”拥有货栈的最高级批发商,在中间集镇“兼具批发、零售两种功能”的商人,在“基层集镇”经营小店铺的商人,以及在各级市场中巡回转运的“行商”,农民需要的商品通过这个体系向下分散到所有层级的市场[15]37-38。但是,引岸制度规范下的巴县盐商,既是“运商”又是“零售商”,必须对整个食盐贸易体系中几乎所有环节负责。除非盐商有足够的资本、政府有强大的缉私力量将官盐贸易网完全封闭起来,否则这种情形在实际食盐贸易中不可能长久维持。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川盐湖广市场的扩张,作为集散中心的巴县聚集着大量食盐和以贩盐为生的人群,严重冲击了巴县的官盐贸易网络,其主要表现是盐商的分化、消亡和官方文本中被称为“私贩”的人群在各级市场的食盐流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乾隆六十年(1795),盐商秦仁田禀称,巴县“引盐堆积如山,包斤不动”[16]258。有缴纳盐税重责的盐商,为维持经营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将盐引出租给外省客商行销,分散官盐运销环节的责任。盐商分化为正商、运商。正商,又称坐商、引商,是巴县领引纳课的官商,嘉庆初年以后归由秦姓世代充认;运商,又称行商、号商,是向正商租引、实际从事食盐贸易的外省客商⑥。值得注意的是,盐商分化不是巴县特有的现象,乾隆末年以来四川许多资本不富、无力行盐的官商,皆纷纷将盐引“出典与山陕客民行销”,获取租金收入以缴纳课税[5]卷二二《征榷》。二是雇募“盐巡”,在本城与各场镇严缉私贩。盐巡,又称商巡、盐丁、巡丁,受雇于“平日在渝千斯门经营事务”[16]262并不下乡的盐商,每月到各场镇查拿私盐。盐巡直接听命于盐商或在各场镇开设盐店的盐商代理人,是缉私的主要力量。《巴县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乾隆末年以后商雇盐巡与私贩之间的讼争案件,其过程一般是私贩挑盐在某场贩卖,与该场官盐店盐丁发生冲突,本场约客作为见证人对簿公堂。此类案件,自乾隆末年起,历嘉庆、道光、咸丰朝,呈不断上升的态势⑦。
巴县私盐案件多发生在各场镇中。被指称为“私贩”的群体,其身份构成十分复杂。一是在场镇中开设栈房、铺面的商人。如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白市驿廖花胡子、曾正彪等人“系该地土著富豪,各开铺面”,雇脚夫张必珍等44名到甕坝沱挑盐回来贩卖,遇盐商秦裕成所雇巡丁廖元川阻拿构讼[14]6-2-330。二是在各场镇中从事转场贸易的小商小贩。如嘉庆二十二年(1807)九月,北碚场“贩卖烟叶生理”的傅绵,“到璧山县接龙场把烟卖完,因见那里盐价便宜,家乡卖盐的不识姓名年老妇女收买零盐五十四斤,挑回转卖”,被在北碚场秦森盐店充当巡丁的雷顺等人砍死[14]6-2-307。三是误买私盐的普通百姓。如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在石龙场开饭店生理的黄泽佑,因“误买綦盐十二斤”,被盐商秦森在该场的经理人岑南斗及所雇巡丁指为私贩[14]6-2-5340。四是明火执仗“抢毁盐店,不法已极”的大伙盐枭、啯匪。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运商张泰来禀称,巴县“私枭拥众,率领啯匪,各执枪炮数百余人,大伙兴贩霸踞引岸,敢与弁兵迎敌,全无顾忌”[16]263。这些不同种类的“私贩”,其实就是施坚雅理论中活跃在各级市场中的商人,食盐通过这一私盐市场系统向下流动,而误买私盐的老百姓也只不过是这一体系中的普通消费者。
盐商分化和雇募盐巡缉私几乎损害了其他所有群体的利益。一是盐商分化使地方政府盐税征收困难,“号商既出租于引商,而所完课羡,又需交引商自行封纳,引商往往私自挪用,延不交库”[17]70。二是官盐店、盐巡与私贩之间冲突不断,严重扰乱了地方社会秩序。构讼案件中被盐巡拿获的大伙私枭很少,很多都是盐巡借缉私之名报私仇、勒索钱财而抓获的小商贩与普通百姓。如嘉庆十二年(1807)四月,经营石龙场盐店的岑南斗,“藉与商人(秦森)卖盐名色,雇募巡丁,以泻洩忿之阶,凡属同伊稍有仇隙者,即诬卖私盐大题,纵令巡丁纠结多人,或拦路估夺,或入室搜寻,受害之家,男号女涕,惨不胜言;又有一等无业痞徒,冒充巡丁,滋扰害众”[14]6-2-304。三是本有缉私之责的各场镇乡约、客长,面对私盐案时往往站在盐商与盐巡的对立面。如乾隆六十年(1795),走马岗场客约刘正科等人对“本场开盐店之王姓为富不仁”、肆意抬价的行为十分不满[18]339。又如嘉庆六年(1801),白市驿约客何廷秀等在盐巡缉私时袖手旁观,“剧霸匿凶”,盐商秦森禀称:“欲得私枭,先拘约客,不惟引岸无私、凶手有着,更得地方宁靖、暴去良安。”14]6-2-330官盐贸易网络濒临瓦解,私盐贸易蓬勃发展,地方政府盐税无征,更出于地方稳定的考虑,倾向于放弃专商引岸制度。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四川总督常明上疏建议在巴县革除官商,食盐自由贸易,即“仿照巴州等处盐课归丁、公同完纳之法”[5]卷二二《征榷》,将盐课摊入地丁征收。虽然此举并未成功,但足以说明巴县盐商的处境已是四面楚歌、摇摇欲坠。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到道光年间,四川许多州县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都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革除官商,截止道光末年已有30余州县推行了盐课归丁改革[19]51-62。
对食盐贸易有垄断之权的官商来说,咸丰年间议准的“川盐济楚”政策使其处境雪上加霜,“川盐由原来只能以走私方式销往湖广,变为堂而皇之进入湖广销售,潜在市场成为现实市场”[20]85。私盐、私贩的标签被政府撕去,盐商缉私几乎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如咸丰六年(1856)三月,盐商秦懋枝禀称:“有私贩刘老四率领夥贩二十余人,船载私盐二只,约有四百余包,直抵县治不远之龙隐镇河岸,各执矛杆火枪上岸”,巴县县令却将此事推给江北厅,批示:“江北巡丁盘拿私盐,有无受伤,自能向江北厅禀报,毋庸过虑具禀。”[14]6-4-910又如咸丰七年(1857)十月,盐商秦甸巡役余贵、高槐“在临江门拿获悍妇私盐二十余斤”,“守城义勇严春林、冯得胜、傅家二等恃势不服,朋将巡役余贵□□在地毒凶打□□颅,血流不止”[14]6-4-911,孤立无援的盐商秦懋枝、运商张泰来最终于咸丰八年(1858)告退,得到知县张秉堃的批准[14]6-6-3248-5。
综上所述,巴县的官盐、私盐市场截然两分是雍正年间确立的专商引岸制度造成的结果,若政府和专商无力完全控制巴县繁荣的食盐转运贸易,官盐贸易网络的崩溃是可以想见的。乾隆末年以来,尽管商人采取了种种措施,试图维系官盐贸易网络的有效运转,但在私贩、地方胥吏广泛参与食盐贸易以及地方政府不配合缉私的情况下一切归于徒劳。至咸丰八年(1858)以后,巴县终于形成既无“专商”又非官盐“销岸”的食盐自由贸易状态。
三 “摊课归丁”、官运改革与商专卖制的终结
咸丰年间,盐商告退给地方政府留下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部颁的盐引如何处理?一是盐税由谁缴纳?同光年间,巴县地方官、绅粮、商人等群体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博弈,先后经历了绅粮“卖引救课”、招商领引以及“摊课归丁”的争论,最终于光绪四年(1878)纳入到丁宝桢在全川范围内的官运改革中,巴县被划为官运计岸,由“黔边盐务江巴分局”委员经理,官督商销的专商引岸制度在巴县宣告终结。光绪四年(1878)八月,知县李玉宣回顾了巴县自盐商告退后的盐法变迁过程:
敬禀者。案奉宪札,转奉督宪,以盐课是否归丁,或系商人领引承办,承办之商是否实系认真配运行销,饬即逐一详细查明禀复,等因。奉此。遵□卑县盐务,自咸丰八年(1858)以后,因无商承办,详明由三里绅粮卖引救课。嗣于同治八年(1869),设□因招商争控,奉各宪访查地方情形,详请将卑县应行盐水引五百四十五张,陆引陆百五十张,每年征税银贰千零叁拾贰两七钱八分五厘,羡截银贰千七百五十贰两一钱四分五厘,由陈秉钧、罗公信等领引配运行销,完纳税羡,试办十年,限满请展。本年五月,据绅粮龚启元等以盐课应行归丁,呈奉督宪批县,查取各绅粮情愿归丁认结,呈□核办,已将各绅粮来县结认姓名造册,禀请宪台察核转禀详咨,迄今未奉批。兹奉前因,所有卑县盐务现据绅粮恳请归丁,业经转禀请示遵办缘由,理合禀覆宪台,俯赐核转示遵。为此,具禀。[14]6-6-3241-7
咸丰八年(1858)盐商告退之后,盐税不由商纳,改由“三里绅粮卖引救课”。根据山田贤的研究,道光年间登上历史舞台的“绅粮”是绅士和粮户两个社会阶层的统称,“在地域社会发挥着领导作用,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为州县政府所认识”[21]215-223。巴县粮户是载入当地粮册的有地民户,获得功名的粮户被称为“绅粮”。由三里绅粮“卖引救课”、代缴盐税是他们在地方公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盐引买卖尽管不合朝廷盐法,但在道光年间已十分普遍,主要是归丁州县“藉称课税不足,将引转售别县”[5]卷十八《引票》。咸丰七年(1857),四川总督吴振棫“请酌拨各属滞引并兼配犍富二厂花盐、巴盐,税厘征收如例,既而各商争趋以积引改代往济”[5]卷十一《转运》。也就是说,政府承认各州县滞引可到犍富二厂配盐直接运销湖广,为数甚多又无商承领的巴县盐引受到济楚商人的青睐,此时三里绅粮“卖引救课”应该能够保证政府的盐税收入而不误考成。然而,自咸丰十年(1860)起巴县抽收济楚川盐“渝厘”后,“每引巴盐收厘金19.5两,花盐收银25两,其余边计各引运费极重,行销甚绌”[22]425。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淮盐运道疏通,曾国藩等人推行了一系列“禁川复淮”、规复旧岸的措施[20]85-90。川盐湖广市场受到很大影响,本省盐引也日行壅滞、贬值,此时巴县三里绅粮“卖引”已经无法“救课”。
盐引积滞,税课无出。同治八年(1869),巴县开始重新招商认引,由本地绅粮陈秉钧、罗公信二人承领水引545张、陆引650张配运行销,缴纳盐税羡截银共计4784.93两;陈、罗二人并非占有引窝的正商,经营方式为“同领夥办”,在县域内“未分引岸”[14]6-6-3248-2,不会出现乾隆年间盐商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况。为缴纳盐税和保证引盐销路,陈、罗二人采取抬高盐价并重新招募巡丁缉私的措施,以“教民吴昭”为“巡丁头目”[14]6-6-3241-7,这与乾嘉时期秦姓盐商的做法并无二致,故而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招商试办十年之期结束后,光绪四年(1878)五月,绅粮龚启元、石渠等人直接向到巴县巡查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呈请盐课归丁,丁宝桢当即批示:
据呈该县盐务积久弊生,请摊课归丁,依照璧山各县章程办理,以挽流弊、遏乱萌各节,本系因地制宜之举。惟按丁摊课,须出地方粮户踊跃输服,乃能办理。仰巴县即行传讯各里绅粮,能否甘愿照办,取具切结,由县切实申详。本部堂酌核办理,毋稍含混为要。[14]6-6-4525-12
盐课归丁、摊课归丁、按丁摊课,都是指将盐课摊入地丁钱粮中征收,革除专商,废引不行。发起者龚启元为工部郎中,籍隶西城里;石渠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户部主事,籍隶居义里。二人都是巴县“三里绅粮”中的头面人物⑧。盐课归丁遭到商人的“百计阻扰”,知县李玉宣也“一心延搁”。六月二十四日,巴县三里各甲粮民数百人联名向川东道姚觐元具禀盐课归丁势在必行的原因:一是盐商“可于盐中暗藏□□同夫马加价,与其由商转取之民,而每年课祗数千,昂价已逾数万,何如民径输之官,而每年价减数万,课仍只数千”;二是革除商人可以“显绝私枭”[14]6-6-3238-9。禀状中将盐商抬价类比于夫马加价,而夫马局又是“某些官员捞取好处的场所”和“地方官员贿赂上级的一种机构”[23]92,绅粮可能向道台暗示了商人与巴县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据继任知县陆葆德称,“该商每年三节,向有规费银两”呈送巴县知县[14]6-6-3245-2。若行归丁,知县的盐商规费银两落空,巴县地方官自然不愿革除盐商、推行盐课归丁改革。
道台姚觐元接到三里绅粮的禀状后,随即批饬:“仰巴县遵照督宪批示,迅即传集绅粮,毋稍迟疑。”[14]6-6-3238-9在总督、道台的压力之下,至同年七月,“赴道□认结绅粮”、“来县具认结绅粮”、“传集公所面听总结各绅粮”者,已达398名[14]6-6-3236。巴县档案中还保存了大量城乡各“载册粮民”甘愿摊课归丁的具结状,并标明每户“应完粮银”;此外,还有忠平团、四义团、玉皇团、复兴团等25团团首、监正所管民户的具结状[14]6-6-3237,6-6-3238,6-6-4525。
与此同时,一些与盐商存在利害关系的绅粮,则坚决反对盐课归丁。候选县丞何国衡、候选通判吴昭等人于光绪四年(1878)七月十二日向四川盐法道蔡逢年告状,攻击“石渠同伊夥江作孚争充本邑盐商”,争商不遂后,蒙蔽道宪请求归丁,各粮户的具结状皆为石渠等人伪造,绅粮雷晋廷、赵仙洲、周韫山等人都未参与其中,“具结其中难保不无假冒顶替情弊”[14]6-6-3238-6,6-6-3238-7,6-6-3238-8。八月初二日,三里绅粮又具禀已经调署华阳县事的李玉宣称:
具禀。……绅等睹骇,切石渠以进士官户部,例不充商,争于何有,结系道府县当堂亲收,有谁主议盐务大局,归丁即是力顾。查具呈之何国衡,系罗公信姻家,李鞾系管公信讼稿,均伊同党。教民吴昭系公信巡丁头目,刘承缙系公信食客,其余控讼人等,均是峡匪冯次舫豢养棍徒。公信等非商非运,恃教霸岸,藉引贩私,昂价病民,招匪酿命,案集如鳞。恩宥咸知地方不堪其扰,盖不能不望妥议具覆于贤父母也。绅等前已具情愿甘结,而该词称雷晋廷系属窃名。闻经道宪委员饬查,已取晋廷亲押,并无递窃结状,可见窃中有窃,悉系公信所为,希图阻公专利。为此禀恳俯顺舆情,访之众论,分别伦类,以靖地方而留德政。[14]6-6-3241-7
反对归丁的人,不仅与盐商罗公信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大部分都是天主教教徒。不少取得功名的教徒,即所谓的“教绅”阶层,如盐商巡丁头目、候选通判吴昭系教民,而“峡匪冯次舫”系天主教会爱德堂⑨会首。学界多认为,同治朝以后,重庆“教案”频发主要由于教会势力与传统绅权展开了激烈的权势竞争⑩,却未深入讨论背后深刻的经济动因。上引材料表明,教案频发更多的是与食盐贸易等具体经济利益的争夺相关。巴县盐商与天主教会上层势力(教绅)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借助天主教会的庇护,“恃教霸岸,藉引贩私,昂价病民,招匪酿命”,试图垄断巴县的食盐贸易,并从事走私活动,在盐课是否归丁的问题上与其他绅粮抗衡。因为涉及教民冲突,地方官不敢贸然处置,知县李玉宣遂将问题抛给总督丁宝桢以答复绅粮:“究竟为何办理,督宪自有权衡,非本县所能窥测。”[14]6-6-3241-7
在三里绅粮与盐商、教绅围绕是否推行归丁的问题争吵不休时,丁宝桢提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就是把巴县纳入到贵州边岸的“官运商销”设计之中,即“由政府直接组织食盐由场至岸的购运批发业务,到岸后招商领盐销售的专卖形式”[24]22。光绪四年(1878)六月,丁宝桢“委候补道唐炯赴泸州设局总理一切事宜,并于犍、富、射三厂设购盐分局,永、綦、合、涪四边岸暨近边之各厅州县设售盐分局,各委妥员分司其事”[25]1717。为防止本省“计商私贩搀越边岸之路”,丁宝桢在与贵州接界的泸州、合江、綦江等十余州县也先后施行官运,是为“官运计岸”,相当于在边岸与计岸之间建立起一个私盐防护带。由于巴县、江北厅“界在泸、合、涪、綦之中”,私盐易于透漏官运边岸,加之巴县食盐“代销之行号,又多系教民承充,现值教民多事,亦不可不防其渐”,为此,丁宝桢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折呈请将巴县、江北厅提归黔边盐务总局江巴分局管理,并定于次年正月初一日开始“照黔边章程发商行销”[25]1795-1796。改行官运后,巴县盐引不再颁给商人,盐课由官运局扣除成本后缴纳并向户部奏销,射厂、富厂购盐分局(厂局)向井灶买盐,交由官运局直接控制的船帮运到江巴分局(岸局),再由江巴分局核算成本、定价卖给巴县“裕济通”“同仁和”等行号承销[14]6-6-3261-7,这些行号由兼营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商人组成。
官运商销的成功之处在于盐课征收方式的有效性。官运局通过核算成本、定价卖盐的方式,在食盐转运环节就已经预征了盐课,并将其附着在江巴分局卖给巴县行号的卖价当中,行号进一步将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终表现为食盐价格的上升。只要官运还在维持,那么盐课的征收便不成问题。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商运还是官运并没有什么影响,高价的官盐依然不受欢迎,政府对县域内食盐流通的控制依然十分微弱。光绪七年(1881)六月,丁宝桢“访闻近日沿江州县又多贩盐私枭,各处缉捕废弛,实为地方大害”,要求地方严查,巴县政府遂在城厢内外及沿河一带姚公场、石桥场、白市驿、走马岗等51处场镇遍贴告示[14]6-6-3251-15。光绪年间,巴县的卖盐行号没有像此前专商一样的权力招募盐巡,缉私的主要力量是江巴分局雇募的勇丁,此外地方政府的差役、各场镇首事亦有缉私之责,但是局勇与此前商雇盐巡的遭遇非常相似,“各乡监正、团保并不认真查拿,甚至包庇私贩,希图渔利”[14]6-6-3251-6,县域内的食盐贸易又恢复到乾嘉以后官盐与私盐激烈竞争的局面。
四 结论
王朝国家食盐专卖制度在地方的表达是盐课征收体系的建立,然而“定额化”的盐税难以根据市场状况及时做出调整,政府对食盐贸易的控制手段显得极为有限,结果是专卖制的崩溃与私盐市场的逐渐发育。如雍正年间巴县虽然确立了规范的专商引岸制度,但实际上地方政府连最基本的缉私责任都未能承担。乾嘉以后这一专卖制度逐渐沦为具文的过程,便是巴县食盐贸易自由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曾小萍提出“清政府极少干预四川盐业市场,同时也几乎不予扶持”[26]30的观点,虽然失之笼统,但对食盐贸易持续繁荣的巴县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官、私盐截然两分是国家专卖制度造成的结果,如果政府放弃界定者的身份,放弃对食盐贸易的管控,同样可以征取足额的盐课,那么在实际的食盐贸易中严格区分官、私盐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带来无休止的讼案。现存有关清代盐法的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显得较为支离。要厘清某一地区较长时段内的食盐贸易与盐法制度的互动过程,连续性较强的地方档案史料显得十分珍贵。清代巴县的案例告诉我们,私盐贸易并非纯粹的市场问题,而是始终与政治、社会密切相关。对于盐商等既得利益者来说,滥用“私盐”的标签通常成为其与他人争夺盐利的有力工具,地方各类人群在食盐贸易中争夺“盐利”的博弈过程,便是新旧制度更替的过程。一项新制度的出现,无论是雍正年间确立的专商引岸制度,还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分化,抑或咸同年间的革除盐商与绅粮卖引、光绪年间的盐课归丁之议和官运改革,都可以说是制度对某时段食盐贸易格局的承认与规范。
注释:
①清代官盐销区划分缺乏市场合理性的代表性论述,主要有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第二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久谊《清代盐专卖制之特点——一个制度面的剖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7期);清代私盐种类及其对官盐贸易破坏性影响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考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②张学君、冉光荣认为,清初到雍正九年(1731)以前,四川以零星商人贩售的票盐为主;雍正九年(1731)至光绪三年(1877),为商运商销的引岸制时期;光绪三年(1877)以后,改为官运商销。这一阶段划分为许多川盐史研究者所接受。参见: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张洪林《清代四川盐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③本文在征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巴县档案》时,使用的四位数字分别代表“全宗号-目录号-卷号-页码”:全宗号为巴县档案代码,目录号为时间代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编为1,嘉庆朝为2,道光朝为3,咸丰朝为4,同治朝为5,光绪朝为6),卷号为该卷档案在某朝的序列号,页码是指该处引文在该卷档案中的页码,本文详注至“页码”的地方主要是卷内文件张数较多、以缩微胶卷为载体的光绪朝档案。
④雍正年间“计口授盐案”规定了川盐每年额行贵州市场的官盐总量,康熙中叶以来逐渐发育成熟的运销格局得到承认与制度化,称“黔岸”或“贵州边岸”。下表根据雍正《四川通志》卷十四《盐法》的数据制作而成,其中“官盐数量”一栏,根据四川“水引例配正盐五千斤,陆引例配正盐四百斤,每百斤为一包,水陆二引,每百斤均准带耗盐十五斤”计算得出。通过下表可知,经过重庆转运贵州的官盐数量约占总量的48%。

盐产地原额水引(张)原额陆引(张)官盐数量(斤)备注川北盐潼川州26301512250射洪县2204012673000中江县1490856750蓬溪县51801978500小计3134018020500约48%需经重庆转运运道:沿涪江、嘉陵江顺流而下,经巴县转长江水道贩运入黔川南盐富顺县1759010114250荣县145008337500犍为县11100109250乐至县12069000资州270155250内江县700402500小计332910019187750约52%不需经重庆转运合计646310037208250
⑤巴县“场镇”是周围乡民进行土特产品、日用生活必需品交易的场所。参见: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相关部分。
⑥嘉庆朝至同治年间,巴县运商一直由张姓开设的“泰来”盐号充任,《巴县档案》中但凡涉及盐商事务的档案,“具禀人”一栏皆题为“正商秦某某、运商张泰来”。
⑦据笔者目前检阅的“巴县档案全宗”,嘉庆朝以后商雇盐巡与私贩构讼案件数分布如下:嘉庆朝6-2-304,6-2-305,6-2-306,6-2-307,6-2-309,6-2-330,6-2-5340,6-2-6786;道光朝6-3-531,6-3-537,6-3-538,6-3-541,6-3-551,6-3-552,6-3-555,6-3-560,6-3-561,6-3-572,6-3-786,6-3-1115,6-3-1116,6-3-7848,6-3-10246,6-3-10273,6-3-10456,6-3-10560,6-3-10674,6-3-10783,6-3-10783,6-3-10805,6-3-11052,6-3-12063;咸丰朝:6-4-300,6-4-316,6-4-894,6-4-895,6-4-910,6-4-911,6-4-934,6-4-1291,6-4-3369,6-4-3378,6-4-4157,6-4-5955,6-4-6315等等,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态势。
⑧就石渠的情况来看,自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便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如同治七年(1868)因巴县“向无门班”导致投刑数人招结匪党扰乱地方,石渠请求知县“协恳裁制”;同治八年(1869)巴县三圣庙附近不少居民“入庙骚扰、毒取鱼虾、取党估捕”,石渠请求知县严禁此类行为。
⑨重庆天主教会爱德堂由教民罗广济等人于咸丰六年(1856)创立,冯次舫于同治二年(1863)入会后“倡首募捐”修建大花厅、经手承买田业并成为会首,到“光绪初年,经冯次舫等□□立义学、病院”。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⑩较大规模的“重庆教案”有同治二年(1863)第一次重庆教案、光绪二年(1876)重庆江北厅教案、光绪十二年(1886)第二次重庆教案。相关研究参见:艾小惠《重庆教案》(《史学月刊》1957年第5期)、曾绍敏《第二次重庆教案述论》(《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邓常春《晚清四川教务教案视野中的官绅民教及其互动》(四川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梁勇《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李重华《1876年江北教案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
[1]邱澎生.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C]//邱澎生,陈熙远.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2]王尔鉴,王世治,等.巴县志[M].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重庆市图书馆藏.
[3]马琦.清代贵州盐政述论——以川盐、淮盐、滇盐、粤盐贵州市场争夺战为中心[J].盐业史研究,2006,(1).
[4]李俊甲.太平天国时期川盐在湖南湖北市场的进出与银流通[J].盐业史研究,2006,(1).
[5]丁宝桢,等.四川盐法志[G].光绪八年(1882)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8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范金民.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贸行为[J].历史研究,2009,(3).
[7]张渝.清代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8]黄廷桂,张晋生,等.四川通志[M].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鲁子健.试论林儁的盐务改革[J].盐业史研究,1994,(3).
[1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M].道光十年(1830)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馆藏十八卷电子扫描本.
[11]罗传栋.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1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朱之洪,向楚,等.巴县志[G]//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6).成都:巴蜀书社,1992.
[14]巴县档案全宗[G].四川省档案馆藏.
[15]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17]王守基.盐法议略[G].北京:中华书局,1991.
[18]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19]黄凯凯.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J].史学月刊,2016,(8).
[20]黄国信.从“川盐济楚”到“淮川分界”——中国近代盐政史的一个侧面[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21]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M].曲建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3]邢飞.丁宝桢与四川夫马局改革[J].中华文化论坛,2015,(9).
[24]鲁子健.试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J].盐业史研究,2000,(2).
[25]罗文彬.丁文诚公(宝桢)遗集[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第7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26]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凌兴珍]
Salt Trade and Salt Management Changes of Baxian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Kai-kai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he essence of the salt management problem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nopoly and the market regulation. The monopoly system divided the salt trade into official and illegal salt market. But the “fixed” salt tax collection system was difficult to adjust with the market change,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 and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illegal salt market. Salt merchants, Gentry and other vested interests often use the powerful tool of “illegal salt” label to attack their business opponents and the changes of local salt management system is only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various market players. As a distribution center of Sichuan salt expor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Baxian county preserved a wealth of archival materials, which provids the possibilit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alt trade and salt system in a certain area for a long time.
the Qing dynasty; Baxian county; salt trade; Sichuan salt exporting; salt management changes
2016-11-14
黄凯凯(1992—),男,江西新余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F129.49
A
1000-5315(2017)04-01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