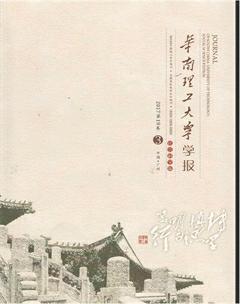公民文化与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及路径选择研究
徐伟明+解丽霞
摘要: 公民文化作为现代城市治理的理念和技术,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以价值认同增强城市凝聚力,以制度有序规范城市软实力的生成机制,以公共参与激活城市软实力的内生性资源。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城市软实力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城市精神已形成与价值认同不平衡相并存;市民参与意识增强与制度供给不足相并存;市民道德素质较高与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相并存;参与方式多元化与象征性参与的现实相并存。鉴于此,本文以培育公民文化为现实切入点,创新城市软实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社会资本的孕育与建构,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创新。
关键词: 公民文化;城市软实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②,表明我国的软实力建设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最终要靠区域或城市去贯彻与落实,尤其是要依靠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目前,理论界主要从大型赛事、文化资源、传媒、社会资本等方面入手,去探究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路径。然而,提升城市软实力、培育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要靠城市文化的发展、公共管理的完善、城市创新力的激活和国际沟通的加强等,更需要彰显一种现代精神,而这种现代精神主要通过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普通市民的素质及公共参与等方面来彰显。从根本上说,要提升城市软实力必须从城市的基本元素——公民生活去分析,把公民文化放在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背景中去理解。以公民文化的视角自觉探讨广州城市软实力,有助于拓展广州城市软实力的提升空间,对于加快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城市软实力的另一维度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正式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根据奈的阐释,软实力是一种“让他人想要你希望他要的东西的能力”[1]2,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三种资源。“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全球学界与政界对软实力的研究热潮。国内学者对于城市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步较晚,学者主要采用以“投射法”将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投射到区域或者城市软实力的研究,通过列举软实力的资源或构成要素来充实城市软实力的内涵。从现有文献看,倪鹏飞较早提出城市软实力的概念,他明确地将城市竞争力分为硬力和软力。其中软力包括“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和秩序力”。[2]41-42马庆国先生认为,区域软实力应理解为“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3]11陈志、杨拉克把城市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之和”[4]131。庄德林、陈信康把国际大都市的软实力概括为“城市文化、公共管理、人力资本、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和国际沟通力”[5]六个方面。现有学者所列举的城市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而言都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普遍侧重于城市软实力的“静态资源导向”的归纳,而对于“动态资源导向”的城市软实力(如公民素质、公民“文明”能力、社会资本等)论述不多。在城市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任何一个地域或种族的居民,不用他自己選择,也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最能反映这个城市的软实力。本文从公民文化视角讨论城市软实力,主要涉及公民的价值观念、道德素质、公共生活的规范、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软实力的强弱程度是与其公民文化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公民文化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精神。它强调以价值认同为基础,以制度有序为前提,以积极参与为路径,主要表现为公民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理性参与。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公民文化的回应”。[6]73斯宾塞也曾说过:“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7]8增强城市软实力不仅仅通过发展城市经济、创新文化、完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对公民自身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3期徐伟明 等:公民文化与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及路径选择研究
(一)价值认同是增强城市凝聚力的前提性条件
城市凝聚力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现代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巴黎、伦敦、纽约,之所以有它们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绝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物质条件”[8]19,同时也因为它们的文化条件和精神条件。这些城市都有自己鲜明的、富有个性的、具有文化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城市精神。每个城市的公共生活都会形成公共价值,它是理性公民共同认同的城市精神。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价值认同是市民对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内涵精神以及习俗等产生一种信仰和情感的共享和认同,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在价值认同的主导下,市民对自身社会角色形成身份确认,如主人翁意识,城市主人意识的形成。当市民的价值认同转化为对城市的归属感时,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表现为市民以城市主人的角色关注城市发展,参与城市建设、维护城市公共利益。因此,要增强城市软实力就必须增强城市凝聚力,而增强城市凝聚力的关键是实现市民为城市公共生活福祉而行动的社会价值观的认同。
(二)制度有序是催生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保证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9]3公民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支柱性理念和技术,既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公共生活,本身又内含保证公民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制度机制,即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和“输入”机制。如果说制度是城市文明的外在规范,那么,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态度,情感和行为所表征的公民文化,则是衡量城市软实力的内在标度。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作为市民城市生活的基本模式,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资源性条件。“制度影响着个人和集团在已有制度内外的行为方式,影响市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影响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期望,影响社区的语言、认知和规范,而且还影响各种概念如民主、正义、自由以及平等等的涵义。”[10]159任何制度都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能通过规范市民城市生活提高市民的民主智慧和道德素养,又能够保证市民的利益诉求在契约中获取依据,从而催生市民对城市的吸引力和认同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1]11只有不断完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城市才有可能和谐发展。
(三)公众参与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内生性资源
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根本力量是普通市民。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既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的引导和参与,更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城市学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在讨论城市规划时曾说:城市设计不能仅仅规划居住、工作、文娱和交通,而必须把整个城市规划成一座舞台,供人们进行积极的市民活动,教育学习和进行生动而自治的个人生活。由此可知,城市发展离不开市民城市生活的理性参与。在参与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理念表达了这样一组现代行为方式, 即城市市民广泛地自下而上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它凸显了参与活动的个体能动性和自下而上的层面。”[12]“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果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很难使其行动合法化”。[13]80-85公民积极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反映基层市民的基本价值诉求。阿恩斯坦在其《公民参与的阶梯》中谈到,公民参与“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使得未享有公民权益的人能够参与到信息分享、目标和政策确立的过程中。总之,公民参与是一种方法用以促进社会改革使人们能够分享富裕社会的资源”。[14]再好的城市发展理念如果得不到基层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没有市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实践,城市治理也仅仅只能停留在制度构建的层面,并不能达成现实的任务。
二、广州城市软实力的现状分析:基于公民文化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广州作为一个努力朝着构建国际大都市形象迈进的南方都市,国际化的程度日渐明显。如何使城市的公民文化水平与国际化都市的形象相吻合,是近年来学者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为了充分了解广州城市公民文化的现状,课题组以调查问卷和座谈的形式本文数据来自2013年-2015年广州市公民文化与城市软实力课题组的调研及追踪分析,课题组在广州以多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400份。 ,对广州城市软实力展开调查,探究广州城市软实力的基本现状。
(一)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已生成,然而市民对城市价值认同不平衡
西方学者斯宾格勒认为:“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来的城市精神。”[15]城市精神是城市软实力的内在支撑,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主体做出的客观选择。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提出了“城市精神生活理论”,他认为“不同的城市是建构在不同的城市精神基础上的,不同的城市市民也铸造了不同的城市精神”。[16]267广州城市精神表述为:“真智、富强、合作、创新、荣誉、用心”,其中,“合作”即“多元包容,平等合作”,这是广州能吸引700万外来人员的文化因素。在广州城市软实力的调查中,有476%的受访者“知道”广州城市精神,而将近505%受访者答案中包含“多元”或者“包容”的字眼,有163%的受访者“不知道”广州城市精神。调查结果表明,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已为广大市民基本接受,并成为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国最好的移民城市之一,广州没有歧视色彩,其包容精神和平等意识深深地浸透在市民文化之中。但广州每3个人中就有1个外来人口,广州市居民主要由新广州人、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居民构成,这对广州市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带来了考验。调查发现,当被问及“您认同广州城市精神吗?”,364%的受访者“认同”广州城市精神,并愿意为广州建设做出贡献,这部分受访者中将近812%是新广州人和本地居民。352%的受访者对广州城市精神“沒感觉”“与自己没关系”。可见,广州城市精神要充分发挥城市凝聚力的作用,还需增强广州市民对城市精神的价值认同。
(二)市民参与意识增强,然而市民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
现代化的城市必定是民主化的城市。如果没有市民的参与,任何一个民主化城市也是难于维持的。美国学者科恩认为:“民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它就是自治。”[17]273课题组就市民关心及参与广州城市发展的情况展开调查。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关心广州城市发展?”,近906%的受访者表示“关注过”,其中有52%受访者表示“经常关注”(经常浏览广州市政府官方网站)。阿尔蒙德曾说过:“可以假设,如果人民注意政治的和政府的事务,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制定决策的过程。”[18]99可见,大部分市民是关心广州城市发展的。当被问及“关于广州城市发展问题,你是否向政府发表过自己建议,如有,通过什么方式发表?”,有542%的受访者曾向政府发表过自己的建议,主要集中在网络或向街道办提议两种方式,86%的受访者参与过社区问题的商议。结果表明,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公共责任意增强。城市的发展需要制度性的生活规范来维持,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市民的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调查显示,近542%的受访者并“不清楚”自身在城市管理中的权责,但“听说过”法律允许市民参与城市管理。326%的受访者认为法律在保障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权益“较少”。公众参与在目前的这些法律性文件中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概念阶段,缺乏可操作的程序性规范,由此产生城市管理制度性供给不足,造成市民的参与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也将影响城市的治理水平。
(三)市民道德素质显著提高,然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
公民道德素质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与社会风气离不开公民的道德素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民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积极参与公共活动,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调查显示,662%的受访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一般”会主动让座,298%的受访市民表示“经常”让座,这说明广州市民具有较高的道德意识。当被问及“对城市社会中的随意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不文明行为”时,816%的受访者表示“深恶痛绝”,但上前制止的比例只有216%,这说明大部分市民的道德行为有待提高。社会资本是社会的粘合剂。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促进合作运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9]199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福山认为:“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20]18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社会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在广州城市的社会变迁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调查中发现,当被问及“其他人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时候,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但仍有235%的受访者认为是不可信的;当被问及“有人在大马路摔倒时,您愿意去帮忙吗”时,只有452%的受访者直接做出肯定的回答,有36%的受访者表示要“看情况”,这表明社会信任度有待提高,社会资本较为薄弱。社会资本是城市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必然促进社会交往,在相互交往中形成城市经济的繁荣。
(四)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平台增多,然而市民参与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
随着政府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公众评议的发展,以及听证在立法和一些重大公共决策的广泛运用,城市参与的广度有了一定的拓展。但在参与程度、参与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差距。公众参与程度是有发展阶段的。美国学者谢尔·阿斯汀将公众参与的发展阶段分为“不是参与的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实权的参与”。[21]240-141象征性参与阶段表现为对公众参与存在模糊的认识,整体上缺乏公众参与的自觉,公众参与的作用甚微。调查数据显示,关于观点“您是否参与过城市公共决策”,在受访的389人中,有1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间接地参与过”,而7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而对于决策大都是通过网络或报纸的渠道被告知。564%的受访人认为“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有何想法”,只有356%的受访人不同意这个观点。由调查结果可知,广州的城市参与水平尚处于象征性参与(告知性参与、咨詢性参与、限制性参与)。政府在已经做出决策以后才将决策结果告知市民,象征性地收集市民的意见。市民其实只是在被动地接受这些决策,而未真正起到参与作用。市民参与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参与不应是单向流动,而应是信息的双向流动,是双方意见的沟通、交换,体现为政府与公众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培育公民文化:提升城市软实力的现实切入点
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开始意识到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在通过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加强城市管理、创新城市产业文化等手段提高城市软实力,然而这些方法和措施的运用都离不开城市公民文化的培育。任何城市的现代化水平都与其公民文化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公民文化培育作为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切入点,也将成为推动城市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战略。
(一)“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
没有城市公共精神作为基础,就没有现代民主城市的产生。作为城市公共活动的价值取向,公共精神能够唤起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热情,促成与民主政治相应的公民文化的生长。一旦市民被赋予公共精神,在认知上容易形成共识:个体利益的实现必然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前提,在行为上表现出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公共习惯,在情感上表现为对城市发展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热情。针对公共精神的认知与理解,要使公共精神在现实中获取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其根本途径在于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城市公共生活是以责任作为其价值体系的基础,每个市民都是作为责任主体参与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立足点在于通过市民在参与中学习、讨论和感悟,形成市民对城市的共同意识,以共同的意识引导市民的社会责任和在公共领域活动中的行为。同时,公民教育也是化育市民公共精神的重要路径。教育的很大优点在于可以容易地把需要数年完善的技巧传授给后来者,它可以训练个人参与城市生活的技巧。市民的公共精神本身有其养成规律,要把公共精神内化为市民的个体认知,再外化为具体的行为, 就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科学的教育、引导, 增强市民对公共精神的认同与自觉。
(二)社会资本的孕育与建构
任何一个城市社会资本的发育状况都会直接影响其公民文化的成长。英国学者英格尔哈特曾经把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人际信任作为测量公民文化的重要指标,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诸要素尤其是信任与公民文化呈正相关关系。那么如何提升城市资本的存量来发展公民文化?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是神秘莫测的。政府能够制定一个削弱社会资本的政策,但却很难明白如何创建它。”[22]13如果要致力于城市资本的积累,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来解决影响社会资本构建的障碍性因素,如市民收入不高、就业率低等社会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加快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积极改善社会条件,增加市民社会福利,从而提高市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社会信任的增进还在于创设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载体。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发展市民参与网络议政,包括制度化参与网络和非制度化参与网络。强化市民的制度化参与,如市民咨询、听证会、信访等;创新市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平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利用传媒、网络等手段参与公共政策开始盛行,市民可在这些平台上进行意见表达,市民与政府之间可以针对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共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三)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公民文化倡导在参与式研究与行动研究的视野下创设解决城市与社区公共问题的新机制。作为民主实践的平台,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既能够增进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其参与能力和政治效能感,又消除市民参与政治的惰性心理,促进城市公民文化的生长。因此,培育社会组织是发展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空间。在城市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优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健全社会组织对政府让度空间的承接与管理机制。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向,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23]288同时,政府还需不断完善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如制定政府资金资助政策、税费减免优惠政策。总之,社会组织是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重要渠道,只有在组织与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才能使市民真正介入到城市发展的目标和公共政策的确立过程,享受社会富裕与城市繁荣的成果,真正实现“民治才能民有”的现代民主城市的目标。
(四)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创新
公民文化本质上是与民主制度相藕合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民主制度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离不开民主制度的教育和体验。在民主制度的规范下,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接受公共理性,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并将民主制度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促使公民文化发育成熟。制度是城市文明对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共同要求,它“是社会生活中的群体或个体的互动有序化,使社会关系结构化,也使城市文化的创造与演变有了方向和目标”。[24]18制度性供给不足是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设施性阻碍因素。要保证市民行使城市管理的权利,不能长期以临时举措或政治手段作为这一制度的保障,而需要在法律上和程序上保障参与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方面,创建制度化的表达机制,健全市民参与制度和程序,如逐步完善市民建议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反馈制度、申诉制度等各项制度。另一方面,在法律程序上保障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路径。就城市规划决策来说,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制定和项目决策的法定程序之中,建立城市规划编制、项目决策以及用地审批等规划程序的法律监察制度,监督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不符合规划决策程序的做法,以保障规划制定的科学民主和实施过程的依法管理。
参考文献:
[1]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马庆国,楼阳生.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陈志城,杨拉克.城市软实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5]庄德林,陈信康.国际大都市软实力评价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 (10):36-41。
[6]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7]斯宾塞: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8页。
[8]饶会林:城市文化与文明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诺斯.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0]March,Polso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The Organization Basis of Politics[M].New York:Free Press,1989.
[11]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2]缪青.公民参与和社区和谐:理念、变迁和制度化的趋势[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3):92-96.
[13]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 Sherry Aronstein.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April, 1971.
[15]刘世军:城市精神与上海传统之再确认[N].《文汇报》,2003-03-11(10)。
[16]王旭,黄柯可.城市社会的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宋秀贤,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8.
[18]阿尔蒙德和S·维巴著: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9]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0]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Sherry Arnstein.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1969. Richard T. LeGates & Frederic Stout(Ed.) , The City Reader(second edition)[M].Rout ledge Press,2000.240-141.
[22]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饶会林.城市文化与文明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