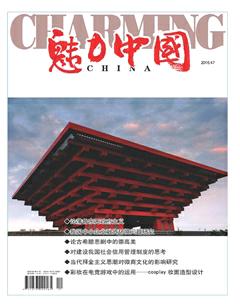中国书法艺术浅谈
摘要:书法是中国的国粹,究竟何为书法,各家说法不一。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汉字书法的特性: 一,汉字的实用美与艺术美;二,汉字结构造型、点画动势、用笔节奏的特點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图案性和具象性的区别;三,书法与文学的关系;四,汉字线条本身的形式美及与西方艺术美的不同
关键词:中国书法;结构造型、象形文字;点画动势
书法是中国的国粹,究竟何为书法,各家说法不一。有人说书法是用毛笔写汉字的艺术,这就把硬笔书法、甲骨文、钟鼎文排除在外。硬笔书法是硬笔写的,甲骨文、钟鼎文是刻铸的,但我们无论如何无法否认它们当中都有书法美,尤其是甲骨文和钟鼎文中那种因刻铸所产生的独特的美。把它们的美排除在书法之外,很难自圆其说。
有人说汉字的书法艺术在于汉字具有象形性,但象形性只是六书造字法之一,其它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而且其象形性随着文字的发展变迁以及几次的汉字简化,越来越弱。实际上,现在汉字的象形性远比古埃及象形文字弱,而抽象性却很强。所以,象形性不能看作书法美的根基。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有象形性,也有独特的美,如果象形性是汉字书法美的根基,那么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美为什么就不能也算作书法美?
我认为,汉字的书法艺术在于结体的点画之间有一种造型的“势”,它使线条之间产生动态的呼应和彼此牵引呼唤的动势,结果使抽象的汉字具有了形象性。而且,点画之间这种造型的“势”给线条和用笔创造了充分表现的舞台。也就是说这种“势”及其所造就的抽象的点画之间的动态象形,加上刻写人的用笔个性和风格才是汉字书法艺术性的根基,至于是毛笔写的,还是硬笔写的,还是刻铸的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当然用毛笔书写,更容易写出不同的笔意,使艺术性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从造型角度来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图案式的符号,它可以加以描摹,但它不能像汉字那样从用笔上来“写”出点画的笔势。甲骨文、金文,尽管是刻铸的却有“用笔”的感觉。
汉字书法美不在形体的描摹和具象,而在于上文所说的点画之间的“势”,在于点画之间的呼应和用笔产生的节奏感。在西方古典绘画中,线条是再现物象和人物的手段,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无所谓美与不美。在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线条不只是手段,还是目的,也就是说,线条除了用来描摹物象、人物,构架汉字外,其自身就呈现独立的形式美,成为独立欣赏的对象,只是书法比绘画更充分体现这一点。在汉字书法艺术中,线条有自身的“质感”,而在西方绘画中线条被消解在物象或人物中。
但是,书法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汉字这个载体,否则,无论其中有多少书法的形式美,都不能算作书法。以此类推,山水画中的皴法具有线条的审美特质,但离开山石之形,其皴法线条再美也不能算作山水画。中国绘画中线条的审美特性还只是半独立的,而书法艺术中的线条之美的独立性比绘画就更进了一步。
书法离不开成千上万汉字先天具有的笔画造型和动势,你想甩开现成的汉字,想另创一套自编的线条,以求其抽象美作为一种新的书法艺术,那只是痴人说梦、想入非非的扯淡。
中国书法艺术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或纯粹的“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说,书法艺术不是像西方艺术那样借用线条、色彩、构图逼真地表现宗教、神话和历史等强烈而且明确的“文本内容”,而是表现笔墨线条本身的“形式美”,尽管文字的含义对欣赏笔墨线条的“形式美”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是“实的”,不如说是“虚的”,从每种意义讲,可能是一种含糊的“心理作用”。
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纯艺术与实用的界线难以划分。书法艺术本源于实用,离不开文字,文字是文化中最实用的东西。最早的书法是在抄写和记录过程中逐渐总结出的一些工艺性的经验:如何把字写得更清晰好认,更精致、工整、漂亮,从而也更具有实用性。
在实用的工艺美之外,慢慢创造出抽象线条的形式美,如用笔产生的笔法、笔势、笔意及其韵致,从而产生一套复杂的书法艺术的森严法则。
书法美有不同的层次:低级层次讲究实用的工艺美,即工整、易识、精致、漂亮、规范。这是纯实用的层次,所追求的美是工艺性的,不是纯艺术性的;中级层次除追求工整、规范、精致、实用外,又萌生了对笔法技巧、笔墨趣味,对于线条的形式美的感悟,但只能刻意求之,不能得心应手,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个层次上书法艺术产生了;高级层次虽然不一定完全摆脱实用,但对于笔法、笔势、笔意,已胸有成竹,并能挥洒自如地操纵线条,不受实用和规范约束,达到抒情写意的目的。。
这高级层次,就是纯书法艺术的本质特点。
书法还和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最初产生于抄写产生的铭文、文告、经籍、碑文、书信,等等,其中任何一样都与文学相关联。
我们欣赏书法时,不用先搞懂文字内容,可以直接欣赏书法的形式美,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字内容与书法毫不相干。文字内容引发的情感一定程度影响对书法的欣赏。最典型的例子是颜真卿的“祭侄稿”。当你不了解“祭侄稿”的内容,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境况,仍然可以欣赏“祭侄稿”,欣赏它的“意不在书”,天机自动,欣赏“无意於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境界。但当你了解那一段悲惨的历史,并读完“祭侄稿”,知道此文是颜真卿在其侄子被俘,惨遭杀害后写就,你无意间会发现“祭侄稿”中有怒气、有悲愤、有极度的痛苦和悲懑激昂之情。
西方人欣赏中国书法困难重重,其原因在于西方艺术中没有中国书法的形式美。如:通过有意识地协调和控制掌、指、腕、臂,融入书写者对书法美的感悟和经验而产生的笔力;通过提、按、顿、挫、转、折、方、圆等用笔的起伏而产生的节奏感; 通过中锋用笔所形成的沉着浑厚的立体感。
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是西方艺术的“明星”,对画中美丽女子的神秘微笑的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微笑表现的是少女初尝世俗性生活的甜美而产生的窃喜,抑或是对世俗生活的揶揄?微微上翘的嘴角到底表现什么情感?我们可以欣赏女子丰满而韵味十足的身姿、姣好的面容和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手指,但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欣赏其中的笔触、笔墨、笔意和笔势,以及线条的形式美。我认为在西方印象派之前,西方绘画中基本上不表现形式美。西方人习惯于表现和欣赏形象和色彩的逼真。直到印象派之后,尤其是后印象派之后,西方人才对线条和色彩的纯形式美有所醒悟,而这种西方艺术中的形式美也不同于中国书法中的形式美。
中国一些书法评论家认为中国书法中的韵律感、节奏感在表现人的情感方面不亚于,甚至胜于音乐,我认为这实在是夸张得有点离谱。书法的抒情手段依靠的是线条的种种变化——提按、疏密、向背、起伏、疾涩、纵敛等等,总之,是通过造型时对线条意态形象的倾向,联想生活中具象的情境、氛围。在这儿抒情依旧是心理上一种含糊的类比。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公孙舞剑”之类,无非是对“势”的一种想象启迪,是线条在时间中的挥动,定形于空间的框架,从而引动视觉上的感悟,而音乐是通过旋律、节奏等音乐手段和不同乐器的音色将人的情感如镜般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音乐和情感之间有比较具体的对应关系,而书法却不能。
参考文献:
[1]启功 著 启功给你讲书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1。
[2]邱振中 著 书法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作者简介; 刘清浩,1957,男, 山东青岛人,教授,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文化艺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