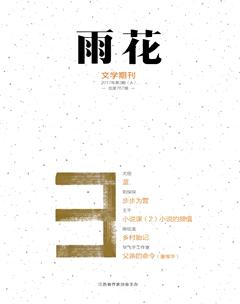温暖的冬天
李传华
我刚从乌鲁木齐到南京工作的那一年,是12月中旬,那几天细雨如丝,室外温度10度,我穿着一件单外套去上班。周围的人大多穿羽绒服或大衣,她们看我衣着单薄,就问我:你不冷吗?我说:10度,不冷!
真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作祟,无知者无畏啊。渐渐地,我就体会到这种10度和北方的10度完全不同,南京的冷湿答答的,那种湿寒气如同绵绵细雨无声地浸到人的骨头缝里,浑身上下,从外到里都是冷。而在北方,即使睫毛上挂了霜,人穿着棉衣棉裤包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在冰天雪地里行走哈出来的气也是热乎乎的。北方的冷只浅浅地停在表皮上,因为人一旦静下来就进入有暖气的房间,室内的温度可以达到二十好几度。
后来我真是越来越怕冷。之前住的那套房子采光很好,可即使室内洒满阳光,冬天在室内穿的比在外面还多。在家我总是穿着厚厚的高帮棉拖鞋,厚厚的羽绒服,看电视时腿上还要盖个小被子,手捂在被子里,人瑟缩着。每次洗澡前都要做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以巨大的勇气去把电暖风机开启,等卫生间烘得不太冷了才敢进去。有一年春节前,新疆的亲戚来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回去后和我妈妈说,我在南京太可怜了,家里没有暖气,冬天太难过了。
后来决心换房,前期去看了好多壁挂式锅炉,打算买了新房就自己装个来取暖。南京这个城市不南不北,不在全国集中供暖范围之内,有暖气的房几乎没听说过。可是从市中心到郊区这样一路看下来,居然真的有集中供暖的新房卖。位置偏、生活不方便、到单位没有班车站、开发商是小公司,这些问题全部忽略,迅速决定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能集中供暖。
因为有暖气,家里总是暖融融的,南京的冬天好过了,人也舒展了起来,幸福感增强了好多。
到了供暖季,家里的地面是温的,我喜欢光着脚走在上面。往年冬天把洗衣机甩干的床单被套晾在户外,很多天都不干,收的时候还会有股怪味,现在,洗好了的床单被套就直接铺在擦干净的瓷砖地面上,要不了多久就干了。楼上的邻居说,他家小孩子的小袜子也是这么弄干的。邻居还说,平时家里就四五口人,到了冬天,会住七八口人,除了两边的老人,他姑妈也来住,大家都是图个热乎,家里热闹得很呢。
今年10月下旬,南京气温突降,连续几天都只有几度,我换上了厚被子。小区业主群里有邻居就开始叫起来,要求供暖公司提前供暖,也有人说才十月,气温还会上升的,春捂秋冻,秋天应该适当地冻一冻。两个观点交锋,吵了个不亦乐乎。因为往年供暖起始时间和周期是固定的,要到12月才開启,可这突然冷到透,好多人都受不了了。
越来越不耐寒的人真的多了,就像我。当然,后来还是没有提前开,因为不久温度确实回升了。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怕冷。在南方长大的人,他们的耐寒能力要比我们这些北方人强,还有人心疼几千块钱的取暖费,所以就拒绝开暖气。
我有时想,他们这么计较这个钱,当初又何必买在这个小区呢?当年周边的楼盘很多,别家的价格还稍微便宜些呢,买这里的房子不就冲着暖气来的吗?
在北方,暖气是冬天的标配,想都不用想的,一定要有。
我一个同事来自东北,有次谈到房子的话题,她说因为暖气费比较贵,所以东北的房子空置的很少,不会让暖气浪费在没人住的房子里。
说到东北,想起前一阶段去沈阳出差,从机场坐出租车到市区,喜欢唠嗑的司机和我一路聊,说他在铁西区有套楼房,出租了,自己住在近郊农村,晚上回家,睡在大炕上面,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想烧多热就烧多热,开车累一天了,回家睡在热炕上,可解乏了。
去沈阳故宫参观,看到皇宫里的取暖也是大炕。巨大的炕沿着房间的四面墙围成一个不封闭的四方形,炕特别宽大,上面还有小炕桌。只是西边墙的炕略窄些,那个尺寸不够一个人睡。我猜想因为寒风打西边来,墙钻风,不适合睡人吧。皇宫里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烟囱,体现着皇宫的威严,但更多的是功能上的务实。我还看到有的房间的炕是从屋外加热的,估计是为了不影响里面的人休息而设计的吧,或者是为了安全。
那次,我在沈阳故宫,听到皇太极整天坐在正屋的西屋炕上,整天望着爱妃逝去后空荡荡的厢东屋,后来因思念过度患心肌梗塞而死的爱情故事。
想象一下骑马善射的皇太极脱了靴子盘腿坐在炕上一脸悲伤的样子,顿时就有了穿越感。好像我也跨过了几百年,穿着厚厚的旗袍,把两只手拢进厚厚软软的镶着白色绒毛的袖筒里,化作隐身人,在故宫里无声地走来走去,静默地看平时威严的皇上和生着细长眼睛的爱妃的柔情故事。
沈阳的同学请我吃饭,说咱们去吃朝鲜大炕吧。朝鲜大炕?太新鲜,于是欣然前往。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春意融融,这不算什么,特别的是我们坐在热乎乎的大炕上吃烤肉,不一会儿就浑身发热,眼见的棉外套脱了,毛衣脱了,到后来同学十来岁的儿子只穿了件短袖,吃得热火朝天。同学的妻子看我吃的热,贴心地帮我叫了朝鲜冷面,大冬天吃冷面,必须在大炕上才配。
这个大炕太舒服了,我甚至让同学帮我拍了照,店里的服务员看着我一个劲地笑,一定觉得我少见多怪。其实我真的不是少见多怪啊,我打小就是睡着这样的炕长大的。这个大炕一下子就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
很小的时候,住在新疆北疆的农村。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平房里,条件简陋,不仅没有集中供暖,连土暖气也没有。每家每户都是在自己家生炉火,通过火墙传导把大炕加热。大炕,就是全家的床。
要自家取暖,就必须要有煤炭。每年入冬前,家家户户都要买一大卡车煤来。我记忆中煤是来自一个叫“雀儿沟”的煤矿,距家大概一两百公里远。煤的价格并不高,但是运费很高,一车的运费往往和煤的价格持平。往往是邻近的几家排着队来,这一家拉来一车煤,附近几个家的小伙子都去帮着卸车,下一家再去拉一车煤来,另外的几家帮着卸。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起来,住在平房里的年代,邻里之间互相帮助,非常和睦,感觉还是很温馨的。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的煤房,在自家院子里厢房的位置。煤房里面堆着大块大块的煤。要用的时候要先搬出几个大块的,拿榔头把它敲成比拳头小一些的碎块儿,然后用一个磕破了瓷面的搪瓷洗脸盆装了拿去烧火。
有的时候煤块清理得不干净,会有遗漏的小的雷管在里面,必须要小心地拣出来。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从家里的火炉旁边经过,忽然就有一个雷管窜了出来,正好飞到了我的腿上,现在腿上还有一个当时的伤疤。这是身体对冬天取暖的记忆。
烧火炕挺有讲究的,怎样烧的既不太热也不至于冷,有一些技巧。晚上睡觉前,要把炉子封起来,里面的煤炭既不充分燃烧但是也不会迅速熄灭这样的状态,家里的温度保持在不用人操心又让人比较舒服的状态。
家里的那面灰色的火墙,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听说是附近一个能工巧匠上门来打的,火墙外的每块砖都均匀平整,每条缝都一样细致光滑。那个时候小,不懂得欣赏,现在早就无处可寻了。
想到我小时候的生活场景,就会联想到当年的父母,现在的我都比他们那时的年龄要大了。六十年代,父母在三十岁的时候从江苏到新疆去生活,火坑火墙在老家都是没有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适应的。不知道他们看着能工巧手砌砖时是不是觉得很新奇,不知道他们第一次生火的时候是不是手忙脚乱,是不是一个人添加煤块,另一个人反复去摸摸炕面的温度,一起琢磨怎样控制火力才最合适。
这种火炉带的火墙和火炕,用一个冬天后,家里就会被烟尘熏黑。每到开春,家家户户都会找来石灰水,把墙壁整个粉刷一遍,于是一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那种幽暗光线下的靠火炕助眠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苟且。冬天的家里,也会有绿色的植物,往往是好多个浅浅的盘子里,养着青绿色蒜苗,在窗台上,依着漂亮多变的冰窗花,长出一排齐刷刷的茂密森林。青蒜苗可以观赏,可以吃。这是贫瘠年代的诗意和远方啊。
后来搬到县城,依然住的是平房。房子交给我们的时候,就装好了土暖气。所谓的土暖气,就是通过自家的火炉加热几个房间暖气片的温度,让家里暖和起来。
那个一进门就能看到的火炉,除了供应暖气,也可以在冬天里烧水做饭。我初高中都是走路去上学,中午要回家吃饭。中午父母往往不在家,我要自己热剩饭吃,偶尔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一个上午家里没人,火依然没有熄,我要用火钩子把炉门打开,把弱弱燃烧的煤块扒拉松,让空气进去,让火烧得旺起来,再把炉圈从里到外一圈一圈地取下来,然后把锅搭上去,等到做完了以后,再用火钩子把炉圈由外向里先大圈后小圈放上去,整理平整。如果要烧开水的话,就只取中间的一两个圈儿,把水壶坐上去就可以了。等到要离开家的时候,再把炉门封起来,这一套动作相当的熟练。
北疆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很常见,可我记忆中却没有寒冷过,大约是有暖气的缘故吧?
其实冷还是很冷的,冬天洗的衣服,妈妈往往会端到院子里,挂在铁丝绳上,没多会儿衣服就冻得硬邦邦的,等到过段时间,我们再把硬硬的冰衣服收进家里晾起来,很快就干了。后来学了物理,知道了这其中的道理,这就是“升华”了,由冰直接到气体,不会湿淋淋的。
我会把小衣服搭在暖气片上烘干。一般都是拿一块白布铺在一节一节疙里疙瘩的暖气片上,把洗干净的衣服平放上去,很快就会干的。我现在在瓷砖地面上铺晾床单,是在向当年的自己致敬吧?
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个个都是“架火”的能手。“架火”是新疆的说法,就是生火的意思。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呢,家里人多的话,小孩子未必要“架火”,但在学校必须要会。我上初中的教室里没有暖气,需要烧火炉取暖,每天同学排值日,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同学们到校前把教室里的火架好。
估计现在的孩子完全想不到架火是怎么回事了,即使是北方的孩子,大多也没有机会做这个了。
架火不算多难的事。要先准备一些柴禾在炉膛里,上面盖上敲好的煤块,留出一定的空隙,为的是让空气进来。柴禾要搭着架起来,好给底部支撑出一个空间,这大约就是“架火”这个说法的来历了。柴禾下方最好有些干燥的细枝,把报纸或硬纸卷巴卷巴点着了,伸进炉膛里引燃细枝,细枝烧旺了,柴禾才会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煤块的边缘慢慢变红,火就架好了。
架火说起来简单,但弄得不好也会搞自己一身烟火,或者不小心把头发和眉毛烧了。
有的时候,教室里的火炉效果不好,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天然的小火炉,但如果火烧不好弄熄了的话,平房教室也很冷。我记得有天值日生就没弄好,课间休息时,有几个调皮的男生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下左右晃动有节奏地挤,一边挤一边连声地喊:“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呀么挤热乎!”他们的大棉衣蹭在后面的黑板上,我花了好多心思写写画画的黑板报被他们抹掉了最下方的一长溜,好生心疼了一阵子。
北方的暖气,和干燥混合在一起,人身上的静电就特别大。在乌鲁木齐生活的那些年,我下班回家拿钥匙开门的时候,经常会被电到,火花“刺啦啦”地闪,还发出响声,人就会感到小麻小疼。后来接受了教训,每一次开门都很谨慎,不敢用手直接去碰那些金属或塑料的东西,戴着手套去拉门把手,或是用胳膊肘去触碰灯的开关。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欧洲出产的那些大牌的壁挂锅炉,工业化的产品,先进是先进,但却没有记忆中的烟火气息。
想到烟火气息这几个字,就想到了儿时那些温热的烟和火。
在那些静静落雪的夜晚,村庄里白茫茫一片,全家人围坐在红彤彤的火炉边,那种色调,想起來就很温暖。有的夜晚,妈妈会把麻袋里的玉米棒子倒出来,我们一起搓玉米粒儿,一边搓一边说说笑笑。有的时候,妈妈会炒一大簸箕葵花籽,大家嗑着瓜子儿,愿意说话就说话,不想说话就一颗接一颗地嗑。瓜子壳散在地上,我把它们扫起来倒进火炉里,炉子里就呼啦啦地放出亮亮的光来,发出好听的炸裂声。还有的晚上,大家守着那个红灯牌收音机,听说说唱唱的节目。还有的时候,爸爸会和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猪八戒的,我特别喜欢听,因为弟弟属猪,我就叫他“猪八戒”了。那些炉火的红光照映着我们脸颊的时刻,也是有味道的,隔不了几天,妈妈就会从炉膛里刨出几个烤土豆或者烤红薯烤玉米给我们吃,房间里弥漫着又香又甜的热乎乎的味道。后来我也学会了,怎么能烤得又有焦香又不糊。吹掉土豆外皮的炭灰,小心地剥掉皮,沙沙绵绵的土豆要多好吃就有多好吃。如今,我时不时也会烤土豆,用烤箱切片烤出来,虽也好吃,但总不如那时的滋味好。
以前,妈妈总是不吃烤红薯,让她吃,她就说在老家吃的太多不爱吃了。我一直奇怪,烤红薯松软香甜,可谓人间美味,她怎么会不喜欢呢?
成年后我才知道,其实妈妈一直喜欢烤红薯的,她那时是留给我们吃的,看着几个孩子吃得欢天喜地,她可开心了。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视,连看一场电影都难得,北疆漫长的冬天里,我们却一点也不寂寞无聊,也没有觉得苦寒。
我怀念冰天雪地的北疆,那个小小的没有围墙的热乎乎的小院,那里有幸福的一家人,有我还年轻的父母,有我稚气未脱的兄弟姐妹,还有那个快乐满足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