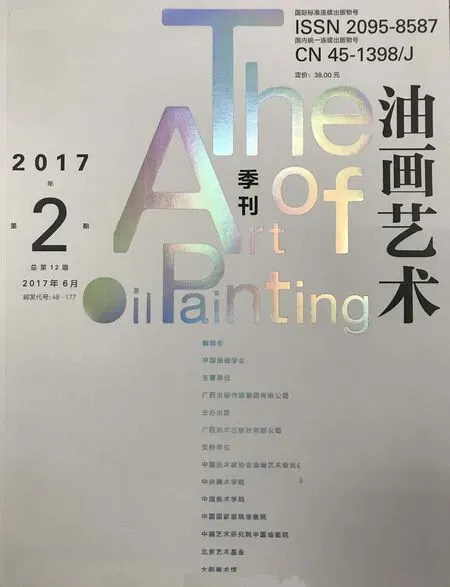西南油画与当代油画的源流与现状
吴永强
【提要】新潮美术兴起,西南油画先后经历了云南“新具象”与生命之流、川渝“新生代”与“新伤痕”、都市经验与全球化、“新卡通一代”与图像转换等阶段,实现了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型。如今,在市场支配艺术和艺术家集群化的语境下,西南油画进入了一个多元而迷茫的时代。
1979一1984年,以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画家群为主体的四川画派 ,以“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写下了西南油画史上的经典一页。从知青题材的“伤痕”作品,到罗中立的《父亲》,四川画派又陆续摆下了乡土绘画的盛宴,遂令西南内外,跟风者众。从1979年的“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全国美展”、1981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到1982年和1984年的两次四川美院师生进京作品展,西南油画不断以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和“小、苦、旧”的题材形象收获赞誉。然而变化总在盛景之后,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之后,随着新潮美术的兴起,西南油画随四川画派一道走向沉寂。不过正是在沉寂之中,新的种子开始发芽。
一、云南“新具象”与生命之流
西南油画的新因素最早出现于云南“新具象”群体。1985年,云南画家张晓刚、毛旭辉、潘德海联合上海画家侯文怡、张隆(昆明籍)、徐侃先后在上海、南京两地举办展览,取名为“新具象”。随后,他们吸收西南三省成员,发起组织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形成一场“新具象”运动。按照毛旭辉的解释,所谓“新具象”,就是“心灵的具象,灵魂的具象” ,他们借此表达对自然主义、矫饰主义的反对和对生命直觉的推崇。“新具象”成员也曾追随过乡土题材,如张晓刚的《天上的云》《暴雨将至》,叶永青的《牧羊村的撒尼姐妹》,毛旭辉的《圭山组画》等,均取材于西南边远山村,不过这些作品并未屈从于乡土自然主义,而是借鉴了早期现代派的语言风格,因为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乡土题材本身,而在于传达内心情绪和追求形式上的现代感。在这方面,周春芽也可算一个例子,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藏族新一代》《剪羊毛》,同样用乡土题材承载了一种表现性意趣和有现代感的形式构成。他们与1980年出现的重庆“野草画会”异曲同工,在西南油画界埋下了现代性的种子。
“新具象”的出现,使这颗种子始得发芽。“新具象”成员的作品不仅告别了乡土写实模式,也与当时北方的理性绘画相对应,成为“85美术新潮”生命之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稍后出现的昆明“南蛮子”群体、贵阳“原始风”、成都“红黄蓝画会”以及四川美院新一代学生画家的创作中,我们都能观察到这种流向,那就是借鉴现代形式来表达直觉感悟并强调原始生命体验。当时,高名潞曾撰文讨论四川美院81级毕业生的油画作品,通过将其与该校77级作品和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同年级作品比较,文章指出,再现距离和理性,重视形式风格和表现 ,是新一代四川美院油画创作的特点。其后,牟群在一篇评价1986年四川美院第二届“学生自选作品展”的文章中,将这一批学生称为“第二代四川群体”,认为他们“以形式崇拜和自由追求为己任”。 两篇文章都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年轻一代的西南油画家正在与过去作别。其实,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上一代画家身上。例如,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周春芽等,也从过去借鉴印象派、后印象派转向了对表现主义、原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吸收。
虽然提倡主观表现,可是在“85美术新潮”时期,许多西南油画家仍然保持了乡土温情,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带有地域色彩。“南蛮子”宣称“以西南的文化的蛮风来复苏沉睡的边疆冷土” ,贵州画家以现代派形式来释放山地文化的野性,四川美院青年画家如庞茂琨、朱小禾、张杰、陈卫闽、翁凯旋、鲁邦林、任小林、李强、阎彦、罗发辉、杨述等,也常在笔端流露出对乡土的缠绵。这或许可证明西南油画仍未斩断乡土绘画的文脉。不过,恰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它们与矫饰主义乡土绘画的区别,后者是跟风和模仿,前者来自心灵的实诚。在他们的画面中,再也见不到矫饰化的乡土自然主义和“小、苦、旧”形象模式,而是形式多样,充满个性,富有现代感。即使采取写实手法,也有作者独特的现代性追求。
但是,在提倡观念更新的历史氛围中,乡土意识却受到重新审视。德国艺术史学家贝尔廷曾从当代艺术与全球文化身份的角度区分了“世界艺术”和“全球艺术”的概念,照此区分,“世界艺术”属于地域性艺术,“全球艺术”才是表征多元文化平等的当代艺术 。1986年11月,“云南油画新作展”开展期间举办了云南油画讨论会,会上,毛旭辉提出要“更新绘画的区域性概念” ,主张把区域性放到大时代的复杂体系中,自然而非硬性地呈现区域性特征。联想到贝尔廷的观点,我们觉得,他似乎已经本能地趋近了“全球艺术”观念。
二、川渝“新生代”与“新伤痕”
川渝“新生代”油画以对都市经验的传达,与生命流绘画拉开了距离。但同时,又以对艺术家个体生存经验的专注而与北方“新生代”油画发生了呼应,因此与后者一道,共同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油画由集体主义向个体经验转化的趋势。
北方“新生代”油画以方力钧、岳敏君等的“泼皮艺术”(或称“玩世现实主义”)为内容,它将起源于历史转折的宏大叙事隐藏于个体生存图像,而川渝“新生代”油画只是对纯个体经验的传达。后者以心理叙事的方式展开,具有个人化、私密化和自恋性特征,并着意于暴露“青春残酷”“肉身焦虑”和对伤害的迷恋,而不论它们采取卡通、艳俗、表现还是模糊化的图像形式。正是在这个理由上,王林将其称为“新伤痕”。其焦虑感,来源于面对都市异化的无所适从;其对伤害的迷恋,表征了个人在物化现实中的沉沦与挣扎。
这样,川渝“新生代”油画就不仅在共时性层面上与北方“新生代”油画拉开了距离,也在历时性层面上与“85美术新潮”的集体主义、英雄情结和宏大叙事渐行渐远。后者在“北方艺术群体”所追求的崇高和“理性”、浙江“85新空间”所表现的冷漠感中得到了具体呈现。在川渝“新生代”油画中,我们再也见不到理性绘画所追求的“静力学效果”和“静呆美”,而只见到异质的图像、陌生的情境,伤感的气质和莫名的哀伤,从这个质调上看,它倒似乎显得与本土生命流绘画存在血缘关系。
三、都市经验与全球化
川渝“新生代”艺术足以成为一个标志,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西南油画的关注点从乡土题材转向了城市题材。尽管仍然有以罗中立、陈卫闽、陈安健、陈树中等为代表的西南画家以乡土题材作画,但他们也不再遵循过去乡土绘画的逻辑,而是基于对都市生存和现代化的反思,致力于建构一种“新乡土”风格。而那些直接针对城市经验和都市人格进行创作的画家,更是以其作品为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留下了视觉证据。必须提到,西南画家所表现的城市经验,并不仅仅以“新伤痕”形式出现,而是采取了多元的角度,形成了多样的图式,在四川美院画家中,钟飙、龙全、俸正杰、何森、张小涛、翁凯旋、王大军、杨劲松、刘芯涛等人的作品如此,在贵阳画家中,董重、蒲菱、李革等人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在1997年由王林策划,辗转重庆、成都、昆明三地的“都市人格”系列展,以及同年由管郁达在贵阳策划的“都市人格1997——重返乌托邦”展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这种转型同样发生在成名更早的艺术家中间。例如,20世纪90年代,张晓刚创作了《手记》系列、《天安门》系列、《大家庭》系列,叶永青创作了《大招贴》系列,毛旭辉创作了《家长》系列、《剪刀》系列,周春芽创作了《太湖石》、《绿狗》系列,这些作品不但以各自的方式反照了作者的都市经验,而且无不以鲜明的本土化和个体化特征,宣告了对现代主义的放弃。但就其本土性文化特质而言,它们却不是依靠执着于地域性文化经验取得的,而是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围绕中国现实经验或历史文化,依靠个体性观照而取得的。即便是围绕大巴山题材进行创作的罗中立,也不再以俯瞰的姿态发表对农民的同情,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呈现农村生活状态,创造了关于中国农村的人文图像。在文化上,它们反映的是中国经验而不是地域性经验。这种对本土性立场的关注,凸显出中国文化的身份问题,有利于使当代艺术成为一种手段,以帮助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与世界的平等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地区,同样生活着一些候鸟型艺术家,由于经常穿梭于国内外,对他们而言,文化身份的问题更显得迫切而紧要。在这些画家中,重庆的何工可谓一个典型。何工在创作中将本土立场融于对个体立场的捍卫,表达了对后殖民文化和一切固有偏见的批判。他以与新表现主义精神共鸣的作品,披露了其在国际上行走的历程,为西南油画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近距离“接轨”,留下了一份生动的档案。
四、“新卡通一代”与图像转换
21世纪以来,与市场化同步,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陷入消费文化语境,艺术家需要面对流行文化、网络传媒、动漫游戏等信息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景观。在这种情况下,“新卡通一代”应运而生。我们知道,“卡通一代”是一种新生代艺术样式,尽管发端于广州,却繁荣于北京和川渝,所以早就与西南油画结下了缘分。忻海洲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陆续创作的《城市卡通人》系列,一度成为西南新生代油画的身份图式。而“新卡通一代”的代表人物,也以熊宇、高瑀、陈可、沈娜、熊莉钧、李继开、杨纳等占据多数。忻海洲曾写道:“人们在文明的游戏中被雕塑得卡通化了,我发现,我们都是城市卡通人。” 到了21世纪,当游戏、动漫、网络、虚拟、“新新人类”不再仅仅是一些词语,而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日常经验中的现实时,“城市卡通人”以新的面貌还魂,成为西南油画进入21世纪的一道绚丽景观。
“新卡通一代”包含了“70后”和“80”后两代人,而以“80后”为主。如果说作为“60后”新生代的“卡通一代”还在努力用卡通图像来隐喻其个人对时代遭遇的总体感知,试图为自己成年后才陆续赶上的消费文化和网络文化发明易于识别的符号,那么,“新卡通一代”则更倾向于用游戏、动漫图像来指向自我,指向他们在消费社会和网络文化中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相比于上几代人而言,这种生活波澜不惊,就好像隔绝了历史,处于时间的空白地带。不过,作为艺术从业者,艺术界的走向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片空白,这些年轻的西南艺术家觉察到,背衬都市经验的“艳俗艺术”“卡通一代”“青春残酷”余绪未散,而新生代自传体仍然是一种能够生效的艺术生存途径;而在一个碎片化的生活图景中,也的确只有回到自我,心灵才能得到安放。所以,西南“新卡通一代”表面上附着于网络时代的卡通艺术、果冻艺术等潮流样式立身,内中却萦绕着早前“新生代”式的自恋和多愁善感,这让他们围绕游戏、动漫形象和虚拟世界,为21世纪的西南油画注入了新的具体性。
高瑀和陈可这两位不同性别的画家,也许能够作为恰当的例子,帮助我们认识川渝“新卡通一代”油画创作的特色。高瑀吸收日本动漫和村上隆、奈良美智等艺术家的影响,把在中国有“国宝”之称的大熊猫打造成了一个符号化、内含傲慢、充满颠覆性的卡通形象GG。有评论者猜想,GG的状态和情感出自高瑀本人,带有画家自传意味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卡通创作成了艺术家协调自我冲突、舒缓情感的一种手段。陈可把得自奈良美智的启示,连同日韩卡通艺术的整体影响,悄悄置换为一种颇具女性细腻感的情境性叙事。其形象涤除了奈良美智笔下小女孩的那股邪气,其画面带着淡淡的忧伤,私密、敏感,幽远,充满孩子气,但又激起了人们窥视的欲望。如果我们可以把新卡通一代叫作“后新生代”,那么这两个例子就寓言了“后新生代”西南画家的一种创作取向,即既追求图像转换,又试图顾影自怜,玩味私情。这种取向有川渝“新生代”的遗传因子,又在传递过程中因与快速遭遇的消费社会和网络时代发生碰撞,随之散播开来,成为一种特质,不断在“新卡通”、“小清新”艺术以及“手感秀”的西南“新新人类”绘画中渗漏出来。
五、多元而迷茫的今天
如同国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除了集中于院校,跨越体制内外、久留或暂住北京、部落化生存和接受“文化产业”的介入,是西南地区画家的基本生态。而部落化生存,是一个常在的现象,这说明,就大多数人而言,如今艺术是一个职业而不是爱好。成都的“蓝顶”“浓园”“高地”,贵阳的“城市零件”,云南的“丽江工作室”以及一度火爆的昆明的“上河会馆”“创库”等,还有散布在这些城市和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村落或艺术聚集区,集中了大量创作油画的艺术家。而且,伴着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低迷,客京滞留798、宋庄等地的西南画家有逐渐回流的趋势,目的地一般以成都为多,因此成都画家的数量在西南三省城市中居于首位,也相对更为集中。
面对一种艺术进行式,我们实在无法一一点出画家的名字,也无法对今日西南地区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油画创作状态做出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例如,如果我们说贵州是野性的,那么一个温和的画家的作品就将给出反例;如果我们说云南是简约的,那么一个云南画家的复杂的构图就将证明我们的说法;如果我们说成都是重手感的,那么仅靠挪用图像就能得到一件作品的画家就将令我们住嘴。在这个艺术都难以被定义的时代,还指望依靠一个笼统的叙事来指认一地艺术创作的真相,已经变得十分可疑,所以我们宁愿相信,艺术家创作的真正差异性只存在于个体之间。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一种现象学起点上,对西南油画的今日状况形容它是“多元化”的,虽然这个词在许多时候几乎等于无话可说。
不过,一些碎片化的观感依然是可以说出来的。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川渝两地来说,有的画家注重文化观念的传达,有的画家注重个人情感的表现,有的画家关注图像转向,有的画家注重传统体验,有的画家趋于外向的介入,有的画家希望保持内向的纯粹……但在这多声部的合唱中,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一个旋律,似乎就是“溪山清远”,犹记得这是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主题词之一。在创作上表现为用油画、水墨或跨媒介手段来处理风景、静物题材,或解构和转换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鸟图像。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文化上的或观念上的说辞来替这些做法辩护,但往往辩护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文字之中。而且最近几年,国内画界兴起的一股旅行作画风潮也深深地影响了西南画坛。油画家们近到郊外,远到异国他乡,在原野间竖起画架挥运画笔。这当然能够促进油画这门艺术再次面对自然。我们或可说,在这种情况下,油画便得以重返其活力始发的现场,并向图像统治绘画的权势发出挑战。不过,这股风潮也慢慢滋生出以写生同化创作的现象,好像画家只要带上眼睛,具备一副手艺,便可接二连三地制造出作品,再也不必受思想、观念、情感和想象力的折磨了。与此同时,写生画展被大量举办,写生——的确只是写生——之作填满了大小展览,它们编织出一道景观,让人误以为,除了写生,油画家已经无事可做了。其结果是,油画更深地放纵了对物性的沉湎和对社会现实的疏离,而与此同时,明明只是写生,画面上只要淌着颜料,留下屋漏痕,就会被指认成“当代艺术”……对比之下,我们就未免怀念起何工一类的艺术家了,因为我们在他通常是结合跨媒介材料的油画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流放者的气质,一种即使被边缘化也不放弃“异争”的姿态,这也许才是西南当代油画值得追求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