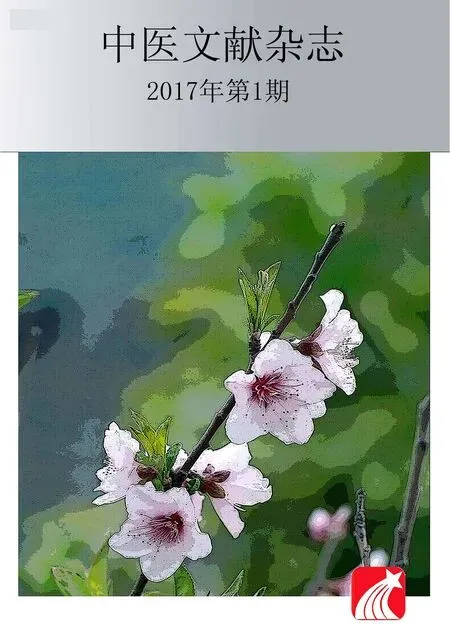老梅春深馥郁香,留得清气在人间
——海内著名经方家孙砚孚先生小传
无锡市惠山区康复医院(江苏,214181) 沈桂祥
·医林人物·
老梅春深馥郁香,留得清气在人间
——海内著名经方家孙砚孚先生小传
无锡市惠山区康复医院(江苏,214181) 沈桂祥
经方医家 孙砚孚 小传
先业师孙砚孚先生(见图1),江苏无锡人,1913年3月1日出生,卒于2003年6月29日,享年90岁。副主任中医师,海内著名经方家,1932年7月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亲炙于当代名医陆渊雷、章次公、曹颖甫诸先生,其融汇中西的学术思想,盖得诸师承。

图1
孙砚孚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东北边远小镇港下,自幼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培养。少小就读于无锡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造就了他的爱国情结,立志报国。少长毕业,只身拜师问业于江阴名医许卓云、安徽秋浦中医传习所教师王绶臣两位先生,学习岐黄之术,立下服务乡梓、济世活人之宏愿。其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于1932年毕业,返乡行医,无论贫苦贵贱,昼夜寒暑,诊金多少,有求必应,赢得了家乡父老的信任和尊敬。
港下小镇地处锡城东北一隅,与常熟、江阴边远村镇相邻,其时交通闭塞、贫困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和缺医少药的状况,时刻冲激着孙砚孚的心灵,矢志为改变家乡面貌,造福人民作不懈努力。
砚孚先生早在考入上海国医学院之前,便想到家乡要发展,要进步,首先要办学校。经过一番筹划,1930年2月,与同乡有识之士孙某一起,个人出资,借孙家坟堂为校舍,办起了单班复式初级小学,取名“私立港下初级小学”。1932年7月,先生上海国医学院毕业返乡,适逢该小学因校舍简陋被当局勒令停办的困境,毅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力排封建迷信势力,以关帝庙为校舍,将泥菩萨抛入河中,使小学得以重建,成为现今的“港下实验小学”前身,开一方“废庙兴学”先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砚孚先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又积极筹建“无锡怀东中学初级补习学校”,被推举为校董,参与学校管理,兼职任教。该校即现今“港下中学”前身。
先生一生热衷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继出资办学建校义举不久,又出资兴办施诊给药局、民众书报社、蚕桑共育室、丧葬殡礼室,开通邮柜、轮船航班等,造福乡里。
抗战时期,国家存亡之际,先生拒绝担任日伪伪职;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苦难,先生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确保地下党新四军领导人管文蔚同志的人身安全,掩护在家一周。先生的风骨气节、民族大义和爱憎分明的高贵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一生处事低调,常教育晚辈要“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常以吴玉章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以自勉。
2013年,在砚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当地百姓在互联网上举行了纪念活动,“老梅春深馥郁香,留得清气在人间”。
先生崇尚仲景之学,学验俱富,精于辨证,擅用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治疗支气管炎;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泻心汤治疗胃、肠炎;理中汤治疗虚寒腹泻;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茵陈五苓散治疗急慢性肝炎;当归四逆汤治疗冻疮、血栓性脉管炎;白头翁汤、葛根芩连汤治疗痢疾;大柴胡汤治疗肝胆胰腺疾病;大承气汤、大陷胸汤治疗肠梗阻,并主张“要主动进攻连续作战”,曾有一昼夜计服生大黄63g、芒硝36g之多而使重症肠梗阻得以解除,免于手术的验案(见《江苏中医》1988年第9期),如此等等,疗效卓著,可谓擅用经方者矣。但亦不弃时方,多见于治疗妇科诸疾,兹不赘述。先生注重辨证,批评医者治病套用成法的陋习,贻误病情,在治疗“偏枯”时,告诫“半身不遂不要概投补阳还五汤”(见《江苏中医》1992年第9期)。1958年,他在《上海中医杂志》第9期撰文《掌握辨证治疗的原则,消除伤寒温病的纷争》,力主消除“寒温纷争”,主张“有是证,用是药,详于辨证,毋斤斤于病名,浑称‘伤寒方不可以治温病’、‘温病方不可以治伤寒’,那是不够妥当的!”先生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极富革新思想,重视总结经验和参加学术争鸣,其议论每发前人所未发,多真知灼见。当代著名中医学家沈仲圭先生读砚孚先生的《诊余杂集》中“读伤寒论札记三(调胃承气的力量胜于小承气)”后,在1979年2月15日给砚孚先生的信中说:“你学有根底,见解高超,对调胃承气汤与小承气汤的作用,实际是相反,此种理论,非一般中医同志所能道出”;在1985年1月14日给砚孚先生的信中说:“今在《中医杂志》1984年12期‘百家园’见有你所撰评议陆九芝‘阳明为温热之薮’,写得极好!可见你学识经验,不同凡俗,且持论平允,文笔畅达,如此佳作,不易多观!文末附录章次公医案,尤为实践证明。”本着叶天士《温热经纬·外感温热篇》“温邪则热变最速”,在急性热病的治疗中,孙砚孚赞成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和笔者恩师朱良春国医大师的“堵截疗法”、“先发制病”思想。他在《乙脑治疗赘言》中说:“要药先于病,早为防堵,依照‘上工治未病’之旨,及早用清热解毒重剂。”其于药物研究也颇多心得,曾有《葶苈用法小议》、《苍术胜白术》、《用药一得(麻黄、枣仁、黄药子、牛蒡子)》发表于《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先生重视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学验俱富,由此可见一斑。先生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撰文《著书立说必须与实践结合》、《医学与夸饰》(《中医杂志》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3期)以抨击时弊。其学术经验文章多见于《中医杂志》及省市级期刊。“文革”期间,蒙受批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大地重光,先生得以平反昭雪,乃奋笔撰写医学文章,连同以前所写,结集刊印《诊余杂集》及《诊余杂集拾遗》专著存世。先生酷爱文史,国学造诣颇深,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仅《资治通鉴》便通读了3遍,并要求我诊余通读,尝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所得常用于临床,恒多佳效。
先生曾任无锡县中医学徒班、无锡县卫生学校中医班、西医学习中医班教师。生前供职于无锡县人民医院、张泾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从医凡70载。先生一生为人谦虚谨慎,他在《八十书怀》诗中这样写道:
八十春秋瞬息过,
毫无建树愧蹉跎。
少壮不学根底浅,
老大徒悲学术疏。
诊断未能洞症结,
处方自难起沉疴。
人民待我多丰厚,
我与人民苦无多。
砚孚先生德高望重,为医做人,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自1959年始,我与砚孚先生相从凡40余年,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作《传》以志纪念。
K825
A
1006-4737(2017)01-0049-02
2016-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