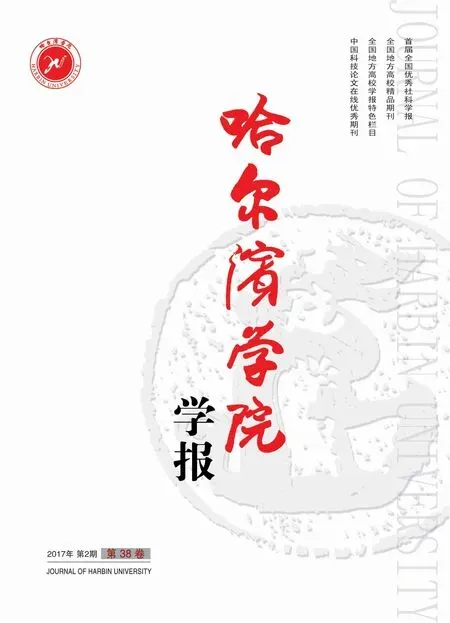传统民歌在现代上海生存现状探析
——以浦东山歌为例
毕安琪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传统民歌在现代上海生存现状探析
——以浦东山歌为例
毕安琪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在上海这座现代开放的国际都市里蕴藏着丰富的传统音乐种类,浦东山歌就位列其中,被称作东乡调、东乡民歌。浦东山歌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上海的传唱历史悠久,形式多样。文章旨在解读传统民歌在现代开放的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并对浦东山歌非遗文化保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吴越文化;吴歌;浦东山歌;非遗
上海,一座位于长江、黄浦江入海汇合处的国际大都市。古老斑驳的石库门,小洋楼、咖啡吧和老唱片里都流淌着香艳的上海情。19世纪后上海作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深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逐渐成为国际化商业金融中心。这座看似飘扬着西方音乐,散发小资情调的城市依然孕育传承了诸多传统音乐种类,如昔日上海港上空飘扬的苍劲有力的码头号子、巷尾里弄传出的细腻婉转的民歌小调,茶馆剧场上演着的优雅评弹。这些传统音乐保存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在文化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成为众多文艺工作者关注的事项。
一、吴越文化背景下的吴歌
长江流域的文化体系主要包括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上海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吴越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发展起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不断的考古发掘向人们证实了那一时期发达的制陶业和水稻种植业,彰显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春秋战国时,吴、越立国,称霸一时,几千年来,吴越不分家,彼此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从此形成“本地为体,外来为用”的吴越文化模式。吴地最早的民歌形式,相传也是周太王长子泰伯来到此地建立吴国后从北方带来的,又逐渐融合了当地土著民歌的元素。据记载,泰伯曾到无锡梅里“以歌代教”,向当地百姓传授歌谣,至今民间还有“梅里花、梅里果,泰伯教民唱山歌”的说法。
如今所讲“吴歌”,即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生的民歌总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吴歌传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晋书·乐志》云:“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这时在吴地大城市中流传的歌曲多是由吴地农村歌谣加工改造而来的。明代,雅俗文化齐头并进,吴歌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时期,冯梦龙在其编纂的《山歌》中共收录吴歌300多首,他认为凡是为“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的一切“民间性情之响”,都可列入山歌的范围。[1]另醉月子在《吴歌》中也收录65首。文人采集到的曲目可能只是民间流传的吴歌中的一小部分,但却足以显现出吴歌的鲜明特色以及吴歌的传播之广、数量之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内容上来看,吴歌既包括反映劳动生活的劳动歌、歌颂男女爱情的爱情歌,也包含时政歌、仪式歌以及儿歌等。从体裁上看,吴歌可分为一人独唱的四句短山歌、内容庞杂的长山歌和数人合唱的大山歌,另外还有此地流传的号子、小调都纳入其范畴之内。除号子、大山歌外,吴歌的旋律多温婉细腻,抒情缠绵,这与吴地地处江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较繁荣有直接的关联。在吴越文化区内孕育出的浦东山歌与吴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浦东山歌的内容题材、结构形式、风格特点都带有鲜明的吴歌印记,下文笔者将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浦东山歌的源流与特征
上海民歌三大体系,即西乡民歌、东乡民歌与海岛民歌,浦东位于上海市东部,因地处黄埔江东而得名,本文所讲浦东山歌即东乡民歌。浦东山歌虽被称之为山歌,但经过调查发现,当地人是将其作为所有流传在上海浦东地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儿歌的统称。它们可能最初是为劳动所唱,但现在大多唱于日常休息娱乐的场合,大部分民歌都具有小调的特点。对浦东山歌颇为了解的奚保国先生说:“山歌”就是我们这里乡间民众对民间歌谣的俗称,自古有之。浦东山歌的传唱范围以张江镇为圆心,呈放射状遍布全区。“据史志记载,唐朝开元元年,浙江‘盐官’(海宁)修筑了约长150里终至吴淞江的‘捍海塘’。如今航头至龙王庙(花木镇)这一段沪南公路就是筑在这条捍海塘上。”[2]可见,唐代时浦东已局部成陆,有了能让人们繁衍生息的土地,就有人群聚集在此从事农耕活动,于是村落林立。唱山歌是农耕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情趣,所以当地一些对其有研究的人都认为浦东山歌大约产生于唐代。
有关浦东山歌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1935年黄炎培先生主编的《川沙县志》,1958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将川沙、南汇、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崇明等七县划归上海市。1993年,浦东新区管委会成立,川沙县的建制撤销,成为了浦东新区。该志书收集了浦东民间歌谣约90首。黄炎培先生在山歌的史志记载上开创了历史先河,记录难能可贵。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逐步开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民歌陆续在音乐刊物上刊登。1962年,由廖一鸣收集整理的“问答山歌”在《上海歌声》上发表,这也许就是第一首有曲谱的浦东山歌。1964年,南汇县沈庄文化站站长陈应时收集整理了浦东山歌《长工苦》的曲谱,也发表在了《上海歌声》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浦东地区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浦东山歌收集整理工作,此后留下了较多的浦东山歌文字资料。
1.浦东山歌分类
浦东山歌是一个统称,包含在浦东地区流传的所有民歌种类,所以,它的分类可按歌词内容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劳作类、生活类、爱情类、习俗类、传授知识类以及儿歌。劳动类,如《踏车山歌》《打夯歌》《莳秧山歌》等,爱情类,如《郎唱山歌像铜铃》《姐在园里采石榴》,生活类,如《长工苦》《问答山歌》《对花调》等,传授知识类,如《十二月花名》《九行十八镇》等。
2.歌词内容
浦东山歌的歌词多以七言体为主,如《一把芝麻撒上天》,“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民歌万万千,南京唱到北京去,转来还唱两三年。”另外还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的混合形式。歌词出现这种混合的形式,有的是因为歌调结构需要,有的也可能是歌者即兴发挥的歌唱结果,并无特定规律。山歌歌词结构多为四句体、六句体和八句体,因此也被称作四句头山歌、六句头山歌和八句头山歌。浦东山歌中也有很多时序体民歌,尤以“十二月体”和“五更体”为主。如《长工苦》,歌词从一月唱到十二月,所以又称《十二月长工》,主要讲述在旧农耕时代,穷人家为了生计,到富人家里做长工,他们在既吝啬又刁钻的富人家里受苦的遭遇。
3.曲调结构
浦东山歌的曲调很多由吴歌发展而来,随着口口相传多有一些改变。浦东山歌多为五声调式,基本上以四句头山歌的曲调为主,八句、十二句、十六句的山歌基本都是在四句头山歌的曲调上反复以及扩充,如《踏车山歌》。浦东山歌也包含许多小调,如对花调、紫竹调、踏车调、逢熟吃熟调等。当地人说这些小调有的也是从四句头山歌、六句头山歌演变过来的。因浦东在上海之东,进而人们把这些小调统称为“东乡调”。另外,浦东山歌里传唱的一些小调是外来人口定居在此后从各自的家乡带来的,例如从宁波传来的“马灯调”,无锡人带来了“无锡景”,从苏州传来了“花名调”“孟姜女调”。其中一些外来民歌在浦东流传了数百年,被当地人填上了上海吴语歌词,用浦东话唱起来更贴近浦东山歌的特色。
4.歌唱形式与歌唱场景
多数人认为“山”指代具体的山脉,山歌即在山间演唱的民歌,但上海地区并无高山,当地人认为“山”具有神圣、崇高、尊重的含义,于是山歌在此传承就有了新的含义和解释。浦东山歌的歌唱形式较为多样,有独唱、对唱以及集体齐唱。对唱又分男女对唱、两男或两女对唱。浦东山歌中的劳作类民歌并非是边劳动边演唱的歌曲,其实大部分劳作类山歌还是在劳作之后的休闲时间里农民围坐一起歌唱,解除疲劳,消遣业余生活,如浦东人民经常演唱的《踏车山歌》与《莳秧山歌》。即使偶尔在劳作场景下演唱,也只是调节情趣,舒缓疲惫的心情。习俗类浦东山歌多在特定的仪式场景下演唱,在家中有白事时演唱哭丧歌,上梁歌即在农民盖房上梁的场景中使用等。生活类山歌多数也是人们在农闲时或傍晚后为了娱乐休闲进行歌唱。
三、浦东山歌现存状况调查——传承人口述
2014年,笔者在实地采风中接触到环东村浦东山歌队和这支队伍的组织者奚保国老人。奚保国曾用名苞谷,生于1941年,1962年起连续两年代表川沙县参加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群众文艺交流演出”,演出中领唱浦东山歌《答歌》《长短山歌》《闹元宵》。受母亲张彩华的影响,他从小爱唱山歌,与当地许多唱山歌的民歌手都进行过学习和交流。奚保国对“浦东山歌”有一定的专门研究,并编写了《浦东山歌》教唱教材。通过面对面的采访,笔者又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传统民歌的生存境遇。
环东村浦东山歌队是浦东山歌流传地中心张江镇中最具代表性的歌队。有关环东村歌队的基本情况,奚保国这样讲述到:“我们唱了快十年,从2007年组建开始算起。上海地区,尤其是浦东对社区文化比较重视,所以每个镇居委会都有文艺团体。2007年镇里组织合唱班,文化中心邀请我来进行辅导,那个时候招进来的学员都是纯朴的农民。合唱是要求有唱法的,但她们都是大白嗓,所以跟不上学习的要求。这时我想起年轻时候唱的山歌,她们一定是可以学唱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对浦东山歌很感兴趣,学员们也很赞同。因为都是祖辈留下的歌,所以她们对父母曾经唱过的这些山歌也有一定的印象。”
就这样,环东村浦东山歌队组建了起来,奚保国带领着这个队伍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次演出和比赛,也为传播浦东山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是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接着上升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自从她们开始学唱浦东山歌,镇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上海市的很多媒体也争相前来采访,并给她们拍摄了专门的电视片。我们环东村浦东山歌队是上海优秀学习型团队,以前组织合唱班的时候人数不多,二三十个,改成唱山歌后,镇里的人都积极参与,最多时人数达到六十人,这些来学民歌的人对以前的传统多有怀念之情。山歌队的队员都十分聪明,可能也是因为很多曲调在童年都听到过。歌队的代表曲目有《十二月花名》《一把芝麻撒上天》《逢熟吃熟真开心》《郎唱山歌像铜铃》《九行十八镇》《胸膛勿挺背要驼》等。浦东山歌作为申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时,申报片中的歌曲也都是由这支山歌队演唱的。所有队员都出自环东村,所以我们直接取名叫‘环东村浦东山歌队’。”
每次歌队演出的表演形式都是由奚保国先生根据回忆他童年时看见村里人唱山歌的场景而编排,奚保国说:“浦东张江镇称得上是山歌之乡,基本每个村庄的人都会唱山歌。这种唱歌的场景在五十年代前还是存在的,但现在歌队的队员也都没有见过了。这些歌是在过去农闲的时候、晚上乘凉的时候、冬天晒太阳边缝衣服边唱的,展现了镇里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有喜事,做寿庆,随口演唱,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方式,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普及程度很高的。”
另外,他对“山歌”概念的理解和分类也给予了一定的看法:“对于‘山歌’一词,我的理解它就是乡间民众对民间歌谣的俗称。最早在冯梦龙的著作里出现了‘山歌’一词,这些歌曲的采集范围都是吴语地区。冯梦龙将我们这个地方唱的歌统称为山歌。目前大家比较爱唱的山歌有《十二月花名》《逢熟吃熟真开心》《九行十八镇》。《九行十八镇》是讲述九个行业,十八个村镇的特色,在其他吴语地区也有流传。民俗学家顾继刚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响应了刘半农提出的歌谣运动,他也曾经采集过《九行十八镇》,但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浦东有自己的特产特色,所以这里流传的《九行十八镇》歌词将很多浦东的特产加入进去。我们在田里劳动时也唱插秧山歌,人称《莳秧山歌》,还有踏车山歌、打夯歌,这都属于劳作类的。劳作类山歌既可以劳动的时候唱,也可以休息的时候唱。另外还有习俗类,如哭嫁歌、哭丧歌、上梁歌,都是在仪式上唱,平时不唱。现在还是有老歌手会唱的,有这些仪式的时候就请人来唱,尤其在浦东的南部地区有一些会唱仪式的民歌手。此外就是生活类的,《十二月花名》《逢熟吃熟》,这些民歌反映的是特别典型的农村生活,歌词较长,多用十二月体。浦东地区还有更长的歌如《阿姨接姐夫》,大约有上百句歌词,内容讲述了姐姐死去,小姨子接姐夫的悲剧。浦东山歌都是口口相传即兴演唱所以离得远的村镇同一首曲调也会略有不同。”
环东村浦东山歌队现有19人,歌队队员生活的村落最早形成于唐代。村中原都是盐民,后来晒盐的人搬往更靠海的地方,外来人住进村子,拔草变耕地,在此耕种繁衍生息。宋代时,这里是最大的盐场,可惜流传至今的盐民山歌目前只在南汇地区还存在着。近些年,奚保国先生把他童年记忆中的山歌都已陆续记谱整理成册,他认为记录要尊重过去,所以大部分现在所教唱的山歌和传统山歌基本保持一致,歌词也都是过去传唱的内容。只是有些曲调稍加修饰,更符合当今群众审美。
四、探寻持久传承的有效途径
浦东新区张江镇原是有名的“山歌之乡”,由于很多原因,浦东山歌在20世纪后期从民众间寂音了数十年。随着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形成社会共识,2012年,当地政府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山歌开启了全面的保护计划。2013年初,浦东山歌成功申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组建浦东山歌队
浦东新区从2009年起相继开设“浦东山歌班”,请当地擅长唱山歌的民歌手进行教学指导。歌队人员主要为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他们定期集中排练积极参加各类演出,有力地扩大了浦东山歌的传播度。“非物质”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主要是靠人的群体来口口相传进行延续,很多濒临消失的文化种类都是因后继无人而无法传承,所以,组建歌队是保护浦东山歌的第一项重要举措。
2.整理资料记录曲谱
整理资料记录曲谱的工作主要是由张江镇文化发展咨询专家、浦东山歌传承人、年逾古稀的奚保国先生组织开展的。奚保国作为一名“局内人”,更具有抢救这一文化遗产的紧迫感。近十年,他收集整理流传于浦东地区的所有经典山歌,编写了《浦东山歌》歌曲教材,并于2012年编辑出版,成为浦东各社区的教学丛书。2015年,奚保国先生又挖掘整理了十多首老山歌,创作了2首新山歌,编辑成《浦东山歌曲集教材2》。
3.搭建传承平台
2010年,在张江镇合唱队展演活动中,环东村山歌队以一首浦东山歌《问答山歌》使全场为之一振,听歌的人仿佛找到了童年记忆。2012年,张江镇组织排练了浦东山歌音舞组合《张江之韵》,并于2012年和2014年两度公演。每年6月14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浦东新区都会组织“浦东山歌普及教学成果展示活动”,这成为普及浦东山歌的一次检阅。参加展示的有十多个文化团队,其中还包括东方江韵幼儿园的“小小山歌队”。
面对已经褪色的“山歌之乡”,市县政府文化部门为尽快让其重现昔日光彩,对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也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每个区域都应选择出能最大程度代表一个乐种艺人群体的传承人,而浦东山歌的传承人较少,活跃在传承发展浦东山歌工作中的只有年逾古稀的奚保国老人,而传承人的断裂可能会造成文化遗产的灭绝,所以,培养典型的浦东山歌传承人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其次,“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民间艺术的生存机制——也就是使它能够活态地传承下去的自我生存能力”,[3]精选出浦东山歌中的代表作对其进行更符合听众审美地整理修饰,让其自身具有更有利于传播的音乐性。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代表作能否经久不衰的传唱下去会直接关系到浦东山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传承与弘扬。
最后,文化部门应加强对传统音乐的制度传承,增强支持力度,在更有组织性的进行管理和推广中提升整个群体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
五、结语
在开放的现代化环境中,传统的浦东山歌能流传至今并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体现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它作为一项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随着上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变化,但在现代生活中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却是永远不变的法则。所以要找到使地方文化特色持久传承的有效之路,在传承基础上有所创新,使浦东山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地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1]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2]奚保国.浦东山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3]李清资.海南少数民族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略[J].人民音乐, 2010,(6).
责任编辑:李新红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Songs in Modern Shanghai——An Example of Pudong Folk Songs
BI An-qi
(Chinese Conservatory of Music,Beijing 100101,China)
There are rich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usic genres in Shanghai (the modern open cosmopolis),in which Pudong folk songs are included, also called as Dongxiang melody and Dongxiang folk songs. As on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this musical genre has a long history in Shanghai with diverse varieties. It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songs in the modern and open environment. The protection of Pudong folk songs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lso analyzed and discussed.
Wu-Yue culture;Wu songs;Pudong folk song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6-06-27
毕安琪(1991-),女,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004—5856(2017)02—0124—05
J60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