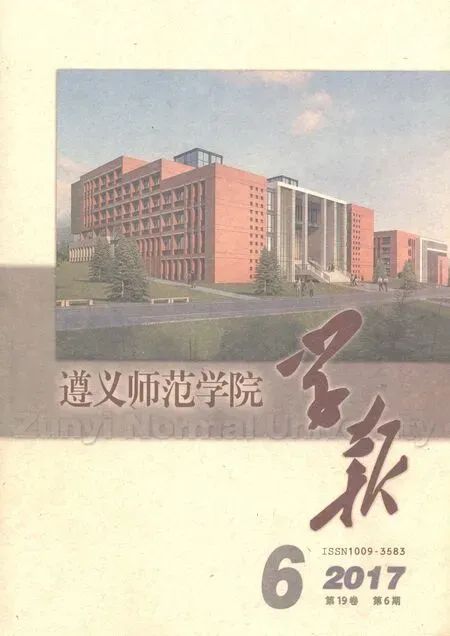试析黔北传统花灯现状成因
徐开良
(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黔北花灯,分老花灯和新花灯。习惯上,人们把老花灯称为“传统花灯”,把新花灯称为“新式花灯”。传统花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由当地村民自发组织演出,自愿观看,演出时间主要在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其程式、角色、唱词等都相对固定;新式花灯继承了传统花灯的角色、唱词及部分程式,演出时间也有较大调整,除正月演出外,其他时间如有重要活动也演出。它主要由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热心村民,对花灯唱词进行加工改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创编演唱的一种新花灯。[1]P232而今,活跃在黔北大地的主要是新式花灯,而传统花灯几乎难觅踪影。黔北传统花灯处在“没有人编、少人演、无人看”的尴尬处境,日趋式微。
一、黔北传统花灯的历史演变
黔北花灯始于何时,至今已无可考。据黔北花灯唱词“灯从唐王起,戏从唐王兴”,黔北花灯始于唐代。而真正记载黔北花灯的史料,当数成书于清康熙二年的《平越隶州志》,其“风俗篇”记载:
黎峨风俗,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双鬟低亸……翠翘金钗,服鲜衣,半臂拖袖,群手提花篮,联袂缓步,委蛇而行,盖假为采茶女,以灯做茶筐。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为十二月采茶之歌,歌竹枝,俯仰抑扬,曼音幽怨,亦可听也。
史料记载了黔北花灯演出的情状,与现在黔北花灯差别不大,可见,清代黔北花灯盛行于清道光年间。又见“西南巨儒”郑珍与莫友芝合编的《遵义府志》记载:
正月以姣童扮男女,一执扇、一执手帕,边歌边舞边唱《采茶》……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谓之曰“闹元宵”。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仁怀厅志》卷六也载: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又为传柑节,凡演龙灯、狮子灯、麒麟灯、车子灯、花灯,均于初八日夜起,至十五日鸡鸣止,谓之闹元宵。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湄潭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篇载:
淫声艳曲,湄俗所无,惟正月元宵城乡剪彩为灯,名曰‘花灯’。拣少年为女装,伴以鼓乐,沿门踏唱,主人酬其镫费,或觞以酒。
由此可见,黔北花灯在明末清初就已经相当盛行了,这可从清代进士贵阳人罗文彬《乙亥日记》记载看出:
正月初十日,戊申,微睛……行六十五里,抵牧猪箐,宿得兴店……有入店唱灯者,鼓锣喧阗,人声嘈杂,数刻乃去。正月二十一日己未,阴,卯刻起,舆夫来即束装行,泥泞路滑,舆夫艰于行路,行五十里,落幕始抵后坝,宿吴兴店……复有唱灯者来,不堪其扰,遂闭门寝。
日记中的“牧猪箐”即是现息烽县与播州区乌江镇之间的核桃箐一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花灯在这些地方是很盛行的。通过查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所编《余庆县志》卷,民国十七年(1928年)《绥阳县志》“风俗篇”,民国十八年(1929年)《桐梓县志》《瓮安县志》《开阳县志》“风俗篇”,均有黔北花灯演出的专章记载。综合一些老花灯艺人的回忆,黔北花灯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都是很兴盛的,是当时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样式。
新中国成立后,黔北花灯得到了空前发展。“花灯活动掀起了新的热潮,在一部分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黔北各县区乡的花灯搞得蓬蓬勃勃。在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年代,是黔北花灯空前繁荣的时期,那时人才辈出,花灯作品也不少,在全省享有声誉。”[2]
十年动乱期间,花灯艺术遭受重创。粉碎“四人帮”后,黔北花灯又重放光辉。各地花灯队纷纷恢复或整合重组,除演出传统节目外,还以“新闻灯”的形式,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歌颂农村改革政策,歌颂党的强国富民决策,由于参加人数多,演出范围广,黔北花灯艺术得以重放异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黔北花灯几乎遍及黔北地区(即原遵义地区)各县乡镇村寨,这些地区一到逢年过节都可以看到花灯演出。据统计,当时遵义县就有近百个花灯队,遵义市郊各乡也是上百个,正安县有140多个,余庆县有120多个,其他各县花灯队也多达几十个。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花灯已渗透到农村广大群众中。无论是礼仪、祭祀、祝寿、祈子、建房等都要唱灯。一年一度的春节到来之际,各地早就着手筹备春节的花灯活动,到处张灯结彩,家家备办物件,纷纷成立“上九会”“龙灯会”“花灯会”。这些演出队完全由群众自发组织,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后来,花灯活动由春节期间表演转向平常,如结婚、建房等都可以请灯班表演,即“季节性”转向“常年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黔北花灯因班子轻便灵活,组建方便,演出形式活泼,内容短小,深受群众喜爱。
九十年代起,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电视电影的普及,人民的艺术欣赏水平大幅度提升,进入新世纪;网络的普及,电脑进入千家万户,广大群众欣赏高品位的艺术类节目成为家常便饭,黔北传统花灯因此受到重大冲击,正逐渐受到冷落,存在问题受到严峻挑战。
首先,花灯演出难觅观众。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们逐渐从乡村进入城镇,过上了“都市化”的生活,追求精致时尚、形式美感的观众很难对相对粗放的花灯艺术形式有兴趣。而农村的演出市场也由于居民结构的急剧变化而收窄,花灯表演除了在传统节日活动有少许市场外,平时几乎难觅观众。
其次,花灯艺术人才越来越少。一是作为黔北花灯“领头雁”的花灯专业剧团退出演出市场,艺术人才纷纷改行,花灯专业演员后继乏人;二是在花灯演出的主阵地农村,因老一代民间艺人的逐渐离世,村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学习花灯演出的人越来越少,以致花灯艺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找遍许多村子都难觅一个花灯艺人的现状。
第三,可供演出的优质花灯剧目缺乏。专业创编人员由于演出市场的大幅度收窄甚至消失,所编剧目无人问津,“编了无用”,导致创作激情消失。所以花灯剧本少之又少,优秀的花灯剧目更是难觅。
二、黔北传统花灯现状成因分析
黔北传统花灯日趋式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功利性与宗教色彩浓厚
黔北传统花灯的表演按其功用,主要有春灯、寿灯、喜灯、愿灯、孝灯、瘟灯六种。春灯,是春节期间,灯班沿村逐户为家家户户恭贺春节,祈神保佑主家来年和顺、大吉大利;寿灯,是祝贺老人生日而表演的花灯,主要为了增加热闹气氛,祈神保佑老人长寿多福;喜灯,因主家有婚娶、生子、建房等喜事,邀请灯班跳灯欢娱,以悦神保佑主家福禄富贵、多子多福、家发业兴;愿灯,如果人们心中感到不安,或感到有“祟”时,如生病、无子、无嗣等,就许下“愿心”,当摆脱了羁绊后,就以为得到了神灵的庇佑,则请唱“愿灯”谢神,了却“愿心”;孝灯,是丧家邀请灯班给亡故的老辈或亲人演唱的花灯,一为慰藉亡人,尽其孝心,二为教育后代,传承孝道;瘟灯,旧社会一些地方经常发生如瘟疫、水灾、火灾等灾难,有时发生多人死亡,乡民们则认为有妖鬼邪魔作怪,就请来灯班唱“瘟灯”,祈天神将兵,驱魔辟邪以求得安宁健康。
上述黔北传统花灯功用,表面上,都是以追求热闹、欢乐娱人为宗旨,其内质,都带有乡民对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如求吉、求财、避灾、除邪、驱鬼等,这些追求又带有一些虚幻和憧憬,人们依靠自己的思维和力量又不能理解,便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幻想:借助于外部的、超人间的神灵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人们这种幻想常附着宗教思维特性。这种想借助超自然神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其实质就是宗教的世俗功利,这是黔北花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时代的进步,黔北传统花灯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就越来越难被具有现代思维的人们接纳,最终被人们抛弃实为必然。
(二)表演仪程迷信与落后
黔北传统花灯是一种具有独特程式的民间艺术,是由祭祀、歌舞、曲艺、戏剧和纸扎等民间艺术松散结合的综合体。其表演程序大致为:打贴——出灯法事——梳妆——说春——猜谜测字——盘灯——开财门——打唐二——砍五方——参神——唱调——采茶——造船——辞神——打加官——扫殿——辞主人——穿花——盖魁——演灯戏——卸装——退刹。这些程式,祭祀占有重要成分。这些祭祀活动,都与其表演形式紧紧相扣,都是请端公带领灯班的角色们共同完成。下面着重说明其中部分比较重要的祭祀仪式。
“出灯法事”,灯班在出灯前,主家在堂屋神龛前燃香亮烛,供上祭品,在堂屋四角燃起香烛,端公玄衣红袍,在神龛与“排灯”击铰念咒、磕头作揖,祈神保佑灯班唱灯顺利。内容主要有“烧文书”“点三香”“请二十八宿诸神”和念“安位咒”“解秽咒”“灵官咒”“土地咒”“金光咒”以及“请功曹”等,这些仪程与傩祭法事“开光”大同小异。
“花灯退刹”,是灯班在化火前,由端公带领,将所有灯笼聚于清净的河坝,围成一圈,然后端公烧文书,念咒,最后点燃灯笼,灯班人员唱着花灯调,在灯焰上跳来跳去,目的是净身上邪气,鬼怪才不得附身,以保平安吉祥。这种祭祀活动,与汉代宫廷年末驱疫赶鬼的傩祭程式相似。“砍五方”,是由端公或灯友,身穿铠甲,戴鬼脸,手执钢鞭或大刀,跳进主家香烛明亮的堂屋,东西南北中一阵疯吹,高唱:“开路先锋节节高,来到主家砍五方,带领兵马千千万,妖魔鬼怪全杀光……砍倒五方,主家安康,砍开五路,主家豪富。”然后冲至院坝,奔腾跳跃,喻为逐鬼驱邪,实与巫觐避邪禳魔的情形相似。
“造船”,是指为了祈神协助驱邪,保佑主家无灾无难,由巫师用茅草扎成小船,放于香火前,供上酒肉,边舞边念咒语,后以鸡冠血滴染,送到大路岔口焚烧。喻邪载船而去,这祭祀表演,与民间巫师“冲傩”“打替身”相似,实质就是驱邪祭祀。
“扫殿”,由灯班一人扮成跛脚土地神,手执蚊刷,打扫灯堂,以洁净之地迎神。边扫边舞边唱:“土地神,土地神,来到贵府扫殿门……信人如若诚心好,吾神对他显神灵,左手拿朵白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颜氏夫人生孔子,韩氏夫人生老君,牟尼夫人生我父,万古流传到如今,吾到坛下走一走,挥动金鞭驾起云,重将拂尘扫一扫,扫开主家大财门。”
“参神”与“辞神”,前者为灯班来到主家,在香火前参拜神灵;后者为跳灯将完,灯班在“香火”前辞别神灵,如天地君亲师位,门神、灶神、财神、土地神等,以歌舞表示,态度虔诚。
“盖魁”,是指灯班唱戏完毕之前,一人扮成金甲将军,为魁屋,手执钢鞭上,在主家堂屋大声吼道:“金魁金魁杀气腾腾,大吼三声,带鬼出门……手提金铜锏,年霄会上斩邪魔,主家大吉大利……。”
从上述黔北传统花灯表演程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程式始终贯穿着黔北传统花灯的脉络——宗教的祭祀。从出灯法事到花灯退刹,历经了七道祭祀活动。通过对神灵的崇拜祈求,以歌舞娱神,以祭品媚神,以沟通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向神灵表达人的敬畏、虔诚、愿望,通过取悦神灵,祈求赐福消灾,又模拟神灵形象,对人的愿望和功利追求给予一定满足。祭祀的气氛,时而杀气腾腾,时而阴森恐怖,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目的是让人们在心理、思想上产生一种敬畏。这些礼仪,皆为虚妄。这在过去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迷信思想较浓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文化知识普及程度较高的今天,人们就很难接受了。
(三)角色世俗化
黔北传统花灯以其宗教的世俗功利为宗旨,安排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这一套程式,其角色表演始终世俗化地渲染“神”力,强调非人可以达到的力量。
黔北传统花灯的主要角色有:端公、报子、春倌、唐二、财帛星、文曲星、武曲星、开路先锋、土地神、幺妹。其中,主要角色是端公、唐二、幺妹和土地神。“端公”是主持花灯表演祭祀的重要角色。他是半人半仙的角色,通过他,凡人才能与上天神灵沟通思想,表达意愿,才能把天上的神仙请到凡界。在黔北民间的“古傩”中,有一堂法事,叫“还四官菩萨愿”。黔北传统花灯也有类似程式,主要以唐二为引子,做还愿法事。戏中表明,唐二是战国时期的人,是苏秦的书童。他俩一同进京赶考,途中,唐二腿有病,百治不好,向四官菩萨许愿后就好了,后来,就把唐二也视为诸神之一,让他和主人做个“二愿同交”,成为花灯的角色。唐二表演诙谐,俚俗,逗人发笑,是花灯中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保持了傩中丑角的特点。“开路先锋”,也是傩中驱鬼邪开路武将,还有“财帛星”“文曲星”“武曲星”等则是天帝玉皇的殿臣。这些角色,皆是模拟“人格化”的神,他们有的出自巫教,有的来自道教,都一起出现在花灯表演中,形成一个小小的神佛世界。按理,这些神佛的出现应按自己的身份去展示相应的角色内容,但在花灯表演中,他们并没有或部分没有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各行其职。如唐二本应是愿事主持,在花灯中,却以丑角出现,与幺妹跳花灯。又如幺妹本是上天十二花园的姊妹,按职应是司管花的花仙,却不知何故下凡界与唐二跳花灯。就连司管地方的“土地神”也参与了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的花灯歌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黔北传统花灯中的角色,全部是以神佛的面目出现,其表演把花灯堂营造成一个“神佛”的世界,营造一种严肃的宗教氛围,以渲染宗教思想。这种表演营造的“神界”,只与愚昧与落后结缘,难被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现代人接受。
(四)内容繁冗
黔北传统花灯的表演,以祭祀、曲艺、歌舞、戏剧为主要内容,祭祀表演中艺术较强的当算曲艺、歌舞、戏剧。这些表演,内容单一,唱词单调,但程式冗长,这样的表演形式,显得陈旧、落伍。在黔北花灯表演到高潮——“采茶”时,灯班所有角色悉数上场,集说、唱、歌、舞为一体,很简单的情节,却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情节大略是:丑角唐二要邀幺妹跳灯,因为幺妹是天上的花仙,便先请来了土地神,托他去请幺妹,结果没请来,后来唐二和土地神一道请,幺妹才答应下凡跳花灯。但是,幺妹的出台,却又经过了一段冗长的宗教祭祀,即梳妆、拜年、参神、扫堂,后才与唐二跳灯舞蹈、唱采茶歌。随后,又经谢神、辞神祭祀,才开始唱灯,结果把黔北传统花灯中最富艺术表演的采茶,也牢牢地维系在宗教的礼仪之中,通过宗教祭祀的重复再现,强化花灯的宗教意识,用现代人眼光审视,就显得很落后。
另外,黔北花灯的曲艺,“打帖”“说春”“打唐二”和“开财门”,亦是如此。“打帖”,就是“报子”,向主家约时玩灯。每到一家,得向主家说一大堆吉利话,绕来绕去,大致意思都是祝愿升官发财、大富大贵等等。“说春”,是由春倌扮人状,手拿“春帖”,恭奉主人,祝福吉祥,念唱:“一进门来朝上望,主家坐栋好华堂,主家就在华堂坐,天地君亲坐中央。天地君亲坐中央,梓童帝君坐两旁,自从春官来参拜,儿子儿孙状元郎。”“盘灯”,是开财门前的一个礼仪,灯队来到主家的门前,门关着。主家向灯队盘问:“何为天何为地,何人掌印定乾坤,天下有无人和义?”一般大致这样答:“夫为天,妻为地,玉皇大帝掌乾坤,孔圣就有仁和义……”“东方财门姊妹开,南斗七星送财来,送财送到主家门,斗大的黃金滚进来,五子登科人延寿,大吉大利大发财。”就连最自由、最诙谐的“打唐二”段子,也显得陈旧、冗长。如段子:“唐二本姓唐,来到主家旁,主家阴德好,天赐金银屋,金子赏櫈银柱柱,金甑子来银箍箍,老唐不说舔肥(奉承)话,茅厕头里油珠珠……。”其他仪式也是如此,表演内容都重复许多奉承不实之语,让人难以有兴趣听完。
花灯歌舞,多为“送寿”“二十四孝”“木莲救母”等具有落后宗教色彩的曲调。如“穿花”一出,本是黔北花灯的压轴歌舞,但唱词内容仍重复强调宗教与功利,仍旧是一些陈旧的奉承祝福。如:“一唱东方甲乙木,主家加官又进禄,二唱南方丙丁火,招财童子就是我,三唱西方庚申金,穿些金银谢主人,四唱北方壬癸水,穿出是非与口嘴,五唱中央戊己土,主家发财修金屋……天瘟穿出天堂外,地瘟穿出地狱门,羊瘟穿出羊肠坝,马瘟穿出青草坪,主家金屋穿条街,诸神百鬼不敢来……。”
黔北传统花灯多为“灯夹戏”,即灯班在歌舞中或演唱完毕后,又演出折子小戏,当这些程序表演完成,耗时已经很久了,加之其表演又始终维系在宗教功利的主旋律上,冗长乏味,对现代人来说,就更难接受了。
三、结语
分析黔北传统花灯的内容与形式,我们不难发现,贯穿黔北传统花灯的是一种坚实而巩固的精神内核——宣传宗教,追求功利,表现迷信。它以落后陈旧的演出形式,大量借用“傩”这种宗教活动形态,兼蓄“儒、佛、道”的思想,并吸收一些民间传说成份,构成了一套完整表演。正因为黔北传统花灯落于窠臼,导致它成为民间艺术“古董”,落后的糟粕部分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时代主流相逆,固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这正是造成黔北传统花灯逐渐走向衰落、日渐被新花灯所取代的原因。
[1]陈忠禄.余庆花灯[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2]崔克昌.黔北花灯初探[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