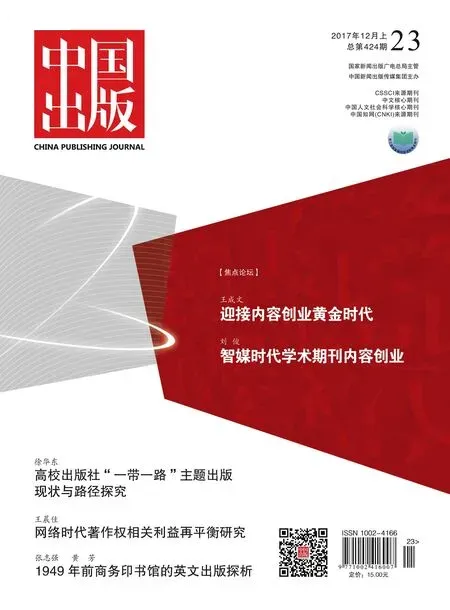侵犯著作权单位犯罪司法认定之反思*
——基于14份典型判决的实证分析
□文│陈 萍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大背景下,各种文化产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为繁荣我国文化市场增添了全新活力。但由于不少中小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缺乏著作权保护意识,极易触碰单位[1]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红线。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践中典型司法判决的反思,努力在鼓励创新创业和保护著作权之间寻求科学有效的刑事规制机制。
一、对判决书样本的总体评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选取,以“侵犯著作权罪”为案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称《刑法》)第220条”为法律依据,共检索得14份有效刑事判决文书。[2]从犯罪地点来看,集中分布在上海(5起)、河南(1起)、浙江(2起)、广东(1起)、江苏(2起)、山东(2起)、湖北(1起)7个省级区域。从犯罪主体来看,14份刑事判决中共同犯罪9起,单独犯罪5起。从犯罪对象来看,针对音像制品的2起(14.28%),针对文字作品的10起(71.44%),针对计算机软件的2起(14.28%)。从犯罪手段来看,通过网络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6起(42.85%),通过传统技术手段(盗版印刷、非法安装)实施犯罪行为的8起(57.15%)。从刑罚主体来看,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并罚的13起(92.85%),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1起(7.15%)。
关于单位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处刑,上述判决书样本呈现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1.关于是否追究单位
根据《刑法》第220条的规定,“单位犯侵犯著作权罪的,应当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侵犯著作权罪规定处罚”。侵犯著作权罪是故意犯罪,对单位犯罪施以双罚制,既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又能剥夺单位不法利益,是最为有效的刑罚方式。但在刑事司法中,这种双罚制并未得到有效遵守。14起案例中,有2起(14.29%)只追诉相关责任人,而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比如,在上海同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何爱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何爱伟是上海惠生图文设计制作室实际经营人,其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从网络上下载《之江新语》等电子版书籍或购书拆装、打印、复印、裁剪、装订成册,并通过淘宝网店,以低于市场售价的价格进行销售。其行为是作为该制作室实际经营人、以制作室名义、为制作室利益而实施,应当作为单位犯罪来处理,正如同案的杨某某和蔡某某之于上海同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一样。又如,蒋俊、葛正明等侵犯著作权案中,蒋俊系科茂公司软件部经理,其相应犯罪行为系其以科茂公司名义实施,犯罪相应的违法所得亦归单位所有,应属于科茂公司的单位犯罪,但公诉机关对科茂公司不补充起诉,法院只能按照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对蒋俊进行定罪处罚。
2.关于如何适用缓刑
根据《刑法》第220条的规定,单位侵犯著作权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应与相应个人犯罪同等定罪处罚。14份刑事判决共有50名自然人被告,30名(60%)适用缓刑,20名(40%)未适用缓刑,其平均刑期为23.7个月。蒋俊、葛正明等侵犯著作权案中4名被告人均适用缓刑。从案例数来看,14起案例中只有不足3起(21.43%)案例中自然人被告未适用缓刑,其中广东新飞仕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张某甲等侵犯著作权案18名自然人被告中6名(33.33%)适用缓刑。尽管有学者认为,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基于满足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合理利用的需求,在刑事方面降低惩治标准确实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3]但是,单位中2人以上共同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参与犯罪人数较多,有组织性,对于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鉴于其主观恶性较大且犯罪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应当谨慎适用缓刑。比如,山东某印刷有限公司、张某侵犯著作权案中,被告未经许可印刷、装订盗版图书32566册,非法经营数额为418662.95元,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张某应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以下,仅因其具有自首、悔罪等情节,就减轻为缓刑,似乎有量刑畸轻之嫌。
3.关于如何确定罚金
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文称《解释(二)》)第4条的规定,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1倍以下确定。14份司法判决中,有7起并未明确查明非法经营数额,对单位罚金数额范围在2万元到10万元之间,平均数额为4.8万元;另7起明确查明非法经营数额,数额范围在8万元到270万元,总计约427万元,平均约60万元;后7起对单位处以罚金共227.1万元,平均约55万元。其中,2起并未对单位处以罚金,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其中蒋俊、葛正明等侵犯著作权案,非法经营数额为9万元,对蒋俊处以23.45万元罚金;其余5起案例中,有4起按照上述倍比制确定罚金,但对上海同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例外,其非法经营数额为8.7万且未对权利人进行赔偿,而罚金仅0.1万元。上述畸重畸轻的罚金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侵权著作权罪罚金数额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不足。
二、对侵犯著作权罪单位共同犯罪认定之反思
在9起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共同犯罪样本案例中,有6起涉及单位和个人的共同犯罪,有3起只涉及单位内相关责任人员之间的共同犯罪。对于前者,如何认定共同犯罪数额进而予以量刑是实践和理论中争论较大的问题;对于后者,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是共同犯罪、如何合理量刑,最高院曾特别予以答复(《法释〔2000〕31号》),但该答复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价值并不明显。结合上述样本案例,笔者就此简要分析评述。
1.单位与个人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
根据《解释(二)》第6条的规定,单位实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的行为,按照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具体而言,对单位和个人,起刑点均是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或者未经许可复制发行著作权人作品1000份。那么,单位和个人共同侵犯著作权时,如何认定犯罪数额进而科学量刑呢?有观点认为应当对单位和自然人分别定罪。[4]笔者以为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共同犯罪仍宜以主犯来确定犯罪数额,因为单位和个人的共同犯罪属于复杂的共同犯罪,即各共同犯罪之间存在一定分工的共同犯罪,有的为实行犯,有的为帮助犯。[5]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以其身份为标准,才能客观地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否则,对于提供帮助的从犯(尤其是自然人)而言,可能超出其故意范围,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这也得到司法判决的认可。比如,在上海同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何爱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认定何爱伟(销售涉案书籍4647本、销售金额共计87717.85元)为主犯,并据此对上海同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以共犯予以定罪量刑。当然,若涉案被告均为主犯,且能查清各自数额情节,则可分别定罪量刑。比如,在邹峥、陈某甲等侵犯著作权案中,邹峥非法经营数额55万多元,上海墨龙印务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主管人员陈某甲印刷盗版CFA书4万多册,上海弘磊纸制品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主管人员吕某装订盗版书4万多册,王某、赵某印刷盗版书3万多册,非法经营数额36万多元,法院认定各被告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在量刑时予以适当区分。
2.单位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划分
根据《法释〔2000〕31号答复》,“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该答复对共同犯罪的理论形成一定冲击,因为共同犯罪的量刑标准本身按作用确定,而招致很多批评之声。相关责任人员在单位内从事侵犯著作权行为,必定存在共同故意(当然部分责任人员是放任的间接故意),将相关责任人员认定为共同犯罪并不存在理论障碍。该答复既认为可以不区分主从犯又认为应当按照作用量刑,客观上是提高了某些直接责任人员的量刑。具体对侵犯著作权单位相关责任人员而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是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主管人员)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将直接责任人员(一般是技术人员、会计等普通员工)认定为从犯则在量刑上有一定区别,因为根据《刑法》第27条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该答复的实际后果是排除了部分直接责任人员从轻处罚的可能。然而,该答复使用非强制性的“可以”用语,法官具有相应自由裁量权。样本案例中区分主从犯的2起:在上海有趣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余肖龙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认定宋志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在广某、罗某、罗某、冼某侵犯著作权案中,在共同犯罪中,罗俊毅起主要作用,是主犯;罗斌、冼志刚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不区分主从犯的1起:在某某在线(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李某、王某、徐某某侵犯著作权案中,法院认定王某(技术总监)、徐某某(高级工程师)目的是通过实施上述犯罪行为获取非法利益,两人均具有明显的犯罪故意,其行为在犯罪中均起到主要作用,不按照从犯处理。至于最终量刑结果,2起区分主从犯案例中,从犯宋志刚处以3年缓3年罚金1万元,同案主犯余肖龙处以3年缓4年罚金2万元;从犯罗斌处以1年3月缓2年罚金1万元、从犯冼志刚处以1年缓2年罚金0.5万,同案主犯罗俊毅处以2年缓3年罚金2万元;1起未区分主从犯案例中,王某和徐某某均处以10月缓1年罚金1万元,同案李某处以1年缓1年罚金2万元。可见从结果看,区分主从犯与否对直接责任人员(宋志刚、冼志刚、王某和徐某某)最终量刑轻重影响并不明显。因此,笔者认为该答复理论基础不足,实践操作不易,司法机关可对相关责任人员按照主从犯定罪量刑。
三、对单位侵犯著作权罪单位刑罚机制之反思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应当依靠自身的层次性、精确性、适时性和肯定性去影响人们对利弊得失的计算,从而制止人们去实施于人于己均无益的犯罪。[6]结合判决样本分析来看,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处以罚金,数额确定规则应当更加科学合理,且可辅之以禁止令,增加以单位为对象的资格刑。
其一,根据刑法第220条,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应当判处罚金,但该条并未明确处罚标准,是典型的无限额罚金制,即刑法不具体规定罚金的数额,而由法院根据犯罪的情节并参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自由裁量罚金数额的制度。《解释》第15条曾规定,单位侵犯著作权犯罪按照定罪量刑标准的3倍定罪量刑。然而,《解释(二)》第6条规定,单位侵犯著作权罪以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即对单位和自然人采取相同标准来确定罚金数额。笔者认为该标准并不可取,侵犯著作权单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规模大、涉案金额高,比同等自然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高。因此,其罚金的确定标准应当高于相应个人犯罪。《解释(二)》第6条的规定并未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对单位施以较个人更重的罚金在引入法人犯罪的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常见。比如,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38条,对法人的罚金数额为自然人犯相同罪行的5倍;如果某罪行对自然人不可判处罚金,则判处法人的罚金数额为100万欧元。[7]基于此,笔者以为,我国对侵犯著作权单位犯罪宜处以相应个人犯罪3倍的罚金。
其二,我国现行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只判处罚金的刑罚设置太过单一。从学理上来说,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中,对单位的刑罚体现了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否定评价,但罚金刑这一单一刑种的设置不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难以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8]然而,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只是一种附加刑,这与单位侵犯著作权罪的严重危害性并不相符。另外,如上文所述,现有司法实践中罚金数额仍普遍偏低,而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又普遍适用缓刑。因经验、技术、知识以及信息的限制,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再从事著作权相关业务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极大。这已经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引入针对自然人的禁止令,“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法院可根据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在蒋俊、葛正明等侵犯著作权案中,对被告判处缓刑同时,禁止被告4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计算机软件销售活动。这不仅可使其失去再次实施侵犯著作权罪行为的机会,而且可对该领域的其他从业人员起到警示作用。其实,这种剥夺从业资格的禁止令同样可以适用于单位。比如,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39条规定,适用于法人的刑罚,除罚金外,还包括解散、禁止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一项或者若干项职业或者社会的活动、关闭协助实施被指控行为的企业或者企业的一个或几个部门、不得进入公共市场、禁止公开募集资金、禁止签发支票和使用银行信用卡等。[9]鉴于自然人禁止令的刑事司法经验,我国已有基础借鉴法国法律规定对单位增设资格刑,根据其罪行轻重,可以永久性或暂时性剥夺或限制从事某项业务活动全部或部分资格。具体到犯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而言,可以判处剥夺其出版的从业资格、禁止从事与著作权相关的行业、限制其商业活动能力等。
注释:
[1]本文所称“单位”为刑法单位犯罪意义中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当然司法实践中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仍以公司和企业为主。
[2]网站直接搜索结果有16份刑事判决,其中“陈某某侵犯著作权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滑刑初字第575号〕”与“卢某某、毕某某、于某、于某某、马某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3)章刑初字第47号〕”各有一份重复,故有效刑事判决为14份。
[3]陈志鑫.“双层社会”背景下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标准新构——基于30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J].政治与法律,2015(11)
[4]马荣春,周建达.论单位共同犯罪的责任追究:定罪与责任分担[J].政治与法律,2010(2)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八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70
[6]黄风.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112
[7]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do;jsessionid=1BEF5FE6B0236507C8D2FA35957759F1.tpdila20v_1?idSectionTA=LEGISCT A000006181734&cidTexte=LEGITEXT000006070719&dateTexte=20170912[EB/OL].2017-09-12
[8]李翔.单位犯罪司法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1
[9][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