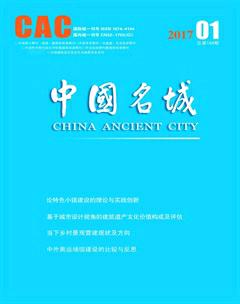马尼拉的城市发展与规划
张敏+Jose+Danilo+Selvestre+林天鹏
摘 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尼拉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情况。文章共分四节,第一节概括了马尼拉城市的形成过程及目前马尼拉大区行政区域的基本状况;第二节介绍了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中心——Intramuras(西班牙王城)和经济中心——Binondo(中国城);第三节分析了美西战争后马尼拉城市发展的趋势,介绍了目前最重要的两个CBD——Makati的Ayala新城和Global City;最后阐释了西班牙传统文化和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代表人物Daniel Burnham对马尼拉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影响。
关键词:马尼拉;历史;西班牙王城;中国城;Global City;Daniel Burnham
Abstract: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anilas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first chapter, the brief history and general data of Metro Manila have been presented; The second chapter has introduced the Intramuras,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Binondo, the economy center formed in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The third chapter has showed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Manila after US-Spanish War, and introduced Ayala New Town in Makati and the Global Cit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BD in todays Manila. At last, the influence of Spanish Culture and Daniel Burnham, the promoter of American City Beautified Movement onto Manila has been analyzed.
Key words:Manila ; history ; Intramuras ; Binondo ; Global City ; Daniel Burnham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7)-01-71(12)
1 马尼拉的基本情况
马尼拉是菲律宾共和国首都,地处吕宋岛西南角,宏观区位上正处于南中国海东岸线的中间点(图1),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前,马尼拉是一个名为Maynila的回教徒马来人村庄,同时也是当地土族酋长统治周围地区的中心。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开始环球航行。他绕过南美洲与南极洲之间的水道(即麦哲伦海峡),横渡烟波浩渺的太平洋,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于1521年到达菲律宾南部,并以西班牙国王菲律普的名字命名该片岛屿。在菲律宾中部宿务一次当地部族的冲突中,麦哲伦介入其中,被土著人砍杀致死,因此他并没有到过马尼拉。
1564年,一支由米格尔·洛佩斯·雷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率领的西班牙探险队从墨西哥出发,1565年2月抵达菲律宾宿务。在听闻了当地人有关吕宋岛富饶资源的描述后,继续北行并于1570年到达了马尼拉。一到马尼拉,他被马尼拉湾周边的地理环境所震撼:马尼拉湾本身宛如突入陆地的口袋,它西南通过一个收紧的出海口与南中国海相连,西侧与南中国海之间是连续的三座死火山,隔绝了由大海而来的狂风与巨浪;海湾东北侧是马尼拉村和周边大片的农田与平原;海湾东南侧翻过一道狭长的陆峡是面积巨大的Laguna淡水湖,这简直上帝天赐的建港建城的良址(图2)!
为了掌控马尼拉一带的土地和村庄,西班牙探险队和当地土著发生了战争。经过几个月的屠杀后,西班牙探险队和当地酋长终于1571年签订“和平”条约,战败的土著被迫将马尼拉的掌控权让给西班牙。1571年6月24日,雷加斯皮正式宣布马尼拉为西班牙东印度群岛的新首都。
十九世纪末,老牌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已日薄西山,新兴的资本主义帝国——美国正蓬勃兴起。借支持当地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名义,美国于1898年发动了美(国)西(班牙)战争。经过短短100余天在加勒比海和远东的同时作战,以牺牲3000名士兵生命的代价(真正战死的仅400余人,其余多为病热而死),美国就轻易取得了胜利。它帮助古巴取得了独立,并将菲律宾、关岛、夏威夷、波多黎各等收入囊中。
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菲律宾据为己有并成立傀儡政府。1945年,美军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海战,重返马尼拉。1946年,菲律宾正式独立,首任总统是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A Roxas)。1965年,“抗日英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赢得大选,但他改变前任各届总统四年任期的习惯,多次自导自演、“连选成功”,直至民怨沸腾,最终于1986年被迫下台并流亡夏威夷。但在他的铁腕统治下,菲律宾的国际外交、招商引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经过40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马尼拉早已从马尼拉湾畔的一个小渔村演变成南中国海东岸的一座多种族聚居、东西文化荟萃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会。今天,整个马尼拉大区(Metro Manila)由Manila、Quezon City等12个市(city)及Taquia等5个区 (municipality)组成(图3),总面积636平方公里,总人口994万(2004年数据),人口密度约15600人/平方公里。具体各市、区面积及人口数(2004年数据)见表1。但随着人口的膨胀和都市的发展,城市建成区早已突破Metro Manila的行政边界,其大致建成区面积如表2。
今天的马尼拉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富有浓厚热带情调的大都会,也是东南亚地区著名的会展和旅游胜地,城内、城外名胜古迹众多。马尼拉是一个巨大的都市绵延区,但一般公认的市中心是位于西班牙王城(Intramuras)南的黎刹尔公园广场。该广场占地58公顷,原名鲁纳达公园,为纪念菲律宾的民族英雄黎刹尔博士而改为现名,其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黎刹尔博士是个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早年学医,后从事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896年12月30日被殖民当局杀害,年仅35岁。黎刹尔广场北部有一座著名的中国花园,园内有假山、水池等。
2 马尼拉旧城的形成及现状
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早期地图可以看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建立的马尼拉市选址在帕西格河(Pasig River)流入马尼拉湾的河口处。帕西格河南岸是政治文化中心——Intramuras(西班牙王城),北岸是商业与经济中心——Binondo(中国城)。绝大部分运输船只是停泊在帕西格河内,而不是马尼拉湾沿岸,因此城市生活也多是沿着帕西格河展开(图4)。
2.1 政治中心——Intramuros(西班牙王城)
Intramuras由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末开始建造,因此也被当地华侨俗称为“西班牙王城”。它位于帕西河(Pasig River)河南岸,其名称来自拉丁文“Intra”(里面)和“muros”(墙),亦即“城墙内”的意思,这也完全符合王城区的构造——一个被厚厚城墙包围的城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王城区实际上就是马尼拉市。
根据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皇家法令,雷加斯皮为马尼拉规划了最早的蓝图(图5)。它被设计成星形要塞,占地64公顷,周边被2.44米厚、6.7米高的石墙包围着,以抵御当地土著的反叛和中国海盗的侵扰。雷加斯皮在王城内兴建了道路、堡垒、教堂和学校。王城最终于1606年竣工,当时即成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行政、军事和宗教中心。菲律宾最古老的大学、教堂和修道院都坐落于王城区内,其中最著名的天主教学校有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和雷特兰圣胡安学院(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教堂有马尼拉大教堂和圣奥古斯丁教堂等。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府本来也设立于王城区内,不过19世纪的一场地震使总督府迁往了王城以东、帕西格河上游沿岸的马拉卡南宫,即今天的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府。
二战时期,马尼拉王城区受到严重破坏。1942年,日本侵袭菲律宾时,美军守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发现自己无力保卫马尼拉,因此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之城。1945年,美军重新返回马尼拉,节节败退的日军见大势已退,就在撤退过程中肆意破坏马尼拉城市和屠杀马尼拉居民。麦克阿瑟将军虽然反对轰炸马尼拉王城区,却批准美军炮击,古老的西班牙王城区在疯狂炮击下被炸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图6)。
1980年代,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下令修复长年失修的王城区,王城区管理局(Intramuros Administration)也因此而成立。当局修葺了大部分的废墟,然而,由于管理局的内政问题和马科斯政府的倒台,王城区内仍然有好些废墟被搁置,一些遗址也被新的现代建筑所取代。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王城区是马尼拉境内唯一保存西班牙风格建筑较为完整的城区(图7)。由于马尼拉经济的快速发展,王城区外许多散布的西班牙古迹逐渐被拆除,唯有王城区内的西班牙古迹未受太大的现代化影响。
除北侧天然的帕西格河外,西班牙王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但在美国统治时期被填平,目前已成了高尔夫球场。南侧护城河之外,马尼拉市开辟了宽阔的黎刹尔广场,它犹如北京故宫外的天安门广场,成为马尼拉新的城市中心。
目前,西班牙王城区已成为马尼拉最重要的旅游景区,咖啡馆密布,教堂众多,环境卫生也应算马尼拉最好的地区之一(图8、图9),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私搭乱建、任意改造等。2010年 8月,环球遗产基金(Global Heritage Fund)发出《拯救消逝的遗产》(Saving Our Vanishing Heritage)报告,把马尼拉西班牙王城区列为世界12个最趋渐边缘化、正面对无法挽救的损失和破坏的遗产之一,报告指出问题来自管理不严格和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

2.2 经济中心——Binondo(中国城)
早在11世纪的宋代,中国南方沿海便有渔民陆续移民吕宋岛。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后,发现当地土著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生产和管理技能很差,因此默许和纵容大量有组织中国侨民的到来。这些侨民大多来自福建沿海,他们吃苦耐劳,生活技能很强,因此逐渐垄断了马尼拉的餐饮、修理、建筑施工、商业零售等各行各业,甚至进入殖民政府担任税务、文书等工作。
但西班牙殖民政府规定,唯有合法的“白种人”(西班牙语Blancos) 才能在王城区内居住,非白种人在日落之前必须离开王城区。“白种人”包括菲律宾西班牙人(即在菲律宾出生的西班牙人)、半岛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西班牙-汉人混血儿(西班牙语Tornatrás)和西班牙-马来裔混血儿(西班牙语Mestizos)。基于种族歧视和当时的社会道德观,男白种人可以和非白种女人结婚,女白种人不可以和非白种男人结婚。但是和男西班牙人结婚的非白种女人可以自动合法地被归为白种人,她们也可以和丈夫居住在王城区内。
因此,除极少数嫁给西班牙男人的中国妇女外,绝大部分华人被禁止居住在西班牙王城内,他们只好选择在帕西格河北岸的Binondo地区安营扎寨。这里与西班牙王城隔河相望,来往方便。帕西格河又是福建侨民到达马尼拉的落脚码头,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侨民聚居的首选之地(图10)。
中国城只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但一般认为以“中菲友谊门”牌坊为入口(图11)、以“亲善门”牌坊为终结,大致面积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60万,人口密度接近7万人/平方公里,号称世界最大的中国城。它由近百条横七竖八的街巷为骨架,其中最有名的是王彬街。王彬本是一位普通的印刷厂华工,但因在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此受到菲律宾政府和当地华侨的尊崇和景仰。但实际上王彬和黎刹尔一样,都是美西战争后意识形态宣传的成果。
在中国城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中,分布有杂货铺、金饰店、药铺、书店、餐厅、茶馆、诊所、银行、影剧院等形形色色的商业店铺,还有中国式的儒释道庙宇等。
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实行公开的种族歧视政策:白种人豁免缴纳任何税赋,当地土著(马来裔Tagaloo人,华人戏称其为“他家禄人”或“他家乐人”)需要缴纳基本税务,汉人与前两者的混血儿按双倍标准缴纳税赋,纯种华人则需按四倍标准缴纳税赋。但这种极端歧视性的繁重税赋并没有压垮中国侨民的生存意志,反倒使他们更加发愤图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侨民最终掌握了菲律宾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据粗略统计,目前华人仅占菲律宾总人口的2%,却掌握了30%的经济总量,许多知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如SM(商业零售)、PNB(菲律宾国家银行)、菲航、超群(连锁餐饮)、美加(房地产)等都在华商巨贾的控制之中。
华商当然不仅仅做小生意,也从事金融、保险、证券等高级业务,因此在帕西格河的北岸形成了马尼拉最早的CBD——埃斯柯达(Escolta)大道,它犹如上海的外滩,从西班牙统治时期起,就是一条繁荣热闹的街道,银行密集、高楼林立。
华人死后,大多不能叶落归根,因此部分集中葬在Binondo再往北的“华侨义山”(当时地处城外,另外离祖国更“近”一些)。不明事理的游客来到华侨义山定会大吃一惊,它完全不像我们心中的墓地,全然就是一座人去楼空的中国式城镇(图12)!真实尺度的建筑、真实尺度的街道,甚至亭台楼阁、花园广场,应有尽有。唯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整个“小镇”空无一人,“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让人不免感觉后脊涌上一股凉意。“华侨义山”现象反映了华人厚葬的习俗,体现了他们的富有,也凝聚了他们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因为为了迎合顾客的消费时尚,Binondo的商业建筑必须不断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但华侨义山却顽固坚持着纯正的中国形式和传统。
3 马尼拉的新区开发
3.1 城市的扩张和重心的转移
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菲律宾作为美国的附属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上世纪前半叶很长一段时期内,菲律宾的人均GDP仅次于日本,在全亚洲排名第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也很快,在早期西班牙殖民政府建立的雅典耀马尼拉大学、德拉刹大学等基础上,20世纪又建立了菲律宾大学、菲律宾师范学院、菲律宾女子大学、远东大学、亚洲经济管理学院等。其中菲律宾大学是于1908年6月由兰德公司资助、美国政府为菲律宾人开办的第一所大学,该校的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默里·巴特利特博士(Murray Bartlett)。建校之初,全校仅有两个教学单位,即美术学院和农学院,之后在十年内,陆续建成了医学院、工程学院、教育学院、音乐学院、法学院、文学系、兽医学系等7个院系。1948年12月,即在校庆40周年时,原设在马尼拉市的菲律宾大学全部迁往马尼拉市东北的奎松(Quezon)市的迪利曼(Deliman)。目前,菲律宾大学已拥有40余个院系,是菲律宾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除高等教育外,在美国的帮助下,初等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也很快。全民基本普及了英语教育,上世纪初多次举办远东运动会,菲律宾俨然成为新兴国家的样板。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因为历史的传统渊源和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等太平洋军事战略上的倚重,美国仍旧给予了菲律宾许多支持和帮助,如在1966年作为第一出资人建议将亚洲开发银行总部设在马尼拉,这有助于菲律宾保持区域性的国际中心地位。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也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大力推行“大米自信”计划,并学习香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鼓励引进外资,使菲律宾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
从马尼拉城市发展来看,住宅建设(绝大多数为私人独户住宅,品质大多不高)以原马尼拉市为中心,在整个马尼拉大区内成铺天盖地的蔓延之势。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以西班牙王城为原点,向东北方向沿着宽阔的奎松大道布局,奎松大道的终点即是著名的菲律宾大学。但商业办公机构不同,为了靠拢城南的尼诺阿基诺(Ninuo Aquilo)国际机场,新的CBD大多布局在城市的东南方向(图13)。
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导致了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原来马尼拉的空间中心像西班牙本土所有的城市如马德里、Teledo一样,是西班牙王城内以马尼拉大教堂为背景的马约尔广场(Mayor Square)。美西战争以后,新政府整治了西班牙王城外以南的大片空地,形成了黎刹尔公园广场(Rizal Park),它更像华盛顿的中央草坪,尺度更大、更加生态,广场周边不再是教堂,而主要是政府和文化机构(图14)。
西班牙统治时期,马尼拉的船运码头主要聚集于帕西格河内,最早的CBD是Binondo南部沿河的Escolta大街,应该讲当时的马尼拉是一座小型的河口城市。但随着黎刹尔广场的开辟、特别是罗哈斯(Roxas)大街的建设,马尼拉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滨海城市。
罗哈斯大道是沿着马尼拉湾几乎笔直向南的一条交通及景观性干道,以马尼拉湾的落日和滨海绿带的椰子树而著称,因此也称“落日大道”。它北自帕西格河的入海口,南至马尼拉国际机场,全长28公里,宽约50米。临海一侧是宽阔的滨海散步道和游艇码头,道路东侧是各色写字楼、宾馆饭店和高层住宅。它最初称为“甲米地大道”,后来改为现名以纪念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A Roxas)。
马尼拉早期的城市生活主要沿帕西格河展开,但随着Binondo地区环境质量的下降特别是帕西格河污染的加剧,除运输船只外,帕西格河沿岸已少有人光顾。每到傍晚,罗哈斯海滨大道便成了游人聚集之处,大家或倚靠护栏,望着波光粼粼的马尼拉湾夕阳西下,或找个吧座,品着烧烤和啤酒,听着阵阵传来的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吉他弹唱,在轻微拂面的海风中,真能感受到美好城市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辛福感和快乐感(图15)。
由于菲律宾独特的历史背景和马尼拉优越的地理环境,马尼拉一直是著名的国际会议城市。在罗哈斯大道城区段南部建有大规模的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它是一组向马尼拉湾突出的现代建筑群,占地12公顷,安排有多个会议厅、宴会厅、展览厅。会议中心还附设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文化中心等,经常举办大型的商品博览会和文艺活动。
3.2 城市中央商务区
如果说Binondo代表着马尼拉CBD的过去,Makati的Ayala新城则代表着马尼拉CBD的现在、Global City更代表着马尼拉CBD的未来。
Ayala新城地处马尼拉都市中心区南部,属马尼拉大区的Makati市管辖。它西边紧邻滨海的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南距阿基诺国际机场不远,包裹整个马尼拉都市中心区的半圆形EDSA轻轨地铁穿新城而过,因此地理位置非常优越,非常适合建设大型商务办公区(图13)。
Ayala新城主要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形态构成:一是沿十字交叉的两条城市主干道——Makati街(东西向)和Ayala街(南北向)密集排布的高层和超高层写字楼,行走期间,仿佛置身纽约曼哈顿;二是隐藏在这些沿街写字楼后的低层独户别墅住宅,以作为办公建筑的配套开发。阿亚拉地区原是西班牙财阀阿亚拉的私有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投入开发,经过多年不间断的扩建发展,到上世纪末基本成形,今日已成为马尼拉最大的中央商务区,成了马尼拉新兴国际化大都会的形象代表。除写字楼、住宅外,还集中了繁华的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如Greenbelt)、马尼拉第一流的宾馆饭店、无数的餐饮咖啡馆,不少外国大使馆也迁建此地(图16)。
Global City项目地处一个叫伯尼法西奥城堡(Fort Bonifacio)的地方,它西北紧邻Makati的Ayala新城,开车不到十几分钟即可,西南临近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图17)。此地原是马尼拉南郊一片地势较高的风景游赏之地,已开发建设有一些度假别墅和高尔夫球场,使用者多为Ayala新城的高级管理人员。该地最著名的景观是美军墓园,该园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美军墓地,在20多公顷的疏林草坡上密密麻麻环形排列着17206个洁白的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代表着一位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和盟军将士。十字架上刻有死者的名字、家乡、阵亡日期及年龄。所有十字架按死者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不分年龄大小及职务高低,一方面体现众生平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便于家属寻找。站在宁静秀美、庄严肃穆的墓园之中,远眺Ayala新城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确实有种洗涤心灵的感觉,深刻意识到所有幸福生活都来之不易(图18)。根据菲律宾和美国两国政府签署的协议,这个墓园被划为美国的“境外领土”。

在墓园北侧山坡之下,正在规划建设一处名为“环球城”(Global City)的大型科技产业园。该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用地203公顷,主要安置IT方面的产业,以迎接国际性的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园主体路网被规划成方格网加同心圆的模式,一方面体现“环球”(Global)的性质,另一方面也为了取得与邻近的美军墓园的呼应,象征着墓园格局的延伸和放大(图19))。Global City1997年开始规划,目前仍在开发建设中。
4 马尼拉城市规划的特点及问题
4.1 Daniel Burnham规划对马尼拉的影响
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管理菲律宾,为了体现美国文化的先进性及迎接马尼拉大规模发展建设时代的到来,美国政府聘请了本土规划师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Hudson Burnham)为马尼拉编制了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最负盛名的城市规划师之一,其主要规划作品有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和1909年的《芝加哥规划》,另外也为克利夫兰、圣弗朗西斯科、马尼拉等许多城市编制过总体规划。他最大的历史影响在于推动了“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
城市美化运动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776年美国独立后,由于房地产开发的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积淀的薄弱,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量地采用了由测量师或土木工程师绘制的棋盘状道路系统,如纽约(1811年)、旧金山(1849年)、芝加哥(1834年)等,这种系统管理上方便、经济上高效但视觉上乏味。
芝加哥的城市问题更是突出。芝加哥原是芝加哥河向东流入密歇根湖处的一片沼泽地,1833年时居民不到200人。随着联系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水路打通,特别是覆盖全美的铁路网联成之后,由于区位条件良好,这个小镇迎来了旋风般的发展。1840年芝加哥人口4470人,1890年时人口已超过100万,跃升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但由于缺乏规划控制,芝加哥城市的发展呈现恣意生长的面貌。城市布局无序,组织缺乏效率。大部分市容肮脏丑陋,烟雾污染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芝加哥河变成不忍目睹的污水沟,街道、铁路和港口都非常拥挤,尤其是肆意穿行的铁路轨道割裂了城市与湖滨地区的联系。大量涌入的新移民聚居在人口密度极高的贫民窟,环境恶劣、犯罪滋生。1871年,芝加哥发生了著名的“奥利里牛圈大火”,仅仅因为奥利里家的一头牛踢翻了油灯,便导致1.7万座紧密相连的木质房屋化为灰烬、十万居民无家可归,这迫使市政当局必须有所作为。
城市美化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16-19世纪的巴洛克城市设计如奥斯曼的巴黎改建、英国的“公园运动”等,但它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潮,则兴起于美国。1893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芝加哥举办哥伦布世界博览会。会场设在密执根湖畔,由规划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和景观建筑师奥姆斯特德负责总体规划,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师按照欧洲古典风格设计了各个展馆。宽阔的林荫大道、巨大的人工水池、华丽的古典建筑与当时芝加哥呆板划一的城市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1903年,专栏作家Mumford Robinson呼吁借哥伦布世博会的东风改善城市的形象, “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一词正式诞生。
1909年,芝加哥市政府委托丹尼尔·伯纳姆编制了《芝加哥规划》(Plan of Chicago)。伯纳姆就6个方面提出了纲领性意见:改进湖滨地区、修建外环公路、调整铁路站场、建立公交系统、开辟公园和林荫大道、建设市民文化中心和管理中心。但中心思想是强调城市格局的规则化、几何化、古典化,以恢复城市失去的视觉秩序与和谐之美,尤其注重把这种城市设计作为改善物质环境和提高社会秩序及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早在城市美化运动之前,美国一些城市中已经出现了采用拱门、喷泉、雕塑来装点城市的“城市艺术运动”,只不过城市美化运动将这种手法从零星景观推广至整个城市结构,更促进了城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伯纳姆很懂得“公众参与”,当时还专门制作了针对儿童的普及版《芝加哥规划》,使“城市美化运动”的思想深入人心。1989年,伯纳姆被美国规划协会追授“国家规划先驱奖”,可谓实至名归。
二十世纪初的马尼拉的城市问题与芝加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年的战乱已使城市破败不堪;西班牙殖民当局忙于维护自己的统治,根本无心无力进行任何公共事业建设;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也使马尼拉不堪重负。
在马尼拉规划中,伯纳姆再次延用了城市美化运动中常见的放射状林荫大道、圆形广场、大型公建、绿地公园等典型的豪斯曼形式主义的城市设计手法,为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首都绘制了一份新古典主义加巴洛克风格的城市规划蓝图(图20)。
但马尼拉规划同芝加哥规划一样存在过于形式主义的问题,忽视经济社会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再加上美国在菲律宾统治时间较短(1898-1942年),因此今日的马尼拉城市布局与伯纳姆的规划相去甚远。伯纳姆的规划基本仍旧以帕西格河为发展主轴,大部分城市在河北地区发展,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机场建在南郊,整个城市的重心都有南移的趋势。
尽管如此,伯纳姆的规划仍旧在马尼拉留下了浓墨重彩:开辟了黎刹尔广场,拓宽了罗哈斯大道,向东北方向打通了奎松大道,其终点便是今日的菲律宾大学。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城市美化运动的思想对马尼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例如,由于内河航运的衰败特别是河水的污染,帕西格河早已失去了在城市生活中曾有的重要地位,沿河两岸脏乱不堪。但如果通过有效的污染整治和景观设计,完全可以把它重新打造为有似塞纳河、泰晤士河的景观廊道,从而恢复包括Binondo在内的整个北城地区的经济与活力。
除伯纳姆外,伯纳姆的助手William Edwards Parsons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北部夏都——碧瑶的设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Parsons1872年出生于俄亥俄州阿克伦市,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98年又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工程硕士学位,后来去法国巴黎的Ecole des Beaux-Arts 深造,深受欧洲古典主义的影响。有人说他才是马尼拉规划的实际操刀者,但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4.2 西班牙文化对马尼拉城市的影响
相比于美国统治的短短40年,西班牙对菲律宾300多年的殖民统治其影响是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的。
首先受西班牙影响,菲律宾成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天主教国家,80%的国民都信奉天主教。因此在马尼拉大大小小的教堂星罗棋布,且大多采用古典形式,不少美轮美奂。如建于1599年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是菲律宾最古老的天主教堂,马尼拉大教堂则是菲律宾最重要的罗马式天主堂,教堂内珍藏有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著名艺术家捐赠的大量青铜制品、镶嵌工艺品和雕塑(图21)。
传统的天主教允许分居但禁止离婚、鼓励生育禁止堕胎,因此导致菲律宾人口增长很快,大部分家庭都有4到6个孩子。2015年,菲律宾人口已突破1亿,是世界上第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官方统计马尼拉大区人口在1000万左右,但事实情况是整个都市连绵区人口可能超过了1500万。过快的人口增长使马尼拉市政当局很难提供足够的住宅和市政服务,道路、供水、排污、空气似乎都在超负荷运行,失业情况严重,吸毒现象普遍。
西班牙人民尽管信奉传统的天主教,但普遍性格却是不拘小节、热情奔放,这种性格在菲律宾人民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遗传”,他们大多乐观、安贫乐道,城市、建筑甚至汽车也多有花里胡哨、不太认真的感觉(图22)。
这种“不认真”在城市管理中是个大问题。菲律宾有较完备的规划法律体系,如1991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Code,RA7160)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编制和实施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来决定和管理城市的增长。这种规划主要包括几方面的内容:评价土地的经济发展潜力,确定最佳使用方式和空间形态,提出促进规划实施的政策和办法,理清中央、地方和私人业主的关系。道理说得很清楚,但似乎没有人真正去执行。私搭乱建现象非常普遍,贫民窟遍地开花,与富人住宅比邻而居。大的综合开发项目大多由私人财团来组织。
二战以后菲律宾按照美国模式建立了民主政体,但“民主化”加上“不认真”却让城市管理雪上加霜。规划不精细、管理不严格是马尼拉城市建设的一大特点。过度的“民主化”还使政府的权威丧失、集中和调控资源的能力有限,导致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一方面寡头财阀享受着豪华的花园别墅,另一边穷人却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不少人甚至住进了无人管理的高级墓地,过着“人鬼同居”的生活(图23)。
菲律宾有着与东亚近邻非常不同的独特历史、人种结构和多元文化,曾经一度相当繁荣但目前又面临许多问题。马尼拉作为菲律宾的首都,自然集中体现了菲律宾的所有特征,值得当今中国学者去了解和研究,以为“一路一带”的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参考文献:
[1]Erlinda Enriquez Panlilio.The Manila we knew[M].Manila: Anvil publishing Inc, 2006.
[2]Emerlinda R. Roman.Site and symbols:up Diliman landmarks[M]. Manil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office of the chancellor, 2000.
[3]Lorelei D.C. De Viana.Three centuries of Binondo architecture,1594-1898,A social-historrical perspective[M]. Manila:University of Santa Tomas publishing house, 2001.
[4]Gerard Lico.Architecture in Philippines life[M].Manila: Philippines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2010 .
责任编辑:于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