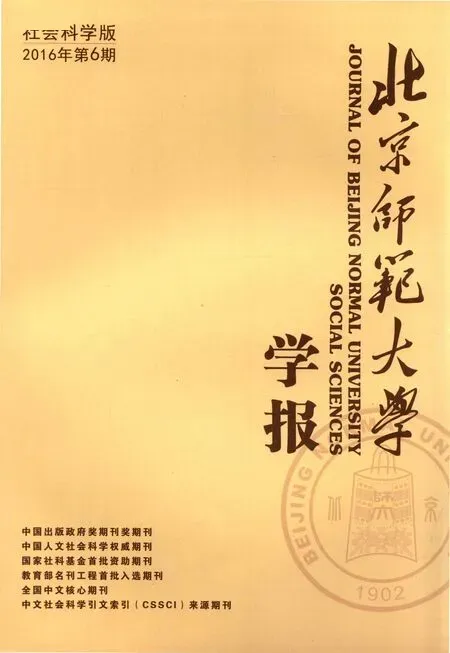《西游记》命名的来源
——兼谈《西游记》杂剧的作者
李小龙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西游记》命名的来源
——兼谈《西游记》杂剧的作者
李小龙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在《西游记》研究史上,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的存在主要与《西游记》作者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人们几乎忽略了二书相似的命名。不过,由于丘处机的西游使道教地位遽升,从而激化了佛道二教的矛盾,导致了数次佛道大辩论,并以道教的失败告终,引起当时对《道藏》的大规模禁毁,于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期未为人所知,所以虽然二名相近,但似并无因袭关系。梳理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源流,第一次以“西游记”为名的是元人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此剧孙楷第先生曾指为杨景贤之作,实不可信,仍以吴氏为当。从《西游记》杂剧现存孤本中可以看到将此剧与《西厢记》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记录,可以推测,《西游记》一名实为吴昌龄仿拟《西厢记》而成,然后,取经故事也被纳入到这个命名之中,直到最后《西游记》小说使这一命名成为取经故事的总名。
西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记杂剧;西厢记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命名,无论是人名还是书名,都希望既文约义丰,又典雅端正。同样,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命名也一直是作者们苦心经营的部分。不过,有一些书名在作品势能的衬托下显得很强大,若抛开原作,似乎也不过尔尔。《西游记》便是如此,这个命名辨识度很高,那是因为其后隐藏了大量的形象与情节以及每个人不同的阅读体验与情感记忆,也就是说,大多数读者对此名都附加了冲决罗网的渴求与人天神鬼的幻想。如果我们剔除这些“附加值”,就会发现,“西游记”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命名,不过是向西游历的记录罢了。
正因为“西游记”这个名字太普通了,也就有了较高的重复率,这些重名反过来给学界的研究带来了重重困难。比如有清三百年间就认为此书的作者是丘处机,原因便是丘处机有一部同名之作,直到清代学者从《道藏》里找出了丘处机的原著,才证明了二者并非一书(详参下文);然而,又因为天启年间《淮安府志》记录吴承恩也写过一部同名之书,从鲁迅与胡适二位先生开始,就将此书的作者再定为吴承恩,这已经成为当代人的文学常识。尽管如此,学界的质疑一直存在,关键在于《淮安府志》对其所录的《西游记》并无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此书或许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样,只是与传世小说名称偶同的游记罢了——章培恒先生即指出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收入“史部地理类”①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据此可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神魔小说《西游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简单的书名呢?其命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正是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否影响了《西游记》的命名
1218年前后,道号长春子的全真教士丘处机受成吉思汗征召,远赴西域并于1221年谒见成吉思汗,1227年丘处机去世,其弟子李志常将一路随行所作之记录整理为书,即《长春真人西游记》(1228),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使用“西游记”三字为书名的作品。
《西游记》小说的明代刊本均未明确标出作者,直到清初《西游证道书》才第一次将著作权判给丘处机,于是,清代三百年皆知此书为丘处机所作。不过,这只是就常识层面而言,其实,清代已有学者用确证否定了丘处机的著作权。乾隆五十九年(1794),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所藏《正统道藏》中发现了丘处机所作原本《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为其写跋,指出此书与小说《西游记》并非一书*钱大昕著,陈文和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按: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之被发现为乾隆六十年(1795),但据其曾孙钱庆曾所续《钱辛楣先生年谱》,知当为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发现者,参见《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一卷第39页。;几乎同时,钱大昕的朋友纪昀也用小说的方式表明此意,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指出“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太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用明制*纪昀撰,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两位清代最伟大的学者同时对这一问题做出反应,一是正面以文献来论证,一是侧面用小说来说明,总之,从学术上讲,后世大部分学者已经将此二书划清了界限。
二书虽非一书,但章回小说《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也不是全无关系。从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开始,元代的道教势力便蒸蒸日上,丘处机死后,佛道二教争斗频仍,终于酿成大的冲突,后来由朝廷出面组织二教进行大辩论(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戊午年,即1258年),据《至元辨伪录》卷四,在辩论前后有如下记载:
皇帝恐先生每心内不伏,特传圣旨再倚付将来,令子细持论。若是僧道两家有输了底,知何治罚?释曰:“西天体例:若义堕者,斩头相谢。”而道士相顾,莫敢明答。帝曰:“不须如此。但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
……
帝问张真人曰:“你心要持论否?”张真人曰:“不敢持论。”上曰:“你每常说,道士之中多有通达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如此方法,今日尽显出来。”张真人并无酬答。时逼日没,阁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虚,即依前约,脱袍去冠,一时落发。”*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2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451页。
看到这里,熟悉《西游记》的人都很有会心,因为这种僧道赌斗就发生在《西游记》“车迟国斗法”一回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大闹天宫其实也是佛道赌斗的表现*胡小伟:《从〈至元辨伪录〉到〈西游记〉》,《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也就是说,这二书间其实还是有联系的——就在详载这次影响佛道二教气数之赌斗的《至元辨伪录》中,也提及丘处机之西游*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289册,第440-441页。。不过,这种关系并非直接影响,而是佛道论辩影响及于民间,并由民间逐渐演化而为小说情节的间接影响。
其实,两者之间最可能有关系的是书名,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二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承袭关系吗?《长春真人西游记》写于1228年,自然早于章回小说《西游记》,从逻辑上看自有可能,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极小,原因正是前及之佛道大辩论。有趣的是,这场论辩恰与丘处机的西游有关,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即指出:“这场斗争表面上仍由以往佛道之争的争端——老子化胡说引起。1232年,丘处机之徒造《老子八十一化图》以颂扬和炫耀丘处机西游宣教的丰功。”*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辩论的结果一如《西游记》所艺术化的——道教惨败,《至元辨伪录》记载:
除老子《道德经》外,随路但有《道藏》说谎经文并印板,尽宜焚去。又据祈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据《道藏》经内除老子《道德经》外,俱系后人捏合不实文字,情愿尽行烧毁了,俺也干净……除《道德经》外,说谎做来底《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了者。今差诸路释教泉总统中书省、客省使都鲁前去,圣旨到日,不问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军民、人匠、鹰房、打捕诸色人等,应有收藏道家一切经文,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添气力用心拘刷,见数分付与差去官眼同焚毁。……自宣谕已后,如有随处隐匿道家一切说谎捏合、毁释教、偷窃佛言、窥图财利、诱说妻女如此、诳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诸般经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气力拘刷,与隐藏之人一体要罪。*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289册第437-438页。
此次禁毁规模极大,官府也很卖力,连道家为主持刊行《道藏》的宋德方立碑都要删去相关表述,陈垣先生说:“今终南重阳宫有王利用撰《披云道人道行碑》……内容本《祖庭内传》,而凡涉刻经事,均删略,或以他词易之,盖撰于焚毁道经之后,有所讳也。”正因如此,其焚经的成果颇为“辉煌”,陈垣先生指出:“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垣全集》,第18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21,422页。有学者统计云,“相当于半部《正统道藏》被烧绝了”*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可以想象,在官府与僧人如此严厉的禁毁之下,这部记录丘处机西游、引发佛道争端的导火索的书籍《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命运——在最初的禁毁中它便难逃劫难,在13世纪中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很难重回人们的视线,直到明初开始纂修的《正统道藏》,才又将此书搜罗并收入。不过,这次的收入也仅仅是文献意义上的收录,因为就传播意义而言,此书的收入并未产生实际的意义,可以说,从最初的禁毁开始,近六个世纪中,无人知晓它的存在,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5)钱大昕将其抄出,它才重见天日。
当然,从某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在钱氏之前,也偶有人看到过《道藏》中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如查慎行(1650—1727),他去世之次年,钱大昕才出生,早于钱一辈人。查氏《初发江干》诗有“江路羊肠迴,江风羊角合”之句,其自注云“丘长春《西游记》‘风初起如羊角者千百,须臾合为一风’,可证庄子‘羊角而上’语”,《舶趠风歌》诗亦有相似之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3,1270页。。另外,查氏苏轼诗注中亦及此一则,更证实了这一点,其《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团团羊角转空岩”句下注云:“《道藏》载丘处机《西游记》云‘风初起如羊角者数十,须臾合为一风’。”*见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此注所引之文字正出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知他确实看过此书。但遍检文献,亦仅此一例,可知此书从传播意义来看,真正流布人间,仍当自钱大昕抄书始。
因此,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看,《西游记》的作者(无论是明朝后期最终的整理写定者还是此前那些为《西游记》的最后定型立下功劳的次要作者*关于“次要作者”的概念,请参见郭英德师《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2期。)都不太可能看到这部著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需要讨论,就是《西游记》的作者虽未看过此书,但曾经听说过这样一部已经失传的道教著作,那么也有可能袭用其名。但这种可能一方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无法讨论;另一方面从情理上看也不能成立,因为使全真教“趋于极盛的关键,是教首丘处机西游宣教的活动”*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523页。,也就是说,丘处机的西游是道教极盛的关键,“西游记”三字对于道教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而细读《西游记》小说的文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道教的揶揄——《西游记》是一个揶揄一切的文本,但对于儒生、佛教的揶揄都是偶发的,或者说是游戏心态的不自觉流露,而对道教却有意的,甚至可以说是精心设计的,从中可以感觉到《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在明代道教复炽的环境下,一种对道教深深的反感。那么,他以记录道教最辉煌时代的书名来命名他那嘲笑道教作品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当然,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测他故意用这样的名字来制造反讽的特殊效果,但这种推测或许离情理更远,而且我们也更无证据来支持它。
二、小说《西游记》与杂剧《西游记》——兼论杂剧的作者
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小说《西游记》与其他世代累积型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都有最初的历史触发、民间传说的叠加、说书艺人的敷演、以及元杂剧的开拓。就元杂剧而言,正如另两部作品拥有大量的“三国戏”与“水浒戏”一样,小说《西游记》的前源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西游戏”,有趣的是,“西游戏”中有一部集成性的杂剧,其命名竟与小说《西游记》完全相同。那么,作为小说《西游记》成书渊源中的一个环节,正如《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或失传的《水浒传词话》对《水浒传》的影响一样*关于《水浒传词话》之讨论,参见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由明新安刊大滌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一文,《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7-101页。,这部杂剧对小说《西游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或许,最明显的便是命名的沿袭了。
因此,要想探究小说《西游记》命名的渊源,则先需讨论杂剧《西游记》命名的来源。不过,由于杂剧《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在学界尚有争议,对作者的不同认定会导致此剧创作时间在小说《西游记》产生前后的差异,因此,我们需先探讨杂剧《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此六本二十四折的《西游记》杂剧虽曾有载录,然早已佚失。上世纪初,日本学者盐谷温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发现了此万历甲寅(四十二年,1614)所刊孤本,其书名为“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署有“元吴昌龄撰”的字样,盐谷温氏于1928年将此书以日本东京斯文会名义排印出版(卷首附二页正文书影,并附全书插图),后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依此排印本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至此,此书方为世人所见。另外,明人孟称舜编选的戏曲选集《柳枝集》中曾收入此作的第四本“二郎收猪八戒”,亦题为“元吴昌龄著”*参《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所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1939年,孙楷第先生于《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发表文章《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孙楷第:《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4-265页。,其副标题就叫“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他认定此剧为元末明初人杨景贤之作,最主要的证据是据天一阁《录鬼簿》所录等资料,知吴氏有《西天取经》一剧,其剧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经”,而今本《西游记》杂剧中未见“老回回东楼叫佛”之事,则吴氏之《西天取经》并非今之《西游记》;此外,《录鬼簿续编》杨景贤名下有《西游记》一目*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05页。;另外,又据“传是楼旧藏的一部抄本《词谑》,其第二篇引杨景夏的《玄奘取经》第四出,文与今本《西游记》第四出同”,从而将此剧作者定为杨景贤。孙楷第先生此说一出,至今为学界定论,各种著作都径引为“杨景贤《西游记》”,鲜有持不同意见者*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较为慎重,仍以吴作收入,参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405-500页。此外,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一文并不同意杨景贤说,但也不承认吴昌龄说;田同旭《〈西游记〉杂剧作者应归吴昌龄》(《淮海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算是第一篇明确提出《西游记》杂剧作者当为吴昌龄的论文,亦颇详实,然其文多从社会文化条件及作者艺术才能等无法定性之角度论证,故无法论定,另外,也有条件地承认了杨景贤的著作权,只是将其标为“俗本”。。实际上这一推论或受当时盛行之疑古思潮影响,其推理逻辑漏洞颇多,尚不足以定谳。
一方面,从杨景贤的角度看,并无坚实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著作权。暂且不论《词谑》所记“杨景夏”是否即“杨景贤”、《玄奘取经》是否即《西游记》等问题,甚至也可以暂时搁置我们对孙楷第先生所见抄本的疑惑——其恰比传世刊本多出此节且现已失传,就是《词谑》一书本身也有问题。《词谑》分四个部分,即词谑、词套、词乐、词尾,四部分并非一整体,孙楷第先生所云《玄奘取经》第四出即收于《词套》,顾随先生评《词套》云:“《词套》首列马东篱之‘双调夜行船’,张小山之‘南吕一枝花’。其后所举各套,亦皆信手拈来,不合惯例。余颇疑作者当时有意选刻一部散曲,此则为其蓝本。否则后人摘录作者读曲之评语而附之以曲词耳。是以文辞时有颠倒错植之处……《词套》卷中所收诸套,既多修改,殊难据以校勘他书。”*顾随:《读〈词谑〉》,《顾随全集·著述卷》,第2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6页。其选词之修改作者自己也曾透露,孙楷第先生曾引其“前后套词,无有不经改窜”之语,但这还只是“改窜”,其实还有更大胆的“改易”,如第二十七套云:“《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第一出,不知何人作,大势亦中选,止有【那吒令】不成词。摘取《玉箫女》套中一咏易之。”*(明)李开先:《词谑》,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2、1617页。即此可知其书之随意,在这种改动之下,其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便是个疑问。
另一方面,再从吴昌龄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孙楷第先生推理中更多可议之处。
其一,孙楷第先生说在天一阁抄本《录鬼簿》上卷吴昌龄《西天取经》剧下,注了两句题目正名“老回回东楼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经”,所以孙先生说:“吴昌龄的《西天取经》有回回叫佛事;没有回回叫佛事的,便不是吴昌龄曲。现在所称的吴昌龄《西游记》……竟没有一处类似这件事的地方。这不令人恍然大悟么?”这段推理似可商榷,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吴昌龄在有关取经题材上只写过一部杂剧,事实上,吴氏很喜欢神话题材,他曾写过《那吒太子眼睛记》与《鬼子母揭钵记》*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如果既写了《西天取经》,又写了《西游记》呢?
其二,孙先生举出明天启四年止云居士所编《万壑清音》,其书收《西游记》四曲,“其中两折是今本《西游记》所有的(《擒贼雪仇》在今本卷一,今本题第四出,篇名四字全同,《收服行者》即今本卷三第十出之《收孙演咒》),一折是今本《西游记》没有的;一折是与今本《西游记》完全不同的”。而“今本《西游记》没有的这一折便是《回回迎僧》;演老回回东楼阁上叫佛,下楼迎接唐僧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孙先生的判断是:“无疑的,这是吴昌龄《西天取经》杂剧的一折。不过,这位编《万壑清音》的止云居士太糊涂了。他把来源不同的四折北曲放在一个《西游记》题目之下。”在上一条中,孙先生故意把《西天取经》和《西游记》不加分辨地当成一本书,从而得出没有回回叫佛事的便不是吴昌龄所作的结论;这条材料表明《西游记》中曾经包含回回叫佛事,但因为有先入之见,孙先生又努力把二书分开,说回回叫佛事“无疑的,这是吴昌龄《西天取经》杂剧的一折”,不应该属于《西游记》,但《万壑清音》这条证据无法绕过,孙先生只好说“编《万壑清音》的止云居士太糊涂了”。其实,止云居士是否“糊涂”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探讨。《万壑清音》共选剧三十七种,其中流传于今的有二十九种,有学者进行对比,认为“与现存的版本相比勘,《万壑清音》所选收的这二十九种剧在曲文与情节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卓明星:《〈万壑清音〉所辑佚曲论析》,《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但还未发现这样乱点鸳鸯谱的例子。
事实上,如果不存先入为主之见,我们会发现,《万壑清音》所选恰成为天一阁本所录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与今本《西游记》之间最佳的逻辑环节。也就是说,今本《西游记》与天一阁本《录鬼簿》所录之矛盾恰好因此书提供的中间证据而得以解决,此杂剧原本当有“老回回东楼叫佛”的情节,但今本《西游记》已经后人改动,所以缺少此一情节,而《万壑清音》恰恰保存了这一段。而且,我们说“今本《西游记》已经后人改动”也可再由《万壑清音》得到证明:那就是除以上所提及的三折外的一折,孙先生说此折“其事为今本《西游记》所有而词白完全不同。便是《诸侯饯别》一折”。则可知止云居士所见《西游记》杂剧《诸侯饯别》一折虽然在今本《西游记》中得到了保留,但已经改动。
关于“回回迎僧”一折是否今本《西游记》中一折,还有一旁证。吴昌龄确实很喜欢写到“回回”(他还有《老回回探狐洞》、《浪子回回赏黄花》二剧*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第139、141页。),今本《西游记》中也有两次提及,一是第六折《村姑演说》:“见几个回回,舞着面旌旗,阿剌剌口里不知道甚的。”一是第十一折《行者除妖》“(行者云)你姓甚么?(沙和尚云)我姓沙。(行者云)我认得你,你是回回人河里沙。”*吴昌龄:《西游记》,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448页。与此可作对比的是,细检元杂剧,提及“回回”者,仅《酷寒亭》、《玉壶春》、《衣袄车》和《延安府》四种各一次。而吴昌龄之所以喜欢写回回,则与他曾经"西京出屯"的生活经历有关,有学者便指出"比如他写了几部与回回有关的杂剧,可以肯定是其前期生活的曲折反映"(参下文引张继红、郭建平先生文)。
最关键的是,吴昌龄作《西游记》除上所论外,还有坚实的文献支持,即今本《西游记》杂剧前有勾吴蕴空居士所撰《总论》与孟称舜的引述以及其前作者的题署。另外,书目之著录亦多可援证,如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在其《也是园书目》中便记录了“吴昌龄西游记四卷”*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按: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原本引此书误为“王昌龄《西游记》”,前书汇编时将“王”径改为“吴”;另,钱氏原文为“四卷一本”,且下注“抄”字。参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41页。;曹寅《楝亭书目》的记载更为详细,“西游记,抄本,元吴昌龄著六卷,一函二册”*(清)曹寅:《楝亭书目》,引自《丛书集成新编》,第6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40页。按:前引焦循《剧说》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曹楝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龄,比于临川之学董解元也。’”既知焦循当见吴氏《西游记》,并与小说相对比,又可知曹寅不但藏有六本之《西游记》,而且对吴昌龄氏甚为服膺。;明人臧懋循《元曲选》与清代梁廷枬《曲话》均载吴昌龄“《西天取经》六本”*(清)梁廷枬:《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页。 ⑥ 洛地《〈录鬼簿〉的分组、排列及元曲作家的“分期”》,《戏剧艺术》,2004年第3期。:这几处记载指向的都是长篇的《西游记》,绝非孙先生所力主的四折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那么,在这两种书目中,都将作者归于吴昌龄,则一定与他们目验曾经存在的原本有关,也就是说,历史上存在过的钱曾藏本、曹寅藏本以及现存万历所刊孤本均署为吴昌龄。这些都是很难绕过的证据。
总之,古典文献的考论常有文献不足征之困。在文献记载出现非此即彼的矛盾时,又没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判断对立文献各自的可靠性与成立的概率。就《西游记》作者问题来看,证成杨景贤与证成吴昌龄的文献可靠性与概率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如果认定杂剧《西游记》作者是吴昌龄,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杂剧命名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关吗?吴昌龄生平虽不详,但据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录为“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中,可知其为元代前期人。《录鬼簿》《说集》本在其前隔一人录有姚守中,此人为姚燧(1238—1313)之侄,一般来说,姚守中应当比姚遂小二十岁左右,而吴昌龄则与姚守中相近。这样便可推测吴当生于1258年前后,也就是说,吴氏恰当出生于佛道戊午(1258)大辩论前后。当然,洛地先生曾推测其书排序“是按作品之多寡排列的”⑥,但这种顺序只合于曹楝亭本,与更近原本的明《说集》本并不相侔。细察后者,虽然钟嗣成对所录诸人也并不完全熟悉,所以排列并不是全都精确,但大体来说仍是以年代为序的。关于此还可找到参证,张继红、郭建平二位先生曾将贾仲明《凌波仙》中“西京出屯俊英杰”一句与《元史》记载相印证,指出他当于至元二十九年(1293)“于燕只哥赤斤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因此推断“他的生年应在元朝建国(1260)之初,或稍早于建元”*张继红、郭建平:《吴昌龄生平考》,《中华戏曲》,1996年第2期。,这与前论正相吻合。所以,与前文考辨《西游记》小说作者无法看到《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样,吴昌龄也同样很难看到这本书,甚至比前者更难,原因就在于吴昌龄出生前后,《道藏》便开始被严厉禁毁,在吴氏开始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时,面对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有一个有关道书禁毁之后的空白。
当然,以上只是证明吴昌龄很可能看不到《长春真人西游记》,但并不能确定。不过,这一点能否确定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根据杂剧《西游记》存世版本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吴氏此剧的命名其实有更确切的来源——并非《长春真人西游记》,而是《西厢记》。
三、《西游记》的命名与《西厢记》
一部小说的命名,最应从故事源流入手。所以,我们需要梳理唐僧取经故事的历史演变。
唐僧取经故事最早来自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取经,玄奘归国后,向弟子辩机口述了一部著作,即《大唐西域记》,此书算是《西游记》发生的根苗。前者的主线是对异方地理的介绍,所以“西”与“记”之间的字是“域”,而小说的重点则在于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历程,故改用“游”字。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西”与“记”二字却相同,这或许对小说《西游记》的最终定名产生某种影响。
接下来,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乃师写了一部传记,叫《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书以人为主,故事性强了,也多有神异色彩,应该说从故事上更接近《西游记》,但从命名上却与后来的《西游记》更远了。此后,玄奘取经的故事进一步神异化,并在民间传说与文学上取得新的成果,就是一部平话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此书已经是具体而微的《西游记》,但命名却更遥远了。就正在此时,杂剧作为元代新流行的文学样式在三国故事、水浒故事与取经故事三大领域都产生了不少作品,在艺术的打磨上为这后来的《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完成做最后冲刺,吴昌龄的杂剧《西游记》也应运而生,并且,他为作品选定的名字也成为取经故事最后的定名。
不过,如果仔细考量取经故事的演变与命名的历程,会让我们怀疑,取经故事最终定名为“西游记”或许并非最佳选择。
事实上,这个故事最早的核心是玄奘,所以,起始阶段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名正得其实;此后,相关故事逐渐神异化,玄奘的地位下降,故事的核心变成了取经,于是平话体小说命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命名者希望平衡这两个核心,所以把上个阶段的核心词“三藏”与目下的核心词“取经”同时放入书名之中,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三藏”其实位于修饰位置,也就是说,已经不重要了,从学界称引此书时多用“取经诗话”的简称便可知道;再到元杂剧,如上所引,便有吴昌龄的《西天取经》,连“三藏”二字也不见了(有人也引为《唐三藏西天取经》,那是因为《录鬼簿》录其题目正名的下句正是此七字,按照惯例下句会是此剧正名,但称简名会将前数字省略*参见李小龙:《中国古代小说回目研究》,第2章第2节,《元杂剧题目正名的移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101页。)。这其实正是取经故事数百年流传史自动选择命名的结果。但吴昌龄此剧却突然把合理的“取经”二字从命名中删去,而用了此前从未见过的“西游记”为名,其实,正如本文开篇时所说,“西游记”三字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张力——《石头记》三字也不如《红楼梦》有张力,但《石头记》抓住了小说的核心要素,所以并不是一个不称职的命名,而《西游记》则并非如此,这个名字并没有抓住小说的核心,“西游”是什么?向西的游历吗?这完全隐没了唐僧取经的宏愿与师徒四人的艰辛,也并没有展示出取经历程之险恶与光怪陆离的妖魔世界。事实上,现存《西游记》百回本之前的引首诗均提到一个书名,即“西游释厄传”,加“释厄”二字可以看出次要作者对过于平淡的“西游记”三字的增饰。
那吴昌龄为什么会将这样一个集取经故事之大成的杂剧定名为“西游记”呢?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对当时的经典《西厢记》的仿拟。如果有一道填空题,“西□记”,让大家在方框处填写一字,使之成为一部文学著作的名字,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填“游”,但也有理由相信,会有一部分人填“厢”(当然,也有可能填“域”)。相对于《西游记》,《西厢记》其实也是大名鼎鼎,这两部书大家都很熟悉,不过人们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名字竟如孪生兄弟一样。或许会有人说,《西游记》和《西厢记》确实相似,但恐怕只是偶尔撞衫,未必有承袭关系吧?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今存《西游记》杂剧的孤本前有勾吴蕴空居士所撰《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总论》云:“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先成,昌龄见之,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幽艳恢奇,该博玄隽,固非坎井之蛙所能揆测也。其于《西厢记》,允称鲁卫。”*《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柳枝集》的编者孟称舜在所收《二郎收猪八戒》上有自作之评,第一则亦与前引之语相类*《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孟氏之说或即来源于蕴空居士——此人虽晚,但既然能看到“抄录秘本”,则其语或有出处。
首先,“西厢记”与“西游记”的名字非常相似,仅一字之差,想与《西厢记》对垒,从命名上看,《西游记》自是相当适当的选择。
其次,现存元杂剧中,篇幅如此曼长者仅此二剧(《西厢记》二十折,《西游记》二十四折),《西厢记》的体制在当时已是惊世骇俗的特例,没想到还会有人继之,正如万历本前弥伽弟子《〈西游记〉小引》所云“曲之盛于胡元,固矣。自西厢而外,长套者绝少,是本乃与之颉颃”;蕴空居士之总论也说:“北调仅《西厢》二十折,余俱四折而止,且事实有极冷淡者,结撰有极疏漏者。独是编二十四折,富有才情,最堪吟咀。”可见二本在体制上或有渊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面对勾吴蕴空居士与孟称舜的记述,若无确切反证,自不可简单否定。
当然,也可能有学者怀疑今本《西游记》杂剧为万历末年伪造。但一是这种怀疑并无文献佐证;二是此剧多有元人痕迹(孟称舜在选本中两次指出此点);三是在此书问世半个世纪前,李开先就已经引录了其中一出,据孙楷第先生的校注可知与今本“文字微有不同”而已,则其必非万历末伪造甚明。至于“此本之前为何未见流传与载录”之类质疑,稍悉文献流传历史都会知道,这并非罕见的事例。
对于吴昌龄《西游记》与王实甫《西厢记》的关系,也曾有学者提及,如顾随先生便说:“吴氏拟为西厢记之说,未见于他籍,不知确否。《录鬼簿》吴与王实甫同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属于元代第一期之作剧家,则其生世,自当不远。见王作西厢而别作西游以敌之之说,亦或可信。然吴氏之作法实与王氏大异。夫既曰‘唐三藏西天取经’,则必以唐三藏或一行五众为中心人物矣。然六本二十四折中,无一折为五众所唱之曲,行者间或歌一二章,又皆科诨之词也。彼其见王西厢崔张所唱者不佳,而红娘所唱者独妙,遂故使所有曲词尽出旁观者之口欤?”又云“吴氏苟为《西厢记》,虽未必即驾凌王氏,亦岂遽多让哉”*顾随:《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西厢记〉与〈西游记〉》,《顾随全集·著述卷》第二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2页。。虽然顾随先生并未确定,但也承认有这种可能,且从杂剧《西游记》“设想既奇,曲文尤恢诡可喜”的部分认为吴氏亦有此能力。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个锦上添花的证据,那便是徐大军先生《后西厢时代的影响焦虑》一文指出的,杂剧《西游记》第十三出《妖猪幻惑》*吴昌龄:《西游记》,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3册,第456-459页。“嫁接了《西厢记》经典的崔张月夜佳期一段,其中有递柬——裴小姐让丫环梅香寄书信与朱郎,今夜来赴佳期;有月夜佳期——猪八戒幻化的朱郎赴裴小姐的月夜佳期;而裴小姐等待朱郎的花园里,有太湖石,有朱郎可以跳过的短墙头,有裴小姐安排下的香桌儿,而她就等着月儿上时烧夜香等待着朱郎来赴约”*徐大军:《后西厢时代的影响焦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辑,2015年内部印刷(未出版),第532-534页。。这一处对《西厢记》经典情节的嫁接移用恰为吴昌龄受《西厢记》影响的确证,辅以前文的各种线索,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影响肯定存在,而且也很可能不只存在于文本层面,同时也体现在其命名上。从这个角度看,吴昌龄《西游记》实际上是最早的《西厢记》影响焦虑下的产物。
《西游记》杂剧并未如作者希望的那样与《西厢记》并驾齐驱,但这个名字却从某种程度上为作者达成了目的,因为有了那部完全袭用此名的章回小说,它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力都绝不逊色于《西厢记》,出色地为吴昌龄打胜了对抗《西厢记》的反击战,甚至又成为新的典范,影响了后来文本的命名:再看一下前文给出的填空题,如果作答者是一位对古代小说比较熟悉的人,那么他也许会犹豫是不是要填上一个“洋”字,因为《西洋记》是在《西游记》出版不久问世的另一部著名神魔小说,《西洋记》之袭名《西游记》小说,正如《西游记》杂剧之袭名《西厢记》,一望即知。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小说《西游记》得名的历程。
最早自然是玄奘本人的《大唐西域记》,或许最早提供了“西□记”命名的原型。其故事流传过程中一直以“唐三藏”、“取经”或“西天取经”之类关键词为名。此外,金章宗时期(1190—1208)的董解元依元稹《莺莺传》及此后的说唱作品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约一个世纪后,王实甫又据此创作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受欢迎的名作《西厢记》。同时稍后,吴昌龄欲与王实甫争雄,另出机杼,选择民间流传极广的取经故事为本,依“西厢记”之名为此类故事取名《西游记》,这一仿拟《西厢记》的简单命名却迅速成为取经故事的总称,并流传开来,而当时尚未敷演为长篇巨著的说经类小说作品也迅速采用了这一名称。这一点可以从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的记录得到证明,其中有一段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1-292页。
关于《朴通事谚解》的时代,朱德熙先生《“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一文据书中所记步虚和尚说法事考定,认为其当作于至正六年(1346)以后、元亡(1368)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朱德熙:《“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也就是说,吴昌龄的杂剧《西游记》约产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在这半个世纪中,小说已经迅速接受了这个新的命名,还产生了相当稳定的说经作品,从《朴通事谚解》可以知道其作品相当受欢迎——而且,根据这一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作品在最初是把取经故事原来流行的命名与新的命名组接在一起的,所以在上引对话中,对话者先提了其全名为《唐三藏西游记》,这个命名可以看作是《唐三藏西天取经》与《西游记》的过渡形态,而中国古代的小说与戏曲都有较长的繁名与较短的简称,这个说经作品的简称正如对话中显示的,便是《西游记》。这或许是《永乐大典》中所引《西游记》平话的前身抑或就是它自己。此后,取经故事便在“西游记”的框架下继续丰满、演化,直到二百余年后,产生了集大成的百回本《西游记》,至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伟绩与孙悟空上天入地的神通便都有了众所周知的新名称,“西游记”三个字也从平淡无奇的名目变成了容括中国文学奇幻想像力的渊薮。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The Origin of the NameXIYOUJI(JourneytotheWest)
LI Xiao-l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XIYOUJI(JourneytotheWest), QIU Chu-ji’sChangchunZhenrenXiyouji(ZhangchunZhenren’sTraveltotheWest)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WU Cheng-en’sXIYOUJI; in fact, people were almost ignorant of the similar names of the two books. QIU’s story quickly promoted the status of the Taoism, which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caused several times of mass debates. These debates ended in the failure of Tao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classical Buddhist works in large scale. Under that condition, QIU’s work remained unknown for a long time. That is, the two books bear similar names, but have no inheritance relation at all. In fact, the name ofXIYOUJI(JourneytotheWest) should be coined by WU Chang-ling who imitated the love story ofXIXIANGJI(TheRomanceofWestChamber).
XIYOUJI(JourneytotheWest);CHANGCHUNZHENRENXIYOUJI(ChangchunZhenren’sTraveltotheWest);XIYOUJIPoeticDrama;XIXIANGJI(TheRomanceofWestChamber)
2016-02-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古典小说命名方式与叙事世界建构之关系研究”(10CZW041) 。
I109
A
1002-0209(2016)06-006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