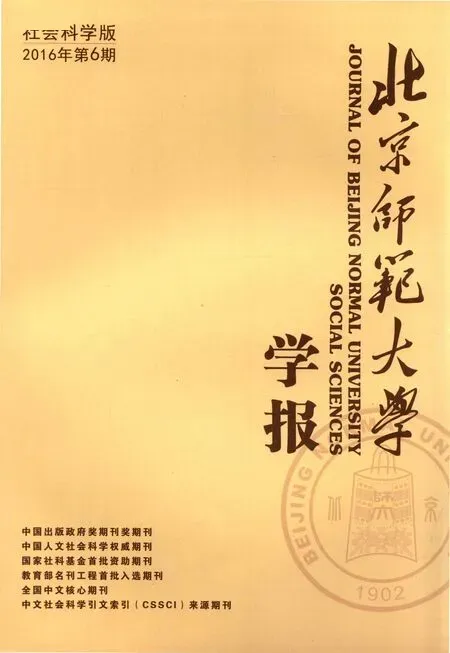拒斥·卫道·好辩
——论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高华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拒斥·卫道·好辩
——论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高华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
孟子对先秦诸子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的“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而其批评的锋芒还涉及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所谓“兵家”。孟子对于道家杨朱学派的批评虽抓住了杨朱思想中最重要的主张,且切中了其可能产生的流弊,但未能“同情”地理解杨朱学说的立论目的和宗旨,存在强人从己的偏颇。孟子对墨家“兼爱”、“节葬”、“非命”等观点的批评,既可见出其儒家思想与墨家的歧异和对立,也反映出其明显的独断论倾向。而孟子对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以及“兵家”的批评,也并非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评判,而多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他。孟子先秦诸子批评的特点,既与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立场有关,同时也是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情形使然。
孟子;先秦诸子;学术批评
孟子,名轲,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是先秦儒家除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家,历来被称为“亚圣”。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先秦诸子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他以天下为己任,以儒家孔子为圣人而师之,于其他诸子学派则“距”而“辟”之。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之三《孟子》一章“极论为政用先王之道”时,即云孟子为“大儒”而于诸子百家皆有所“距”。其言曰:
……孟子“距杨、墨”。杨朱,老子弟子。距杨朱,即距道家矣。“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为孙膑、吴起、张仪、李悝、商鞅之类。)则兵家,纵横家、农家,皆距之矣。“省刑罚”,可以距法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可以距名家。‘天时不如地利’,可以距阴阳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杂家。“齐东野人之语,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说家。此孟子所以为大儒也。①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杨志刚校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
这就是说,孟子对先秦诸子所“距”所“辟”的,不仅是人们以往所说的杨、墨二家。他和先秦诸子百家,实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其学术批评的锋芒,几乎涉及到当时诸子的各“家”各“派”。尽管历代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成果似乎不计其数,但对孟子与先秦诸子学派的关系却少有系统和深入的考察。而这也必将影响到对孟子思想的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准备就孟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做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孟子对杨朱思想的抨击与误解
《孟子》一书中批评先秦诸子最为激烈的,是所谓“辟杨、墨”。而“杨、墨”中的“杨”,即是杨朱。《孟子》书中或称“杨朱”,或简称“杨”。《孟子·滕文公下》曰:
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在这里先称“杨朱”,既而称“杨”,最后又曰“杨氏”。《孟子》书中有时也称杨朱为“杨子”。《孟子·尽心上》载: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孟子此处所谓“杨子”,东汉赵岐注曰:“杨子,杨朱也。为我,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为也。”赵氏这条注释,说明孟子此处所谓“杨子”,即是《滕文公下》所谓“杨”或“杨朱”。而赵氏之所以要注明此“杨子”即是“杨朱”,殆因为“子”在上古乃尊称,通常表示晚辈对师长辈的尊敬;孟子在《滕文公下》篇既直称“杨朱”之名,且詈之为“无父无君”之“禽兽”,而此处敬称曰“子”(先生),前倨而后恭,令人不解,故赵氏特加注解。孟子更多的乃直呼杨朱为“杨”。《孟子·尽心下》载: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由以上诸篇中孟子的言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杨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孟子影响最大的一位诸子学者。孟子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学者“逃墨必归杨,逃杨必归儒”即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孟子如此重点批判的当时影响至巨的杨朱,在《史记》的“列传”中既无其人,在刘《略》班《志》中亦未著录其书,好像先秦并无此人似的。今本《列子》书中虽有《杨朱》一篇,但学术界一致认定这一篇非先秦的原物,而是东晋张湛所作的“伪书”。这就不仅与《孟子》书中的记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且也为后人研究孟子与先秦诸子的关系,乃至研究孟子思想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对杨朱其人其学完全没有探讨的可能了,根据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在先秦两汉的载籍里,除了我们上面所引《孟子》中的《滕文公下》篇和《尽心》上、下篇言及杨朱其人和他的学术主张外,《庄子》一书中的《应帝王》《骈拇》《胠箧》《天地》《徐无鬼》《山木》《寓言》诸篇,《荀子》书中的《王霸》,《吕氏春秋》书中的《不一》,《淮南子》中的《淑真训》《氾论训》和《说林训》,以及枚乘的《七发》,杨雄的《羽猎赋》,也都提到杨朱其人,甚或有关于杨朱事迹的零星记载。其中《庄子》一书中的《应帝王》《山木》《寓言》又称杨朱为“阳子居”,《吕氏春秋·不二》篇称杨朱曰“阳生”,而杨雄《羽猎赋》中“杨朱”作“阳朱”。前人的旧注及考证成果已经证明,这些所谓“阳子居”、“阳生”、“阳子”或“阳朱”,其实即是杨朱:“就是《庄子·山木》篇之阳子,《韩(非)子·说林上篇》已作杨子,此阳、杨二字混用不分之证一。《孟子·尽心》篇之杨朱,《吕览·不二篇》作阳生,高诱注引《孟子》亦作阳子,或易《孟子》原文,或高氏所见《孟子》本不同,均无不可,此阳、杨二字混用不分之证二。古书多数作杨朱,而杨子云《羽猎赋》忽作阳朱,尤为奇特,此阳、杨二字混用不分之证三。”*顾实:《杨朱哲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页。
杨朱在先秦两汉载籍中或作“阳子”、“阳生”、“阳子朱”、“阳朱”等,则其人其事其学说亦可言其大略。
根据《庄子·应帝王》篇的记载,杨朱曾师事老子,为老子弟子。《庄子·应帝王》篇曰:
阳子居(成玄英疏:“姓阳,名朱,字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徹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寓言》篇又有“阳子居南之沛”、受教于老子的记载: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蹵然变容曰:“敬闻命矣!”
《列子·黄帝》篇亦有相同记载。大概是《列子》书采用了《庄子·寓言》中的这则故事。只是张湛注《列子·黄帝》篇的这段文字时却说:杨朱在《庄子》书中“云杨子居,子居或杨朱之字,又不与老子同时。此寓言也。”否认杨朱为老子弟子。而《荀子·王霸》“杨朱哭衢涂”,唐杨倞注云:“杨朱,战国时人,后于墨子,与墨子弟子禽滑釐辩论。其说在爱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子相反。”
我认为,阳子居既然即是杨朱,《孟子》中又屡称杨(朱)、墨(翟),则杨朱、老子皆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非寓言人物,这是可以肯定的。且《孟子》书言杨朱,从来都放在墨翟之前,称“杨(朱)墨(翟)”,而未言“墨(翟)、杨(朱)”,则可知杨朱生活的年代当不晚于墨翟,而应稍早于墨翟。墨翟生活的年代,《史记·孟荀列传》曰:“或曰并孔时,或曰在其后。”说明墨翟虽与孔子年辈稍晚,但曾“并时”生活过很长时间。清人孙诒让著《墨子年表》,定墨翟生卒年为周贞定王元年(前468)至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钱穆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定为周敬王四十年(前480)至周定王二十二年(前390)之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94页。。但依我看来,如果说以墨子“并孔子时”为太早的话,那么墨翟生年定为孔子去世之时,或未及见孔子之时,则明显失之太晚。《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尽管论者以之为“非谓墨者亲受业于孔子也”之说不无道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04页。。但由墨子止楚攻宋,当楚惠王宋景公之世(宋景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80年而论,“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汪中:《墨子序》,汪中著,李金松校笺:《述学校笺》,(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5页。案:笔者认为,《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记楚惠王灭陈后欲攻宋之事,即《墨子·公输》所记墨子止楚攻宋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此事于宋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九年,公元前480年),为孔子卒前一年。此时墨子止楚攻宋,则已非少年,至少应在“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后。——年龄或已在40岁之上,而固当及见孔子。参见拙作:《“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文史哲》,2013年第5期。。墨子受学于孔子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在年代学上如此。墨子止楚攻宋的时间在孔子去世前一年,以此时墨子四十岁计,则其生卒年代不当晚于公元前520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平王九年,宋元王十二年),略与孔子弟子颜回(前521)、宰我(前520)相当。《史记》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庄子》书中又在记杨朱受教于老子之时,并载孔子见老聃之事,则杨朱年岁当略早于墨翟,与孔子相当,并与孔子一同受教于老子也。——这也可以说是《孟子》以往先秦两汉载籍皆称“杨、墨”,而从未称“墨、杨”的原因。
关于杨朱的学术思想,孟子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又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不二》篇曰:“阳生贵己。”仿佛杨朱的“为我”、“贵己”之说,乃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学说。其实,杨朱“为我”、“贵己”学说之根本宗旨,并不能等同于后世所谓“自私自利”,而只是为了特别强调“养生”而“重生”,为了“全性保真”。《韩非子·显学》篇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显然是针对杨朱的主张而言的,但韩非子称持此思想主张之人,为“轻物重生之士”。这也就说明,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或“贵己”之说之根本宗旨,只是特别看重自己的生命、而将天下看得很轻的“轻物重生”,只是一种很特别的“养生”理论。故《淮南子·氾论训》将孟子所述杨朱的这一思想观点表述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诱注:“全性保真,谓拔毛以利天下弗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案:“谓拔骭毛以利天下弗为也”,原作“谓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为也。”顾实谓“不拔”之“不这当衍”。此从其说删“不”字。参见顾实:《杨朱哲学》,北京: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4页。明确将孟子所非杨朱的“为我”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说,界定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而与所谓“自私自利”并无关系。
当然,由于整个先秦诸子学“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都在阐述“内圣外王之道”,而“皆务于为治也”(《淮南子·氾论训》)。所以,杨朱(阳子居)创立“为我”或“贵己”学说的根本目的,实际也只是为了通过“全性保真”而修己、修身,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故杨朱(阳子居)问学于老聃时,开口即问“明王之治”:“今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徹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而《列子·杨朱》篇杨朱自述其“为我”、“贵己”为“治内”也,并认为“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因为“拔一毫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贵己”之说,其实是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的“为我”、“贵己”之学,既是“全性保真”的“重生”、“养生”之学,也是所谓“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之学,符合“内圣外王”之旨。
从《孟子》一书中对杨朱的批评来看,孟子批评时所针对的,是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思想观点。孟子认为,杨朱的这种思想主张是有违君臣大义的,因而“是无君”的;而“无君”之人,也就忘记了君臣大义——最大的人伦原则,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故孟子斥之为“禽兽”。客观地讲,孟子对杨朱的批评,虽抓住了杨朱思想中最为关键的主张,而且十分准确地切中了杨朱思想主张可能产生的流弊;但却并未能“同情”地理解杨朱学说立论目的和宗旨,而明显存在强人从己的偏颇。
从思想的源头上看,杨朱是老子弟子,他的“为我”或“贵己”的思想主张,应该是由老子由“养生”而“修身”、“修身”而国家天下自然“治”的政治思路而来的*案:关于杨朱之学的源头,蒙文通《杨朱学派考》曾谓“杨朱之学,源于列御寇,而下开黄老。”拙文《由詹何看先秦道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亦采其说。今 与老子思想比较而论,则杨朱亦对老子观点多所承袭。。《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这都是以自身贵(重)于国家天下的观点*陈澧《东塾读书记》曰:“《老子》云:‘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吴草庐注云:‘爱惜贵重此身,不肯以之为天下。’杨朱为我之学原于此。”(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9页。)。杨朱“贵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观点,正是在这样思想背景下必然的结论。孟子看到了杨朱学说“贵己”、“重生”思想的特点,也准确地切中了杨朱思想主张可能产生的流弊,但他却没能真正把握杨朱“为我”或“贵己”的思想主张提出的目的,实在于“修身”或“养生”——用《淮南子·氾论训》的话说,即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强调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真性”)的极其坚定的决心;不能因为外物(包括名利、富贵或贫穷)的拖累而使之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这种“贵己”或“为我”的思想,本质上也是一种“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之学”;它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张,在最终目的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不同的只是,杨朱是以“为我”、“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的方式来“修身”;而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是通过“仁、义、礼、智”之“四善端”的扩充而“修身”。但在孟子在对杨朱之学的批评中,他却把二者间这种“修身”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当成了二者在思想目标上的根本差异,仿佛杨朱的“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是完全忘记了君国天下大义的“禽兽”,以至于造成了在此后中国的学术史上对杨朱学术思想的长久的误解。东汉赵歧注《孟子·尽心下》“杨子取为我”时说:“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虽似为杨朱辩解,但仍和孟子一样,同样存在着对杨朱之学出发点的误解。
当然,在杨朱“贵己”、“重生”或“为我”的思想观点中,也的确包含了极端的“全性保真”的“养生”观点的思想因子。因为这种“养生”观点认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其中就既有摒弃“累”其形(身心)的外在荣华富贵的一面,也包含有主张充分满足人的各种自然欲望的一面。《吕氏春秋》之《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诸篇,旧说以为“果真杨朱书也。”*顾实:《杨朱哲学》,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5页。其中《贵生》引子华子之言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又曰:“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所尊者薄之矣。……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反映的正是一种要无条件地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观点。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思想因子,实际已内含于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全性保真”主张之中。因为,既然凡人的自然本真之“性”都应“全”或“皆得其宜”,那么对“綦色”、“綦声”的追求乃至放纵,就成了“全性保真”的“贵己”、“尊生”或“养生”理论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有可能成为现实中“纵欲主义”的理论借口的。《管子·立政九败解》和《荀子·非十二子》都批评当时的杨朱末流的“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或“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而类似《列子·杨朱》篇中那种纵欲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观点的出现,也证明了杨朱“贵己”、“尊生”、“为我”的思想主张,最后的确曾被一部分人导向了“禽兽”般的“养生”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不能不说,孟子对杨朱“为我”或“贵己”思想主张的批判,确实是相当深刻、准确,具有预见性的。
二、孟子对墨翟学术思想的激烈批评
墨翟也是孟子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在批判杨朱的“为我”之学“是无君也”之后,孟子又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尽心下》亦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批判的锋芒,始终针对着墨子的“兼爱”之说。
墨子其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有极简短的记载,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后世学者多将墨子的生活年代定得较晚,如孙诒让以墨子生年为周贞定王元年(前468),钱穆以墨子约生于周敬王四十年(前480)。我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断定墨子止楚攻宋事发生于楚惠王九年(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而此时墨子当不少于四十岁,故推断墨子生年当不晚于周灵王二十五年(前520)*拙作《墨子生卒年新探》,待刊。。这个年数,约同于孔子弟子颜渊、子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两种说法都可成立,并不矛盾。《孟子》书皆称“杨、墨”,也是符合实际的。
从今存《墨子》一书来看,墨子的学术思想有尚贤、兼爱、天志、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命等主张。《汉书·艺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基本是依据《墨子》一书的内容概括而来的。
《孟子》一书中对墨子及墨家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兼爱”学说而发。墨翟有感于当时天下自利相残而祸乱不断,认为其原因“皆起于不相爱”,因而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以期能实现“圣王之道”。(《墨子·兼爱》上、中、下)
但在孟子看来,墨翟的“兼爱”主张显然存在着两个根本的错误。其一,是它违背人“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仁爱本性。因为,孟子所说的这种人的仁爱本性,乃是儒家的等差之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这是儒家“爱有等差”之仁爱的基本原则。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乃是一种无差别的“爱”(即《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僈差等”)。孟子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人的仁爱本性的“爱”,所以他将其斥之为“无父”的“禽兽”。其二,孟子认为是墨翟的“兼爱”主张,实际还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即“二本”问题。《孟子·滕文公上》篇“墨者夷之”将墨家的“兼爱”实践概括为“爱无等差,施由亲始”。对此,孟子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朱熹《集注》曰:“孟子言人之爱其兄之子与邻之子,本有差等。……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序,故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这也是就墨子“兼爱”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而言的。
显然,孟子上面对杨朱“为我”及墨子“兼爱”思想主张的批判,也不完全是无懈可击的。杨朱的“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固然有孔子批判隐者的“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之弊(《论语·微子》),但孔子对这种独善其身行为的批评亦仅此而已。但孟子却斥之为“无君也”和“禽兽也”,这乃是对他人思想的自由权利的漫骂和粗暴干涉。而孟子说“等差之爱”才是人的仁爱本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缺乏事实根据和逻辑论证的。因为正如庄子所说:“虎狼,仁也。”(《庄子·盗跖》)民间也有许多类似的谚语,如“虎毒不食子”,“乌鸦有反哺之恩”,等等,这些都说明“等差之爱”根本就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仁爱本性,“爱”乃是包括虎狼和禽鸟在内的很多动物都具有的普遍本性,怎么能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并詈斥为“禽兽”呢?
除了批判墨子的“兼爱”思想观点之外,《孟子》书中批判的锋芒还涉及墨子的“节葬”和“非命”观。《孟子·滕文公上》曰: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者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则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在这里,孟子由“墨者夷之”而对墨家的“薄葬”(“节葬”)主张提出了批评。首先,孟子认为,由“墨者夷之”的言行来看,他虽也主张“薄葬”或“节葬”,但在实际生活中又“葬其亲厚”,即“厚葬”,这不是以墨家批评的儒家“厚葬”思想来对待自己的亲人吗?这就不仅显示了墨家学者在言行上的不一致,而且也说明正如《庄子·天下篇》所云:墨子的“薄葬”(“节葬”)主张,“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不可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墨子这一思想主张其实是很难实行的,即使是墨家学派中人也不能做到。其次,孟子还从“葬礼”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说明“厚葬”乃“必有其道”,而“薄葬”(“节葬”)既违背了“仁人”之孝道,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虽然尝有“不葬其亲”而“委之(沟)壑”的情况,但这样会使自己的亲人“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使见之者痛彻心肺;这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葬礼,亦即“厚葬”之所由也。墨子提倡“薄葬”(“节葬”)而非儒家之“厚葬”,这等于要再回到“不葬其亲”而“委之(沟)壑”的时代,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对于墨子的“非命”思想观点,孟子似也曾以其特有的立场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墨子·非命上》曰:“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墨子认为,这实际是否定国家的治乱、个人荣辱皆“以为其力也”(《墨子·非命》),是否定它们“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故墨子提出“非命”之说。墨子的“非命”之说,显然是针对孔门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观点而提出来的。因此,对《孟子》书其涉及“命”的论述,也就应该看成是孟子对墨子“非命”观点的一种回应。孟子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这说明孟子认为:“所谓命就是一种客观的决定力量。”*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123页。为此,孟子还特意区别了“命”与“性”、“正命”与“非正命”。他说,尽管人的本性即仁、义、礼、智与人的口、耳、鼻、四肢之欲不同,后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而前者则“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是应该而且“可学而尽”的,“故不谓之命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由此他提出了在道德修养上的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立命”之说:以“坚持原则,竭尽了主观的努力,最后达到‘莫之致而致者’”,“才是正命”;而“如果立于危墙之下而死或犯罪桎梏而死,那都是自己的活动有以致之,便非“莫之致而致”了,所以都是“非正命”*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总体来看,墨家所“非”之“命”是完全前定的“命”,与人的主观努力无关。而孟子所谓“命”,既排除了道德领域的仁、义、礼、智,以为其中“有性焉”,“君子不谓命”;又认为“任何事情的成败,有主观条件,也有客观条件”,只有尽力发挥了主观的作用,所得到的结果才是“莫之致而致之者”,才是“正命”,反之则是“非正命”。孟子的所谓“命”,虽客观外在者,“但不废人事”。这与墨子所“非之命”,“意义是不同的”*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125页。。由此可见,孟子所谓“命”的论说,虽然并非完全针对墨子的“非命”而发,但由于孟子是墨子思想主张的激烈批判者,在儒、墨论争的思想背景下,说孟子的“命”论是对墨子“非命”之论的一种回应,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孟子对其他诸子学派的批评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引陈澧《东塾读书记》(三)之言,以孟子曾“距”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说明“此孟子所以为大儒也。”近世学者则对此做了进一步补充,其范围亦超出陈澧之上。罗焌《诸子学述》分辨“诸子之异同”有曰:
今案孟子以齐桓、晋文之事为未之闻,以管仲、晏子之功为不足为,以伯夷、伊尹之圣为不同道,碌碌余子,类皆辞而闢之。《万章》上篇九章,《告子》下篇宋牼一章,皆闢小学家言也。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此闢名家之诡辩派也。(《公孙丑》上篇)其直闢农家,则曰:“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其直闢纵横家,则曰:“公孙衍、张仪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焉得为大丈夫乎?”(《滕文公》上、下篇)其直闢兵家也,则谓慎滑釐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篇)至陈仲子齐人之所谓廉士者,而孟子谓其无亲戚君臣上下,比之于蚯蚓。(《滕文公》下,又《尽心》上)……是皆儒者之苦心,固非好辩也。而视百家之互相訾謷者,又何以异乎?*罗焌:《诸子学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罗焌在陈澧所述的基础上,先是补充了孟子对历史上齐桓、晋文、管仲、晏婴及伯夷、伊尹的态度,然后增添了《孟子·万章上》《告子上》对“小学家”的批评和《孟子·公孙丑上》对“名家之诡辩派”的批评,而最后所述《孟子·滕文公下》及《尽心上》对“齐人之所谓廉士”陈仲子之学说的态度,为陈氏《东塾读书记》所不及。
由罗氏补充的“诸子异同”来看,《孟子》以齐桓、晋文之事为未闻,以管仲、晏子之功为未足为,以“伯夷、伊尹之圣为不同道”,其实并不属先秦诸子学的内容,难以看出孟子本人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孟子·万章上》第九章乃叙“伯夷、伊尹之圣为不同道”,看不出与所谓“小学家”有多大的关系;《告子上》章乃记“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之石丘”。宋牼告之以“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而孟子批评宋氏的行为:“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必然会亡国;只有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相接也”,才能“王天下”。宋牼,即及《韩非子·显学》篇、《庄子·逍遥游》之宋荣子,《庄子·天下》及《荀子·非十二子》称宋钘。《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列,尹文《汉书·艺文志》属名家,《宋子十八篇》列于《汉书·艺文志》之“小说家”,《荀子·非十二子》则将其与墨翟并称。而从《孟子》书此处所记宋牼将说秦、楚“二王”罢兵而言,宋牼很可能与墨翟相近,“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上说下教”,“强聒不舍”。(《庄子·天下篇》)与所谓“小学家”并没有多大关系。更何况,从来无人以“小学家”为先秦诸子之一派,所谓“闢小学家言”也就无从谈起。孟子本人即以“好辩”著称,其“好辩”的原因是当时天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邪说暴行有作”,而孟子则“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由于孟子是把“杨、墨之言”称为“淫辞”、“邪说”的(同上),所以他的所谓“闢名家之诡辩派也”,实际仍只是“闢”杨、墨二派之“名辩”的作风,而不是“闢”另外的某个先秦诸子学派。《孟子·告子下》有孟子批评慎滑釐“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实属意引《论语·子路》“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说慎滑釐“不教民仁义,而用之战斗,是使民有殃祸也。”但这只能说明孟子对“用民于战”的态度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也很难说是在“闢兵家”。因为慎滑釐其人在《汉志》“兵书略”中既无其人,也无其书,战国时诸侯国的将领是否即是“兵家”人物实难论定;况“兵家”亦并非先秦诸子学派之一,《汉志·诸子略》“九流十家”中既无“兵家”,《兵书略》中虽称“兵家者,盖出于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但此所谓“兵家”的内容皆与政治思想(即所谓“此务为治者也”)无关,而只是“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这些具体的作战技法而已。故孟子对慎滑釐“不教民仁义,而用之战斗”的批判,应该算不得所谓“闢兵家”。只有罗焌所述《孟子·滕文公下》和《尽心上》二篇中孟子对陈仲子的批评,才可以说是对陈澧所谓“孟子所以为大儒也”而“距”诸子百家之说的补充。《孟子·滕文公下》载: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臣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陈仲子,《荀子·不苟》、《非十二子》皆称“田仲”,王先谦注:“田仲,齐人,处於陵,不食兄禄,辞富贵,为人灌园,号於陵仲子。”*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页。《战国策·齐策四》赵威后问齐王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而不杀乎?”所言正是陈仲子。孟子以为“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臣擘焉。”这可见陈仲子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但《史记》既不载陈仲子其人其事,《汉书·艺文志》亦无陈仲子之书。《荀子·非十二子》曰:“忍情性,綦谿利跂(王先谦曰:”綦谿,犹言极深耳。利与离同,杨说是也。离世独立,故曰‘离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批评所针对的就是陈仲子离世独立、异俗隐逸的思想特点和作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巨瓠,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淮南子·氾论训》曰:“季襄、陈仲子立节以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诸书虽然见闻异辞,但都反映了陈仲子离世高蹈、异俗洁身的品行,明显具有道家思想倾向。
对陈仲子,孟子既称之为齐国士人中的“巨擘”,即表明他对陈仲子“廉”、“直”的品行是予以肯定的。孟子批评陈仲子的,一方面是说在实际生活中,陈仲子并不能真正或完全实行他的所谓“廉”、“直”,因为陈仲子不能如蚯蚓那样“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而必须借助社会分工中他人的劳动成果来生活。——这就正如孟子批评农家学者许行不可能做到“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一样,是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来说明了陈仲子“诚廉”之不可能;另一方面,孟子又如孔子批评道家的隐士那样,从“义”的角度来批评陈仲子离世独立、背俗高蹈的所谓“廉”。《尽心上》载孟子之言曰:
“(陈)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孟子此处对陈仲子的批评,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论语·微子》中孔子对“隐者”荷蓧丈人的批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联想到上文刚刚引述的荀子对田仲、史鰌 “离世独立,故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的批评。孟子对陈仲子的另一方面的批评,显然是依孔子批评“隐者”的基调而来,即是着眼于陈仲子离世高蹈、自洁其身而背离君臣之“义”或“大伦”、“大分”而言的。稍有不同的是,在孔子和荀子那里,“欲洁其身”,虽可以称之为个人的“廉”德,但尚不能称之为“义”,只有“大伦”、“大分”才能称之为“义”;但在孟子这里,“欲洁其身”的“廉”似乎也可以归之于“义”的范畴,只不过这种“义”较之于亲戚、君臣、上下之“义”,乃是“小者”,而治国家(“箪食豆羹之义”)、“有亲戚、君臣、上下”之宜,才是士君子之“大义”。陈仲子弃国家、亲戚、君臣、上下之“大义”而不顾,而欲保持个人的“廉”操,这虽然也是合“义”的,可称之为“巨擘”;但毕竟是取舍失当、本末倒置了,故孟子曰:“以其小者信大者,奚可哉?”应该说,孟子对陈仲子的这种批评,是与其后荀子所谓“田仲、史鰌不如盗”的批评异趣的。
而综合《孟子》七篇来看,孟子对先秦诸子批评最多的,其实当是“九流十家”中不入流的“小说家”和孟子自己所在的儒家。《孟子·万章上》载:“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对咸丘蒙所说的尧与瞽瞍“北面”朝见帝舜的事,以为属“齐东野人之语也”而予以批驳,并由此引出对及“小说”之文字不可拘泥于字面解读,而应该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结论。在这里,孟子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即是《汉志》“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意思。这既是对“小说”性质的一种界定,也是对“小说家”的一种批评。孟子认为“小说家”言为“野人之语”,故所言是不经的和不可信的。孟子的这一批评,也是对孔子所谓 “道听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观点的继承。但孟子又并不是因简单地继承孔子的观点而对“小说家”言加以摒弃,而是主张应根据文学语言表面的文辞“以意逆志”,真正把握作者的本意。这显然是对孔子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实际上,《孟子·万章上》皆可视为对“小说家”的批评,即是“距小说家”的。如《万章上》记万章问孟子曰:“有人言‘伊尹割烹以要汤’,有诸?”孟子对此说进行了驳斥,曰:“否,不然。……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近代以来的研究者即认为其当出于《汉志》“小说家”之“《伊尹说》二十七篇之中。此书荟萃丛谈也。所记皆‘割烹要汤’一类传说故事及其他杂说异闻”;“《孟子》‘伊尹的割烹要汤’,谓此篇也。”*张舜徽:《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可见,孟子此处所“距”者即为“小说家”矣。又如《滕文公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以“于传有之”,但孟子认为因桀、纣属“残贼之人”,故汤、武诛伐乃诛独夫民贼,不属“弑君”。孟子此处云汤、武征伐之事,不同他处称“《诗》曰”“《书》云”,而称“于传有之”,即将之归于“传说”之类。这与《荀子·正论》所谓“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一样,都是将此“说”界定为“小说家”言而加以批评的,也属于所谓“距小说家”之例。《孟子·万章上》还载有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和“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其子’。”但此种传言在《荀子·正论》中亦被记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之类,即同样也是被当成“小说家”言而予以批驳的。故王先谦《荀子集解》曰:“世俗以为尧、舜德厚,故禅让圣贤;后世德薄,故父子相继。……《孟子》亦云:‘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1页。即认为孟子所“闢”的“尧以天下与舜”、“禹传子不传贤”诸说,与《荀子·正论》中的“世俗之说”、“尧、舜擅让”一样,也都属于“小说家”言。
孟子自己所属的先秦儒家,也是他批评最多的另一个诸子学派。当然,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同于孟子对其他诸子学派的一味“距”和“闢”,而主要是一种肯定与颂扬。孟子对孔子可谓推崇备至,因为在后世一般儒者的眼里,孔子如同尧、舜、伯夷、伊尹,都是“圣人”。但在孟子看来,孔子贤于诸人“远矣”:“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借孔子弟子宰我、子贡、有若之口评价孔子曰: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逮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在《万章下》孟子更直接地表明了其对孔子的推崇:
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显然,孟子在此是通过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的比较,而给予孔子最高的评价。因为诚如朱熹所云:“孔子仕、正、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四时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1-372页。故《孟子》全书多处引述孔子之言行,然无一处稍有微辞,皆以为处世行事之典范也。而孟子亦每以继承孔子之道自任,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除孔子之外,孟子最推崇的另一先秦儒家人物,当数曾子(曾参)。《孟子》一书中《梁惠王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滕文公上》《滕文公下》《离娄上》《离娄下》《尽心下》多篇,既皆引述曾子言行,而且在这些引述中,孟子往往是以曾子为人格典范,以曾子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如《公孙丑下》孟子在解释自己为何不赴齐王召命时,即引“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这是孟子即以曾子为榜样,以曾子之言,说明在权位面前,士人应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德抗位。《滕文公上》记滕定公世子遣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又引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这表明,在孟子看来,“孝”的要义乃如曾子所云,在于对父母事奉、安葬、祭祀诸方面而皆合于“礼”。又如《离娄上》,“礼”是孝子如何 “事亲”时,也曾引“曾子养曾晳”为例,说明“事亲”重要的是如曾子“能承顺父母之志”,而不可如曾元事曾子,“但养口体”。(孟子对曾元事曾子“但养口体”的微辞,也可以说是《孟子》书中对儒家学派中人的唯一一处否定性的批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5-296页。。《孟子·滕文公下》在答公孙丑问“不见诸侯”之义时,也引述了曾子“胁肩诋谄笑,病于夏畦”之语,说明君子应持“圣人礼义之中正”,而不可取“小人侧媚之态也。”这显然是采取曾子的言辞以为是非标准的。
除孔子、曾子之外,孔门七十子中的子路、曾晳、颜渊、子夏、宰我、子贡、冉牛、闵子骞、有若及孔子之孙子思、曾参之子曾元、曾参之孙曾西等,亦曾为孟子论述所涉及,但孟子对他们基本皆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余论
《孟子》书中先秦诸子批评所涉及的诸子人物,自然并不止如上所述。而且,他批评的有些诸子学者,其学派归属尚存在争议或并不明确。如《告子下》所谓“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之石丘,”其中的宋牼,又称宋钘或宋荣子,《庄子》《荀子》二书把他和墨子归于一类,似乎认为他是墨家,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班固原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又似乎是说宋牼乃在小说家和道家之间,但上文引近人罗焌之文则称之为“小学家”。可见,这个问题并无定论。又如,与孟子论“性”的告子,向来多认为他是“孟子弟子”,自然应数儒家;但东汉赵歧的《孟子注》却称之为“兼治儒、墨之道者。”《告子下》又有“先名实者”的淳于髡、以治水闻名的白圭、《滕文公下》的魏人周霄、宋臣戴不胜等,历来无人知其学派归属。这些实际都说明孟子学术批评涉及的范围的确十分广泛,远远超出了所谓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之列。
尽管孟子先秦诸子学术研究批评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其批评的重点仍在杨、墨、儒及“小说家”等数家。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孟子个人对杨、墨特别排斥和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立场有关,但我以为,更主要的则应该是当时学术发展的现实情形使然。《孟子·尽心下》称当时学术界“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说明当时最兴盛的诸子学派乃杨、墨、儒三家。孟子对先秦诸子的批评,离开了杨、墨、儒三家,那他还批评什么呢?至于“小说家”之言,则并非杨、墨、儒之外的某种思想观点,实只是其形式上与“经”相对的“传”、或与学术界书面语相对的民间口头传说而已*高华平:《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即只是形式上不同的杨、墨、儒学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对“小说家”的批评,仍然还是对杨、墨、儒的一种批评。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Mencius’ Academic Criticism of Pre-Qin Scholars
GAO Hua-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Mencius assesses Pre-Qin Scholars by choosing to focus on the YANG Zhu School of the Taoists and the ideas of “universal love”, “frugal funeral” and “ajiva” (disobeying attitude to fortune) of Mohist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oncerns other schools. Mencius’s criticism of the YANG Zhu School capture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but has its own drawbacks: it failed to understand with “sympathy” the argumentative goal and purpose. His appraisal of the other schools is much biased, usually by emphasizing one point and ignoring others. This characteristic is associated not only with Mencius’ apologist stance of Confucianism but with the then academic development reality as well.
Mencius; Pre-Qin scholars; academic criticism
2016-04-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15ZDB007)。
I109
A
1002-0209(2016)06-0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