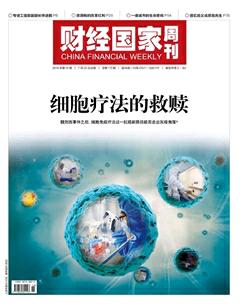基层金融监管难题
聂欧
各种新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基层监管涉及多方但力量奇缺。
“我们很迷茫。”一名沿海省份金融办官员坦言,近期省政府要求起草关于该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管理办法,省金融办、银监局和农办三个机构在会上“掐”了起来,各执一辞。最终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或是由该省副省长兼任一把手的省农办,或是专业能力更强的省银监局,“反正轮不到金融办”。
在他看来,金融办是协调部门,主要在省银监局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省联社”)等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沟通,“什么都参与,但什么都无法主导。”

我国基层的金融监管体系权责不清、亟待重构。
类似观点,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走访的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同样存在。受访人士表示,我国基层的金融监管体系权责不清、亟待重构。
一方面,地方金融办权责不对等,既与“一行三会”的监管边界颇存争议,又难与省联社等机构“和而不同”,仅在诸多机构的交叉点或空白点发挥作用,对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P2P、小贷、担保等新机构,缺少“监管的牙齿”。
另一方面,“一行三会”仍沿用19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机构设置,存在监管重叠和空白,且由于缺乏省、市、县层面的统一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均难与所属权责均衡匹配。
受访人士认为,最棘手的是决策、监管、审批和调查等一系列权责在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分配、协调问题,以及如何减少基层监管资源的重复浪费、防止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各种新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基层监管力量奇缺,需要顶层设计。”一位省银监局官员直言。
金融办“牙齿”何在
“我们会被撤还是被并?”前述金融办官员称,地方金融办长期以来就定位不明、权责不清。首要一点,尽管与省银监局、省联社等同属正厅级机构,且与省联社同属于省政府管辖,但金融办的“地盘”稍显边缘。
其一,金融办多在“一行三局”(央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的权责交叉点或空白点发挥作用,且多为协调和联系作用。
其二,长期以来,地方金融办没有立规定策的权力,尽管将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会等划归其分管,但并不具备制定管理办法之权,仅负有具体监管之责,权责不对等。
其三,金融办是否具备监管权也存在争议,尽管一系列新金融、类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往往留给了能力相对薄弱的金融办。
“监管权日后应该会有,现在新机构太多,‘一行三会管不过来。”前述金融办官员建议,中央层面颁发牌照的如支付机构等,应由“一行三会”主责;地方政府颁发牌照的如小贷、担保、资金互助会等,则落地金融办。
那么问题来了,金融办监管的“牙齿”何在?
融资担保公司在2009年就实行属地管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规定,各省市政府按“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原则,确定相应部门负责本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关闭和日常监管。
2015年8月,国务院法制办《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由各地方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工作,并由各级政府负责协调处置其风险。
而上述文件中“确定的部门”,即各级地方金融办。
前述金融办官员对此表示,不仅是融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也划归了金融办监管,但他们至多是看看账,走走场,“理论上还拥有一点处罚权”。
他建议,地方金融办未来应与省银监局、省联社等“更强大的资源”进行整合,避免央地监管边界随着各类新机构的骤增而混乱。
基层系统自身“缺陷”
难题长期存在,一定程度还源于基层监管系统自身的制度缺陷——纵向上,表现为省级、市县级金融办之间缺乏协调统筹机制;横向上,金融办与银监局、农办、央行等机构的决策权或重叠,或空白。
记者调研发现,各地省级金融办在“纵向上”的权限差异较大——部分较为“强势”,一定程度上拥有对市县级金融办的领导权;但大多数却缺乏实权,与市县金融办“两张皮”,至多是制定文件分发下去,却很难干预其执行。
“一个处室通常三五个人,小一点的省金融办总共就10多人。”一名地市级金融办官员说。他所在市的金融办,目前还隶属于该市发改委,作为发改委的一个处室而存在。
这一问题到了县级层面则更为明显:一些县级金融办,均隶属于当地发改委或经信委,只有三五位工作人员且流动性较大。另一种情况则恰恰相反,温州等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其市县级金融办队伍则颇为强大,与浙江省金融办鲜有关联,具体工作也很少上报。
“一省之内,政令落不下去,风险报不上来。”前述省级金融办官员很无奈,“各省自身并未形成上通下达的系统,管理怎可能有序进行?”
横向上,省银监局、省农办和省联社等相关机构与省金融办之间,也常就同一问题各执一辞。
以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例,其形势多样、风险复杂,迄今未确定监管主体和监管办法,原则上只能依靠四类文件进行规范:
一是银监会2007年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只对银监会发牌的全国49家资金互助社有效;
二是央行发布的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的试点意见,目前亟待进一步出台放贷人条例,扩大试点、加强规范;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以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条文,为监管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尚缺乏对资金互助组织的针对性;
四是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提供了基本原则,但在操作层面,还需更多的实施细则。
前述省金融办人士直言,金融办将坚持小额、坚持资金封闭并禁止揽储,但其他部门要求加大互助会运作的灵活性,方便农民,可由互助会向会员借款后再放贷给有需求的会员,加大机构的放贷杠杆。“他们对政策草案颇有意见,但提完意见却不负责具体监管,出了风险仍是金融办承担。”
在他看来,全国层面至今没有针对资金互助组织的统一管理章法,是地方上各机构互相推诿的主要原因。三个厅级单位各执一辞,争论已持续多时。“如果另两个部门坚持己见,金融办只能让步。”
改革工程浩大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金融基层监管体系改革尤其央地监管边界的划分,几年前就已摆上了我国金融监管决策层的桌面,但迟迟未决。
由此牵涉的,不仅是前述地方金融办的权责,还包括各地省联社的转型和改革,以及“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深度整合,等等。
多位受访人士均认为,这一项系统性工程所需触动的既有利益层及所需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或不亚于眼下中央下大力气、大决心的国企改革。目前,现实难题至少有两点:
其一,是首先要确认一系列新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究竟是谁。
资邦控股董事长陶蕾认为,由于监管主体不明确,诸多监管细则不到位且监管分工不明细,企业业务开展很为难。
事实上,地方金融办虽拥有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责,但却并未发挥多少效用,使得近几年来小贷公司风险四起、频繁关张,一部分已异化为了民间高利贷。并且,P2P近来不断传出跑路消息,虽然其监管划归银监会良久,但却至今未出台监管细则,往往是地方金融办从工商登记的角度,对P2P进行了简单的备案式管理。如此众多的新金融机构,正日渐加大监管难度。
“我们只负责制定P2P监管办法,具体工作由金融办负责。”一位地市级银监局官员指出,“P2P注册在地方上,理应是谁批谁管。如果硬要塞给银监局,那就要从注册开始管起,把银监局的人员配起来,财务要够用。”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这一说法却引发了诸多金融办官员的争论。观点一,P2P的监管规则还没出,出了再说;观点二,金融办应该接手监管,中央也应赋予金融办监管权;观点三,金融办已有的责任都难以顾全,P2P这一“烫手山芋”不能接,应该主要依靠央行今年刚刚牵头成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来管理。
一位中央监管部门官员直言,谁都对这些新机构的监管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管,不想管,也管不了”。
其二,是“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如何整合。
“央行地市及县一级的分支机构,应该用起来。”前述银监局官员直言,当前基层监管力量奇缺,银监局人少事杂,“一行三会”之力应该统筹。
据他介绍,央行地市级分支机构通常约有200多员工,并每年从当地银行系统借调一些流动员工,包含汇率、信贷、清算等诸多部门,但因基层多为细节性工作而少有政策制定,工作压力并不大。
相比之下,地市级银监局仅几十位员工,通常负责30-60家银行机构的具体监管工作以及少数新金融机构的管理,人手奇缺。
“我们对此很困惑。”一名江苏省农商行高管称,当地监管机构繁多,但监管资源却要么空白、要么扎堆。例如,该行每月、每季度和每年均须以同一套统计数据的三种格式,分别上报给央行、银监和金融办。并且,该行平日须接受超过三个监管机构的视察,每季度平均接待超过10次现场检查,“若没有专人负责,根本应对不过来”。
“金融监管改革是系统性工程,必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前述“一行三会”官员称。
一方面,是分大类监管:由中央监管部门发放营业牌照的机构,应由中央部委监管;由地方工商注册或地方金融办备案的机构,如小贷、担保、评级、P2P等则归属金融办,对银证保起到配合和查漏补缺作用。毕竟,大量新金融机构的业务还局限于小范围区域,一部分仅有工商注册甚至没有办公地点,中央部委要伸手监管,略显困难。
另一方面,整合“一行三会”监管资源,可在各地央行分支机构下设相应的处室。例如,央行某地分行行长兼任外汇管理部主任,将分别设分管外汇领域的专职副行长、分管地方金融的专职副行长、分管银行业监管业务的专职副行长等。而各专职副主任,将分别来自于银证保。
其中难题,是央行从上世纪90年代就延续至今的“总行—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县支行”五级制度,若要以此作为框架来整合基层监管资源,则需在全国各省份和大部分地市设立相应级别的分支机构,工程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