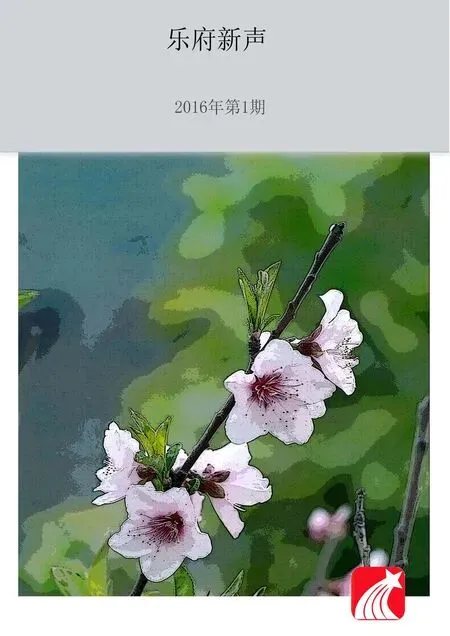时空对接
——试论古曲《十六板》、《普安咒》与巴赫赋格技法的共性特征
翟纬经
时空对接
——试论古曲《十六板》、《普安咒》与巴赫赋格技法的共性特征
翟纬经
[内 容 提 要]本文从“时空对接”的角度出发,将中国古曲中的《十六板》与《普安咒》与巴赫的赋格写作技法进行对照,以论证不同时间与空间维度下音乐艺术表现技法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巴赫/赋格/《十六板》/《普安咒》/点描式变奏/闯入式进入
多年来,经过于苏贤等前辈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宝贵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复调音乐。西方的复调音乐传统是在九世纪的奥尔加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传统复调音乐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这个独立体系的基础之上,与西方复调音乐分属于两个领域。虽然两者传承着各自民族的审美价值,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复调思维基础是一致的,技术原则的共同点也很多。正如于苏贤在《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一书中所述:“复调音乐是建立在横向思维基础上,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线条(旋律的、非旋律的)按照特有的逻辑规律加以纵向结合而构成的多声部音乐。……这个概念的内涵表明了复调音乐思维的共性特征是线性的。无论西方传统复调音乐,还是中国传统复调音乐,甚至20世纪的创新复调,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1]于苏贤《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3页。
基于上述原则,将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与巴赫赋格的写作技法加以联系、对照,其目的并非套用西方传统复调音乐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传统复调音乐现象。“事实上,中、西方复调技术的共同点都是基于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科学性”[2]于苏贤《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页。。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复调音乐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清楚的了解到人类音乐艺术审美的共性特征是不受时间与空间制约的。
现将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与巴赫赋格写作技法的共性特征归纳如下:
1.闯入式进入在复调结构中的应用
当一个复调段落尚未结束,另一个复调段落的开始部分便进入,从而形成两个音乐结构的紧密衔接,即闯入式进入,其特征正体现出复调音乐特有的连贯发展的原则。在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对位曲14这首庞大的三重赋格的第一赋格再现部,d小调第一主题(T1)闯入于展开部下属g小调紧接段结构内部。见下例:
例1.巴赫:《赋格的艺术》对位曲14:89-105小节

上例从赋格I的展开部第89小节原形主题与倒影主题构成的无终卡农式紧接段开始:bB大调T1于低声部首先进入,1小节后第III声部的丄1紧接进入,至第92小节第II声部g小调T1再次紧接进入。在这个运用综合调式原则创作的紧接段中,低声部的原形主题及高声部的自由对题的调性基础为bB;而第一模仿声部的倒影主题旋律中不断强调的属-主音跳进表明了F大调的调性特征;第二模仿声部的原形主题则为清晰的g小调调性结构。由此论证了这是一个多调性的三声部卡农式紧接段。展开部以开放式结束。第97小节,第III声部的d小调T1正是在此下属g小调紧接段的结构基础上闯入,由此开始了赋格I的再现部。2小节后,第II声部的d小调原始体T1紧接进入,与之构成具有复合功能的紧接段。
对位曲14的赋格II呈示部,T2首部闯入于赋格I再现部的完全功能终止式之上,形成两赋格的“耦合式”[1]耦合式: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引自《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作/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出版。联结。见下例:
例2.巴赫:《赋格的艺术》对位曲14:105-120小节

上例从赋格I再现部第105小节开始,d小调T1于低声部进入。通过结构的延长于第115小节以音乐语义的句逗停顿及IV-V7-I完全功能终止式构成相对独立意义的结束点。在此过程中,第二主题(T2)首部于第114小节在第II声部闯入,将两赋格天衣无缝地联结在一起,形成结构间的紧密衔接。但在音乐形象上,T2以八分音符流动、密集的节奏型与宽广的T1形成鲜明对比。
闯入式进入技法在巴赫的其它作品中更为多见,不一一举例。
中国的古代音乐中,闯入技法也并不鲜见,如民族器乐合奏曲《十六板》[2]《弦索十三套》是清代文人荣斋编辑的《弦索备考》中的十三套器乐合奏曲的总谱部分,《十六板》为其中的一套。便是运用此类技法的实例之一。这首乐曲产生的具体年代虽已不可考,但杨荫浏在《关于<弦索十三套>的说明》中这样写到:“这十三曲……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它至少是18世纪以前的东西”[3]原文出自杨荫浏:《关于<弦索十三套>的说明》,转引自于苏贤:《中国传统复调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十六板》是由两个主题构成的二重复调变奏曲。第一主题“十六板”与第二主题“八板”皆是古老的乐曲。两个具有独立性的乐曲运用对比复调原则结合在一起,贯穿始终。两主题的长度相等,均为34小节,在全曲中均出现16次。“十六板”与其15次变奏是在保持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变奏原则不断变化发展而成的,而“八板”则是以固定不变的原始形式完整出现16次。两主题始终以“动-静”对比关系结合,形成了二重复调变奏曲整体的结构基础。
十六板主题的原始形态由引子开始,其基本结构的初次陈述开始于引子之后标注“正曲起”的地方。“八板”主题在“十六板”引子音乐由散板进入2/4拍子时进入,初次陈述比十六板主题的基本结构提前3小节出现。由于两主题的长度相等,因此“八板”也就要比“十六板”提前3小节结束。“八板”主题的十六次进入均未使用任何连接成分,而是以首尾相连、环环相扣的形式进入。因此,“八板”的每次出现均是在“十六板”的前次进入的最后3小节的结束句上,两主题交错陈述。这种将两主题进入与结束的时间点错开的处理方式加强了音乐的对比性,消除了各个变奏之间的中断感,形成连绵不断地进行。下例最上方一行是十六板主题的原始形态的结束句与八板主题的开始结合进入的总谱:
例3.《十六版》,选自[清]荣斋等编《弦索十三套》,曹安和、简其华译谱,杨荫浏校订.十六板主题的结束句

下例为闯入式进入的十六板主题。
例4.[5]段的最后一小节,十六板主题闯入式进入

上例这个闯入的、并采用扩大形式的十六板主题首部由五个声部层加以重复出现,以消除音乐的结束感,与其后的第六段音乐紧密衔接,构成乐曲展开部的开始。此后,乐曲的第七、第九、第十等多段均运用了闯入式进入,形成了结构上的呼应。
2.点描技法的运用
点描法在库斯特卡著《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的论述是“点描法的名称来自19世纪法国画家所采用的一种技法。……在音乐中的点描是这样一种织体,它以多休止和大跳跃为特征,此技法将声音隔离成各个‘点’。”[1][美]库斯特卡,宋瑾译《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189页。然而,通过对巴赫赋格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早在其《c小调帕萨卡利亚与赋格》中就出现过极富艺术性的点描法。帕萨卡利亚是一首运用固定低音原则写作的复调变奏曲。下例是固定低音主题与变奏14:
例5.巴赫:《c小调帕萨卡利亚与赋格》
【a】原形主题

【b】点描式变奏主题

上例中固定低音主题在变奏14中以圆圈加以标示,其中体现的点描法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如运用休止和大跳跃将固定低音主题的音隔离成点状,并运用十六分音符的连续进行加强了乐曲的舞蹈性特征。通过音型与节奏的变化来突出主题的性格对比,从而增添了音乐的情趣。
在《音乐的奉献》这首“根据‘从至高的天界’而创写的卡农变奏曲”[1]引自由达维特·莫罗奈根据原稿校订,释文译者.杨儒怀《巴赫——赋格的艺术》(适用于室内乐(钢琴))的前言,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中,巴赫再次将点描法运用于主题的变奏。见下例:
例6.巴赫:《音乐的奉献》
【a】原形主题

【b】点描式变奏主题

上例的三行总谱中的中声部是运用点描技法变奏的核心主题,同样运用了休止符与跳跃造成主题的点状造型;低声部的卡农起句A由五个音构成;高声部运用扩大倒影变形加以模仿构成第一应句 1。低声部第二起句B,高声部第二应句仍为扩大倒影 1。而低声部的第三起句C,在高声部的应句中则只扩大而不再倒影了,从而使卡农体现出清晰的调式调性结构。
此外,在《赋格的艺术》对位曲1的再现部中,套曲的核心主题以a小调为基础在三个声部间以点描式进入。这时,主题的艺术形象正是通过点描的手法糅入对位结构之中,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境界。见下例:
例7.巴赫:《赋格的艺术》对位曲1
【a】原形主题

【b】65-69小节

上述巴赫赋格中运用的点描技法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与其后20世纪作曲家的创作虽采用了不同的风格语汇,但表现意义与结构思维则是共通的。现在,将时空逆转反观中国的传统音乐可以惊喜地发现相似的技法在我国的传统复调音乐中早已存在,如《十六板》总谱中的点描技法比比皆是,本文暂不涉及留待以后专题论证。现在研究的是明末古琴曲《普安咒》中运用的点描式变奏技法。
《普安咒》(又名《释谈章》),乐谱最早见于公元1592年。在于苏贤著《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中对这首作品的创作技法与表现特征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这里仅摘引部分内容:“《普安咒》全曲13段加尾声,结构宏大,是一首建立在两个具有特性对比的主题基础上的复调变奏曲。其中之一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固定低音主题。这个固定低音主题表现了佛教寺庙低沉幽暗的景象,贯穿于全曲的始终。……这个固定低音主题,只是作为每段音乐中的低音旋律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后一半。它分别与12段音乐中的低音旋律中不断变换的前一半,构成连贯完整的横向运动的旋律线。……乐曲的另一主题代表有节奏地吟诵经文的形象……称之为“吟诵主题”。吟诵主题的每次出现也是与其后部分旋律联结成有机的完整旋律线,同时又与不断变换的低声部旋律构成对比二声部复调结构。于是,两个固定主题便以交叉形式出现……”[1]于苏贤《中国传统复调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5-6页。这段精辟的文字已将《普安咒》的结构特点论述得十分清楚。乐曲中的两个主题,即固定低音主题与吟诵主题均运用了点描式变奏手法展开,现结合实例加以论述。
乐曲第三段的前6小节是由吟诵主题与低声部旋律构成的对比复调。其中,吟诵主题的基本动机灵活地分布在各个小节中。下例【a】为吟诵主题的原始形态,【b】为点描式变奏。
例8.《普安咒》,夏一峰传谱
【a】吟诵主题与低音结合的片段

【b】点描式变奏的吟诵主题与低音结合的片段

上例吟诵主题的原形与低音结合的片段出现在乐曲的第二段,主题是以B-#C-E-#F-E-#C-B的回文结构为基本动机,其后重复一次来强化这个动机的鲜明性。而在乐曲第三段中,点描式变奏的吟诵主题则通过旋律性延长将基本动机的结构加以扩充,形成旋律的对比。
乐曲第4段的前六小节是第三段中吟诵主题与低声部旋律运用纵向可动对位的变化形式:低声部旋律移低五度,而高声部的吟诵主题向上移高一个八度。从而,使原本复调结构(第三段)的纵向音程产生了新的变化,旋律的音级色彩也相应改变。其后固定低音主题的呈现与其前半部分的衔接十分自然流畅。见下例:
例9.点描式变奏吟诵主题与低音旋律的纵向可动对位

乐曲的第五段,固定低音主题也运用了点描式变奏手法展开。主题的原形出现于乐曲第二段的后半部分(27-33小节),见下例【a】。固定低音主题自身具有的II-V-I终止式构成了明确的E大调调性功能结构。乐曲第五段的后半部分,固定低音主题被分解为隐伏二声部卡农结构,见下例【b】。
例10.
【a】固定低音主题

【b】固定低音主题的点描式变奏

上例【b】中固定低音主题首部的两个音通过旋律的润饰加以推出,而后从第二小节的E音开始,主题的结构音被八度跳进的卡农结构分割为点状进行,并通过旋律性延长将主题的内涵加以扩充。但,固定低音主题中的II-V-I功能性终止式依然清晰可辨,从而明确了E的调性基础。而后,此点描主题在乐曲的再现部(第十二段)中重复出现,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先祖音乐家巧妙地将单旋律拓展为隐伏二声部卡农结构,所体现出的纵横开合的结构思维既加强了音乐形象的鲜明对比,又增添了音乐的情趣。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复调思维与巴赫的复调思维,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结构内涵等方面均具有相同之处。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相同的审美意识,再次论证了人类对美的本质的追求是可以超越时空与地域的。
结语
说到时空对接,离不开传统二字,这里既包括西方音乐的传统,也包括中国音乐的传统。对于巴赫来说,西方早期复调音乐是他所遵循的传统;而对于19世纪以后的作曲家们来说,巴赫则是他们的传统。复调的精神正是这样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完成了时空的对接。而中国的传统音乐,看似与巴赫、与西方复调音乐不直接发生关系。但通过研究我们可以骄傲的说,我们的先祖音乐家也是具有高度缜密的复调思维的。这种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闪耀着民族智慧光芒的复调思维,与西方复调音乐在组织结构与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这正是人类音乐艺术审美的共性特征。
正如伽达默尔[1]伽达默尔(1900-2002):德国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创立者之一。曾任德国哲学总会主席、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著作包括:《伯拉图的辩证论理学》、《伯拉图与诗人》、《论哲学的本原性》等。的理论认为,传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只有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才能真正了解传统,使传统“活”起来。当我们以开阔的眼光看待传统时,不论是巴赫的音乐还是中国的古代音乐,彼此间都不是完全割裂的。无论音乐语言与风格经历了何种变化,艺术家对于美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于苏贤.复调音乐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2]于苏贤.20世纪复调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3]于苏贤.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概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4]于苏贤.中国传统复调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5][奥]申克.陈世宾译.自由作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6][德]保罗·兴德米特.罗忠镕译.作曲技法(第1、2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王进)
中图分类号:J6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16)01-00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