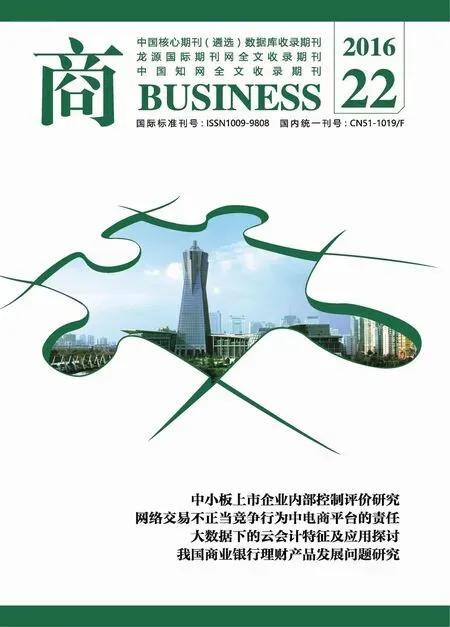从思维方式角度谈“李约瑟难题”
范铭望
从思维方式角度谈“李约瑟难题”
范铭望
摘要: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使中国人对科学与工艺方面的成就,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大白于世,然而由于他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际不清引发了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长久的讨论。要回答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内涵。论文还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讨论和探索。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思维方式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五

注解:
①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