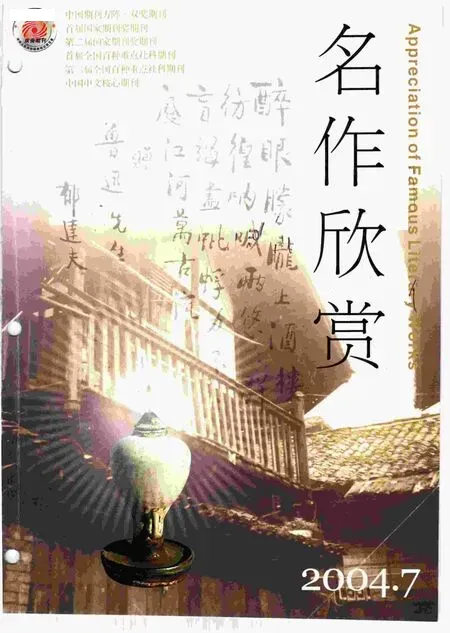漫谈“戴氏四书”的启示
北京 钱理群
漫谈“戴氏四书”的启示
北京钱理群
摘 要:戴明贤先生的“戴氏四书”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的书,沉潜到贵州历史的最深处、文学的最深处、生命的最深处,流连而忘返。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让学者自己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关键词:戴明贤 “戴氏四书” 贵州历史 学术环境
戴明贤先生“戴氏四书”中的前三本:《安顺旧事:一种城记》(初版本题为《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黑白记》,早就陆续读过了;最后一本《子午山孩 ——郑珍:人与诗》,虽然早已承蒙作者寄赠,但由于杂事缠身,一直未及拜读。前年夏天为了准备发言,赶紧补课。但天不作美,正赶上北京从未有过的奇热天气,因此,读到书中所录郑子尹写于道光八年(1828)的《酷热吟》,不禁会心一笑:“爪上流汗珠,发梢生炎风。歊气摄人髓,有声来哄哄。”真的要热昏了。但读着读着,就觉得仿佛有清风袭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心静自然凉”吧。我慢慢沉静下来,沉潜到了贵州历史的最深处、文学的最深处、生命的最深处,流连而忘返。这真是一次奇特的阅读体验,由此形成了对“戴氏四书”的第一感觉:这是让人在燠热中感到清凉,在飘浮里沉潜下来,摆脱浮躁而陷入沉思的书。
我于是浮想联翩,并决定把发言题目就定为“漫谈‘戴氏四书’的启示”。
首先想到的,是《子午山孩》的书前题词:“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周年。”前不久还收到了《贵州日报》寄来的纪念特刊,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贵州的文化建设。那么,我就先谈谈“戴氏四书”对贵州文化建设的启示。
我从一个细节说起。我把“四书”的出版时间做了一个排列:《一个人的安顺》,2004年5月;《物之物语》,2011年8月;《黑白记》,2011年12月;《子午山孩》,2013年6月。于是就有了一个很有趣味的发现:“四书”都写在最近十多年。其实明贤先生本人在《黑白记》“后记”里已经有过明确交代,说他有“文学”和“书法篆刻”两个“精神家园”,但过去都是浮光掠影,真正专心学习,“躲在里面,以享天年”,则是“从六十四岁退休以后才开始的”。在《书展自叙》里,更有具体说明:尽管早已倾心于“书道”,但总是“苦于琐务丛集,临池日减,落笔凋疏,常有‘心虽悟而手不能从’之叹。殆至戌寅休致以后,始得身闲心静,从容涵泳,时有所悟,略见进境,尝镌‘六十始学书印’,以自嘲解,亦实言也”。——读到这里,我又会心一笑:因为自己也是六十二岁退休以后,才“略见”思想与学术的“进境”的。这莫非也是一个“规律”?如果真是这样,就发人深省了。
明贤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退休后,“身闲心静”,得以“从容涵泳”,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在下文还会有进一步的发挥。不过,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吧。于是我又想起了读《子午山孩》的一点感悟。明贤先生在谈到写书的缘起时,一再强调是因为“由诗及人,觉得与这位乡贤前辈非常亲近,种种情怀,感同身受。于是产生了写他的念头”(《后记》),并且提醒读者注意:这“只是我一个人读出来的郑珍其人”,因而采用了“包含了我对郑诗的解读、感受和阐发的一种综合性散文复述”的笔法(《自序》)。我们在读这样的“解读、感受和阐发”时,会随时读到作者即兴插入的“旁白”,直接讲自己现实生活的感受,发表感想与感慨;有时候传主和作者的界限也模糊了。这其实是最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和遐想的:郑珍(1806—1864)与戴明贤(1935— ),这相距一百二十九年的黔之子,他们之间“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明贤先生也有明示:“读郑诗,则是感同身受的两难”,郑子尹“他与生俱来的兴趣是乡居、学术,而家贫亲老的情势推搡着他往学优登仕的‘正途’上走”,“然而他不肯做迎合判卷人兴趣的时髦文字,就做不成官。这个解不开的死结,有如双马分尸,令他吃尽苦头,不仅自己差点死在考棚里,更把两个孙子夭折在了赴任途中”(《自序》)。今天的明贤先生于这位将近二百年前的乡贤的“两难”,有何共鸣之处呢?尽管明贤先生和我这样的人大概早已对“学优登仕”的道路失去兴趣,但在退休前,我们还是“单位”里的人,就必然受到体制内的许多限制。记得我曾经说过,当我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时,我就得戴着某种面具,一言一行都要和我的教授身份相适应,稍有出格,就会被斥为“不像个教授”,还有“言论有自由,教学有纪律”这样的似是而非的约束令。明贤先生在作协任职时大概也是如此吧。于是我们都有了两难,陷入“与生俱来的兴趣”与身份、地位不自由的矛盾之中。因此,退休,即自我在体制的边缘化,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与解放:我说自己从此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明贤先生则说他终可“适怀”,“少年之嗜,老而弥笃,墨乡终老,其乐无极,得失毁誉,原在度外。一言以蔽之:自娱而已”(《书展自叙》)。这样“还我自由身”以后,进入生命的自适自娱状态,就逼近了文学、艺术与学术的真谛,爆发出了不竭的文学、艺术与学术创造力。这样的自适自娱状态,其实也是回到了人的“童年状态”,人类的“原生态”,在那里人的生命是和诗歌、艺术融为一体的。明贤先生说自己心中的郑子尹“像个小孩”,并将他的《郑珍传》命名为“子午山孩”,这都是大有深意的;在我的感觉里,这也是一种自我命名。这算是一种福分:明贤先生终于跳出了连子尹前辈都不能避免、今天仍然束缚着许多人的“学优登仕”的知识分子陷阱,回到了“与生俱来”的兴趣里,生活在为大自然、亲情、乡情和求知之乐所包围的“乡居”和“学术”(文学、艺术)生涯中,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又并未忘怀对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承担——进入这样的境界,“戴氏四书”就自然产生了。或许我们读戴书,最为动心的,就是这书背后的境界:不仅是人生的境界,而且是文学、艺术和学术的境界,更是生命的境界。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我们不应该夸大退休的作用。如果一切取决于退休,明贤先生的经验,对大多数还没有退休的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我们还需要再做两个方面的讨论。
我们在前面引述了明贤先生的一段话,说他在体制内感到的最大不适就是“苦于琐事丛集”。这一点,今天仍在体制内的朋友就体会更深了:整天忙于申请项目,忙于填表,忙于开会,忙于应付各种考核、考查,已经完全坐不下来,没有时间和闲情来搞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了。这背后就有一个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如何进行“文化(文学、艺术、学术、教育)体制改革与建设”的问题。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我对北大和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担忧:我们现在对学术和教学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搞计划经济、群众运动的方式。如规定在某个时间内“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典型的“计划指标”;提出“精品工程”,就是由某位名教授挂帅(大多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连所用的词汇(“工程”“作战”之类),都是工业生产和战争用语。我还谈到,这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投资,一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无用”“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这类“学术工程”就是“花钱工程”,至少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其弊端是显见的:劳民伤财不说,还败坏了学风,导致严重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更为腐败大开其道(《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文收《论北大》)。十几年过去了,这些问题越演越烈,随着国家对文化投资的加大,这样的领导方式又扩大到了文化领域:照样地定指针,搞“花钱工程”。坦白地说,多年的经验,使得我一听说政府加大对某样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就总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也可能是新的灾难的开始。现在,我面对“贵州文化大发展”,也抱有同样的心情。我很清楚,如果按照这样的搞计划经济、群众运动的方式,按战争思维来领导文化建设,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绝不会产生“戴氏四书”这样厚重的,可以传之后代,成为贵州文化积淀的真文学、真艺术、真学术的,所炮制的只能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其诞生之日即是被人们(包括炮制者)抛弃之时。记得当时我提到了赵丹在离世前说的那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我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说的。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想起了赵丹对血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不是不要领导,而是要真正按照文学、艺术、学术的规律去领导。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诸位讨论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从总结“戴氏四书”的经验中,提出文学、艺术、学术健全发展的几个基本规律呢?为了抛砖引玉,我想谈两点。
一是文学、艺术、学术是不能像生产、打仗那样“组织”“定计划”,搞“工程项目”“大兵团作战”的,它们本质上都是个体的精神劳动。我注意到,明贤先生在前述《贵州日报》组织的关于贵州文化发展的笔谈里特意谈道:“(文学、艺术、学术的)原创是一种个体精神劳动,写什么、如何写、何时写,都取决于作者的气质、经历、思考、趣味等因素的化合,带有相当的或然性。”(见《贵州日报》2013年7月12日C8版)这里所说“个体性”与“或然性”都是深刻道出了原创性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是明贤先生对他自己的以“戴氏四书”为代表的创作经验的一个准确概括。不能想象,“戴氏四书”能够采取“文化工程”的方式,默认目标,组织队伍(哪怕是由明贤先生挂帅),统一构思,先拟大纲,规定时间与进度,按计划完成——说句笑话,单是“规定时间与进度”这一条,就足以将明贤先生吓跑。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会有一些集体项目,像我们正在进行的《安顺城记》,就如我所说,是所谓“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但这样的“联合”,也是以“个体性”为基础的;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预感到了其中的难处,即所谓“出众人之手,成一家之言”的矛盾,最后落实下来,执笔的恐怕也会是少数人,也就是即使是集体项目,也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个人性”。当然,对所谓“个人性”也不能绝对化,明贤先生在上述笔谈文章中还讲到文学、艺术、学术的“个人性与社会性”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另做讨论。
其二,文学、艺术和学术绝不能像营销商品一样讲“速效”,它们本质上都是“慢”的活计,是急不得、快不得的。这样才能如明贤先生所说,“身闲心静,从容涵泳”。这是文学、艺术、学术创造必须有的心态和生命状态。我在为《一个人的安顺》所作的序里提到安顺城和人的特点,就在“气定神闲”四个字;明贤先生是最得其神韵的,而且把它有机融入自己的文学、艺术、学术创造里。今天我们总结“戴氏四书”的经验,就应该自觉地将“气定神闲”发展为一个文学、艺术、学术传统,一种文化精神,以之指导今天的贵州文化建设,以至整个贵州的发展和建设。在我看来,这是医治浮躁、虚夸,以及过度追求高速度带来过度紧张与过度破坏的“现代文明病”的对症良药。何况这本身就是贵州老百姓创造的生活与精神传统,将其继承与发展,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不合时宜之论。前面提到的《贵州日报》纪念专刊也发表了我写的文章,编者代拟的题目“小心翼翼地善待贵州历史文化”是符合我的意思的,但却做了一处修改:我的原文是“建议贵州的发展要遵循‘开始要早,步子要慢;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的原则”,发表时将“步子要慢”删去了,显然是觉得这一提法有违“现代”精神。
这正是我深感悲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诸如文学、艺术、学术的个体性及其慢的特质,其实都是常识;我们所主张的,无非是回到常识,或者说按照常识来发展贵州文化。但这样的主张与呼吁,在今天社会里是没有人听的,真的像当年鲁迅所说,有如“一箭之射入大海”,连一点微澜也兴不起。明贤先生一再说“郑子尹寂寞之至”,是内含着深广的历史与现实忧愤的。
尽管说了白说,但不说白不说,我们仍然要呼吁: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常识的、健全的文化发展模式、领导方式。在十年前所写的关于大学教育和学术改革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让学者自己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今天“戴氏四书”的成功,大概是能够为我的这一主张做凭证的:正因为没有人管,听任明贤先生凭着他的兴趣和心之指引,悠悠闲闲写自己的文章,积十数年之功,“精品”就出来了。当然,这是无心栽花花自开,没有人管,是因为他退休了;但我们能不能加以推广,对还在位的教师、艺术家、学人,少管一点,至少少搞点工程,少定点指标,行不行呢?
大家不难看出,我所讲的“宽容”“宽松”和“宽裕”,是从朱厚泽著名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论那里来的。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关于文化工作的一点思考》,收《朱厚泽文存》,1986年7月)这当然有当时的特定背景,其主要精神是要走出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窠臼;但“三宽”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宽裕”倒是我的“发明”,大概是反映了在经济发展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要求吧。我今天重提这些,是想做一个提醒:朱厚泽是贵州人,他的思想,包括文化思想,是贵州当代思想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部分,我们发展贵州文化,就必须注意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资源。明贤先生在前述《贵州日报》关于贵州文化发展的笔谈里,特意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呼吁“感性与理性结合”,这是极有远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学习和研究朱厚泽理论遗产入手?这是极端重要而迫切,又是大有可为的一件贵州思想文化建设的大事。我在下一步准备就此做些研究。这里只能出一个题目,供大家讨论。
以上的讨论,都是关于发展贵州文化的领导方式和发展模式,我们这些普通教师、文人大概只能呼吁,在具体实施层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放弃,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体制,更不能因此而陷入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好像体制不变,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事实上,做事情的完全理想的环境和条件是不存在的,相对理想的环境和条件则是可以争取和创造的。而前人大都是在不理想或不尽理想的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一定成效的。我因此注意到,“戴氏四书”所写,基本上是“乱世”下的人的命运、生存之道:《子午山孩》里清代(19世纪四五六十年代)的内地灾祸、战乱,《安顺旧事:一种城记》里抗战时期(20世纪40年代)的国难,《物之物语》里“文革”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乱。而作为写作“四书”的背景与动力的,却是作者面对的21世纪初的所谓“太平盛世”里的另一种紊乱,即人心之乱,人性秩序的破坏和混乱。明贤先生所关注与书写的,是乱世里的普通百姓、普通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里对人性及民间伦理的坚守,所显示出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以及经过动乱的磨炼而升华出来的精神质量。前面提到我在《一个人的安顺》序言里所提炼的“气定神闲”四个字,其实还有一个修饰语:“看惯宠辱哀荣”,这样,“气定神闲”就有了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历经乱世,饱受磨难,看惯看透,就将一切置之度外,“气定”而“神闲”。我们因此可以说,所谓“戴氏四书”,实际上是透过几个散点透视,书写一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贵州人史、精神史;贯穿其中的,正是这“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贵州文化精神。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精神,应该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贵州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其神韵所在。明贤先生显然是要通过自己的开掘、再现,召回已经被遗忘的历史精神,作为应对现实生活里的人性、人心危机的精神资源,可谓用心良苦。
我还要强调的是,明贤先生是把自己的主观精神渗透于他所发现的贵州文化精神的,因此,也是一个自我发现。这样,我们就还需要讨论“戴氏四书”里所显示的“戴氏精神”。我想从明贤先生自称“散漫的人”(《一个人的安顺》后记)里,提升出一个概念,叫“散淡精神”。这可以说是“气定神闲”的贵州文化精神在明贤先生身上的体现。前面所引明贤先生的话,“得失毁誉,原在度外,一言以蔽之:自娱而已”(《书展自叙》),其实就已经将他自己坚守的“散淡精神”做了很好的概括。我所看重的,是散淡精神的“破障解蔽”作用:活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常受到种种束缚,有着种种障蔽。比如,多少文人、学者为名缰利锁所缚,不能挣脱;许多人更是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散淡精神强调“淡泊自守”就是一剂对症之药:要守住人的本性、本色,切不可为名利熏心失性。与追名逐利相联接的,还有急功近利,这也是束人之网,正需要“不争一时一事”“一切听其自然”的散淡精神来解脱。还有自视太高的自弊,也可以用“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一语自警,如此等等。和明贤先生多有接触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他已经把散淡精神的这些为人处世与自处的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了。这样,他就摆脱了一切有形无形、外在与内在的壁障,获得了自由。很难想象,没有自由心,明贤先生能写出“戴式四书”这样超越、超脱的大书。“散淡即自由”,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警示,也是激励:我们即使做不到明贤先生那样洒脱,总可以尽量拒绝诱惑,多少保持一点内心的安静与自由吧。
在我的理解里,“戴氏四书”是“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的自觉尝试。其要点有三:
首先,明贤先生说,他要写一个“巨变叠起的大时代中的一堆渺小的‘个案’”(《〈物之物语〉后记》),他为自己著作的“定位”是“写‘人’的文学文本”(《〈子午山孩〉自序》),他还说自己的“笔下只有小人物的蝼蚁生涯”,因为在他的历史观里,“不能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黔首黎庶,与强势者同样是构成历史的成分,且能补充官修史册的空隙”(《〈物之语〉序》)。这些都是在强调文学观察、把握、书写世界的特有方式:它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其中又有五个层面,一是个体的人的具体存在,而非群体的概念的人(“人民群众”之类)的抽象存在;二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而非孤立在时代之外的想象的存在;三是在历史细节里所呈现的人的感性存在,因此具有原初性、复杂性、丰富性、偶发性,而非经过理性过滤的某种理念的化身的存在;四是以揭示人的精神、心灵为重心,而不停留于对人的事功的简单描摹;五是关注被官史所忽略的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的存在。“戴氏四书”就是这样一部人史、心灵史,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小人物史。
其二,文学的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极强的形式感。明贤先生在他每一本书的自序和后记里,都要谈到,他写作中,最费心思、再三踌躇的,就是寻求与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内容)相适应的结构、叙述方式,在“找不到惬心的形式”前,即使全部材料准备好了,他也绝不动笔(《〈一个人的安顺〉后记》,《〈子午山孩〉自序》)。我读《戴氏四书》,最为感佩的,就是明贤先生对叙述文本、学术文体的自觉试验:从《安顺旧事:一种城记》的“散文笔调的文化志”,到《物之物语》的“借物写人”,让小对象做“一段历史的发言人”,到《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的“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及诗,人诗共见”。每有一作,必在形式上有新的开拓,这样绵绵不绝的创造力,应是“戴氏四书”最为独特,也最具魅力之处。
明贤先生还有一个着力点,即是语言的试验。在《〈黑白记〉后记》里,他这样谈到自己的语言追求:“书中文字,或文或白,或半文半白,视感觉为准,各适其适,不求划一。”
这句话里包含了三层意思,都很耐琢磨。一是文字里的文白杂糅。记得我在《一个人的安顺》的序言里曾特意赞扬了“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这表明,明贤先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当年周作人所说的“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创造出“有涩味和简单味”的“有雅致的俗语文”(《〈燕知草〉跋》)。二曰“视感觉为准”。明贤先生《黑白记》里有《找感觉》一文,说写字作文,如无感觉就“木然无生气”;写着写着,“突如一口仙气袭来,枯木逢春,枝青叶绿,只须‘跟着感觉走’,怎么写怎么舒服”。这是深知自由驱遣语言的真趣味之言。三曰“各适其适”,就进入化境了。
其三,“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本身,就包含了文学与历史,或许还有哲学的交融。明贤先生在《〈一个人的安顺〉后记》里,还谈到了他对文化人类学的借鉴。这里就有了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以及相应的修养问题。明贤先生又曾讲到“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在书法审美上的体现,涉及‘字内、字外’多个方面。它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积累,与你的艺术生命相伴直至终点的过程”(《〈书谱〉:书论宝典》,收《黑白记》)。这当然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经验之谈。我们读“戴氏四书”,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明贤先生“整体文化素质”中的“通”:不仅是古今中外文化之通,更有各种艺术门类(文学、书法、戏曲、音乐、美术)之通。明贤先生未必对每一方面都做到精通,但他悟性极好,凡有涉猎,即能感悟其精髓,而全部纳入囊中,融会而贯通。这样的大文化视野和素养,应该是“戴氏四书”底蕴深厚之处,一般人难以企及,却是发展贵州文化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说,贵州文化之长,是其民间、民族文化根底的深厚;但历史典籍文化积累不深,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短处。这导致了今天贵州的文人与学者文化素质、修养上的不足,也构成了贵州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明贤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突破,他获得了成功。在我看来,最难能可贵的是,明贤先生在扩展文化视野,提高文化素养,“永无止境,不断积累”上的高度自觉,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我们赞叹明贤先生不绝的文化创造力,但不要忘了这是建立在他的从不懈怠的学习、广泛的吸取基础上的。他不仅有过人的天分,更有少见的勤奋。我们纵然没有明贤先生的天分,但他的勤奋总是可以学习的吧,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以勤补拙”吧。从广义的角度说,明贤先生的“戴氏四书”也是“以勤补拙”:以后天的学习、努力,补贵州文化某种先天的不足。
关于“戴氏四书”,我已经说了不少,但仍意犹未尽。朋友们可能早已发现,我一谈及贵州、贵州文化、贵州友人的贡献,就滔滔不绝,欲罢而不能。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样持续的热情来自何处。明贤先生倒有一个解释,是我可以认同的。他说,除了他对安顺的感情,还有一面,就是证明了我们安顺的魅力。“从全国来看,安顺的历史也不是最早的。安顺的文化来说,也不是最突出的。但有一条,各有各的特点。你的文化代替不了我的文化,你再古,也代替不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魅力所在,特色所在。”(见《〈安顺城记〉通讯》第一期)这使我想到自己的特殊位置,我和贵州、安顺的关系是“既在又不在”:我既“在”其中,就能够把握与感觉贵州、安顺文化的某些“外边人”难以体味的神韵;但我又“不在”贵州、安顺,就能以全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的眼光来发现“本地人”难以看到的贵州、安顺文化的特殊魅力与价值。而本地人往往“身在黔山,不识黔山真面目”,明贤先生强调要从自己“代替不了”的“特色与魅力”出发,来建立“文化自信”,是抓住了要害的。贵州文化绝对是个宝,是贵州的优势,而不是包袱。我多次说过,当下的世界,正面临着全球性的文化危机与文化转机,我们需要抛开一切既定成见,进行世界文明和现存各种文明形态的全面反省和重新认识。在这样的新的视野下,对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贵州文化,一定会有新的观照、新的发现。邵燕祥先生评论说,明贤先生的《子午山孩》发现了“郑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诗的巨大存在,一经这次发现,将永远不会被中国人忘记或忽略”;我们也可以说,“戴氏四书”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研究贵州文化和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对贵州和贵州文化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这是可以期待的。
供 稿:“小众”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xiaozhong_xuanwu
作 者: 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