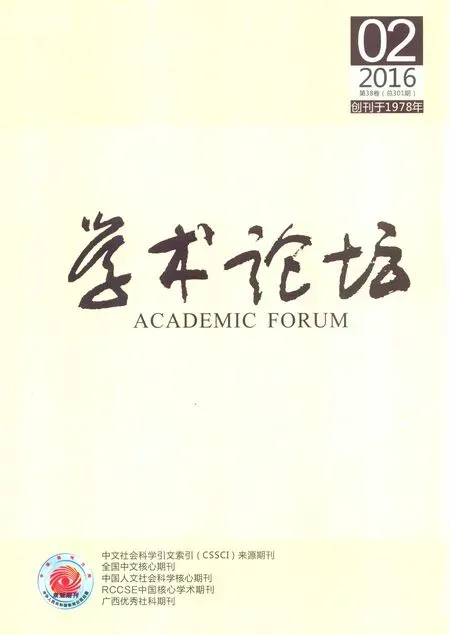农地流转主体的交易成本——基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的比较
蒋永甫,张小英
农地流转主体的交易成本——基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的比较
蒋永甫,张小英
[摘要]农地流转主体是指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农地流出方主体、农地流入方主体和从事中介服务的中介方主体。在土地需求推动的农地流转中,农地流转主体主要是指农地流入方主体。农地流转交易费用也主要由农地流入方主体承担。农地流转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的农地流转主体在农地流转交易中所承担的交易费用存在差异。为了探究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差异,主要对四个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分析。在对不同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进行定性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矩阵法和坐标法比较了不同的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并据此提出降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创新农地流转主体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地流转;流入方主体;交易成本
一、文献与问题
在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一直引起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一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探究了制度安排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关系。邓大才(2009)认为制度安排既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也可以诱发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农地流转的价格。在村庄制度、习惯法和国家制度这三种制度安排中,村庄制度安排对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影响最大,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最小[1]。黄振华(2010)指出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机制的产生是国家制度安排和产权不完整共同作用的结果[2](P230)。Chen Ping-nan(2012)提出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产生的制度根源是土地产权制度,交易成本进而又影响农地流转主体的行为与决策[3]。二是从农地流转模式角度分析不同模式的交易费用。伍振军等(2011)比较了四种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的交易费用:政府扶持市场参与主体(M模式)、政府扶持需求主体(M-模式)、政府扶持流转中介(S+模式)和自发流转模式(S模式)[4]。三是从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角度探讨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关系。黄英良(2005)通过对市场组织、政府组织和专门的中介组织这三种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的比较,发现介于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的中介组织是最有效率的,应通过设立多种形式的中介组织来提高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效率[5]。刘涛(2008)认为微观的农民个体存在客观事实上的异质性,使得分散的农民个体之间的合作成本和组织成本过于高昂,农民个体很难进行组织化,导致农民个体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需要中介组织(如村集体)介入,降低其交易成本[6]。
研究表明,不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可以通过创新农地流转模式和提供中介服务来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但问题在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往往是由农地流转主体来承担,由于主体异质性的客观存在,如何测量不同农地流转主体的农地流转交易成本便成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一般而言,农地流转主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农地流转主体是指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农地流出方主体、农地流入方主体和从事中介服务的中介方主体。狭义的农地流转主体仅指农地流入方主体。在需求带动型的农地流转中,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由农地流入方主体来承担。
二、农地流转主体交易费用的理论
权利的转让、获取和保护所需的成本叫做“交易成本”[7](P2-3)。农地流转交易费用是指农地流转主体为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而付出的成本,包括流出方主体、中介组织、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在需求带动型的农地流转交易中,农地流转交易费用主要是指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
(一)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
罗必良(2008)提出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称为“技术型交易成本”;二是交易制度,称为“制度型交易成本”[8]。高帆(2007)提出交易技术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围绕物流的交易技术,例如仓储、运输等技术,先进的物流技术可以节约交易时间,降低物流费用;其次是围绕信息的交易技术,包括信息收集、传播等方面的技术,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加快信息传播、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信息搜寻和信息处理成本;第三是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是指与交易有关的投资和融资技术,具体包括结算、汇兑、资本运作等现代金融服务,这些现代金融服务需要现代金融技术的支持,先进的现代金融技术可以提升交易速度和质量,降低交易成本;最后是围绕劳动者的交易技术,包括教育和培训等,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劳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9](P82-89)。交易制度也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凡勃伦(1981)把制度理解成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10](P149-150)。制度可以有效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交易制度是规范交易行为的规则体系,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强调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产权制度是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只有物品或劳务的产权清晰才有可能进行交易,明晰产权对减少交易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的明晰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11]。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中,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农地流转交易与企业交易并不同质,影响两种交易成本的因素也不同。农地流转交易的商品与企业不同,不需要考虑交通运输条件对农地流转主体交易成本的影响;农地流转交易涉及的资金流技术主要是地租的支付,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足够满足该技术需求,资金流技术对农地流转交易的影响较小。由于我国农地流转交易的流出方主要是农户,流入方受教育水平也并非很高,交易双方的教育水平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影响并不显著。产权是否明晰和稳定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有研究表明: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说,国家对农民的土地产权保护是严格的,农民的土地产权在法律层面越来越完整和稳定。当前农地产权较为完整和稳定,并没有对土地流转造成影响[12]。
企业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并不同,但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有自身的影响因素,包括是否具有中介组织、农地的细碎化程度、流转规模、农户的流转意愿等。根据实地调研和查阅文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第一,是否具有中介组织。中介组织能够提供各种服务,如交易地标的基本信息等服务,产生服务的规模效益,降低流转主体的信息搜集等交易费用;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是农地集体所有的代理者、是农地信息的拥有者、是农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是农地流转的有效监督者,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为流入方主体综合性服务,能够降低流入方主体的信息搜集等费用。第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法(熟人社会)、血缘关系等,邓大才运用全国21个省市的农地调查问卷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熟人关系、邻里关系、血缘、姻缘关系具有节约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作用[1]。第三,农地的细碎化程度。农地的细碎化程度越高,地块越分散,涉及的农户越多,集中的难度越大,谈判的时间成本越高。吴记峰、吴晓燕(2011)对四川偏远丘陵地区的考察发现:四川偏远地区农地过于分散,细碎化程度高,地块面积较小,这就给农户成片租入土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想成片租入土地,流入方必须一家一户、一块地一块地进行谈判,一旦成片地区有一户不出租土地或对出租条件不满,都会造成交易的失败,使得租入方支付大量的沉默成本[13]。JoshuaM.Duke等(2004)提出农地严重细碎化状态下的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14]。第四,农地的流转规模。流转的规模越大,涉及的农户越多,需要搜集的信息范围越广、需要集中的土地越多、谈判时间也越长,同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增大,导致信息的搜集、土地集中、合同签订、确保合同执行的成本也越高。第五,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越高,流入方主体所花费的成本就越低。反之,就有可能出现“插花地”,为了连片集中土地,流入方主体需要与个别农户进行额外谈判并将土地置换出去,这就导致流入方主体的土地集中、合同签订成本的增加。
(二)交易费用的构成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指度量、界定产权的成本,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定立交易合同的成本,执行交易的成本,监督违约并对之制裁的成本,维护交易秩序的成本[15](P24-27)。具体到我国的农地流转中,交易成本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信息搜集、甄别、选择的费用。流入方主体进入交易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入市费用,主要包括寻找并发现潜在交易对象、获悉交易物品基本信息等费用。农地流转的信息搜集成本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成熟度、农地流转规模成负相关。农地流转是否具有有形和无形市场,决定了流入方主体是否需要支付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三级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完全建立,流入方主体主要依靠村集体或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农地的基本信息,这有利于减少信息搜集的成本。通过中介组织获悉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农地的基本信息也能够降低信息农地流转前的交易成本。
二是土地集中的费用。土地集中的费用主要是指土地连片集中所需的时间、资源等成本。流入方主体进行土地连片集中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中介组织如村集体进行土地连片集中,委托村集体与分散的单个农户进行协商谈判并签订流转合同,这就省去流入方主体分别与单个农户进行谈判再集中土地的环节,极大地减少了流入方主体集中土地的成本。另一种是流入方主体与意向流入的片区的单个农户单独分别进行谈判,该种方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一般是小规模流转土地的流入方主体会采用此种方式。
三是签订合同的交易费用。由于合同内容的确定与合同的成功签订密切相关,本文将合同内容的确定成本也计入签订合同的交易费用。在合约签订前,农地流入方主体需要针对农地的租金、租金的支付方式、农地流转的期限、用途、土地的基本信息(如面积等)、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与流出方进行磋商。其中,农地流转价格、流转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确定涉及双方的经济利益及今后农地的处置权问题,因此需要反复进行谈判和磋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且双方权利义务界定的清晰度将影响到确保合同执行的费用。根据对河南、山东两省的调研结果显示:75.23%的流入方认为租金的确定是谈判的重点,也是产生谈判费用的主要原因[16]。
四是确保合同执行的交易费用。确保合同执行的交易成本属于农地流转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是指农地流转合约的执行成本以及违约行为出现后的调解、裁决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成本是农地流转违约的裁决和调解成本。农地流转的规模越大,流入方主体面临的不确定越大,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高,确保合同执行的交易费用可能越高。通过中介组织进行农地流转,可以为交易后发生的违约纠纷提供裁决主体,有利于降低确保合同执行的交易费用。
用Cis,Clc,Cce,Cse分别表示流入方主体的信息搜集、土地集中、合同签订、确保合同执行的交易费用,其总交易成本的线性函数为:

我国的农地流转是需求带动型的,从需求带动型的角度来看,我国较为典型的一次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过程如下(见图1)。

图1
三、各类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比较
本文是在假设流入方主体处于同一区域的情况下,尝试对各类流入方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小进行比较的。主要从能否接触和利用中介组织、流转规模、非正式制度这三个方面比较流入方主体交易成本的大小。
(一)种养大户的交易费用
种养大户一般是指围绕某一种农产品从事专业化生产,从种养规模来看明显大于一般农户的承包经营户[17]。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专业种养技术,同时种养面积只有达到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要通过流转土地进行经营,才能成为种养大户。种养大户大都是内生于村庄或是毗邻区域的经济能人,其通过血缘、地缘、姻缘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等社会资本进行土地流转,具有高信任度,能够减少甚至省去农地流转中的信息搜集、合同签订及确保合同执行的成本,但还需花费一定的成本进行土地集中。由于一般种养大户流转土地的面积较小,获得土地流转补助需要达到一定的流转面积和流转期限,因此,种养大户获得土地流转补助的可能性也较低。(可以将政府对流入方主体的土地流转补助看成是政府承担了部分流入方主体消除合同执行不确定性的交易费用[19]。)那么,种养大户总的交易费用为:TC种= f(Cis,Clc,Cce,Cse)=a1Cis+b1Clc+c1Cce+d1Cse(0<a1<1,0<b1<1,0<c1<1,0<d1<1)。
(二)家庭农场的交易费用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8]。家庭农场具有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特点。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家庭农场看作是种养大户的升级版[20]。家庭农场的交易费用与种养大户的交易费用基本一致。家庭农场利用内生的社会关系进行土地流转,省去了搜集信息、合同签订和确保合同执行的费用,降低了土地集中费用[21]。一般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面积较小,获得土地流转补助需要达到一定的流转面积和流转期限,因此,家庭农场获得土地流转补助的可能性也较低。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主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识较低,合同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的界定很难达到完整和清晰,因此,容易出现土地流转后的纠纷,导致家庭农场尤其是没有借助中介组织进行农地流转的家庭农场为确保合同执行的成本增加。那么,家庭农场总的交易费用为:TC家=a2Cis+ b2Clc+c2Cce+d2Cse(0<a2<1,0<b2<1,0<c2<1,0<d2<1)。
(三)合作社的交易费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农地流转主体。作为农地流入方主体的合作社主要是指集中土地并进行规模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即农户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入股土地由合作社进行经营,农民可以获得土地的租金和股权分红。合作社的流转面积较大,流转年限也较长,一般能够享受政府的农地流转补助。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和利润优势使得农户主动将土地的信息传达给合作社,使得其信息搜集的费用比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低。从实践中看,合作社组织原则和利润优势使得农户能够自愿迅速集中土地,有效降低土地集中费用[22]。农户流转土地最大的顾虑是收不回土地,合作社的入社原则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收放权,降低了农户违反合同、干扰合作社经营的可能性,减少了合同签订及确保合同执行的费用。那么,合作社总的交易费用为:TC合=a3Cis+b3Clc+c3Cce+d3Cse(0<a3<1,b3≈0,0<c3<1,0<d3<1)。
(四)龙头企业的交易费用
龙头企业是指具有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势的农业企业,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大多属于外来者,大多会借助中介如村集体与农户进行洽谈和集中土地,这就减少了龙头企业信息收集、土地集中的费用。鉴于龙头企业的外来身份,农户对其是否会按时、完整归还土地、地租是否与市场或其他村相等产生怀疑,因此在确定土地价格、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等方面需耗费大量的时间,提高了签订合同的费用。有学者对农户与农户之间、合作社引导、龙头企业引导三种农地流转模式“进行一次农地流转所花费的时间”进行比较后发现:农业公司就农地价格、承让方是否能改变土地性质和种植模式等关键问题与农户进行谈判所花费的时间最高[23]。龙头企业的土地流转面积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可获得土地流转补助,且其能够借助中介组织进行合同纠纷的裁决,降低了其确保合同执行的费用。但由于其主要是以自身盈利为目的,且农户没有土地的收放自由权,因此当农户对租金不满、觉得龙头企业获利过高时就会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干扰。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龙头企业需邀请村集体与农户进行再谈判,这就需要耗费较高的时间成本。那么,龙头企业总的交易费用为:
TC龙=a4Cis+b4Clc+c4Cce+d4Cse(0<a4<1,0<b4<1,0<c4<1,0<d4<1)
本文将通过建立流入方主体的向量矩阵和交易费用坐标系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
设四个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矩阵(Cis,Clc,Cce,Cse),那么四个农地流入方主体对应的交易费用比例矩阵为C=(C1,C2,C3,C4),则种养大户= (a1,b1,c1,d1)T;家庭农场=(a2,b2,c2,d2)T;合作社= (a3,0,c3,d3)T;龙头企业=(a4,b4,c4,d4)T。并且满足以下不等式:

设四个主要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矩阵D=(D1,D2,D3,D4),可以得出(D1,D2,D3,D4)= (Cis,Clc,Cce,Cse)×C,结合以上不等式(1)的约束条件,可以将四个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如下表示:

在满足不等式的情况下,可以得出:

可以得出:0<TC合<TC种≈TC家<TC龙
四个流入方主体的交易费用比较坐标系如下:

四、基于交易费用的农地流转主体创新
(一)构建完备的市场中介组织主体
在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中,市场中介机制较为完备,土地流转的效率要高于通过地方政府、村集体和人际关系网络流转土地的效率,因此构建完备的市场中介组织体系是降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关键。首先,应建立多元化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主体。在我国农地需求不足、农地流转率不高以及中介组织盈利前景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力度支持市场化的民间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对其进行资金和政策倾斜。其次,打造多层次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主体。当前政府主导的农地流转中介机构主要位于省或市一级,县、乡一级的土地产权交易中心较少,且人员配备不足、基础设施较差,使得农地流转主体的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建设和完善县、乡两级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可以减少农地流入方主体的交易成本。最后,健全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服务内容。从农地流转服务需求的角度而言,完整的农地流转交易需要中介组织提供信息发布、信息整合、信息匹配服务、土地价格评估服务、签订合同的服务、政策和法律咨询服务、纠纷裁决和调解的服务等。健全的农地流转服务内容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交易的不确定并减少交易成本。
(二)合理利用村庄差序格局优势
“差序格局”是用来解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概念,它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其对今天的很多乡村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村庄经济能人种养经验丰富、资本较为雄厚,其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意愿较强,大多会成为村庄的种养大户或成立家庭农场。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中国农业经济学年会上指出:在我国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种养专业户、家庭农场是骨干,可以有效率地集中农业生产要素,是今后商品农产品特别是大田作物农产品的提供者,是进行合作经营的核心力量[24]。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新增的农业补贴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倾斜。由此可以看出,积极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内生于村庄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对村庄的土地信息和人际关系较为熟悉,农户对其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因此可以利用其地缘和亲缘优势,节省获取、甄别、选择信息的费用、减少土地集中、签订合同和确保合同执行的费用。
(三)降低龙头企业交易费用,加快农地流转进程
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现代农业是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和发展的,没有龙头企业也就不可能真正建成现代农业[25]。但从交易费用分析中发现,龙头企业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承担着较高的交易费用。高昂的交易费用降低了龙头企业的农地流入意愿。完善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笔者认为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地流转方式是龙头企业降低交易费用,进行农地规模流转的最优选择。该种模式通过合作社将土地集中起来,减少了龙头企业进行信息收集、土地集中的费用。龙头企业并未直接租赁农户的土地,节省了与单个农户签订合同的费用,同时避免了龙头企业直接租赁农户土地将会面临的法律纠纷和失地风险。此外,入社农户不仅获得保底的租金,还可以获得股权收益,这也降低了农户退社的可能性,降低了龙头企业为确保合同执行所花费的成本。
(四)推行“小块并大块”,降低农地流转成本
土地细碎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土地细碎化不仅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增加了农地流转的成本。广西龙州县的“小块并大块”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小块并大块”即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农户将分散的责任田集中整合后,重新分配土地经营权,促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目标。并地后农户分散的土地将连片集中,田埂大量减少,有效增加耕地面积3%-5%,连片集中后的农地有利于改善耕地基础条件、完善排灌渠道和肥力培植等,能够基本建成“田成方、路成行、沟相通、渠相连”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目标。农户并地后再将农地流转给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将能够大大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搜寻、土地集中、合同签订和确保合同执行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
[参考文献]
[1]邓大才.制度安排、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价格[J].中州学刊,2009,(2).
[2]黄振华.大陆农地流转的基本格局[A].徐勇,赵永茂.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Chen Ping-nan.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我国农地流转的困境[J].广东农业科学,2012,(13).
[4]伍振军,等.交易费用、政府行为和模式比较: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4).
[5]黄英良.交易成本和农地使用权流转组织形式的选择[J].理论学刊,2005,(10).
[6]刘涛.农地流转需要中介组织[J].中国土地,2008,(10).
[7]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罗必良,吴晨.交易效率: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视角——基于广东个案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8,(2).
[9]高帆.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0]凡勃仑.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局,1981.
[11]彭真善,宋德勇.交易成本理论的现实意义[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4).
[12]唐浩,曾福生.现实中的农地产权情况还影响农地流转吗?——湖南怀化中方县土地流转的现状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8,(11).
[13]吴记峰,吴晓燕.农地流转:从必要到现实有多远——来自四川偏远丘陵地区的观察[J].农村经济,2011,(5).
[14]Joshua M.Duke,Eleonora Marisova,Anna Bandlerova,Jana Slovinska.Price Repressionin the Slovak Agricultura Land-Marker[J].LandPolicy,2004,(21).
[15]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6]郭斌,李伟.基于交易效率的农地流入方交易费用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4,(2).
[17]王春平.关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几个问题[J].新农业,2013,(17).
[18]杨成林.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
[19]伍振军,等.交易费用、政府行为和模式比较: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4).
[20]滕明雨,等.成长经验视角下的中外家庭农场发展研究[J].世界农业,2013,(12).
[21]周娟,姜权权.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特征及其优势——基于湖北黄坡某村的个案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22]孔祥智,伍振军.土地流转的有益探索——浙江省平湖市渡船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调查[J].农村经营管理,2010,(7).
[23]吴晨.不同模式的农地流转效率比较分析[J].学术研究,2012,(8).
[24]陈晓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中国农业经济学年会上的致辞[J].农业经济问题,2014,(1).
[25]李炳坤.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责任编辑:刘烜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集体产权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机制主体创新研究”(11YJA810006)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6)02- 0043 -06
[作者简介]蒋永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英,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