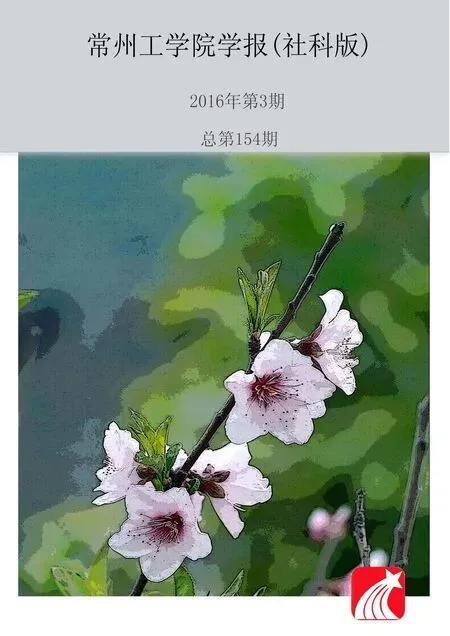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的释明及启示
李亚楠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的释明及启示
李亚楠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释明是大陆法系中的特有制度,随着两大法系诉讼理论的交融,美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尤其是审前程序中也出现了释明倾向。但是,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的释明有别于大陆法系国家中的释明,它主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申请发起,法官多发挥间接释明的作用,且配有强制性制裁措施,很好地保持了法院的中立,提高了诉讼效率。我国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释明制度,在引入释明制度时应借鉴美国经验,理性运用法官释明权,维护法院中立地位,促进诉讼效率。
关键词:美国;审前程序;释明;诉讼效率;法院中立中图分类号:D915.2
一、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的释明
释明制度最初来源于德国,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理论中,其基本含义是法院引导当事人说明、澄清特定事项以及明确其主张[1]129。其产生的原因是为防止应当得到胜诉的当事人因辩论能力和诉讼技巧上的弱势而未获得胜诉。美国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比大陆法系国家更容易造成因辩论能力和诉讼技巧上的差异而判决结果不公的情况,以罗斯克·庞得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们也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点[2],于是,美国开始矫正过去那种“放任不管”的观念,释明的土壤就这样在美国滋生了。除了为克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弊端外,美国的释明制度还有对效率价值的追求[3]157。根据法官的释明,当事人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握核心问题,明确主张,澄清特定事项,提交关键证据等,从而诉讼更有效率。美国的审前程序是民事诉讼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在能够进入审判前,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审前准备[4],因此,释明几乎都集中在审前程序中,甚至有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释明只限于审前程序阶段[5]。
(一)诉答程序中的释明
美国的诉答程序主要经历了普通法诉答、法典式诉答和联邦式诉答三种形式。目前,美国联邦法院和采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州所适用的是联邦式诉答。根据联邦式诉答的要求,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仅需写明管辖权依据、有权获得救济的理由和明确的诉讼请求即可,对事实细节的要求不高。因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文书含糊不清或不明确以致于当事人不能合理地准备应答时,当事人可以提出申请更明确陈述的动议。动议申请应指出起诉状的瑕疵以及想知道的细节。如果法院命令更明确的陈述,该命令未在发出通知后14天内或法院指定的时间内得到遵守,法院可以删掉该诉答文书中的内容或作出其他合适的命令①。也就是说,由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应要求命令对方当事人做进一步的明确陈述,这其实是一种释明。
(二)发现程序中的释明
因发现程序缺乏直接的司法监督,该程序容易被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过度滥用。为克服这一弊病,近年来法官被要求加大对发现程序的控制[6]176,而释明其实是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指挥权的行使[7],其在发现程序中的地位自然也更重要。
在发现程序中,当事人是主体,整个发现程序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搜集证据、整理争点,法官几乎不插手。当当事人认为对方提出的发现请求超出了发现范围、与案件并不关联或者待发现事实属于保密范围等向法官提出异议时,或者要求发现的当事人认为对方当事人的回答不充分就回答的充分性问题请求法院作出决定时,法官才介入发现程序。这时,法官就能够释明当事人进一步说明理由、澄清特定事项、提供书证或物证等了。
(三)审前会议中的释明
在审前会议中,法官主持程序以确保审前程序公正进行,并确保通过审前程序有效地将案件推入和解或审判。法官的释明主要在审前会议中得到体现,因为诉答程序中的释明和发现程序中的释明很多都需要通过审前会议这个平台体现出来。
在审前会议中,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控制是强有力的,而这种强有力的控制有法官的释明在先作为支撑,以便当事人更好地遵循法官对诉讼进程的安排。如在洛克哈特诉佩特(Lockhart v.Patel)的医疗事故一案[6]232-233中,法院指示被告律师出席11月3日举行的和解会议,并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总部的代表同来参加该会议。法院明确、正式地告知被告律师保险公司总部不要派无和解权力的代表来协商。但11月3日这天,保险公司虽对法院的指示没有误解,但仍然只派来了公司地方办事处的一名调停员,于是,法院做出口头裁决并随即发布了书面命令,取消被告的诉答状,宣布对其缺席判决,并于12月12日审理是否应对保险公司处以藐视法庭罪的问题。在此案中,法院明确、正式地告知不要派无和解权力的代表来协商,就是很明确的释明。
二、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的释明评析
尽管从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可看到各种类型的释明,如促使当事人作出充分的陈述说明、消除不妥当的陈述、补充诉讼材料等,但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太注重释明的问题,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也没有与释明含义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说,美国的释明制度,实际上是释明倾向,释明的相关内容实质上是法院在行使案件管理权。正因为如此,美国的释明有其独特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申请发起
释明主要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发起,当事人申请法官命令对方当事人做进一步详细说明或补充说明、提供相关物证或书证等,若法官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要求,就发出命令,要求对方当事人进一步说明或提供书证、物证等。若法官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要求,就不存在向对方当事人释明了。这种制度设计坚持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平衡了释明制度和辩论主义的冲突,是对大陆法系国家释明制度的衍变。
(二)法官主要发挥间接释明作用
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可以提出各种相应的动议申请,法官会询问双方当事人,在听取各方的主张后驳回或接受申请。此时,法官只是通过强制手段的权能加以确认,促成当事人自律整理各自主张,在此种意义上发挥了间接的释明作用[3]158。
(三)多配备了强制性制裁措施
美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法官对诉讼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审前程序中设置了很多强制性制裁措施,使得法官的释明积极有力。如上文提到的洛克哈特诉佩特一案,由于被告无视法官的释明,法官可以直接缺席判决并追究被告藐视法庭罪。慑于不听从法官释明将导致不利于己方的结果,当事人当然会选择听从法官的释明指示。
可见,美国的法官一般不主动释明,而是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即便是法官释明,也多发挥间接释明的作用,促成当事人整理各自的主张。这样的制度构建将法官放在了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官既平衡了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能力和诉讼技巧上的差别,也保持了良好的中立性,避免了过度释明破坏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平衡。美国的民事诉讼冗长,民事审前程序也耗时耗力,有的当事人还滥用发现程序故意拖延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各种强制性制裁措施,使得当事人非常重视法官的释明并遵守它,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
三、我国民事审前阶段的释明现状
目前,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有关释明的规定分散在各个法条及司法解释当中,如《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及第33条对举证及举证责任的释明、第35条对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这些零散的规定使得我国的释明制度远不成体系,但由于我国长期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加之有纠问式庭审方式的传统,释明的司法实践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大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在审前阶段,法官的释明也是无处不在的。例如,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会在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如果被告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法官也可以释明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对管辖权异议的证据。法官在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时,如遇到有关事实不清楚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解释、说明情况,这也是一种释明。在开庭前进行举行证据交换,明确争议焦点的释明就更无需多提了。可以说,在我国,法官的释明几乎随处可见。但是,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仍处于并仍将长时间处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且,我国并未形成真正的辩论主义,因此,释明权建立所需的体制背景尚未形成[8]。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释明又有现实需要,法官的释明权制度需要研究和发展。笔者认为,美国也尚未形成释明体制,但它依然有释明倾向和自己的特色,我国的释明体制可以借鉴它的体例,在形成体制的道路上逐步发展。
将我国审前阶段的法官释明与美国审前程序中的释明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释明与美国的释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区别:
(一)缺少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官释明的权利
在美国的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可以向法官提出要求更明确陈述的动议,法官若同意该申请,就会释明对方当事人给出更明确的陈述,而在我国,当事人只能申请法官进行调查,调查的主体是法官,对方当事人是被调查对象,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法官,而不是当事人在法官释明后履行法官释明所指。因此,美国的法官更容易保持中立的地位,而我国的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二)法官的释明积极,缺少当事人对释明提出异议的权利
在美国,法官的释明多为消极的释明,而我国的法官释明多为积极的释明。在美国,法官在释明前会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综合考虑做出决定;而在我国,法官根据情况自行释明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基本上没有提异议的空间。
(三)释明的力度弱,当事人可选择性强
美国的释明配备了强有力的制裁措施,若当事人不听取法官释明,直接面临着处罚等各种不利后果;而在我国审前程序阶段的释明,法官多是起提示、指导、启发或引导的作用,最终决定权还是属于当事人,法官释明的内容似乎可有可无,当事人可以选择遵循或者视而不见,没有相应的处罚机制或强制性制裁措施,因此容易造成诉讼效率低下。
四、完善我国民事审前阶段法官释明的建议
法官的释明在审前阶段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具体案情向当事人阐明某些法律观点,协同当事人整理争点和收集证据,为后期庭审做准备,促进诉讼程序的高效;二是通过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使当事人知晓其诉讼请求是否适当、陈述与证据资料是否充分、法律适用的观点是否恰当等,让当事人在审前阶段把握法官大致的心证标准与尺度,预测判决结果,从而强化当事人和解的意愿,促进民事纠纷尽快解决。我国法官在审前程序的职权并不小,但在运作中缺乏与当事人程序化、制度化的沟通与交流,当事人对审前程序所能发挥的影响极为有限。释明制度作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就审前准备工作进行有效沟通的一项制度[9],能够在诉讼的早期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陈述及争议焦点,完善证据收集等,避免了无效劳动,有利于提高庭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应尽量发挥法官释明的指导作用提高诉讼效率。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趋势更多的是限制法官的能动性,而不是增强法官的能动性,释明制度的本质是强调法官的能动性,这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在当下的司法状态下,我们更应该小心地维护法院和法官的中立,而不是进一步动摇这种中立。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防止陷入盲目地追求时髦的游戏之中。”[1]135因此,在完善我国释明制度时还应当注意维护法官的中立性。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审前阶段的法官释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完善:
(一)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主动权
在审前阶段,一直是我国的法官在行使职责,主导着诉讼的进行。法官通过必要的审前准备,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掌握案件争点和必要的证据,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当事人的被动地位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如此一来,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依然没被松绑,当事人也仍然施展不开手脚有所作为,不如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主动权,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要求法官释明,这样一方面能够减轻法官的负担,也提高了当事人参与审前准备阶段的积极性。
(二)赋予双方当事人对释明内容的异议权
我国的法官在释明时往往只是单方面进行释明,如果有释明过度或者不当释明,另一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合理机制。法官在进行释明时应兼顾双方当事人的立场和意见,若不能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进行释明,也应当提供给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三)增设配套的制裁措施,增强法官释明的力度
我国没有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法官对审前准备阶段的工作控制力弱,应增设必要的处罚制裁措施,加强对审前准备阶段的管理,使法官的释明力度增强,当事人能遵循法官释明行事,有效提高诉讼效率。
注释:
①参见美国2015年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e款“(e)Motion for a More Definite Statement.A party may move for a more definite statement of a pleading to which a responsive pleading is allowed but which is so vague or ambiguous that the party cannot reasonably prepare a response.The motion must be made before filing a responsive pleading and must point out the defects complained of and the details desired.If the court orders a more definite statement and the order is not obeyed within 14 days after notice of the order or within the time the court sets,the court may strike the pleading or issue any other appropriate order.”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诉讼“释明”概念的展开[J].中外法学,2006(2):129-146.
[2]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57.
[3]陈源.论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释明”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4(2):157-160.
[4]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蔡彦敏,徐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2.
[5]张力.阐明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08.
[6]汤维建.美国民事诉讼规则[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7]韩红俊.释明义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
[8]刘艳丽.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J].中外企业家,2012(8):99-101.
[9]王梦飞.阐明权制度新探[J].法学杂志,2008(6):152-154.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3.021
收稿日期:2015-12-24
作者简介:李亚楠(1989—),女,硕士研究生。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3-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