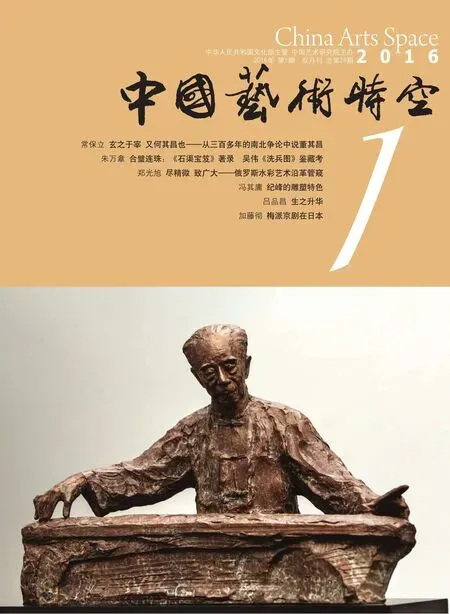游牧的共鸣,共享的多声
程俏俏
游牧的共鸣,共享的多声
程俏俏

【内容提要】近两年为着上海音乐学院《“声音中国”影(音)像生态民族志》项目,我一直在内蒙古和新疆进行人类学考察和纪录片拍摄,关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图瓦人以及哈萨克族的 “声态”与“生态”。本文主要基于此田野和大家说说“潮尔”。
【关键词】生态,声态,潮尔
数年前,来自蒙古国的一种喉音艺术“呼麦”,在北上广的文艺圈儿里变得特别流行,大家纷纷传颂这种可以一人同时发两种声音(最常见的是旋律伴随持续低音,俗称高音呼麦)的奇妙魅力。2009年,“呼麦”由中国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成功,引来了国际上极大的争议,主要的争议内容是:蒙古国说呼麦是他们的;图瓦共和国也说呼麦起源在他们那儿;这俩国家都说中国根本没有呼麦;而中国反驳谁说咱没有的,我们这儿管呼麦叫“潮尔”!

一、共鸣:共享的觉知
这里所说的是流传在内蒙古中部的人声潮尔,同样是以持续低音配合高音旋律的方式呈现,但从演唱方式到使用场合与呼麦都不尽相同。人声潮尔是音乐体裁“潮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蒙语中,“道”有歌的意思,“潮林道”直译即是“潮尔的歌”)。“潮林道”是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锡林浩特市)独有的人声合唱形式,分别有两个声部:上声部所唱旋律为长调,由一人演唱;下声部为“潮尔”,表演者少则一人,多时可达到八人。在过去,“潮林道”是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是给王爷演唱的歌曲,也被称为宫廷宴歌。这或许是当你听到潮林道时一种庄严、尊贵、气势磅礴的感受油然而生的原因,仿佛能看到驻扎了无数个蒙古包的山坡上开始了一部宫斗大戏。
对于这种音乐,当地人在面对我的采访时,大多不愿把潮尔单独提出来,将“潮林道”简单地看作是“潮尔”和“长调”的结合,这两者最终都是为了互相共振和鸣而产生和谐的声音。潮尔歌手在演唱过程中会进行Ehshig Tamehh(元音的搓动),也就是用正确的元音使声响更和谐。当我在采访蒙古国的一位造诣深厚的呼麦手奥特根呼时,他告诉我歌唱蒙古音乐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元音的转换。无论是呼麦、潮尔还是长调,元音转换的好,声音就好。当我继续追问什么是他认为的“好声音”时,他给我的答案是:简单,和谐。
回观“潮林道”的音乐结构,“zei-hei”作为引子,主曲之后以“turrlg”结尾。“turrlg”有大合唱的意思,这也作为整个“潮林道”的高潮部分出现,届时,在场所有人将一起合唱。这个行为来自为王爷演唱的古老传统,表达所有人对王爷的尊敬,而彼时的王爷,也将加入歌唱,共同表示众人对腾格里的荣耀。


除了人声潮尔,蒙古族还有一种弓弦乐器也叫做潮尔。在潮尔表演者和研究者额尔敦布和那里,我听到一段有趣的经历。
在过去,弓弦潮尔并非乐器,而是唱英雄史诗时使用的神器。那些潮尔奇(意为奏潮尔的人)大多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在无垠的草原与戈壁上游吟流浪。牧民们总是邀请他们坐在自家蒙古包里正北的席位(也是最尊贵、主人的位置),此时,潮尔奇反客为主,为这片草原的人们唱起祖先的故事。一直以来,牧民们把潮尔奇看作重要且具有神器力量的人,因为通过潮尔所传递的声响可以治愈疾病,祛除浊气,护佑土地。有的理论说,原来的弓弦潮尔在制作时要遵循“金、木、土、水、火”的原则,金是插在琴码上的蒙古刀,木是乐器的琴身, 土是马尾做的琴弦,水是滋养木头的气,火是松香。在2012年的夏天,额尔敦布和回到自己的家乡东乌珠穆沁旗,当地有一户家境贫穷的牧民坚持请他去牧场为他们演奏潮尔,那些传统的牧民,坚信潮尔可以给他们带来神奇的力量。连额尔敦布和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是,一年之后,那户人家的牲畜和草地愈发丰足,牛羊马不再生病了,草场的雨水也多了……他们甚至可以在旗里买上一套小公寓、送孩子们去上学。当然,本文并不想去探讨这段经历中的神秘力量,但从蒙古人的观念来说,潮尔的声音的确有修复和平衡生态圈的作用。人与动物的疾病、水草不够好的原因是生态圈,或者我们说是能量场中的一部分出现了问题,通过声音特殊的振动改善这个循环系统,在声音的倾听中,让人类与自然相处得更好。在采访时,额尔敦布和说到了一点我十分赞同,他大概的意思是,在现代音乐厅、用音乐会的方式来表演潮尔或其他民间音乐,其实在失去声音原初的意义同时,也遮盖了声音神性的光芒。
其实类似形态(多声)的蒙古族音乐有许多都被叫做“潮尔”,而“潮尔”在蒙古语中本身就具有共振的意味。同时这个意涵也不仅是蒙古人的专利,在图瓦人与哈萨克人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多声音乐形态。我们不由得会问,为什么这些民族都有类似的音乐,都喜欢这种声音呢?于是乎,无论是从聆听还是研究的角度,如果我们还将眼光局限在单一民族的音乐界定中就未免过于狭隘。在从呼麦出发的多声音乐研究上,需要更广阔的田野实践,把问题放置在从东亚至中亚一体的游牧民族之中。这些看似不同却息息相关的游牧民族,他们对声音有着一种共感和共鸣(resonate),这才是打开这扇声音共感之门的钥匙。

二、自然之气(amishul):获得共鸣声响的途径
在锡林浩特地区,有一位名叫道尔吉的当地学者和潮尔沁为“潮林道”起了另一个名字——“草之乐”。他同时给我讲了潮尔草的故事。潮尔草是一种高纤维开伞形花的麻类植物,蒙古人常用它做编织材料。其茎内多有空隙,夏至时层层茎节上便开出半球状的白色小花,一到秋天,草皮干裂,草原上的风透过干茎,会发出各种声音,时而簌簌,时而如口哨,又总有沉着的风声衬托相伴。道尔吉自觉这声音和潮尔相仿,便把这草唤做“潮尔草”,并说这种植物在蒙古歌王哈扎布家的牧场上生长得最多。当然,也有人反驳说,道尔吉所说的“潮尔草”不过是湖边生长的水芹菜罢了。
对于另一位潮尔沁宝日而言,唱潮尔最关键的就是amishul,这个蒙古语词有着复合的含义,它可以用来形容气、呼吸或者像风一样流动的气体。在我们喝下一杯又一杯酒时,他不断的和我说:歌就是一种amishul,要出去,再回来,绕在身体里。他的右手在从喉管到肚子前垂直的比划着,让我突然想到这人的身体不正如那植物一样么?你若想成为一个好的潮尔沁,就要像潮尔草那样不停感受着自然之气。那一晚,我似乎在他的口中听到了整个宇宙。


由锡林郭勒草原再往西去四千多公里,我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听到了极为相似的故事与比喻,只不过这次不是说潮林道,而是苏尔(内蒙古地区称为冒顿潮尔)和斯布孜额。这两种乐器极为相似,有说法称二者是不同民族或族群(新疆蒙古、图瓦、哈萨克)使用不同名称的同一种乐器,因为它的材质,也有人称它作“草笛”。这是一种形制上有三孔、四孔或五孔的单管乐器,无簧片,头尾相通,半径相等,是一种制作起来极为简易,但吹奏却十分困难的乐器。材质上从最初的草类植物,到如今演变出竹质、木制,甚至还有PVC管。吹奏该乐器的同时,乐人会一边用喉咙发出人声的持续低音),与沿着边棱旋转的口吹气流构成双声的共鸣。有些史学家认为苏尔就是中国古代乐器胡笳,这一点我持观望态度。哈萨克音乐人Anuar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吹奏斯布孜额的技巧在于同时使用喉音所发出的气息吹入管中,再返回身体里,并形成一个循环。
在新疆地区采访时,我特意逐一询问当地人对斯布孜额的感觉,得到的都是相似的答案:悲伤、孤冷和回忆。英国人类学家Tina Ramnarine在《离散中的音乐表演》(MusicalPerformance in the Diaspora)一书中提到哈萨克人以吹奏斯布孜额来铭记蒙古国Deluun Sum地区的一座湖泊,那里曾经是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或许这悲伤、孤冷的背后正是来自思乡的情结吧!

三、神性的呼唤
呼麦、潮尔、潮林道、斯布孜额,这些可以共鸣的多声音乐并非都是给人类演唱、演奏的。蒙古族的弓弦潮尔奏给自然与祖先;同样是弓弦乐器的哈萨克族库布孜,则是萨满使用的神器;斯布孜额通常在放牧时吹奏;而呼麦不仅常常在史诗中使用,也可用作与动物交流;在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边境地带也有哈萨克人在萨满仪式中使用类似呼麦的声音,他们将其称为kai。可见这共鸣声与自然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这些共鸣之声产生的可能,宝日曾在闲聊时随口说出一段有意思的话,:“在我们阿巴嘎,有山有水有沙地,在拥有着这么丰富的地貌能生长出丰富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潮尔和潮林道,这也是为什么长在那么远、那么平坦草原的乌珠穆沁人能唱最好的长调!”他随口所说的话,却道出了牧民们对不同草原生态的感受,并给予我一段极富“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描述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Theodore Levin在他著名的那本描述图瓦音乐的书《山水何处歌》(Where Rivers and Mountains Sing)中总结图瓦人的音乐是“音色中心的音乐”(timbrecentre music),我则更愿意称这些自由的游牧人之乐是“自然中心的声景”(naturalcentre soundscape)。在多种多样的音乐表现形式的背后,游牧民们共享着相似的多声结构,共鸣相与。它们连接着牧民生长的土地、养育的牛羊与马驹儿,和他们一代代积淀的情感与观念……这些音乐联系着腾格里,献给自然,以共鸣平衡着他们的世界,向游牧民族不断发起神性的呼唤。
(作者为行耳文化创始人、旅英青年音乐人类学者、电影人)
书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