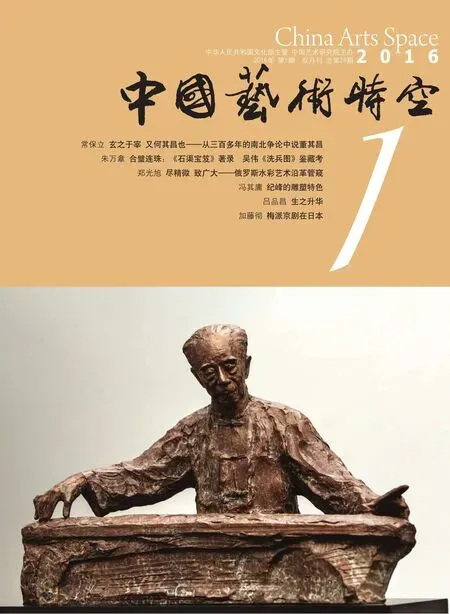异彩纷呈——黄梅戏在新加坡
康海玲
异彩纷呈——黄梅戏在新加坡
康海玲
【内容提要】从黄梅戏近几年在新加坡所推出的一些剧作,即历史故事剧、神话故事戏、现代题材戏、童话故事剧等可以看出:改变旧有模式,选择新加坡的题材内容,创新舞台表现手法等,这些都是戏曲易于被新加坡观众所喜闻乐见并焕发其艺术创造魅力的有力举措。在这方面,黄梅戏《丹心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关键词】黄梅戏 新加坡 本土化
中华戏曲除了在中国本土繁衍生息之外,还随着移民的迁徙及文化交流飘扬过海,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东南亚等地区发扬光大。东南亚是中华戏曲向海外传播的最繁盛地区。东南亚各国的种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语言习惯和审美取向等,必然对戏曲的传播发展造成影响。 新加坡是戏曲在东南亚国家薪火相传的一个重镇。
语言的隔阂是影响戏曲在新加坡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中国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神仙鬼怪等为题材的剧作已经渐渐淡出新加坡华人的视野,脱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这无形之中严重地影响了戏曲的承传。戏曲作为高度发展的表演体系,也是富有活力、不断流变、包容性强的综合性艺术,在漫长的移植传承过程中,为了适应新加坡的现实之需,戏曲一方面必须保留其“中华性”的艺术本质,一方面还得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戏曲内容题材上的更新,特别是从中国化走向新加坡本土化、现代化是激发戏曲活力的重要举措。只有从内容题材上努力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在表演形式方面力求革新,戏曲才能在新加坡生生不息。
在这方面,黄梅戏在新加坡众多剧种中脱颖而出,做了许多有力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黄梅戏在新加坡已经带上了鲜明的新加坡特色,异彩纷呈,以一种不同于戏曲母体的姿态出现在新加坡观众面前,被新加坡观众所喜闻乐见,并焕发出艺术创造的青春。
一、黄梅戏在新加坡的传播
在东南亚11个国家中,新加坡是黄梅戏和越剧唯一得到移植并发展的中国以外的国家,其中,黄梅戏发展的状况比越剧好一些。另外,加上很早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京剧,在新加坡这个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家,几乎每周都有大大小小的戏曲演出,而且如今还繁衍生息着中国五大剧种中的三个(即京剧、越剧和黄梅戏),这是非同一般的。
黄梅戏是安徽省主要地方戏剧种,如今也成了新加坡华人比较喜爱的舞台演出形式,其中包括不少中小学生和大专院校的学生,这种局面和新加坡的戏曲教育离不开。黄梅戏原称黄梅调,又叫采茶调,发源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黄梅山或湖北省黄梅县,主要流布于安徽省安庆市及其周边地区,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先后推出了许多经典剧目,随着《天仙配》、《女驸马》、《玉堂春》和《牛郎织女》等剧目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黄梅戏已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剧种。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黄梅戏演出团体,拥有不少的受众。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青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黄梅戏的影响和培养加深了新加坡人对黄梅戏的兴趣。

新加坡圣婴女中演出黄梅戏《花木兰》剧照
戏曲电影《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等的传播对新加坡华人的冲击最大,这种唱腔委婉清新、富有浓厚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适合于搬演多种题材的戏曲剧种逐渐缩短了和新加坡观众的距离。这三个剧目也成了新加坡华人耳熟能详的保留节目,“天仙配”和“牛郎织女”如今已经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
新加坡大多数剧种都是跟随着早期移民的到来而在本地得以传播的,黄梅戏到新加坡则有所不同。早期随着移民的迁徙,传播到新加坡并得到培育的戏曲剧种,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地方戏(包括海南的琼剧)剧种。这些剧种的传播与移植最初是由一些民间的戏班或艺人完成的,其载体是新加坡华人民间的节庆民俗和宗教祭祀。
黄梅戏的传播与移植较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梅戏传播到新加坡,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黄梅戏剧团到新加坡演出所带来的影响。黄梅戏的正式移植是90年代后期的事,主要通过正规的戏曲教育的渠道,把这种本来和福建、广东籍华人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剧种移植到新加坡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这种传播和移植与华人的宗教祭祀无关,主要是艺术层面和审美层面上的文化行为。在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新加坡黄梅戏在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为戏曲在新加坡乃至于东南亚的本土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新加坡女子小学演出黄梅戏《哪吒闹东海》剧照
二、黄梅戏在新加坡的本土化教育
黄梅戏在新加坡的移植主要是通过系统科学的戏曲教育来完成的。这种通过专业院校体系培养的戏曲教育模式在东南亚最有名也办得最成功,除了普及和提升戏曲艺术水平之外,在戏曲的变革与创新的本土化进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戏曲教育主要由新加坡戏曲学院、城隍庙艺术学院、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等单位承担。新加坡戏曲学院历史较悠久,对戏曲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该学院于1995年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成立,它是一个从事戏曲培训和研究的教育学术机构,肩负着承传与推广戏曲的重任,也积极促进国内外戏曲文化交流活动。学院自创办以来,在大专院校与中小学中开展艺术教育活动,至今已在一百多所学校举办讲座和示范表演,为青少年提供了认识和学习戏曲的机会。戏曲学院目前开设黄梅戏、潮剧和越剧的专业课程,包括剧目教学、化妆、把子功课程等。城隍庙艺术学院、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创办的时间相对较短。
纵观新加坡的戏曲教育,其宗旨如下:
第一,努力引导青少年欣赏和认识地方戏曲。
第二,积极培训新一代的地方戏曲演员。
第三,发展有新加坡特色的创作剧目。
第四,广泛融汇和吸收其文化传统精华,以丰富华族地方戏曲。
第五,提供专业训练与开展研究工作以提高本地地方戏曲水平。
第六,积极与本地艺术团体合作,开展教育性节目与创意性活动。
第七,通过地方戏曲开拓新加坡艺术的国际舞台。
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新加坡的戏曲教育深刻意识到本地创作的重要性,更侧重于戏曲的本土化建设,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新加坡特色、东南亚特色的优秀剧目,为本地创作提供了典范。

新加坡海星天主教中学演出黄梅戏《铁扇公主》剧照(陈泰胜饰演孙悟空,戴伟凌饰演铁扇公主)
三、新加坡黄梅戏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更新
黄梅戏在新加坡的演变,除了用汉语普通话代替安庆方言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剧目的更新、内容的东南亚色彩上。这些年来,新加坡戏曲学院等戏曲教育机构善于挖掘崭新的题材,结合当地的现实生活以及人们的审美取向,特别是各级学生的兴趣爱好,创作演出了一些具有南洋本土色彩、鲜明时代气息的剧作。这类剧作主要有四个类型,分别为:
第一类,历史故事剧。创作与新加坡或东南亚有关的历史剧,旧瓶装新酒。这个“瓶”指的是黄梅戏,“酒”指的是当地的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中宣扬儒家传统文化,讴歌忠孝节义、爱国爱民、尊老爱幼等的传统美德,这是新加坡华族后裔所必须学习和弘扬的。为了给新加坡的年轻人传授历史知识,树立民族的文化形象,激发民族情感,建构其宏大的历史观,并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新加坡戏曲学院、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等结合本地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创作或改编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思想深刻的历史故事戏。
《郑和》就是一部由新加坡戏曲学院创作演出的优秀黄梅戏历史剧作。郑和下西洋主要经过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各族群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发展成为今天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特色。把这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对当今的新加坡华人后裔具有重要的教育激励作用。
首先,再现了一段新加坡人熟悉的历史,重塑了一个新加坡人敬仰的英雄。郑和是明朝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是中国大陆,更是东南亚华人必须家喻户晓的光辉历史。郑和率领的大明宝船队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按照现在的国家划分,则分别属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文莱、印度、孟加拉、伊朗、也门、北也门、阿曼、沙特阿拉伯、索马里、马尔代夫、斯里兰卡、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等国家。其中有七个国家属于现在的东南亚地区。郑和在东南亚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当地民众的怀念。600多年过去了,郑和的形象永远彪炳史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许多民间庙宇,成立了纪念馆或树碑立传来缅怀他为东南亚带来的福音。东南亚各地还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垅、三宝庙等。
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1405年)600周年,在全球盛情重温与隆重纪念这一和平使者的时代背景下,2006年由戏曲学院蔡曙鹏为新加坡博理中学、崇文中学和博理小学学生所编写的《郑和》是第一次以黄梅戏舞台的艺术形式纪念郑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艺术地再现了这位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
其次,以黄梅戏旧有的戏剧结构承载重大的社会命题。黄梅戏《郑和》的戏剧结构较为庞大繁复,它把有关郑和的宏大历史叙述浓缩在九场戏中表现,在现代语境中赋予历史故事以重大的现实意义。
很显然,在戏剧所创造的特殊场域里,华人大中小学生能感同身受,深入理解郑和的贡献:开辟远洋航线;为明朝增加友好的邦交;促进商业发展等。从剧作的布局看,该剧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挖掘主人翁所处的特殊位置,从宫廷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反对派的强烈攻击阻挠,以及智取海盗等的情节来凸显郑和的领导才华和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他下西洋增进国与国的友好往来,建寺庙以促进种族和谐,伸张正义以维护和平, 600多年前的郑和尚有如此的宽广胸怀,更何况是今人呢?对种族亲善,世界和平的呼唤是不同时代的主旋律,当今风云变幻的东南亚时局更要遵循和平、和谐的世界公约。小舞台,大世界,这部具有史诗的宏大与人性厚度的戏传达出了一个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正如2005年6月5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郑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来西亚住房和地方政府部长、最大华人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发表讲话所强调的:郑和勇于实践、崇尚科学的态度,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征服海洋以及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精神,特别值得东南亚当代人学习。马来西亚艺术、文化和遗产部副部长黄锦鸿也在会上说,郑和“以和为贵、以邻为富”的伟大精神,是东南亚以及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更应该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大力提倡。
第二类,神话故事戏。根据印度和马来的神话故事创作改编黄梅戏剧作,也是新加坡黄梅戏本土化的一个特色。黄梅戏这个本来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古老剧种因此着上了东南亚本土色彩。在新加坡,马来族和印族是人数仅次于华人的两个大的民族,其文化底蕴深厚,对华人的影响深远,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族有名的神话故事对华人学生并不陌生,成了他们共享的文化遗产。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戏曲学院很自然地从印族和马来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神话故事的资源。因此,就出现了不少取材于印族神话故事的黄梅戏。其中最先推出的是1999年创作的《放山劫》。 该剧取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导演把它变成新加坡学生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形式搬上黄梅戏舞台。1999年底该剧到泰国参加国际艺术节,在泰国国家剧院上演。2000年,受印度外交部邀请,该剧还到过印度新德里等四个城市巡回演出,得到观众的好评。
华人用黄梅戏的形式表演异族题材的戏,目的在于创新黄梅戏的内容题材,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新加坡当地观众喜欢观赏的、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戏曲剧目,这样做,有利于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来参与,推动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种族之间的和谐。黄梅戏因此承担了更大的时代使命。
第三类,现代题材戏。把新加坡现代社会生活的题材注入黄梅戏中,这是黄梅戏在新加坡寻求发展的另一举措。真正具有时代感的现实题材创作,能够反映新加坡的民生民情,触及社会问题,展示当下华人的精神状态,品格情操。这类剧作因为与生活接近,更能够吸引年轻观众,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丹心谱》是新加坡黄梅戏最为成功的一部现代题材的剧作。
新编现代黄梅戏《丹心谱》的创作演出,既可以向新加坡的青少年推广黄梅戏,还可以配合新加坡的国民教育。该剧是新加坡戏曲学院迎接千禧之年特备的开锣戏,剧作以新加坡“二战”时期真实的故事为纲,注入了新加坡的历史、地理、人文等多方面因素,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新加坡人民熟知的抗日英雄林谋盛的光辉形象,歌颂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受到了新加坡人民的欢迎。这种以华人传统的黄梅戏形式为载体,注入新加坡近现代反帝反侵略主题的舞台演绎,在观众徜徉于艺术鉴赏的同时,又经历了一次爱国情感的震荡,可谓事半功倍。该剧一改黄梅戏载歌载舞的轻松明快的抒情趣味,充分发挥黄梅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个剧种特色,让新加坡的生活气息随着剧情的开展扑面而来。黄梅戏随着新加坡人的主体性格、语言腔调和当地艺术的整合,走上了更加本土化的道路。
《新民的故事》是另一部较为成功的现代题材的黄梅戏。该剧以新加坡新民中学的校史为题材,围绕着这所民办华校办学的艰辛历程而展开戏剧情节,侧面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史。有关教育题材的剧作可以拉近和学生观众的距离,唤起他们已有的情感体验,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在黄梅戏的载歌载舞里,观众看到了办学者叶帆校长当初如何卖猪建校,上世纪50年代学校如何组织文艺晚会筹款,60年代建国后教育改革面临哪些挑战,70年代华校面对哪些困境,以及80年代如何成为政府学校,直至2000年成为自治学校。一出戏浓缩了新加坡华校的峥嵘岁月,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和华人移民的历史也再次展现在新加坡观众的面前。
剧中还根据新加坡学生的兴趣,穿插了诗歌朗诵、交响乐、各民族舞蹈等元素,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方式,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第四类,童话故事剧。用黄梅戏的形式来演绎新加坡青少年感兴趣的童话故事,也是黄梅戏在新加坡走向本土,与众不同的地方。儿童天性爱听童话,把童话故事放在黄梅戏的“旧瓶”里进行演绎,是新加坡戏曲学院的大胆尝试。
童话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但是比起文本的阅读,用黄梅戏的舞台形式讲述童话故事,更能唤起他们审美的愉悦,黄梅戏藉此走进更多青少年的生活里。新加坡戏曲学院把黄梅戏和童话故事结合在一起,认真研究新加坡各级各类学生喜欢的童话故事类型,将经典的国内外童话故事改编成黄梅戏剧目,既提高了学生们的文学修养,又为黄梅戏的创作寻找到更多更好的题材,为戏曲艺术的推广创造了新天地。日本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故事、西洋童话故事,以及中国的童话故事等都曾经被改编成充满童趣、童真的黄梅戏剧作,在新加坡以及国外的舞台上赢得了阵阵掌声。这是黄梅戏在新加坡本土化的成功之举。
《夜莺的故事》是新加坡戏曲学院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的一个精彩剧目。安徒生童话是全球孩子们的精神食粮,新加坡的学生们也不例外。戏曲教育应该从小抓起。由于新加坡的学生接触更多的是英语,要引起他们对戏曲的兴趣,选择那些名著改编的而且动作性强的童话故事,是一条有效之路。剧作者蔡曙鹏在遵循安徒生原著的基础上,以三个喜欢拍马屁的官员贯穿全剧,围绕着夜莺的歌声展开戏剧情节,之间还增加了三位趋炎附势的贵妇人和地府、阎王等角色,使得本来的童话故事更饱满,人物更多元,性格更鲜明,戏剧的趣味性因为改编而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地府小鬼要把皇帝带到阎王殿的场面,妙趣横生,充满了喜剧效果。该剧的推出,让新加坡观众眼前一亮,原来古老的戏曲还能焕发出如此的活力。黄梅戏的年轻观众因此得到了培养。2005年,适逢安徒生诞生200周年,该剧参加了在丹麦举办的戏剧节,在14个国家参演的国际舞台上,黄梅戏以其中国、新加坡、丹麦三个国际多元文化兼具的艺术新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为戏曲再次树立了新形象,也扭转了国际人士早先对中华戏曲所形成的一些负面印象。

新加坡培青学校演出黄梅戏《老鼠嫁女》剧照(张旻玥饰演鼠女,高洁莹饰演鼠母)
四、从《丹心谱》看黄梅戏在新加坡的本土化
戏曲在东南亚,最大的问题或最敏感的问题是本土化的问题。而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冲突是限制戏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合理处理好这对矛盾体,戏曲在东南亚才能顺利传承并发展。
黄梅戏《丹心谱》是戏曲在新加坡本土化的一个成功案例。新加坡演员借助黄梅戏这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演绎一个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传达新加坡人的思想情感。这个黄梅戏新作在新加坡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是三个方面:
第一,剧作的内容题材取自新加坡。这个戏讲述的是“二战”期间新加坡史上一个颇为感人的事件。从1937至1945年,新加坡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前一段是抗日救亡。1937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作为中国的一分子,新加坡的华侨爱国热情高涨,奋起进行救亡活动以支援自己的祖国。后一段是抗日卫新。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占领了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在严酷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史称昭南时期),日军对新加坡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检证,华人首先遭殃,或被杀害,或被拘留,或突然失踪,时局动荡不堪。有志之士奋起反抗,林谋盛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抗日英雄。
这段史实属于新加坡。在这个剧中,华人观众可以重温祖先移民的历史,还可以再次看到日军占领新马一带的残酷罪行,如剧中林谋盛的一段念白:
想当年,
离乡背井南洋来,
太平盛世民安泰。
香港求学,
星洲创业。
邂遇珠娘,
定亲成家。
育女儿,
享天伦。
天伦乐,
乐开怀。
未料到
东洋军国烽火起,
蹂躏神州神鬼泣。
安南半岛碧血洗,
马来亚哀鸣遍地。
星洲证大肃清,
冤死刀下其数无计,
为和平,
离亲人。
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由于观众对移民拓殖、抗日救国、抗日卫新等比较熟悉,该剧的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新加坡观众藉此而自省,身处太平盛世的新加坡,不应忘却过去的艰难岁月,不应忘却曾经为新加坡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
第二,剧种的语言采用新加坡华语。
黄梅戏在新加坡与在中国本土的不同最突出体现在语言方面,即唱词和念白等都采用普通话的发音。新加坡学生接受的教育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则作为第二语文,大多数学生华文水平有限,华语(普通话)水平不高,甚至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已经不会说自己籍贯的方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不可能去学习黄梅戏的剧种语言——安庆官话。用普通话代替安庆官话演唱黄梅戏,这是应变措施。由于两种语言比较接近,这就为语言的替代提供了可行的条件。越剧在新加坡也遭遇这种状况。
语言的演变,俚俗之美的丧失,这是显而易见的。黄梅戏在新加坡,用普通话代替江淮官话进行表演,安庆的方言俚俗等就消失殆尽,戏剧效果自然受到影响。因为诗词倡雅,曲语尚俗,在各个方言剧种中,经常会有一些俚俗土语、口语化成分、时调俗曲的运用,使得剧种具有了俚俗之美,形成了该剧种独有的浓郁而鲜明的地域风格。用江淮官话表演黄梅戏也是一样的道理。另外,由于新加坡华人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中国南方特别是闽南的口音,所以,新加坡黄梅戏的表演在念白方面就表现出十足的闽南腔。
黄梅戏在新加坡的唱腔依然保留黄梅戏花腔和平词两大类。新加坡戏曲学院在课程的课设中,两种唱腔并重。如该院排练的《打猪草》、《蓝桥会》、《夫妻观灯》等剧就采用了花腔,而《天仙配》、《梁祝》等剧最主要的唱腔则是平词。
第三,采用符合新加坡人审美习惯的多种表现手法。
新加坡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从小就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审美取向上表现出崇尚多元的特征。该剧在演出过程中,为了克服黄梅戏传统舞台的虚拟、单一的特色,加入了许多现代科技的元素,如增加了合唱队的叙事以及历史图片的展示,增加了演出的张力,并把演出场域拓向更广阔的时空。
场与场之间增加新加坡历史图片的放映,这样的演出架构是传统黄梅戏不曾出现的。全剧一共间隔插播了四小段历史图片:第一小段为幕启时,白幕上放映了“济南惨案”,“满洲国”、“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图片。第二小段为第二场即将结束时,白幕上放映日军偷袭珍珠港,“威尔斯太子号”、“击退号”被炸沉的历史图片。第三小段为第五场幕启时,白幕上放映英国人在白思华中举白旗带将士向日本人投降的情景,接着放映多张历史图片,呈现日军杀害无辜数万人。第四小段为第五幕,白幕上投射了日军登陆,在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大检证,杀害数万华人,强迫华侨协会交纳奉纳金,宪兵队的灌水刑等历史图片。
插入放映的这些图片是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回忆或故事。起补充衬托或解释的作用,是戏曲舞台的对外延伸,使剧作的脉络更清新,节奏更紧凑。另外,也有利于渲染气氛,调动观众丰富的情感体验。
该剧还善于借鉴电影、电视的表现方式,把故事情节、合唱队的演唱、历史图片的放映与戏曲表演相融合,表现手法多样,创造了一个多维的演出场景,而这些正好符合新加坡人的审美要求。舞台上灯光音响交织,情节跌宕起伏,紧张有致,场与场之间用红灯在屏幕上反映那些历史图片,烘托出战争的血腥凝重和残酷恐怖的戏剧氛围。剧中以情感人,夫妻情、姑侄情、父女情、工友情,款款深情感人肺腑,也深化了剧作的主题,激发了观众无限的爱国情感,揭示了日军在新加坡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四,华、巫、印同台表演,彰显新加坡特色。
多元种族构成新加坡特殊的社会结构,种族的和谐与融合历来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这种现象也投射到戏曲舞台上。华人、印族和巫族(即马来族)是新加坡的三大种族,在戏曲舞台上,华、巫、印三族演员各担其纲,共同演绎,构成了新加坡华语戏曲的一道景观。
这是新加坡种族共处的传统使然。“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各民族的舞台文化兼承着50年代以来自然涵化、交流的良风。华、巫、印族同台演出是盛典上绝对不可缺少的项目。”在任何一场大型的文化展演上,都可以看到至少这三大种族演员的身影,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感知,却可以凭借舞台艺术的形式相聚,体现了新加坡丰富多彩而又共存共荣的文化生态。
2003年新加坡举办第四届“青年剧展”,新加坡戏曲学院演出的黄梅戏《放山劫》,就汇聚了华人和马来族、印族的学生演员,他们之间配合的默契,保证了演出的顺利进行。对于第一次接触戏曲的马来族和印族学生,要求他们用标准的普通话演唱戏曲实属不易,华人学生的热心帮助,培训老师的诲人不倦,以及他们对戏曲的热爱,是异族学生演员完成跨界演出的必备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印族、马来族人对华语的学习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青睐。该剧男女主角分别由华人学生张宇豪和马来族学生Faizah Bte Salan 分饰。这在本地还是第一次。Faizah Bte Salan第一次学戏曲,但是聪明伶俐,一点就通,无论是台步、身段、马鞭等动作,都能表演到位,对角色的内在情感也能尽量把握,因此,表现出的眼神语气、以及一颦一笑等都有戏曲的况味。让不同种族的演员走上同一个舞台进行展示,这是促进不同文化交流的方式,也促进了种族的和谐。
在当前新加坡众多戏曲剧种中,黄梅戏的变革和创新步伐迈得较快,其成功的经验能够给其他剧种提供启示。据《丹心谱》的导演胡其娴所说,这个戏是创作与演出反映本地历史事件的剧目,能积极推动华语戏曲的本土化进程,对发展有新加坡特色的戏曲,有建设性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